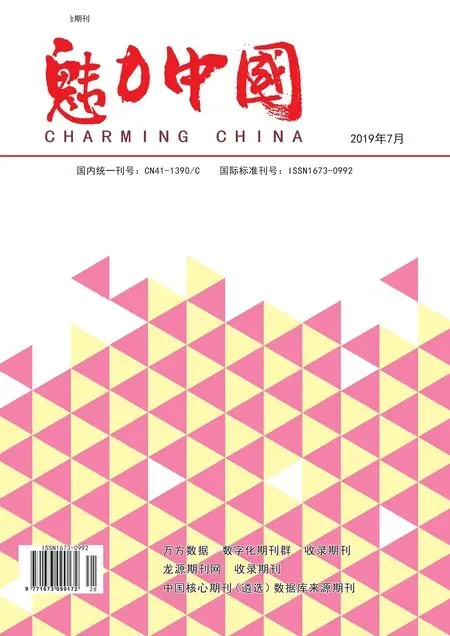我對民族歌劇《弄染之光》的認識
吳發健
(安順市文化館,貴州 安順 561000)
一、概述
(一)追尋光明是人在黑暗中的本能,正如大詩人顧城所言,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卻用他尋找光明。而對于弄染而言,陸瑞光正是這一道光。
1935年的中國是一個黑暗的年代,陸瑞光獨占山頭,善其身,利其器,囤其糧,贍其眷,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山地王國,背負著父親兄長的死亡同腐朽的政府抗爭。
此時的陸瑞光是一方民族豪杰,也是王仲芳等軍閥所忌憚的“山大王”。
然而身在亂世猶如風中顫枝,樹欲靜而風不止,獨善其身始終難以換來真正的和平。紅軍進寨,帶來了共產主義精神,這才是陸瑞光真正所向往的理想。自簽訂協議之時起,陸瑞光真正從一方民族豪杰轉身成為亂世英雄。
因而,弄染之光是一部英雄史詩,更是一部英雄成長史,他記錄著一位梟雄是如何因為承諾,信念,信仰而轉變為英雄的。
二、現實意義
(一)一諾千金
2017年的中國,是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碎片化的信息、虛擬中的對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岌岌可危。網絡連接了所有人,也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變得不再值錢。欺詐,蒙騙遍地橫行。因而一諾千金變得彌足珍貴。作為戲劇人,我們應該通過自己的手段喚醒人們對于誠信問題的重視。
(二)信仰
信仰的力量不在于祈禱之后愿望弄夠一一實現,也不在于許愿過后可以獲得功名利祿,而是在于敬畏之心。心存敬畏才知何事可為,何事不可。然而這正是現在中國所缺少的。沒有敬畏之心,人便成為了金錢的奴隸,為了利益不擇手段,沒有敬畏之心,人便陷入了盲目的狂歡。
佛教國家的人是善良的,基督教國家的人是謙卑的,穆斯林國家的人是勤奮的,然而信仰包括卻不局限于宗教。
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不再是獨一的個體,而成為了群體,成為了社會,成為了國家,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祖先智人能夠戰勝強大于自己數倍的尼安德特人。引用《人類簡史》中的一句話“人類之所以能夠存活至今,源于一個強大的集體想象,集體想象催生集體意志,而集體意志確立了人類的協作與共進。”
(三)抗爭
中國的帝制持續了千年,家不可一日無主,國不可一日無君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北伐戰爭終結這一統治,因而國家陷入了空前的混亂,加之二戰開始,日寇入侵,五千年的文明古國早已內憂外患,滿目瘡痍。
馬克思曾經說過,所為國家機器,其實質是統治階級對于剝削階級壓榨的工具,此時的中國,正是三座大山壓榨人民的工具。
而面對壓迫,仕人選擇見風使舵,軍人選擇服從天職,學生勢單力薄……在偏遠的山區卻有著這樣一群被稱為夷人的百姓選擇揭竿而起,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群人才使得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四)最高任務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提到所為藝術,是古希臘兩者中精神的集合與體現:一則是酒神精神,象征著娛樂與狂歡,一則是日神精神,象征著理性與哲思。在泛娛樂化的今天,人們不再崇拜英雄智人,而是美女帥哥,人們不再相信理想,而是積極的面對現實,高雅藝術被人詬病為不接地氣,理性的哲思被人誤解為不面對現實。
這是一個酒神精神泛濫的時代,而正如尼采所預言的,這個時代將會娛樂至死。
歌舞升平的背后充斥著種種世人所不愿面對的矛盾,而究其根本就是信仰的缺失,信念的缺乏,信任的淪喪。作為舞臺工作者,我們有義務通過自己的文藝作品喚醒已經沉睡的日神。
三、關于文本
藝術往往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從文本的字里行間中作者都在踐行著這一理論。劇本的文字生活生動,具有濃郁的地域特色;而在唱詞方面又具有詩意,行文流暢,是一場詩意與現實結合的文字盛宴。
作者在《弄染之光》中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在風云變幻的年代,一位擁兵自重的布依族英雄成為為國捐軀為信仰捐軀的中華民族英雄的歷程。
生活永遠比戲更加精彩,作者大量取材于歷史史實,使得文字因為有現實積淀作為根基而得以更大程度的延宕。在作者的筆下,陸瑞光不單單只是布依族的英雄,更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的信仰與堅守的承諾將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中成為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
因此,在對于文本的表現方面,應當恪守作者所思,所想,所言,做到語言的生活化,同時嚴格遵守作者對于全劇結構的邏輯性,以展現英雄成長的史詩氣概。
關于舞臺美術
貴州,地處中國西南,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舞臺美術是觀眾對于一部戲劇最先入為主的理解,也是最直觀最強烈的沖擊,因而在舞臺美術方面應當盡可能的體現貴州的地緣特色。
喀斯特地貌的石山,石柱,石林,板巖建造的石墻,石瓦,石屋;配合上郁郁蔥蔥的森林,形成了貴州獨特的視覺符號。
舞美的本質在于在有限的空間內創造無限的可能性,而該可能性源于人類腦中對于美的想象。因而在排練過程中,將因為演員的詮釋而展現出無限的可能性。
本次舞臺呈現打算基于現實元素為基礎,對于地域特色進行詩意表達,因而形成虛實結合之景。弄染的山寨,六馬的叢林,貴陽的刑場將通過元素的提取及觀眾的想象在舞臺上進行全方位虛實結合的體現。
關于人物
誠如莎翁所述,人類是萬靈之長,是宇宙的精華,而作為一部戲劇作品往往真正感動觀眾的并不是劇情之曲折,場景之豐富,音樂之悅耳,而在于人,在于人物。本劇中涉及到大量的歷史人物及史實,因此對于演員的要求不僅僅局限于聲臺形表,更重要的是對于人物的理解以及歷史史實的認知,從而能更加完美的將歷史中真正存在過的這些人物進一步的搬上舞臺。
演員應當從人物的外部行動出發,以其為依據,對于人物的語言,形象,行為等外部條件進行剖析,走進人物內心,在通過自身對于人物的理解有感而發展現出“人物”的“人樣”,而非對于歷史史實人物的機械化模仿,或者對于藝術加工的脫離現實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