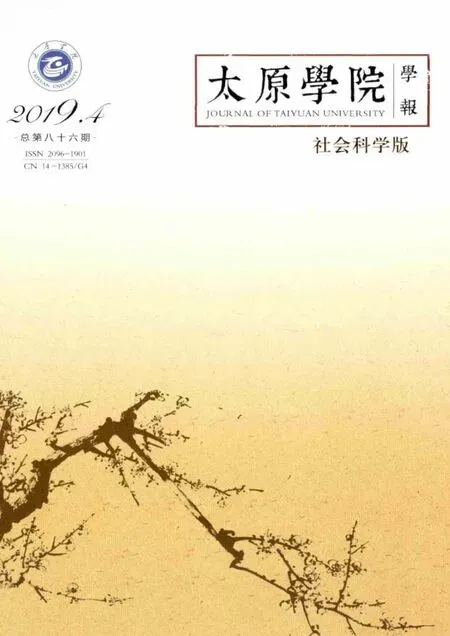互聯網與性
潘綏銘
(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人口學院)
1993年,我在美國訪學期間,第一次使用互聯網。
當時還是非常簡單的即時通訊,只能在DOS系統下敲入純文字,再無其他功能;但是當時使用的人們都興奮莫名。幾乎每一次使用,我都會收到對方的驚嘆。其中一位的評論很經典:啊,真神奇,距離消失了!
但是我當時卻沒有如此強烈的感受。我覺得,這跟雙方及時互相拍電報差不多,甚至只不過是“隔澗對歌”的更高級形式而已。這種感覺似乎直到如今也沒有消失,因此每當年輕人歡欣鼓舞地歌頌“互聯網改變了人類”的時候,我總是倚老賣老地來上一句酸的:一切技術發展,只不過是人類自有功能的拓展而已。
例如,在我研究的“性”領域中,所謂“網戀”,難道不就是古已有之的“鴻雁傳書”嗎?這種活動的基本性質,并不在于使用什么樣的手段來傳情達意,也不在于傳達得有多快和多廣,而在于它把日常生活中的促膝談心和察言觀色,轉化為文字書寫,然后依賴雙方的解讀,最終建立起某種人際關系。可是,這不就是人類之所以發明文字的初始動力和始終如一的目標嗎?所以,說互聯網空前便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夸張為“革命”,那就很容易陷入“技術決定論”了。
再例如,網上的“裸聊”,難道不是從古至今一直發生在性伴侶之間嗎?與那種一枕橫陳、聚首細語的古代生活,除了空間距離的增加,難道真有本質的區別嗎?
總而言之,至少在“性”這個領域中,互聯網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最根本的變化,其實并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那些表面現象,而是僅僅一個關鍵點和兩個中國字:隱身!
隱身,不僅僅是匿名,而是在網上性愛中,雙方真實的身體,居然可以“不在場”了!性,居然可以脫離身體接觸了。
這一變化非同小可。
迄今為止,人類的一切性關系都是發生在兩個或者更多的人之間。不論是什么樣的性關系,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匿名,卻無法隱身。你必須用自己的身體去接觸別人的身體,哪怕是一見鐘情或者暗送秋波,那也需要雙方真實身體的參與,誰也無法隱藏起來。
可是互聯網來了,在網上的一切性的交往中,哪怕是轟轟烈烈的性愛活動,參與的雙方或者多方,不但可以隱姓埋名,而且可以“身在其外”,根本不需要顯現和動用任何一方的真實身體。反之,一切發生在網上的性愛,雖然雙方都是身體隔絕,卻仍然可以引發任何一方真實身體的各種性反應。
也就是說,隱身給“性”帶來的,不僅僅是私密,更是在互聯網空間中的隨心所欲,甚至可以是為所欲為,破除了幾乎一切現存的對于性關系的社會控制。
這像是什么?不就是獨自的性幻想嗎?網上語言叫做“YY”,即“意淫”,非常傳神。這就是說,在任何一種網上性愛中,由于是隱身進行的,因此雙方的性關系已經被改造為單方面的性幻想了,兩個真實的社會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已經被切斷了,至少也是不再必要了。
許多論者喜歡把這種“隱身”稱為“虛擬”而且很喜歡歌頌之。我可能是足夠老了,所以寧可稱之為“獨處”,就是在現實生活中自我隔絕,主要憑借互聯網來與人類聯系。
我雖然很不愿意對此做出任何價值判斷,雖然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這種傾向,但是這種動態現實卻真的給人類社會帶來一個危機——既是危險,也是機會。
比爾·蓋茨早就預言:在電腦技術造成的“虛擬現實”中,我們做愛,已經不再需要一個真實的對方了。現在,再加上互聯網技術,做愛是不是已經可以不需要真實的空間和時間了呢?將來,是不是連真實的身體也不需要了,僅憑腦電波互通就可以做愛了呢?
總之,性,還需要人際關系嗎?還需要身體接觸嗎?甚至,還需要生物基礎嗎?放眼看去,在現實生活中,變性、易裝、性別流動等等現象紛紛“出柜”,萬紫千紅,彌散而炫彩。它們可能與互聯網無關,但是卻像互聯網一樣,無時不刻地挑戰著我們以往的刻板印象,預示著人類發展的無限前景。
我以為,這才是最根本的性革命。
與那些有目共睹的社會現象,例如情色作品、婚外戀、特殊性活動等等相比,“互聯網之性”帶來的隱身和獨處,對于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例如,現在有些人走火入魔般地聲討“小三兒”;可是,如果我僅僅是在網上從事各種“虛擬性愛”,那么算不算“出軌”呢?有沒有“小三兒”呢?盡管道德、法律、意識形態甚至形形色色的“上帝”都可以懲罰我自己,但是誰能夠懲罰和禁止那個隱身的“小三兒”呢?
如是,傳統性道德必將墮落為僅僅鎮壓身體的“緊身衣”,卻再也無法成為控制精神的“緊箍咒”。這讓我不由得想起恩格斯的一個著名論斷:歷史上斗得你死我活的雙方,其實最后都同歸于盡,讓位于一個前所未聞的新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