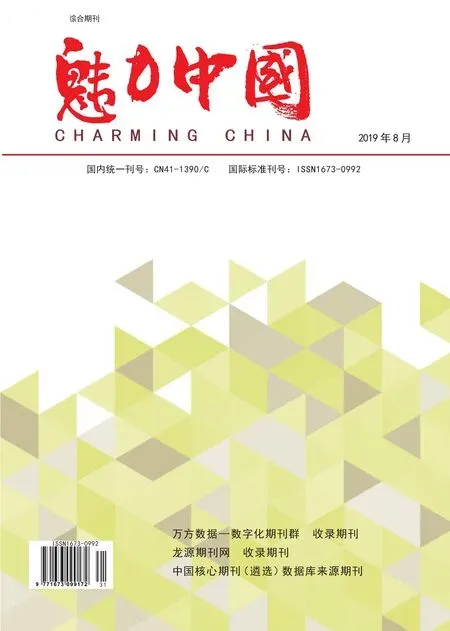金仙文廟建筑特征及保護利用研究
薛玉輝
(劍閣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四川 劍閣 628300)
文廟亦稱為孔廟、夫子廟等,最初是用以辦學為宗旨的將學習儒家經典的學校與祭祀孔子的禮制性“廟”宇相結合的國家行政教育場所和祭孔場所。在其兩千多年漫長的發展歷史中,因文廟而設立學校或因學校設立文廟的制度,使得文廟這一建筑的內涵不斷豐富,并成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的根脈。金仙文廟地處金仙場鎮文廟街,始建于元初,明、清及民國初期復修,整體呈四合院布局,建筑群布局合理,比例協調,用料精細,雕刻之精,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在功能上,金仙文廟除繼承了歷史時期“廟學合一”宣揚教化、治安管理、女子學校的場所外,在抗戰時期成為紅四方面軍的政府所在地及軍政部等駐劍閣,在文廟設立金仙縣蘇維埃政府在劍閣的政府所在地及軍政部等,極大地豐富了歷史文化內涵。
一、金仙文廟歷史沿革
金仙文廟,在清雍政劍州志僅載金仙山、金仙寺等。始建于元初,明、清及民國初期復修,坐南朝北,現存建筑為民國八年重建,占地面積940平方米,總建筑面積740平方米。
(一)“四建”得始終
根據金仙文廟殘碑中記載及相關文獻資料記載,金仙文廟于元朝二年開始創修廟宇[1];康熙五十五年重建未成,僅建基礎;嘉慶八年,金仙奉旨文昌宮春秋祀典與大成殿并重[2];道光十年,金仙文廟重建成功,組織者歲貢、羅映川。時建有“大成殿”“魁星樓”“泮池”及泮池上的“狀元橋”,整體建筑為上下棟宇,東西兩廊之四合大院。
(二)維修及使用情況
道光十五年,金仙已形成二月十四文昌會,八月二十七日祭孔圣的大成會、崇儒會、鄉小學會,文風大舉。光緒三十二年,南部教匪 300 余人占金仙,搶周邊各場,后金仙駐官兵進行清剿文廟被用為地方治安防范處。[3]同年金仙士紳袁覲光在金仙文廟辦起當地第一所初級小學。民國七年,山賊馮濫鼻子據金仙場,文廟被土匪燒毀,片瓦無存。[4]民國八年,文廟再次被毀。金仙商會羅仕镕,商同會長袁宗翰發動老區民眾,重建文廟。[5]民國十八年秋,劍閣縣金仙女子小學成立,校址在金仙文廟。民國二十一年,文廟被作為殺害農民起義的指揮所。[6]1935 年初,紅四方面軍駐劍閣,在文廟設立金仙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及軍政部等。1951年,文廟魁星樓、塑像、文昌木刻像被毀。[7]
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停課,文廟、武廟、火神廟、登仙寺部分文物遭損毀。2005 年老齡協會重修前堂正殿,做樟木仿古門窗,裝修東西廊,重做墻體、地面、梯步等。[8]
二、金仙文廟建筑特征
文廟是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反映在現實中的物化形式,承載著豐富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的信息。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各地文廟基本上都遵循著比較固定的形制建造,即以曲阜孔廟的組群結構為基本模式,再依各地具體的人文、風土狀況而各有差異[9],總體表現為“同中有異”,各地文廟在建筑的構成、等級及雕刻等方面各具特色。
(一)選址特點
建筑群選址砂明水秀,建筑群布局嚴整有序,建筑單體經過縝密設計,營建工藝精良,大成殿、文昌宮石刻、木刻精美,代表了清代當地的較高水平,是結合了多種工藝的建筑藝術作品,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二)布局特色
民國八年重建的金仙文廟建筑和2005年修建的前堂正殿,坐南朝北,整體呈四合院布局,現存前殿(文昌宮),左右廂房,大成殿和泮池以及部分清代碑刻。建筑布局以大成殿-前殿中軸線為中心,前后、左右對稱排列,南為大成殿、北為前殿,左右為廂房。在大成殿前有泮池及部分清代碑刻。
(三)建筑特色
金仙文廟初創時為文昌宮,嘉慶年間文昌宮與大成殿并重,至道光年間已有大成殿、魁星樓、泮池等建筑,初具文廟規格。該寺保存的清代建筑,采用典型的穿斗做法,對研究本地區建筑形制、材料、技術等的發具有重要作用;部分構架上仍殘留有墨線和題記,對研究寺史及清代當地傳統營造技藝具有重要意義。
前殿,又名文昌宮,坐南朝北,懸山頂建筑,高約6米,面闊7間,共23米,進深9檁,通進深9米。建筑前為街道,后為合院,前殿與街道高差約為1.4米。建筑墻體存在較大改動,前檐右次間、稍間為后改板壁墻,左次間、稍間為后改磚墻,左、右山面為后改石墻,后檐左、右次間為后改磚墻。梁架結構明間為抬擔式,用五柱,前一進一步,前二進一步,中進四步,后進兩步。次間和山面用穿斗式屋架,六柱三掛童前后各出挑1檁,中柱前有1根瓜柱,瓜柱前為3根落地柱;中柱后為2根落地柱,2根瓜柱,隔柱落地。屋面采用傳統小青瓦冷攤做法,屋脊為灰塑脊局部用水泥修補。四架梁、平梁梁頭有卷草雕飾,挑枋略微上翹,步枋向上起拱呈弧形。前殿的題記基本可以認定都是清康熙五十五年題寫,證明前殿是康熙五十五年重建的建筑。
大成殿,又名夫子殿,坐南朝北,單檐歇山頂建筑,高6.5米,面闊5間,西側山面出單坡頂。面闊21米,進深9檁,通進深8.4米。建筑下五級臺階為月臺,月臺前有清代泮池。建筑后為自然夯土地面,東側緊貼民宅,西側為自然夯土地面。梁架結構明間為抬擔式,用四柱,前進兩步,中進四步,后進兩步。后檐步枋及四架梁上駝峰雕刻了瑞兔、祥云等紋樣。大成殿屋面采用傳統小青瓦冷攤做法,有勾頭滴水,屋脊為疊瓦脊。駝峰及部分粱枋上施雕飾,前檐步枋上殘存彩畫。大殿僅在脊枋上發現一條題記,沒有與年代相關的信息,根據其他碑記,大成殿是清道光十年創建的,因此現存大殿年代不會早于道光十年。
左右廂房形制基本相同,均為懸山頂,小青瓦屋面。廂房較正殿稍低,高約5米,面闊6間,共20米;進深6檁,前后出挑1檁,共6米。左、右廂房平面墻體改動較大,后檐現為毛石墻體,石塊大小不一,粘接層黏土較厚局部達5厘米,砌筑手法粗糙。前檐墻體在學校使用期間被改至檐柱位置,金仙鎮老齡協會接收文廟后,將墻體移回前金柱位置。現門窗、墻體均為后期重做。
泮池,大成殿北側,青石條砌筑泮池,在距離地面 0.5 米處有 排水孔兩個,泮池上有古柏一株,后加歐式欄桿及水泥花臺。
三、金仙文廟價值闡釋
(一)歷史價值
金仙文廟初創于元朝二年,康熙五十五年始建,其后經過多次重建、修繕,是四川地區現存為數不多的文廟之一,其提供了文昌宮與文廟并置的重要例證。金仙文廟初創時為文昌宮,嘉慶年間文昌宮與大成殿并重,至道光年間已有大成殿、魁星樓、泮池等建筑,初具文廟規格。文昌宮與文廟分別是道家文昌崇拜與儒家學說兩種思想體系的具體表現形式,文昌崇拜是發源于梓潼的自下而上的民間信仰,儒家學說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思想,由于科舉制度這一共同的人文基礎,兩者并置的現象在明代后比較普遍[10]。金仙文廟正是這一現象的重要例證。
(二)藝術價值
建筑群選址砂明水秀,建筑群布局嚴整有序,建筑單體經過縝密設計,營建工藝精良,大成殿、文昌宮石刻、木刻精美,代表了清代當地的較高水平,是結合了多種工藝的建筑藝術作品,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三)科學價值
該寺保存的清代建筑,采用典型的穿斗做法,對研究本地區建筑形制、材料、技術等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部分構架上仍殘留有墨線和題記,對研究寺史及清代當地傳統營造技藝具有重要意義,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四、金仙文廟保護利用思考
文廟是祖先留下的彌足珍貴文化遺產,具有不可再生的特點,一旦遭到了破壞,將是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因而文廟在保護利用中,任何時候都應該將保護放在第一位,保護是前提,只有保護好方能合理利用。金仙文廟保護利用要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應遵循以下幾點:
一是維修工程應秉持建筑群真實性和完整性的理念進行維修及復原。依據“修舊如舊,不改變文物原狀”的總體要求進行維修方案設計。在揭頂和落架,更換檁、椽、梁、枋等木構件,恢復被拆除和改建的墻體、門窗、木裝板、雕飾構件、吊頂等施工中要充分體現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藝、原做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金仙文廟作為物質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也為下一步展示利用預留設計空間。
二是展示利用應以文廟傳統功能的延續和拓展為主線。作為“廟學合一”的金仙文廟在歷史上曾作為先圣先賢和官學進行學校教育的場所。直至清末科舉廢除,文廟的官學文化教育功能漸漸不復存在,祭祀功能也隨著歷史的發展漸漸不被重視。金仙文廟依托部分建筑空間設立《科舉展》等基本陳列,增進人們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了解,并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得以繼承和弘揚;最后依托大成殿、前殿舉辦各種“國學講堂”、“國學班””,實現對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功能,從而起到豐富歷史知識、提高文化素養作用,最終達到弘揚儒學、提升整個社會的人文素質之目的。
三是對文廟建筑群和周邊環境整體修復。文廟的修繕必須體現自身格局的完整性,同時由于周邊民房眾多,且有些破舊不堪,嚴重破壞了文廟景觀。所以在對文廟修復的同時,對周邊環境的改造也應同步進行。
四是加強對文廟歷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在文廟保護和利用過程中,要全面深入挖掘其歷史文化內涵,特別是對文廟內的碑記、石刻、匾額、楹聯以及相關記載文獻等,都應該進行全方位、深層次、多方面的研究,力求做到讓金仙文廟“背后”的故事活起來。
文廟作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場所,承載著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尊重和敬仰。文廟保護刻不容緩,文廟歷史文化研究工作迫在眉睫。我們要加大對文廟的研究保護,讓更多的文廟古建及歷史再現。
注釋解讀:
[1]1994年,挑挖金仙場新街街道,于金仙文廟正殿東側處,從公廁糞池掘出文廟石碑 9 張。其中《文昌宮碑記》載:以為元朝二年創修廟宇規模稍具其後至萬曆年…(注:…為石碑腳殘缺),碑刻全文詳碑刻列表
[2]《重輯崇儒會序》摘錄:嘉慶八年奉旨特頒文昌宮春秋祀典與大成殿并重盛哉,群祀弗可及也…每逢春秋二季逐撥利金虔備牲儀致祭…以彰我朝尊師重道之典且激發人心以各勵夫敦書說理之氣
[3]《善后碑序》摘錄:我地自國初獻逆屠蜀后不見兵戎者三百年矣。《劍閣縣教育志》載:光緒三十二年,金仙文廟辦起當地第一所初級小學
[4]《劍閣縣續志》載:“民國七年八月,山賊馮濫鼻子據金仙場。”《民國八年仲夏碑》載:“近又疊遭兵匪毀敗圣像傾圮,門瓦無存。”2006 年,金仙鎮老齡協會組織“文廟修復籌建組”在修復中,發現民國八年重建使用的西廊幾根柱子,前堂大門左門方等多處有燒焦的痕跡
[5]民國八年仲夏之碑記:近又疊遭兵匪毀敗,圣像傾圮,門瓦無存大□全境之恨…乃商同會長袁宗翰先生鳩工三閱月而規模一新
[6]《劍閣文史資料選輯》摘要:升鐘農民起義失敗后,…劍閣縣長吳龍驤率縣保安團一個中…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到金仙場…將袁化鵬押赴武廟刑場…斃袁于石梯下,吳令割下首級…。將金仙與袁家溝等地農民…關押在文廟五十多人,十二月六日,文廟正殿搭一排長桌,吳坐在那里,將黑名單點名審問…拉到武廟壩子殺害,…殺死二十多人
[7]《回憶拆魁星樓經過》摘錄:“我名龔光華,男,生于1941年6月,在51年春天,母親送我到一個外地老師處讀書。當時私學辦在文廟的魁星樓下面…后不久就把魁星樓拆掉了。…我還記得把文昌老爺吊在原來的戲樓上一月多。”
[8]此次修復于農歷 5 月初動工,十月二十日竣工,二十五日開光慶典
[9]柳雯:《中國文廟文化遺產價值及利用研究》,2008年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10]明內閣大學士李賢在《文昌祠記》中提到,“嘗見天下郡邑學校,往往有文昌祠,而不知其所謂。”作為當朝內閣大學士,李賢定是見多識廣之人,從他的敘述中可以斷定,在明代文昌祠廟與孔廟并置的情況比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