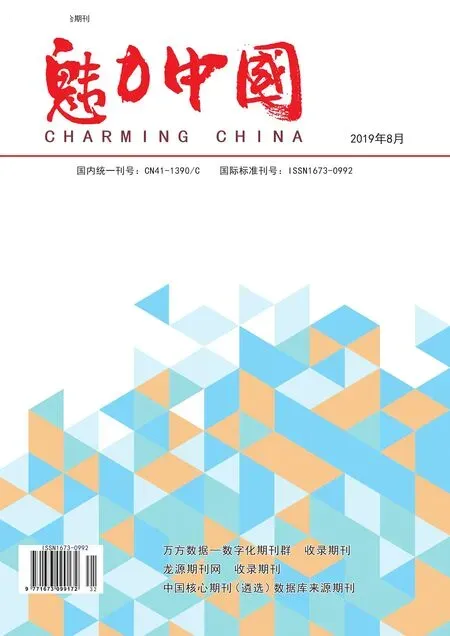夜叉形象之演變
宋獻科
(武警工程大學,陜西 西安 710068)
夜叉是隨著佛教的傳入,開始在出現在中國文獻和人們印象中,考察夜叉形象的演變可以從中分析外來文化在古代中國的接受程度。
追溯夜叉的本義是來自印度神話,據《毗濕婆往世書》所述夜叉與羅剎同時從生主補羅私底耶(或為補羅底耶)或大梵天的腳掌中生出。雙方通常相互敵對。
一、早期佛教傳入時的夜叉形象
中國人最早了解到夜叉是從佛經中來,夜叉本身是一個負面的形象,《大吉義神咒經》中有“凡有二十夜叉鬼母, 彼諸子夜叉等身形姝大甚有大力, 能令見者生大驚懼普皆怖畏。又復能使見者錯亂迷醉失守。猖狂放逸, 飲人精氣。”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中夜叉是一個相貌丑陋的形象,“在過去世時,有一夜叉鬼,丑陋惡色,在帝釋空座上坐”。在佛經中夜叉出現次數最多的是作為天龍八部之一出現的,天龍八部是屬于佛教的護法神,在佛講經時出現。在佛經中,夜叉逐漸又稱為了護法的形象,《大日經疏》中:毗沙門天王手下有“夜叉八大將”。《起世經》中:諸比丘、毘沙門王身邊常有五夜叉守護,“一名五丈、二名曠野、三名金山、四名長身、五名針毛”。
這一護法的形象的塑造,是佛教為宣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形成的,如慈利王自血布施五夜叉,夜叉受比豆梨點化的故事。此處以夜叉受比豆梨點化的故事為例說明。夜叉與龍王受比豆梨度化來自《菩薩本行經》:龍王夫人聽說閻浮提波羅奈國婆羅達王,有一輔相名比豆梨,仁慈智慧,一切經籍無不通達。欲得此心而用食之,欲得其血而欲飲之。龍王請夜叉不那奇幫忙,給他兩顆明珠。夜叉化作商人,持明珠與國王博戲,以比豆梨為賭注,后國王輸,夜叉捉比豆梨徑飛虛空。王失比豆梨大愁憂,夜叉帶到山間想殺比豆梨,問起因,答想龍王夫人得智慧故,比豆梨為其講“人作惡有五事,修善之人有五事好”。于是夜叉聞其所說,心即開解,頭面作禮,稽首其足,即從比豆梨求受教誨。時,比豆梨為說十善生天之法。夜叉聞法,歡喜踴躍奉而行之,龍王及夫人也受其教化,皆奉十善攝身口意持八關齋,諸龍歡喜。并因此而解金翅鳥王之厄。此處的夜叉殺人能飛行是負面的形象,在比豆梨的度化下皈依佛法,本意在說明佛法無邊可普度眾生。從側面,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夜叉是一個可以由壞變好的形象,成為佛教的護法。
二、《太平廣記》所見中古時期夜叉形象
《太平廣記》是宋代四大書之一,收有大量關于唐宋時期的傳奇故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正史沒有反映的社會情況,特別是平民百姓的情況,是了解唐宋時期社會的很重要的一部書。其中專門有關于夜叉的條目,從中可以管窺時人對于夜叉的印象。根據房弈的統計:《太平廣記》中有關夜叉的記載共出現二十四條。今查多出一條共二十五條。《太平廣記》中的夜叉還是和佛教相關,但是已經與普通民眾相接觸,逐漸回歸了他本意,是一個負面的形象,沒有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形象,形象也變得更加豐滿,有了多樣的形象。
《哥舒翰》條言夜叉食人之尸體,《章仇兼瓊》條一飛天夜叉將一小孩掠到高塔之上。《楊慎矜》條夜叉爬門是不祥之兆。《江南吳生》條夜叉變化為人,懼人多。《朱峴女》條夜叉奪去朱峴女至于佛頭之上。《杜萬》條杜萬發現被夜叉所救,并育有二子,一子被夜叉所殺。《韋自東》條太白山有夜叉食盡僧眾,霸占佛寺。《馬燧》條描繪夜叉形狀和吃人狀,“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東洛張生》條夜叉食馬,驢,仆人。《薛淙》條飛天夜叉被金甲天神追趕。《丘濡》條夜叉掠村女。《張越石》條,有夜叉夜乞食于人,不予則打人。《張融》條張融是羅剎鬼。《蘊都師》條有寺中壁畫上夜叉變幻為女子誘惑都師后吃掉其人。在《太平廣記》夜叉卷之外各卷中的夜叉往往只是僅僅涉及到夜叉。
關于夜叉吃人表述的有8條,有一些條目中,夜叉是并不傷人的,在佛經中的夜叉是吃人的,但是是為了體現,再丑惡的物種,再干盡壞事,一旦醒悟,受教化也是可以向善的,在佛經中出現最多的還是向善,護法的形象。然而在佛教在中國流行的過程中,在普通人的印象里印像更深的是醒目的淺顯的形象的夜叉,而夜叉吃人,相貌丑陋在喜歡把事物簡單的分成兩類的普通民眾留下了印象,丑惡的一面就逐漸被傳播開來,很多人認識夜叉的形象還是從佛寺的夜叉壁畫而來,有兩處,“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夜叉形象是從佛教傳來,此時夜叉形象仍與佛教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與佛教、佛塔有關的7條之多。常常出現在佛塔、佛像附近,或是和僧人相關聯。還能看到其來源于佛教的影子。許多例子還是顯示夜叉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出現在了生活中,在夜晚吃飯的時候出現乞食,在大門口出現,預示災禍。將遙遠的不可知的國家和人認為是夜叉。把深惡痛絕的惡人喻為夜叉。已經為人們所熟知接受。
結語
夜叉的形象總結可以大致得出“長丈余,高于常人,目如電光,鋸牙鉤爪,口赤發朱”。在佛經中夜叉的形象最初是丑惡的一面,經佛教教化變成了護法一個形象,是佛教教化的一個縮影。在《太平廣記》中夜叉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已經基本成型,高與常人,目如電光,赤嘴獠牙的就是夜叉。雖然與佛經中希望的形象不一,但是這個形象已經在人們心中形成。到明清小說中,夜叉的形象也有改變,有將厲害的婦人稱為母夜叉,夜叉視為地獄中的屬吏,夜叉作為海龍王的下屬。但是其地位不高的形象始終未變。正如傳入中國的佛教已失去本來的面貌,被國人加以改造更適合中國,夜叉的形象也與其佛經面貌有了很大區別,在佛經中樹立的惡人可通過佛教徒點化向善護法的形象,在唐宋之際在中國人印象中已經開始變化,漸成為惡人的代名詞。這也體現了佛教對中國文化生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