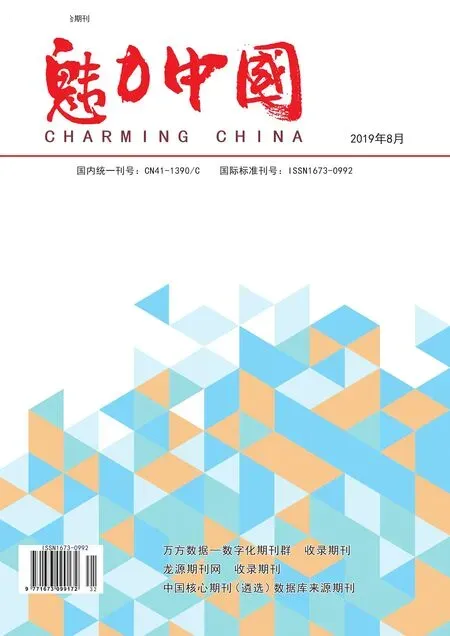淺談?wù)Z言節(jié)奏在塑造人物中的重要性
——以“燃燒的梵高”中的茜恩為例
陳慧娟
(浙江話劇團,浙江 杭州 310005)
引言
語言節(jié)奏對于話劇舞臺表演藝術(shù)來說至關(guān)重要,是演員塑造好一個人物的必要因素之一,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站在舞臺上即為平等,就都是演員,無謂大小,都要做好一個演員應(yīng)該做的事情,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1]把握好語言節(jié)奏是一個演員的必修課,也是成為一個好演員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什么是語言節(jié)奏
學(xué)表演的學(xué)生在大學(xué)期間主修四門課:聲臺形表。而對于話劇而言,臺詞尤為重要,它沒有辦法像影視演員一樣有后期的幫助,所以就更考驗演員的臺詞功底。甚至有的時候臺詞說好了就能塑造好一個角色,如何說好臺詞,就主要從語言節(jié)奏入手。那到底什么是語言節(jié)奏?其實大部分話劇是需要通過有聲語言來表達劇情和情感,而所有的有聲語言表達藝術(shù)都是一樣的,就比如演員說的臺詞和歌手唱的歌是一樣的,都是需要旋律和節(jié)奏的。說出來的臺詞要有高低起伏,氣息要有長短變化,語速要有快有慢,哪怕聲音大小也要不停變化,而不是一味的賣力嘶喊或者硬生生的把劇本里的字背誦給觀眾。這樣觀眾聽起來才不會覺得乏味無趣。使臺詞聽起來像歌聲一樣優(yōu)美,這就是在話劇表演藝術(shù)中的語言節(jié)奏。
二、如何準(zhǔn)確找到語言節(jié)奏
(一)在練習(xí)中不斷摸索
要想把握語言節(jié)奏,最初級的也是我們必須掌握的就是邏輯重音,這個邏輯重音和我們生活中說話的重音是一樣的。也就是找到說臺詞的真實感。但是放到舞臺上的時候演員可能會有一些突發(fā)情況丟掉了語言重音,丟掉了來源于生活的真實感,這是萬萬不可的。在能每次找到語言的邏輯重音的基礎(chǔ)上,就要慢慢摸索如何通過對語言節(jié)奏的把握賦予臺詞二次生命,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也就需要我們不斷練習(xí),通過音色、氣息、語速快慢以及聲音的高低等進行處理。有時候一句臺詞要在私下練習(xí)成百上千遍,也不見得能找到一句臺詞最完美的表達方式,這個過程是有魔力的,讓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其中。而這也正是讓我著迷的地方。比如在我演出的《燃燒的梵高》中,第二場起光的第一句話是茜恩站在路燈下說:“要過夜嗎先生?”就這簡單的幾個字,就要表達出人物的身份、現(xiàn)狀的落魄、所處的環(huán)境、性格的體現(xiàn),也要作為這個人物在全劇中所起的作用打好基調(diào),我私下練習(xí)過無數(shù)次,幾乎是一空閑下來就去思考這句話怎么表達才最好,幾近癡迷的狀態(tài),甚至在上臺前一秒鐘還要溫習(xí)一下在我練習(xí)的過程中我比較認可的節(jié)奏表達。這是我們準(zhǔn)確找到語言節(jié)奏的第一步。當(dāng)然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不斷地練習(xí)才可以做好,尋找語言節(jié)奏,也不例外。
(二)在不同情景下找區(qū)別
前面說的不斷練習(xí)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須要學(xué)會的尋找語言節(jié)奏的方法,當(dāng)遇到不同的角色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同一句臺詞在不同的規(guī)定情境、不同人物說出來的效果要截然不同,哪怕是同一個角色的不同情景下,也要有區(qū)別。比如《燃燒的梵高》中前半段飾演茜恩、后半段變換后飾演天使,一人要完成兩個角色,她們兩個都有“你這個傻瓜”這句臺詞,在茜恩這個角色下的“你這個傻瓜”是被愛時驚訝的不知所措、掩飾內(nèi)心的外化。而在天使這個角色的“你這個傻瓜”則是對梵高感同身受的理解、心疼,對他的安慰。這兩個角色下說出來的相同臺詞既有一樣的態(tài)度,也有不一樣的態(tài)度。這就需要在這兩個角色的相同中找不同,用不同的語氣語調(diào)、氣息變化和聲音大小、節(jié)奏變化來區(qū)別,然后再加以不斷的練習(xí)。在同一劇本的同一角色下,比如梵高在精神崩潰邊緣以及與自己心靈對話時兩次說到:“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可他仍然熱愛著自然與生活,因為他是畫家”,崩潰邊緣時,他是彷徨的無助的,甚至有些猶豫。而在最后一幕中與內(nèi)心的自己對話時,與內(nèi)心對話的他說出的“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可他仍然熱愛著自然與生活,因為他是畫家”時,是堅定的、給予自己肯定的。這兩處的同一臺詞就完全要用兩種語言節(jié)奏去處理。這種找語言節(jié)奏的方法,會使演員更準(zhǔn)確,更快速進入到角色當(dāng)中。這就是在不同情境下找到不同語言節(jié)奏的區(qū)別。
(三)在實踐中找到下一次的經(jīng)驗
不管是專業(yè)還是非專業(yè)、資歷深還是資歷淺的演員,都會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有的時候哪怕在演出中都不一定能找到最佳的語言節(jié)奏,這就使我們不可避免的在此次實踐中找到經(jīng)驗,在下一次演出中有更好的發(fā)揮。不管是什么行業(yè)什么專業(yè),都需要在一次次實踐和失敗中找到經(jīng)驗和方法,這也是激勵著我們,推動著我們向前的很重要的一點。尤其是話劇演員,在舞臺上不確定的因素太多,每一次的表現(xiàn)甚至不受演員自身控制。比如我在演第一次大戲《關(guān)漢卿》的時候,因為太過于重視造成了緊張的現(xiàn)象,當(dāng)時就是在舞臺上就明知道自己出現(xiàn)了哪些問題,但是當(dāng)時的情況,不論是聲音、肢體還是節(jié)奏全都不受我自己的控制,對我自己而言,這就是一次失敗的演出。但是我知道我需要做的,不是一味的自責(zé),而是認真回想自己的不足加以改進,我知道一次失敗不足以證明什么,如果下次不加以改進才是真正的失敗。所以就是這一點,讓我在第二次上大戲的時候有了很大的改變,接下來的每一場下來,我都和導(dǎo)演同事進行了交流,我做到了在我能力的基礎(chǔ)上,在舞臺上一次比一次成熟。所以說我們只能在一次次實踐中摸爬滾打,我覺得這也是準(zhǔn)確找到語言節(jié)奏的最后一步,也是一個優(yōu)秀的話劇演員需要做的反省和總結(jié)。綜上所述,準(zhǔn)確找到語言節(jié)奏要從不斷練習(xí)、不同情景下的分析、實踐中找經(jīng)驗這三個大方向努力。
三、語言節(jié)奏的重要性
(一)更好的幫助演員完成對人物的塑造
一個人物鮮活的立在舞臺上需要從很多方向進行工作,比如肢體表達,調(diào)度走位和語言表達等。其中我認為肢體表達和語言表達尤為重要。尤其是語言表達,我們見過也演過很多話劇是在舞臺上沒什么肢體動作而是全靠一張嘴說出一部戲,那么就更加意味著臺詞對一個演員來說有多么重要。一段臺詞經(jīng)過演員的節(jié)奏處理,才會讓人耐人尋味,才賦予了劇本二次生命。在剛進入到表演課程中,表演老師常說,一個演員在舞臺上在三分鐘之內(nèi)一定要有變化,我的理解為,每一個三分鐘之內(nèi)語言節(jié)奏都要有變化。比如《燃燒的梵高》中茜恩段和梵高分手前的那段爭吵,大段的獨白里控訴梵高把所有錢用于畫畫,在一起后的生活窘迫與當(dāng)初承諾的愛不相同,這段臺詞很考驗演員對語言節(jié)奏的把控,要分析劃分成不同段落、找準(zhǔn)轉(zhuǎn)變的點和每句話的潛臺詞,有哭有笑、有悲有喜,臺詞的速度要有快有慢、有急有緩、有大停頓。這樣才可以用臺詞把生活所迫之下,為了幾個孩子能活下來一個社會底層人的生存壓力下內(nèi)心的無奈。在日常表達中說話都要有節(jié)奏變化,否者傾聽者也會覺得你的敘述平淡無奇。更何況是在話劇表演藝術(shù)中。臺詞說“好”了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把握好了語言節(jié)奏,語言節(jié)奏一旦完整,這人物就塑造成功了一大半。
(二)使觀眾感到話劇的魅力(語言的藝術(shù))
我認為話劇區(qū)別于影視劇的最大一點就是話劇表演藝術(shù)性更強,語言的藝術(shù)更不是一句虛話,而是我們應(yīng)該認認真真鉆研的藝術(shù),如果只是堅硬的把臺詞讀了出來又何談藝術(shù)一說,又如何去給觀眾欣賞,又如何利用舞臺使觀眾身臨其境?它區(qū)別于其他表演藝術(shù),比如器樂演奏、舞蹈表演等,是通過其他沒接和技巧進行。說話作為上天賜給我們的一出生就會的一種技能,我們話劇演員更要做到比普通人更會“說話”。話劇演員之所以是話劇演員,就是因為它區(qū)別于普通人,對語言更有研究,更懂得語言的魅力和藝術(shù)感。在有嘴就會開口說話的世界里,我們話劇演員把握了在話劇表演中的語言節(jié)奏,把話劇作為專業(yè),用既生活化又高于生活的語言去演出,能使觀眾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每一句臺詞的內(nèi)涵,在舞臺上表達出一些觀眾平時無法表達的情緒,讓觀眾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話劇演員通過臺詞表達出來的起伏情緒,如果掌握好語言節(jié)奏,可以直接把第三方的觀眾帶入到戲劇中。會使觀眾感受到話劇的魅力,使更多人熱衷于觀看話劇,欣賞藝術(shù)且弘揚藝術(shù)。
(三)使演員本身成為了一個“會說話”的人
無論做什么行業(yè),它的最終目標(biāo)都是在推進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話劇表演藝術(shù)也不例外,掌握好這個專業(yè)我們需要掌握的硬件標(biāo)準(zhǔn),才會使我們在這個專業(yè)上有所作為。作為學(xué)習(xí)話劇表演的我們來說,這是我們的專業(yè)、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特長,就我而言,我希望我的專業(yè)可以隨著我一步一步的成長,也慢慢進入到一個更專業(yè)的狀態(tài),甚至希望它對我的生活也有所助益。其實在分析劇本,摸索語言節(jié)奏的過程中,會鍛煉作為演員的我們更加透徹的分析文字以外的含義,這帶到日常生活中也未嘗不可。比如茜恩這樣一個“妓女”類型的女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通過分析她的內(nèi)心活動,她就讓我學(xué)習(xí)到了在生活中如何圓滑處事、穩(wěn)妥辦事。鍛煉好這項技能,它會使我們在生活中更懂得“如何說話”、如何把話說的漂亮、如何成為一個高情商的人。在學(xué)習(xí)表演的過程中表演老師也常常說:“學(xué)表演的孩子,哪怕以后慢慢脫離了這個行業(yè),他在其他行業(yè)上也會成為更優(yōu)秀的那個人。”剛開始并不懂這句話的意思,認為這是一句老師激勵我們好好學(xué)習(xí)的話,但經(jīng)過這幾年的學(xué)習(xí)和在舞臺上實踐,我明白了這不是一句空話,在每次的劇本分析中、在每次摸索語言節(jié)奏中,我們都慢慢的在增加我們對文字的感知度,這種學(xué)習(xí)是潛移默化的,不知不覺中深入到了我們的骨子里。所以說,學(xué)習(xí)好如何掌握語言節(jié)奏,這不但對我們的專業(yè)有所幫助,更有意義的是,它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很大的助益。
結(jié)語
話劇舞臺表演是一門藝術(shù),其中分析劇本、研究臺詞、摸索語言節(jié)奏更是大有學(xué)問,它會使我們成功為一個更好的人,這也更是我們這個行業(yè)一生都需要去學(xué)習(xí)的課程。最后,和大家分享我內(nèi)心一直堅守的四個字。不卑:是對于藝術(shù)的追求,不能有一絲的妥協(xié)。舞臺對于我來說,是一片凈土,是一片讓我心靈得到釋放的天空,容不得任何敷衍潦草。不亢:是對于生活,要謙虛純粹,欲做戲先做人,自信而不自滿,得意而不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