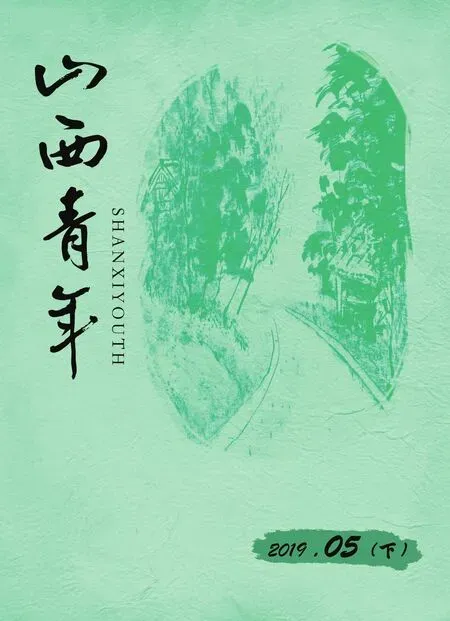校園“黑出租”現象的法律問題的研究*
靜泉霖
(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出租車輛逐漸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而對學生而言,在沒有能力負擔私家車購買與保養費用的前提下,校園周邊的出租車便成為了學生日常出行的首選。“黑出租”的存在,不僅影響了正常的運營車輛市場秩序,更對社會管理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無照運營、亂停亂放等現象層出不窮,增加了政府管制的負擔。因此,本文主要針對校園“黑出租”現象存在的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只有了解此類根本性問題,才能從源頭對校園“黑出租”現象予以治理。
一、校園“黑出租”現象的形成溯源與性質認定
根據2014年9月30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發行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規定》第八條規定:“申請出租車經營的,應當根據經營區域向相應的設區的市級或者縣級道路運輸管理機構提出申請,并符合下列條件……”由此可知,在我國出租車行業的從業資格應當經過相應主管機構的審核與許可,未經許可不得從事出租車經營服務工作。:“黑出租”市場屬于地下經濟的一種,所謂地下經濟,在《經濟與管理大辭典》中概括的比較全面:“地下經濟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經濟活動,這類經濟活動不納入官方統計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內,不向政府申報和納稅。”而校園“黑出租”則兼具“地下經濟性”與“校園性”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校園“黑出租”填補需求空缺及收入可觀
從長期的角度審視校園“黑出租”現象,在各城市校園周圍的交通設施發展往往是較為滯后的,因此校園“黑出租”的營運模式便迅速發展起來。曾針對北京出租車司機收入情況做過統計的學者王克勤得到的數據,計算下來,司機的月收入為6400元。但這個收入是在司機擁有出租車經營權的前提下取得的,如果該司機沒有經營權,則每月要交給出租車公司4400元,那么其收入僅為2000元……除此之外,司機還需要給公司上繳一筆不菲的風險抵押金,其數目根據車況等從3萬到8萬不等。正因如此,校園“黑出租”的吸引力使得更多人與其接觸并實際參與營運。
(二)執法部門針對校園周邊治理難度大
首先,校園“黑出租”營運方式的日新月異將執法方式與執法手段的滯后性暴露無遺,僅憑借執法部門依法作出罰款的處罰方式并不足以懲治黑出租的非法營運行為,而從查處“黑出租”的扣車再到作出處罰后的放車,更多體現了對“黑出租”執法的無力感;其次,校園“黑出租”的乘客身份大多為學生,在缺乏社會經驗和觀念的情況下,很多學生在不自覺間便會產生對“黑出租”司機的庇護心理,更有甚者會同司機一起阻撓執法人員檢查、取證;最后,從事校園“黑出租”的車輛多是低價車、多手車或報廢車輛,在執法人員對其車輛予以查處后,車主往往會做出影響執法部門執行力的棄車、逃費等行為,對執法部門與校園周邊安全的影響不言而喻。而這些難題,又更加滋長了校園“黑出租”的發展趨勢。
二、校園“黑出租”的危害與管制的法律透視
(一)危害與風險并存
校園“黑出租”營運的對象主要是校園內的學生,加上從事“黑出租”營運工作的車輛大都車況較差,缺乏營運安全性能的保障,給學生出行帶來了十分巨大的風險,為其人身財產權益不受外界侵犯埋下隱患;另外,“黑出租”的運行在部分情況下與職業出租車的區分并不明顯,再加之因缺乏有效管制。長此以往,不但會危害整個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運行,也會使學生養成法律意識淡漠的負面思想。
(二)管制與監督并行
在涉及校園“黑出租”問題時,我們往往會陷入這樣一個誤區,那就是一直致力于讓“黑出租”采取公司經營或個體經營的方式,使其“合法化”,而忽略了對其應進行的管制與監督。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應該致力于對公司的出租車輛、出租車司機進行管理與監督;從公司的角度來看,則應該明確公司與各司機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形成系統化,真正的以公司制的角度對司機進行管理,真正達到對“黑出租”從“不敢坐”到“不愿坐”,再到“不想坐”的思想轉變。
三、結語
校園“黑出租”現象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在處罰難、執行難的表象下,是社會建設過程中的管制與監督的缺失以及相關維護出租車司機合法權益的法律規范的滯后造成的綜合結果。只有企業與政府共同合作,將司機的管理與權益的維護相結合,為正常的出租車經營市場提供發展的基礎,也對校園“黑出租”的產生予以明確警示并進行打擊,才能從根源上杜絕校園“黑出租”現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