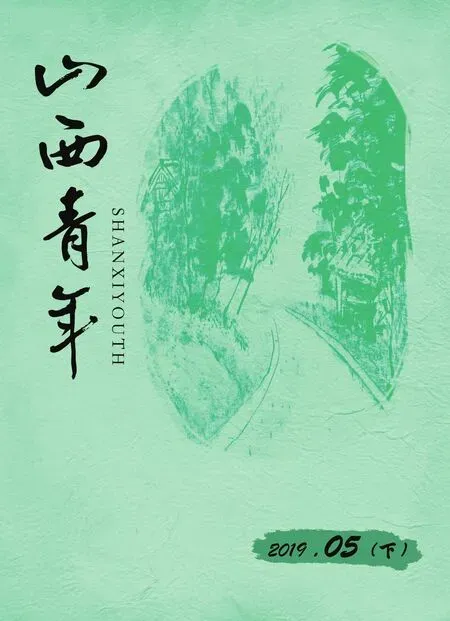馬克思管理二重性思想對人的主體性復歸的意義
張 哲
(太原科技大學哲學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24)
中世紀的人類存在于一個“顛倒的世界”之中,那時上帝是整個世界的中心,人成為依附于上帝的附屬物,屬人的本質成為屬神的本質,原屬人的主體性成為神的主體性。近代之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理性代替上帝成為新的“神圣形象”,人生活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人的主體性建立在對“物的依賴性”之上。現代哲學正是致力于消解人對物的依賴性,實現人的主體性的復歸。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思想正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管理思想的批判及對未來社會的科學設想之上,并始終堅持對人的主體性的復歸,追求人的自由自覺。馬克思從現實的人這一邏輯起點出發,以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為基礎,實現人的本質從理性、物的依賴性到人本身的復歸。馬克思管理哲學中對人主體性的復歸對現代社會管理中對人的壓迫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一、馬克思管理二重性思想的主要內容
馬克思的管理思想是以生產方式的分析為基礎的二重性思想。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分析為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核心思想也被馬克思運用于管理維度,所產生的是以生產方式分析為基礎的管理二重性思想。
馬克思將生產方式分為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即“技術-協作”方式,“即技術以及由他所要求的協作勞動或協同勞動的方式。”[1]對于“技術-協作”方式,馬克思又稱為協作勞動、共同勞動的方式。正是這一方式將個人的力量整合于集體之中,創造了集體生產力。以協作為特征的勞動方式本身就意味著管理,其優勢正是通過管理而實現的。“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3]第二個維度即生產的經濟關系方式或社會關系方式,“包括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勞動產品分配方式,以及它們的具體實現所需要的中介方式,如商品交換方式。”[2]對于第二個維度即經濟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管理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明顯的是,在奴隸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中體現的剝削關系,正是由強制性管理實現的。第三個維度則是前兩者的統一。在這三個維度中,“技術-協作”方式是推動社會發展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力量,決定了后兩者的發展性質與狀態。
馬克思以其管理思想著重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管理特征。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管理具有二重屬性,其一即共同的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職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協同勞動方式,社會各行各業各司其職,滿足不同的行業需要,同時由于分工明確、細致,提高了社會整體的生產水平,與之前的社會形態相比,創造了極大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但是,這一共同勞動過程卻產生了兩個特點,即以工廠為主要生產組織形式和以機器為主要生產手段。這兩個管理特性都極大的提高了生產效率,帶來了生產資料的驚人節約。前者將工人組織起來,在同一個地方勞動,方便了管理。后者將人力變為物力,將生產變為一體化、流程化的生產,使管理變為科學管理。其二,基于社會大生產的協調勞動,產生了剝削工人的經濟關系。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變現為壓迫和剝削關系,資本的貪婪屬性體現在人的屬性。生產的產品也變為剝削壓迫人的產品,其性質是商品,剩余價值是追求目的。
由上述兩個維度出發,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管理特征集中表現在加強勞動強度、監督、減少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及重復性上。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決定了其最大化追求剩余價值的目的,體現在在管理上即不斷加強工人的勞動強度及勞動時間。同時,其價值觀表現為一種“為生產而生產”的生產拜物教思想。這樣的價值觀必然產生了對人的壓迫。
二、對資本主義生產管理方式的批判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協同勞動與經濟關系必然表現出束縛人、壓迫人的特征。馬克思的管理思想對人主體性的復歸正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基礎之上。資本主義管理的特征表現在對人的壓迫及剝削上,是人主體性的喪失。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協同勞作方式還是經濟關系無不在表明人成為受壓迫、受剝削的人。
社會化大生產下的協同勞動將人組織在同一個地方進行勞動,雖然提高了勞動效率,節約了勞動成本、生產資料,但是,從人的角度看,也是對人的一種束縛。勞動應該是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但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勞動成為了一種將人束縛在特定時間、地點的謀生活動,不再是人的自由的活動。機器化大生產必然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也使人成為受機器的壓迫。人在勞動中不再與人相聯系,而成為與物相聯系,人與人的關系必須通過物來體現。人的活動成為受物支配的活動。與之相適應,在社會關系中,由于勞動產品的商品屬性,勞動者成為商品的被壓迫者,而不再是其所有者。尤其明顯的是,人自己也變現為商品的出賣者,人的勞動成為最大、最受歡迎的商品,體現在制度層面,即勞動雇傭制。其結果是產生了異化勞動,即勞動者與產品相異化、勞動者與勞動活動相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及人與人相異化。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動機決定了其對工人的壓迫與剝削。資本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方式是把生產商品所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社會平均水平以下,也就是通過加大勞動時間來完成。工人為了謀生必須遵循工廠主的意愿,也就意味著對其自身主體性的壓迫。
三、使人成為自由自覺的人
主體性是使人成為自由自覺的力量。人的主體性體現在擺脫壓迫、束縛的力量,使人成為自己的主人,成為自由自覺的人。馬克思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使人成為受束縛、受壓迫的因素,重建了人的主體性。首先,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機器成為生產的主要勞動工具。與此相適應,應該成為主體的人異化為受機器壓迫束縛的客體。工具理性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機械化和標準化的工藝程序可能使個人的精力釋放到一個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領域。人類生存的結構本身就會改變;個人將從勞動世界強加給他的那些異己的需要和異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來。這時,個人將會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產機構能夠組織起來,并致力于滿足生命攸關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還是充分地集中起來為好;這種控制并不妨礙個人的意志自由,反而會使它成為可能。”[4]但是,實際上情況正好與之相反,技術非但沒有實現人的自由反而限制了人的自由。工具理性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使人成為喪失批判性、否定性的人,這樣的人喪失了自由和創造能力,形成單向度的人。其次,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生的異化勞動是人的自我異化,它是異化的深層規定性和實質,物的異化不過是其外在表現和形式。因此,馬克思認為,要實現人的解放,實現人的本質活動的自由自覺性和創造性的本性即復歸人的主體性,必須變革不合理的世界,改變財產的占有方式,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改變勞動雇傭制才可能使之成為現實。
四、結語
馬克思對管理中人主體性喪失的深刻批判及對人主體性的復歸,都表明人的本質從理性的回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就是對現實的人的批判。其解決方式即改變現存世界,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也就是對人主體性的復歸,從而使人成為自由自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