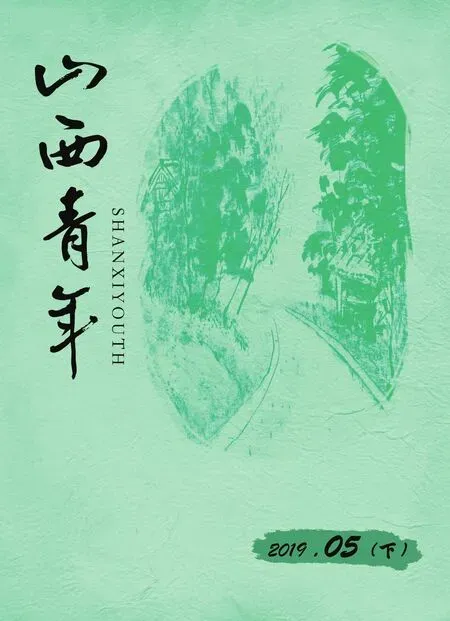我國快遞實名制與隱私權的限制
余 欣
(湖南科技大學,湖南 湘潭 411100)
一、我國快遞實名制的概念及現(xiàn)狀
(一)快遞實名制的概念及法源
快遞實名制,指的是寄件人在寄送快遞時,需要出示真實有效的身份證明材料,登記個人信息,才能進行快遞活動。有些學者認為,快遞實名制不僅包括客戶交寄時需要實名認證,收件人在收取快遞時同樣也需要出示相關身份證明如身份證。但是根據(jù)我國實踐來看,目前更加偏向于寄送快遞時要求快遞寄送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證,而在收件時則存在兩種情形:(1)如果是快遞送貨上門的情況下,收件人則不被要求出示身份證,只需要對快遞包裹進行簽收即可;(2)若是在快遞營業(yè)網點取件,收件人則需要出示身份證并核驗信息。快遞實名制制度起源于2010年公安部在浙江省紹興市的“實名制”試點。隨后在2015年10月26日,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促進快遞業(yè)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將快遞行業(yè)安全監(jiān)管寫入其中。2016年3月1日,快遞實名制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實施。
(二)快遞實名制的缺陷
快遞實名制自實施以來,雖然有效遏制住了“犯罪快遞”這一現(xiàn)象,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身存在的問題。首先,實施標準混亂,特別是對于是否實施收件人實名制這一制度存在相當程度的任意性。其次,快遞實名制缺乏立法層面上的明確規(guī)定,快遞工作人員的一些行為如查驗身份證的行為缺乏法律法規(guī)的授權。最后,快遞實名制造成了個人隱私權的破壞。
二、我國快遞實名制對隱私權的侵入
(一)隱私權的起源及界定
“隱私”一詞來自于英語單詞“privacy”。該詞最早的含義是指“秘密、秘密行為、獨處”,后逐步引申為“私人事務(a private matter)、秘密”。隱私權的起源,目前學界公認最早的隱私權理論于1890年由美國學者Samuel D.Warren和 Louis D.Brandeis通過《論隱私權》一文提出。當下學者們對隱私權的定義仍眾說紛紜,但是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隱私無法界定,只能描述”,若要定義隱私權,只能從其本質入手。
(二)快遞實名制對隱私權的限制
1.快遞實名制對通信秘密和自由原則的限制
我國憲法第四十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然而快遞實名制在實施過程中,寄件時需要寄件人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核實后才能進行寄送。這無疑限制了寄件人匿名或者使用昵稱寄送快遞的權利;以及一旦寄件人身份證丟失,在補辦身份證期間,根據(jù)快遞實名制的規(guī)定,寄件人將無法郵寄快遞包裹,這也是對寄件人通信自由權的限制。
2.快遞實名制對個人信息保護的限制
我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一條規(guī)定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即信息性隱私權。信息性隱私權指的是他人對其個人信息的使用、加工或者轉移所享有的隱私權。該項隱私權理論是對信息化社會發(fā)展的回應。在信息時代,個人信息成為了具有極高商業(yè)價值的商品。通過對個人隱私信息的分析,不僅可以獲取權利人的個人信息及關系網,更可以利用這些信息進行大數(shù)據(jù)分析,以此展開其他的商業(yè)活動。寄件人在寄送快遞時,快遞員會將寄件人的真實姓名、電話、住址、身份證號等真實信息錄入快遞公司的數(shù)據(jù)庫中,以完成實名制的備案工作。此舉無疑有造成寄件人個人信息泄漏的風險。有的快遞公司在實際操作中將收集到的個人數(shù)據(jù)全部上傳至公安部的數(shù)據(jù)庫中進行核對,本地并不保存數(shù)據(jù)。然而公安部的數(shù)據(jù)庫也并非絕對安全。
三、我國快遞實名制與隱私權保護的建議
在我國,隱私權也從民法上的保護走向憲法上的保護,成為憲法上未列舉的基本權利之一。因此,在快遞實名制的實施過程中,我們應當注重對于隱私權的保護。因此,給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加強信息系統(tǒng)安全升級。用戶信息采集從開始,到傳送、處理、保護、消除,都進行一系列封閉的管理,實施動態(tài)的監(jiān)控。第二,不斷加強信息技術的完善。例如現(xiàn)在有些地方部分快遞寄件開始出現(xiàn)隱秘的面單。第三,政府部門加強監(jiān)管。如果發(fā)現(xiàn)個人信息泄露,政府部門會同公安,要堅決打擊,切實保障公眾信息的安全。
四、結語
針對快遞實名制,我們應當予以上升至法律層面,加強法律層面的立法。同時在該制度實施的過程中注重對隱私權的保護,遵循比例原則,盡可能地減少收集個人信息。秩序與自由這兩個基本價值并非非此即彼的關系,它們可以達成一個平衡,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去探索這一個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