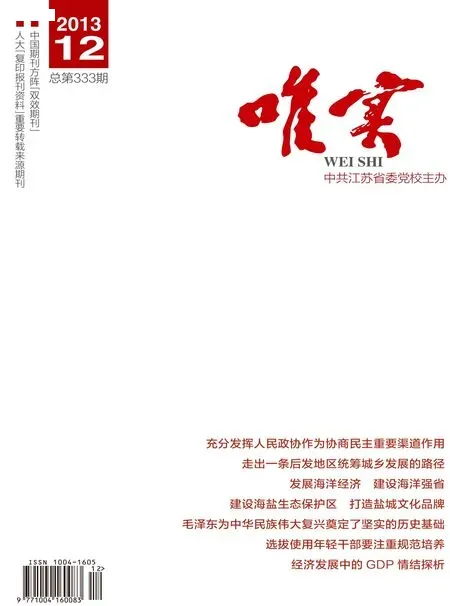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四大轉換
王健 彭安玉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全新探索。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強調要結合國土空間規劃,堅持保護第一、傳承優先,對各類文物本體及環境實施嚴格保護和管控,合理保存傳統文化生態,適度發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態產業。方案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長城國家文化公園、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并列為三大國家文化公園。江蘇已經在2018年率先啟動了《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江蘇段)建設規劃》,探索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規劃建設實踐樣板和典型經驗。如何做好規劃,落實項目,順利啟動,是當務之急。我們認為,建設好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要努力實現四大轉換,即從地理空間到文化空間的轉換,從自然生態到人文精神的轉換,從線型遺產到園帶展示的轉換,從生產生活到文化旅游的轉換。
一、從地理空間到文化空間的轉換
實現從地理空間到文化空間的轉換,要廓清和落實大運河的“地理空間”。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其孕育與發展都離不開河流。尼羅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倫文明,印度河、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黃河、長江則孕育了中華文明。一部人類文明史清楚地告訴我們,經濟發展、城鎮建設、社會進步都與河流密切相關,許多城鎮、經濟區因河而興,沿河布局。一些城鎮雖難以瀕臨自然的河流,也要設法開鑿人工運河以解決運輸、水源、生態安全等諸多問題。與一般的公路、鐵路不同,河流有發達的水系,這使得它的腹地寬大,因而產生了“流域”這一地理概念。流域的開發具有面積大,綜合性廣、帶動性強、效用持久等特點,在當代一直受到重視。隨著后工業化時代的來臨,沿河的景觀、生態、旅游等也日益彰顯,并且成為沿河城鎮復興的重要資源依托。運河是一種特殊的水系形態,它是人工有目的、有規劃建設起來的,與水利、水運、區域發展、城鎮建設的關系更加密切。沿運河一線的城鎮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繁華的昨天,堪稱人文淵藪,而大運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進一步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首先要廓清和落實大運河的“地理空間”,當務之急有四:一是對文獻上的大運河“地理空間”的存疑部分繼續研究和確認;二是將文獻上已經確認的“地理空間”落實到實地的“地理空間”;三是對大運河的“地理空間”進行歷史和現實的功能(如運輸、防洪等)劃分;四是研究天下大勢,判斷發展趨勢,弄清交通結構和空間分布,準確定位現實大運河的使命。
實現從地理空間到文化空間的轉換,要進一步研究大運河的“文化空間”。大運河的“文化空間”與“地理空間”既有密切的關系,也有明顯的區別。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要深入研究大運河的“文化空間”。文化是大運河的靈魂,也是大運河文化公園的靈魂。在江蘇境內,大運河由北而南流經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八個城市,縱貫700公里,“應運而生,應運而盛”,是運河沿線城市共同的歷史傳奇。大運河江蘇段有7個遺產區、28個遺產點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沿河堤、閘、橋、廟、河段、碼頭,碑刻、古鎮、名人遺跡、故事傳說、風情習俗不勝枚舉。如揚州的邵伯鎮是運河邊上的重要古鎮,乾隆御賜的“大碼頭”遺跡猶存,四角樓的天空深邃莫測,東晉名臣謝安筑埭治水的故事在民間傳唱上千年,斗野亭吟詩唱和的北宋七子依舊是老百姓茶余飯后的美談。又如淮安有“南船北馬”“運河之都”的盛譽,“天下九督,淮署其二”,曾經的“九省通衢”,留下了無數的運河文化遺產,著名的有淮安府署、河下歷史街區、清江大閘、漕運總督府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更超過600項,其中國家級4項、省級22項、市級133項,區縣級400多項,還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1名,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11名,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142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2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種類繁多,有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曲、曲藝、傳統體育與游藝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等。加強對大運河“文化空間”的研究,任務繁重,亟待展開。具體而言,要加速研究、挖掘大運河的物質文化;要加速研究、挖掘大運河的非物質文化;要加速研究、挖掘大運河的制度文化。要從大運河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全息”中提煉大運河文化精神,闡述大運河文化地理。
實現從地理空間到文化空間的轉換,要突出打好文化牌,在保護歷史遺存的基礎上,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將運河沿線文化亮點連起來,實現“一條河盡顯文化之美”,推動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從“地理空間”走向“文化空間”,要利用“文化空間”研究的成果對“地理空間”進行文化詮釋;要利用文化化了的“地理空間”對人們進行文化熏陶;要以“地理空間”建設成果為平臺,以“文化空間”研究成果為基礎,精心講好大運河故事;要把經過深入研究和轉化創新的既留得住“鄉愁”記憶,又能讓人著迷的運河故事搬上銀幕,推向社會,走向世界。
二、從自然生態到人文精神的轉換
自然生態是指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與存在的狀態,人類社會把自然生態納入人類可以改造的范圍之內,這就形成了文明。
大運河是一個由河流、湖泊及其相應的水生物和植物組成的自然生態系統,堪稱“天人合一”的杰作。在江蘇境內,大運河沿線植被良好,河湖密布,是我國東部地區重要的輸水通道、生態廊道和黃金航道,生態優勢極其明顯。第一,大運河南水北調工程東線從揚州江都抽引長江水,逐級提水北送,沿途有邵伯湖、高郵湖、洪澤湖、駱馬湖、南四湖、東平湖等調蓄湖泊。第二,大運河沿線是世界八大候鳥遷徙路徑之一,每年經此停歇、繁殖和越冬的各種水鳥有150多種,數量有百萬只。第三,大運河沿線是全國湖泊串珠般分布的密集區之一,由北而南有微山湖、駱馬湖、洪澤湖、白馬湖、寶應湖、高郵湖、邵伯湖、滆湖、太湖、陽澄湖、淀山湖等,其中太湖、高郵湖、洪澤湖、微山湖均居中國十大淡水湖之列。第四,大運河是江蘇“1+3”重點功能區戰略中江淮生態經濟區的縱軸。江淮生態經濟區涉及的蘇中、蘇北5市(揚州、泰州、淮安、鹽城、宿遷)、11個縣級市(高郵、興化、寶應、漣水、盱眙、金湖、建湖、阜寧、沭陽、泗陽、泗洪),將依托大運河自然生態長廊建設,以生態為底色,做足生態文章,彰顯生態優勢。
然而,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僅僅保護好現有的自然生態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要努力提升其精神價值,實現從自然生態到人文精神的轉換。
在大運河流淌的2500年中,客觀上形成了大運河的精神價值。2017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在《打造展示中華文明的金名片——關于建設大運河文化帶的若干思考》中,建議從國家戰略高度審視大運河的功能,以大運河為核心,打造大運河文化帶,使之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金名片,彰顯文化自信的地標性工程,中華文脈的重要標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志性文化品牌。將大運河打造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具代表性的標志性文化品牌,亟待深入挖掘其豐富的人文內涵、文化功能,進而凝練大運河精神。
在人類文明史上,大運河與長城并列為中華文明瑰寶中的雙子星,代表著中華文明的水平。從物質文明上說,大運河沿線無與倫比的巨大工程令人震撼。如在洪澤湖的東側,巍然屹立的高家堰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高家堰位于江蘇省淮安市境內,北起張福口,南至蔣壩,總長67.25公里,其中從蔣壩至高良澗的26公里近湖頂浪最為險要,此段有25.1公里長的石工墻。作為名副其實的“水上長城”,高家堰在歷史上曾經關乎黃淮治理,關乎明清王朝的生命線漕運是否暢通,關乎淮河中下游淮揚七府數千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之安危,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對其戰略地位,康基田于《河渠紀聞》卷十九記載:“高堰為淮揚門戶,束淮敵黃,刷沙歸海,衛高寶興鹽七州邑之廬舍田疇,黃運之關鍵也。”高家堰臨湖全為條石工程,武同舉于《江蘇水利全書·淮一》記載:“每石長一丈,高、寬俱一尺二寸,累石平堤,因地勢之高低,十層至二十三四層不等,堤上有子堰,高四、五、六尺不等。”條石之間以糯米汁拌石灰作為黏結劑,迎湖巨石還有鑄鐵錠緊扣,堤基則用密集的木樁加固。此外,大運河沿線豐富多彩的物質遺產、水工技術、航運技術、至今仍然發揮航運、供水、灌溉、調水、生態、旅游等作用的“活”的航道,無不放射其物質文明的光芒。從精神文明上說,大運河的人文精神,主要指其在國家和民族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獨特的精神品格、人文氣質和文脈地位。這種精神對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人們身分的認同、國家統一局面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國際交往、國際話語的傳播也產生一定影響,并直接影響著大運河在國內外的知名度、美譽度和神圣度。在大運河研究過程中,實現從自然生態到人文精神的轉換,迫切需要進一步深化大運河人文精神的研究,對大運河人文精神的豐富內涵及其影響作出更深刻的概括。
三、從線型遺產到園帶展示的轉換
從自然狀態上看,大運河無疑呈線型狀,大運河遺產也自然呈現出線型分布的狀態,大運河猶如一根紅線將沿途的物質文化遺產、精神文化遺產串連成一個帶狀,也就是所謂的線型遺產。
在江蘇境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布幾乎以大運河為縱軸,呈典型的線型分布態勢。以民間文學為例,民間有蘇州的寒山寺鐘聲傳說、和合二仙傳說、拾得傳說,宜興的梁祝傳說,鎮江的白蛇傳傳說、華山畿傳說,揚州的隋煬帝傳說、露筋娘娘傳說,淮安的巫支祁傳說,宿遷的水漫泗州傳說;說唱文學有吳歌、寶卷等,吳歌如吳江蘆墟山歌、蘇州勝浦山歌、張家港河陽山歌、常熟白茆山歌,寶卷如同里宣卷、河陽寶卷、錦溪宣卷、勝浦宣卷、靖江寶卷等;謎語有常熟的海虞謎語、揚州運河兩岸的竹西謎語。在傳統音樂中,民歌有儀征胥浦農歌,揚州高郵民歌,淮安金湖秧歌、南閘民歌等;勞動號子有鎮江丹徒的南鄉田歌,揚州江都的邵伯號子、泰州興化的茅山號子;古琴藝術有虞山琴派、廣陵琴派、梅庵琴派;江南絲竹則廣泛分布在蘇州古城區和常熟、張家港、太倉、昆山、吳江、吳中、相城等地;十番音樂有蘇州辛莊十番音樂、揚州邵伯鑼鼓小牌子、淮安楚州十番鑼鼓;鼓吹樂有徐州鼓吹樂;鑼鼓樂有宿遷泗洪天崗鑼鼓;道教音樂有蘇州玄妙觀道教音樂、無錫道教音樂、茅山道教音樂、句容乾元觀道教音樂。此外,江蘇大運河沿線的傳統舞蹈、傳統戲曲、曲藝、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傳統體育、傳統游藝、傳統雜技、傳統民俗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有密集分布,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如何將這些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在空間上展示,這是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大問題。通過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打造文化展示區、串聯文化線路,充分展示大運河文化的民族性、多樣性、豐富性,圍繞文化內涵系統構建主題明確、內涵清晰、脈絡完整、功能完善的文化展示空間體系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具有文化教育、公共服務、旅游休閑、科學研究等功能,是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先進的治水智慧、國家的治理制度、一體的城河共生、堅強的革命精神、多元文化交融的活態文化地標,是面向人民群眾的文化休閑場所、文化教育場所、文化交流場所和文化消費場所。國家文化公園應該重點打造核心展示園、集中展示帶和特色展示點。
文化展示區旨在彰顯地域文化特色。江蘇南北地域文化有顯著差異,如蘇北的楚漢文化、蘇中的淮揚文化、蘇南的吳文化。
文化線路串聯國家文化公園和文化展示區,依據文化內涵確定主題,如國家漕運、鹽運治理文化線路,江淮運河大堤、高家堰、清江大閘治水文化線路,杭州、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宿遷、徐州、濟寧、聊城、臨清、天津、北京城河共生文化線路,沙家浜、茅山、溧水、泰州、盱眙、徐州、棗莊、濟南、北京紅色革命文化線路等,也可以根據交通方式確定相應的線路,如水上線路、陸上線路。
四、從生產生活到文化旅游的轉換
大運河是聞名于世的文化遺產,在中國歷史上對于加強南北政治聯系、推進南北經濟交流、促進南北文化交融、鞏固多民族國家統一,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從本質上講,大運河是古代勞動人民順應自然、改造自然的產物,承擔著調水、飲用、灌溉、交通、生態、養殖、捕撈、娛樂、鍛煉、運動等廣泛的生產生活功能。從地圖上可以看到,江蘇主要城市大多分布在運河沿線,從南到北有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宿遷、徐州八市,即使不在運河沿線的城市,也大多與歷史上的漕運線路或鹽運線路有或多或少、直接間接的聯系。如泰州、南通是漢代所開邗溝支線古運鹽河(今老通揚運河)的東端城市,南京則是上江漕糧由長江通往運河的必經之地。很顯然,大運河與江蘇城市的出現、發展、興盛有著內在的關系,而城市又是百姓生產生活的重要載體。在歷史上,江蘇是漕運、鹽運的轉運樞紐及治河中心,留下了大量與百姓日用緊密相連的文化遺產,如蘇州園林、楓橋、文廟,無錫東林書院、惠山寺廟園林、常州戲樓群、鎮江焦山碑林、西津渡遺址、商會舊址、賽珍珠舊居、揚州汪氏鹽商住宅、白塔、何園、菱塘清真寺、邵伯運河碼頭、鐵牛、高郵城墻、奎樓、泰州雕花樓、淮安總督漕運公署遺址、漂母墓、周恩來故居、宿遷龍王廟行宮、孔廟大成殿、徐州漢墓、漢代采石廠遺址,等等。
大運河沿線與人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這些物質文化遺產以及傳說、故事、說唱、謎語、民歌、號子、舞蹈、音樂、信仰、戲曲、美術、民俗等數量相當可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先人留下的極其寶貴的財富,值得后人倍加珍惜,切實保護。合理利用大運河文化遺產,大力發展大運河文化旅游,不僅能喚起人們對大運河文化遺產的珍愛之心,更能喚起對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之責。
大力發展大運河文化旅游,一要充分挖掘代表性的大運河文化價值。簡而言之,要深度挖掘各類大運河文化遺產和文化資源所承載、蘊含的文化價值,形成可以觀看、閱讀、體驗、感悟的文化場景,賦予各類大運河文化資源以文化精神,為具有中華文化標識性的文化價值和文化精神找到賴以依托的載體。二要合理設置大運河文化旅游線路。文化線路要串聯國家文化公園、文化展示區、特色展覽點,依據文化內涵設定展示主題,推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國家公園文化旅游線路的設置要有自身的特色,如生態與文化結合,在江蘇則要貫通吳文化、淮揚文化和楚漢文化。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是大運河文化帶的重點工程,要具體落實到項目上,以“園帶點”的形式展示出來,以文化線路來表達。具體到旅游線路的設置上,應考慮設置航運線路、水工科技線路、城市線路、古鎮線路、非物質文化遺產線路,也可以以人物為紅線串起人物線路,甚至人物線路也可再細化,如明清著名小說作者吳承恩、施耐庵、羅貫中線路,周恩來、“常州三杰”紅色人物線路,等等。三要建立健全標識導覽系統。統籌開展“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標識系統設計,突出標識的系統建設。四要構建快捷高效的交通網絡。暢通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與周邊機場、車站、碼頭等主要交通樞紐的快捷聯系,優化道路線形,減少交通堵塞,美化道路沿線景觀,設置文化標識,完善交通服務設施。五要建設智慧文化公園。通過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數字平臺,實現與實體國家文化公園的協同展示,以提升國家文化公園的智慧化服務水平。
(本文系“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研究”課題成果之一)
(王健: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副院長,江蘇省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彭安玉: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
責任編輯:張蔚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