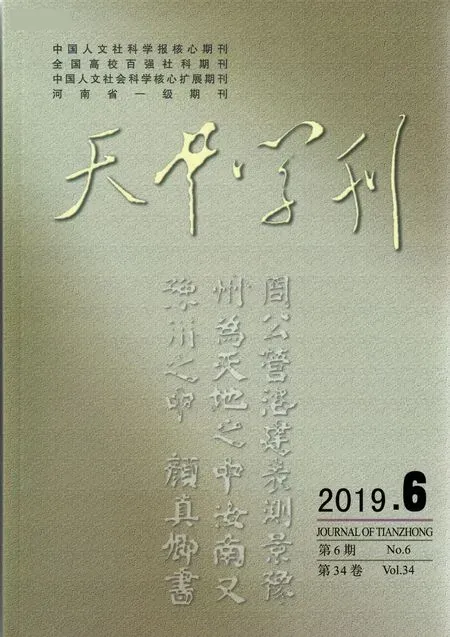山高水長 風光無限
——四十年問學之路漫述
高 建 新
(內蒙古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010010)
改變我們這一代人命運的是1977年國家恢復了已經中斷10年的高考。1977年10月21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中國各大新聞媒體,以《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為題,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將于一個月之后在全國范圍內舉行,“今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到第四季度進行,新生將于明年二月底以前入學”,同時配發社論《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
在我國,現階段還不能普及高等教育,高等學校招生只能選拔少數青年上大學。被錄取的青年,要決心為革命學好專業知識;未被錄取的青年,在實踐中同樣可以學政治、學文化,攀登科學技術高峰。因此,要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不論是上大學,還是下農村、進工廠,都應該鉆研業務,精益求精,向四個現代化進軍。[1]
消息傳來之時,我正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朱日和公社(后來這一帶成了赫赫有名的解放軍北部戰區的戰術訓練基地)紅格爾大隊插隊,那年草原上9月初就下了一場大雪,北風呼嘯,望處皆白,如岑參所謂的“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因為氣溫急速下降,遍地是凍死的牛羊。根據指示,知青必須留在當地與牧民一起抗災。災情緩解之后,已經臨近高考,于是知青們匆匆忙忙參加了當年12月中旬舉行的高考(內蒙古具體考試時間是13日、14日、15日三天),我們大隊29 個知青,包括我一共考上2 個人。后來才知道,1977年全國有570 多萬考生,最后錄取了27.3 萬人,錄取率是4.7%。到了40年后的2017年,全國考生940 萬,錄取了700 萬,錄取率是74.46%。這樣,1978年3月初我進入集寧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現集寧師范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1980年4月畢業,成了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專科畢業生。
兩年的專科學習,極大地激發了我的讀書興趣,可以用求知若渴、廢寢忘食來形容。之后我開始不斷尋找讀書學習的機會,1984年8月至1985年7月在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1987年9月至1988年7月在遼寧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助教進修班”學習。這兩次進修令我擴大了學術視野,近距離接觸了國內的學術名家、大家,如王力、吳組緗、林庚、王瑤、唐弢、周振甫、鄧廣銘、葉朗、朱德熙、蔣紹愚、何九盈、吳小如、袁行霈、張震澤、謝冕、葛曉音、錢理群諸先生。與這些學者的結識使我懂得了做學問如做人一樣,既要有氣象也要腳踏實地、持之以恒。
漫長的問學之路開始之后,我慢慢有了一點學術成果問世,1994年5月破格晉升副教授,1995年7月由集寧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調入內蒙古大學中文系,2003年7月晉升教授。本人現任內蒙古大學人文科學學部委員、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陶淵明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文學地理學會常務理事、王維學會理事、柳宗元學會理事、《光明日報》“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專家委員會委員、《內蒙古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一直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山水田園文學、陶淵明、“絲綢之路”與唐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先后在中華書局等出版社出版學術專著7部,在《文學遺產》《文史知識》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50 余篇,另在《光明日報》《文匯報》《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散文、美學隨筆200余篇。近40年的問學歷程曲折坎坷,一言難盡,雖然說不上典型,但也有一些個人體會,愿與青年學人分享。
一
做學問要有強烈的精神需求,有為學術獻身的充分準備,矢志不渝,堅持到底。治學的目的是通過學術研究豐富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內涵,告慰有限的人生,為傳承中華文化血脈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對于讀書治學,我個人并不同意錢鐘書《談藝錄序》中所謂“托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的觀點。一則,做學問不是被動、無奈的消遣;再則,學問中體現的是生命的倔強與人性的高貴,要以莊嚴的態度對待。從1988年夏天開始,到2008年3月15日凌晨,費時20年的《詩心妙悟自然——中國山水文學研究》一書終于完稿,我在后記中這樣寫道:
這是一個多雪的冬天,夜夜有風從窗戶縫隙暗暗透入,但窗戶上的冰花冷峻而美麗,幻化成令人遐思的各種圖案。除了偶爾和朋友們飲酒、聚會之外,我一直在修改著這本見證我青春時光悄然流逝的小書。對于一生躁動不安的我而言,只有讀書、寫作抑或人在旅途,心靈才是安寧的。我期望自己能夠體味南宋學者李侗(1093―1163)所推重的“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朱熹《延平答問》)的學問與人生境界,何況中國山水文學從萌芽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對“天理”的探尋。
我一向認為,我們對大自然的感悟,實則也是對生命的感悟;有靈性、有深情者,對大自然、對生命方有感悟。我們須用文字記錄我們曾經有過的生命遭遇,包括與永恒大自然的遭遇,否則我們就不能堅實地證明自己和自己有過關系的人的存在,包括我們眼中的、心中的風景。我相信,那些視山水為生命的前賢如酈道元、柳宗元、徐霞客,是懷著如我一樣的情感看山看水、寫山寫水的,這從中國山水文學的發展歷程、從豐富的山水文學詩文創作中也可以獲得明證。無論喜悅還是悲慨,歷經二十年,我終于為自己的這部小書劃上了句號,但對山水文學與山水風景的關注卻不會由此終結,因為即使孤獨,倔強的生命仍在繼續!眼中的風景希望它不要消失,心中的風景必須培育滋養。[2]
我想,學術就是我們“心中的風景”。此書出版之后,獲得了師友們的鼓勵。崔麗《〈詩心妙悟自然——中國山水文學研究〉面世》一文認為:“本書結構完整,行文靈活,只就深有感觸之點入手開掘,征引和分析融合無跡,往往獨有感發,達到一片新天地……本書是作者歷經二十年的心血凝結而成,由喜歡山水到探究山水,由登山臨水到研讀典籍,現實的風景和書中的風景給作者寂寞心靈帶來了莫大的安慰,賦予人生以豐富的意義。文字記錄了作者生命中與永恒自然的遭遇,現實體驗與古今中外的文獻征引相互映發,使本書材料豐贍、意蘊豐厚。”[3]武彬《〈詩心妙悟自然:中國山水文學研究〉評介》一文認為: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作者深入分析,對中國山水文學的評價實事求是而公允,重新深入發掘了中國山水文學的價值,理論探討牢固建立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全書采取了時間先后順序,逐一解決山水文學研究中所必須面對的重大理論問題,最終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山水文學發生、發展的線索。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自身積累的豐厚,加之感悟、思考極其深刻,往往新見迭出,發前人所未發。對于山水文學發展史中的重大理論問題的闡釋,同樣是建立在深入梳理各種史料基礎之上,這是作者的一個著力點。作者對于以往未引起注意卻在山水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理論問題進行了重新審視,詳加辨析、周密論述,從而得出了科學的結論[4]。
學術事業是艱苦的事業,但也是充滿發現、理解和歡樂的事業。它幫助我們理解生存的世界,確立對生活的態度,并學會體驗各種各樣的感情,認識各式各樣的人。緣于此,我們對學術事業始終懷有非同尋常的敬畏和感激。我始終認為,人短暫的一生,能全心全意、認認真真做成一件事情,就是成功的;左顧右盼、首鼠兩端、搖擺不定是做不成事情的,學問之路尤其是這樣。
二
最好的研究是學術目標與人生目標結合,學術興趣與個人愛好統一,這樣的研究是快樂的研究,是你自己愿意全身心投入的研究。確立選題的同時,也確立了你在一個時期內的科研領域和科研方向,這是一個艱難、痛苦的過程。你必須分析你的才性,選擇適合你的研究課題。研究題目一旦選定,就全力以赴,絕不半途而廢。基于此,對于來自學問之外的聒噪,我從不在意。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自己一直喜歡陶淵明,敬重陶淵明,從未有過絲毫改變,因為陶淵明自然真樸的性情與我契合,心有靈犀,值得投入地研究。后來,我有了《自然之子:陶淵明》《〈陶詩匯評〉箋釋》兩本書的出版,我在《自然之子:陶淵明》一書的前言中寫道:
喜歡陶淵明已經有好些年了。最初是吟誦“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羨慕那種清貧中的從容和悠然;到后來是給研究生開設“陶淵明研究”課程,閱讀陶集,搜集資料,知道了陶淵明為堅守自我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知道了陶淵明也曾有過無邊的寂寞和孤獨;再到后來下決心把自己閱讀陶淵明的感受、心得寫出來,竟然有一種過去不曾有過的莊嚴感、使命感。這一過程,前后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其間,蒼狗白云,人事沉浮,自己也經歷了許多事情,也為生存、為擺脫精神深處的寂寞苦苦掙扎過。回頭再看,這才知道自己年輕時對陶淵明的認識是何等淺陋,始知閱讀陶淵明不僅需要知識,更需要眼力、閱歷和始終不渝的價值追求。為了進一步了解心目中這位偉大的詩人,我于2001年11月專程前往今江西九江縣沙河鎮的陶淵明故鄉。打點好行裝之后,心中既激動又有些許不安,就像探望一位久已心儀的藹藹長者一樣。乘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終于到達了沙河鎮。在清寂中,我拜謁了陶淵明墓、陶靖節祠、“陶淵明紀念館”及陶淵明與蓮宗祖師慧遠大師發生聯系的東林寺;之后又登上陶淵明每日對望的廬山。在這片風景美麗的地方,看山聽水,真切地感受陶淵明、追懷陶淵明。感謝生活,感謝境遇艱難帶來的心靈動蕩,這使我從感情上更容易貼近陶淵明、理解陶淵明,即使是面對逝去千年的哲人,心和心的相通原來可以這般幸福溫暖。[5]
《自然之子:陶淵明》一書出版后,我對陶淵明的關注沒有絲毫減弱,依舊有陶淵明研究論文的發表:《陶淵明的現代意義芻議》(《內蒙古大學學報》2008年第2 期)、《“返回到本源近旁”——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解讀》(《名作欣賞》2008年第4 期,后收入《魏晉南北朝文學名作欣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海德格爾與陶淵明》(《九江學院學報》2010年第4 期)、《“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陶淵明〈自祭文〉解析》(《名作欣賞》2011年第8期)、《溫汝能及其〈陶詩匯評〉》(《九江學院學報》2011年第3 期)、《陶淵明彭澤辭官及其文化史意義——以“歸去來兮”為研究對象》(《天中學刊》2013年第2 期)、《廬山風光與陶詩景物描寫》(《栗里論陶——中國星子縣陶淵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陶淵明創作的思想史意義》(《銅仁學院學報》2014年第1 期)、《多元共融 歸于自然——陶淵明與儒道玄之關系》(《名作欣賞》2014年第7 期)、《“由篤實達空靈,其篤實亦空靈”——王叔岷的陶淵明研究》(《銅仁學院學報》2016年第2 期)、《一心塑造自我心目中的陶淵明形象——評清人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銅仁學院學報》2018年第1 期)、《一主二客論死生——陶淵明〈形影神并序〉意涵再探析》(《內蒙古大學學報》2019年第5 期)等。學術研究征途漫漫,永遠沒有止境,而且是開放的,常研究常新。因為興趣,我也寫過《酒入詩腸句不寒:古代文人生活與酒》(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初版,2016年修訂再版)一書,探討酒文化與中國文學、中國文人之間的密切關系,愛酒的朋友時常和我索要此書。
在我看來,學術研究包括選題可以和自己的教學實踐(所開課程,特別是選修課)緊密結合起來,好處是教學相長,事半功倍,一舉兩得。《自然之子:陶淵明》最初就是為研究生開的選修課,我自己是在講授了五年“陶淵明研究”之后,開始整理教案成書的。《詩心妙悟自然——中國山水文學研究》一書的初稿,一部分來自為研究生開選修課的教案。還有《中國古典詩詞精華類編· 山水田園卷》(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曾是本科生選修課“山水文學研究”的教材。
三
通過各種途徑廣泛搜集研究資料,書面文獻之外的實地考察,意義重大,不可輕視。一個選題的獲得和有沒有研究價值,來源于你對這個學科全面、深刻的了解及投入的程度、思考的深度。只有充分占有資料,你自己才會做出判斷,知道這個課題有沒有研究價值。司馬遷當年寫作《史記》,其材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先秦及當代(西漢)人的著作,包括歷史散文、諸子散文及各國史書;二是歷代及當代的政府檔案;三是實地調查獲得的活材料。司馬遷從20 歲開始登山涉水,憑吊古跡,走遍大江南北,實地感受《史記》中人物的生活場景及所在之地的風土人情,所以他筆下的人物才如此生動鮮活。
我一直在全力踐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古訓,注重山水自然對人心的感發,注重各地博物館的出土文物與書面文獻的相互印證,40年來走遍包括西藏、臺灣在內的中國所有省區,我在《路上的風景與書中的風景——我的山水文學研究》(《名作欣賞》2012年第10 期)、《“行萬里路”的文化意蘊》(《中華讀書報》2015年12月16日)等文章中曾有專門闡述。在英國作家阿蘭· 德波頓看來,旅行是一種標識,旅行代表著高貴靈魂對未知世界的不倦探求,旅行幫助人們理解希臘人所謂的“由理性支配的積極生活所帶來的幸福”[6]。旅行是一種心懷解放感的漂泊,旅行不僅喚起了我對山水風景充滿深情的關注,也成就了我的兩本山水文學著作、百余篇山水游記與三百余首舊體詩。蘇軾說的“游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送鄭戶曹》)、陸游說的“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予使江西以詩投政府……》),都是我曾體驗過的。
我個人是因喜好旅行進而研究山水文學的,凡到一處,注意探尋風景勝地與古代詩人創作的關系,如到訪柳宗元被貶十年的湖南永州,考察了當地的自然環境后,一是發現柳宗元短短一生創作的600 余篇詩文,在永州就有331 篇,占其全部創作的50%以上,明白了韓愈《柳子厚墓志銘》說他這一時期的生活“閑居,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的特殊意義,山水風景抑或就是被貶中的柳宗元的生命;二是了解了永州地處長江中游平原以南,是低山、丘陵和盆地交錯的地形,喀斯特地貌復雜,海拔多在300 米以下,相對高度一般為100~200米,灌木叢生,氣候濕熱,對于永州的自然環境,柳宗元甚至在《永州韋使君新堂記》中有過這樣的評價:“永州實為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貍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7]就是這些平常甚至有時讓他有些厭惡的山水,柳宗元卻“揚其異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獨,造其奧以泄其秘,披其根以證其理,深入顯出以盡其神”[8]2345,把它們寫得姿態橫生、美不勝收,造景、造境的因素十分明顯,目的就是要以此來映襯朝政的惡濁,顯示自己高潔的人格和不甘沉淪的靈魂。為了山水文學研究,我還先后探訪了王維筆下陜西藍田縣的輞川,謝朓、李白詩中安徽宣城的敬亭山,還有眾多唐人描寫過的天臺山與國清寺,李白的故里四川江油青蓮鄉,等等。2016年1月,我專程去了徐霞客的故鄉江蘇江陰市的徐霞客故居,寫下了《詠徐霞客四首》,表達我對先賢的景仰之情:
其一
蒙蒙煙雨卷蓑行,竹杖芒鞋似苦僧。
野寺荒村常臥守,獨聞月下老猿鳴。
其二
跋山涉水喜長征,踽踽觀游自有情。
瑤界冰壺濯雪魄,翠微深處賞紅楓。
其三
由來渴慕遠方游,探勝搜奇樂不休。
秋對大荒冬對雪,春歸細雨洗鄉愁。
其四
朝發碧海暮蒼梧,回看人寰水里浮。
藻繪華章誰記取,襟懷天下我身孤。
多年來我一直受惠于旅行,遍看了全國所有的省級博物館,包括臺灣故宮博物院。一些博物館如北京國家博物館、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洛陽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浙江博物館,我去過多次。僅2018年,我就去了新疆、西藏、青海、甘肅、云南、四川、江西、浙江、廣東、遼寧等省,行程達6 萬余公里,時間長達4 個月。在全國各大博物館看了大量文物,拍攝到大量照片,對我的研究大有裨益。《酒入詩腸句不寒:古代文人生活與酒》(增訂本)一書中的200 余幅照片,都是我自己拍攝的。近年來主持完成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北方游牧文化與唐詩關系研究”,大量的材料來自出土文物,如絲綢、汗血馬、舞馬、絲路駱駝、昆侖兒、西域胡商、胡姬、胡僧以及胡騰舞、胡旋舞等,可以印證唐代詩文中的相關記載,至少實現了王國維先生主張的二重證據,如《李白筆下的胡姬》(《光明日報》2017年2月6日第13 版“文學遺產”專刊)、《舞馬:馬中的舞蹈家》(《文史知識》2018年第4 期)、《駱駝——古絲綢之路的不朽象征》(《學習時報》2018年5月7日)、《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酷愛駿馬的唐人》(《光明日報》2018年7月23日13 版“文學遺產”專刊)、《唐代的“昆侖兒”》(《學習時報》2019年3月27日),《大唐琵琶上的絲路駱駝解讀》(《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4 期),均得益于參觀博物館所見文物。
四
學術研究要有長遠規劃,切忌零敲碎打、形不成合力,學術論文的寫作最好是從一開始就能納入自己系統的學術研究中,既有點又有面,既見樹又見林。人生需要有規劃,學術研究也需要有規劃,何況學術規劃是人生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的《山水風景審美》(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年增訂版)一書,起初都是單篇的論文與山水美學隨筆,大多數內容成書前就在各地報刊上發表過,如《芭蕉得雨便欣然》(《草原》1991年第2 期)、《綠影扶疏意味長——談葉子的觀賞》(《園林》1992年第3 期)、《柳宗元鐘情山水間》(《文匯報》1993年9月27日)、《袁中道壯游天下》(《文匯報》1993年12月19日)、《有云更覺千山秀》(《北京旅游報》1993年5月30日)、《登高壯觀天地間》(《北京旅游報》1993年8月30日)、《開窗放入大江來》(《北京旅游報》1993年11月30日)、《一字新聲一顆珠——淺談園林的命名》(《園林》1993年第6 期)、《小議中國的民間節日》(《中旅之窗》1993年第9 期)、《“貂嬋陵園”的斷想》(《文匯報》1994年11月6日)、《江山也要偉人扶》(《中國地名》1994年第2 期)、《數聲鳥啼百花風——略說“花信風”》(《中旅之窗》1994年第2 期)、《觀山觀水皆得妙》(《旅游縱橫》1994年第3 期)、《宜于松者莫如風》(《森林與人類》1994年第5 期)、《謝靈運:中國風景區的開創者》(《綠化與生活》1997年第1 期)、《曲中紅豆最相思》(《旅游導報》1999年7月29日)、《細說青城“幽”》(《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5月12日)。這樣做的好處還在于通過論文的不斷發表,檢驗自己的科研能力,增加自信,同時校正自己的科研方向,體會創造的樂趣。
《山水風景審美》是我花氣力最多的一本書,寫作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沒有電腦(2001年我才貸款買了第一臺電腦),更談不上電子檢索,書中的材料都是自己一條一條讀出來的,而后進行歸納整理,一疊一疊的卡片是用掛歷紙裁成的。因為花了苦功夫、真功夫,所以書出版以后受到了同行的好評,石亞川《〈山水風景審美〉美學研究的新收獲》一文說:“本書既是作者對山水風景的審美‘發現’,同時也是山水風景的審美‘顯現’。作者多年從事高校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尤其偏愛中國古代山水詩、文、畫構成的宏博的山水風景畫卷。作者在這漫漫長廊中探幽訪勝無疑是一種艱苦的跋涉,但在作者看來,卻充滿了‘妙趣’。他以一顆敏感的審美之心,去輕輕碰響古人山水風景審美之弦,于是心之共鳴一次次奏響了。加上作者的理論素養,就形成了個人獨有的文化‘積淀’,但僅有這些還不夠,還有重要的要素,那就是生氣貫注、活潑躍動的生命體驗。其實學術研究冥冥之中有一個選擇研究方向的主宰——人的原初生命本真。這幾乎是任何人都無法違逆的生命本真。高建新對自然山水頑強的審美實踐就是明證。他視自然為生命的‘家’,每置自于自然,就覺得是回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家’。他以‘家’為樂,以尋訪名山大川,登臨覽勝為人生首要快事,以山水風景審美之‘得妙’為首要財富。東到滄海碣石,南及蘇杭瀟湘,都有他探尋的足跡。在西雙版納一游就去了近20 天。以生命本真、生命摯愛去接近大自然,即使一株小花,一片野云,一汪清水,也會使作者怦然心動,霎時沉醉于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作者這種對大自然審美必‘躬親’的實踐精神對我們尋訪美體驗美,豐富我們的生活是極好的啟示。”[9]趙娜《物色相招 人誰獲安——評高建新先生〈山水風景審美〉增訂本》一文說:“‘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文心雕龍· 物色》中這個看似平淡無奇的句子其實充滿靈性,在這里,‘物色’變成了一個明眸善睞、靈機通透的心靈主體,人倒成了自然的過客。過客總是腳步匆匆,然而在這個清水芙蓉、搖曳生姿的主體面前,人的內心早已起了或大或小的波瀾,既已起了波瀾,就再也挪不動腳步,以至于流連忘返了!中國貪戀山水的文人騷客,恐怕無不是以此為端的吧。先生的書,也是因‘物之感人,搖蕩性情’而起,歷二十幾年的旅游登臨,覽古今中外的山水詩文,融四十多個春秋的生命感悟,成丘壑于胸中,驅文字于筆端,如春雨瀟瀟,秋風颯颯,漸積為山水審美書墨一卷。”[10]此外還有劉則鳴《用靈心與自然對話——評高建新〈山水風景審美〉》(《零陵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4 期)、吳栓虎《山水風景新體驗》(《內蒙古日報·新聞周刊》1999年7月16日)、張宇《山水有靈——高建新先生〈山水風景審美〉(增訂本)讀后》(《呼和浩特晚報》2006年11月22日)、王國元《書話三則·〈山水風景審美〉》(《內蒙古日報》2011年2月18日第9 版)等相關評論。
五
持續關注一個領域,集中研究一個課題。經過至少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你在這個領域就有了話語權,就可能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錢鐘書在《詩可以怨》一文中說:“由于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嚴峻局限,我們為方便起見,只能把研究領域圈得愈來愈窄,把專門學科分得愈來愈細。此外沒有辦法。所以,成為某一門學問的專家,雖在主觀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觀上是不得已的事。”[11]“得意”也罷,“不得已”也罷,持續關注一個領域、集中研究一個課題,是讓學術向縱深方向發展的需要,是劉勰說的“博而能一”的“一”:“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文心雕龍·神思》)黃侃說:“‘博而能一’四字最要。不博,則苦其空疏;不一,則憂其凌雜。于此致意,庶思學不致偏廢,而罔殆之患可以免。”[12]“博而能一”始終是治學的門徑與法寶,“博”就是廣采博取、開闊視野、深厚基礎,“一”就是凝神專注,一以貫之,心無旁騖。
我的陶淵明研究歷時20年之后,才有為數不多的學術成果受到學術界的關注:(1)《關于陶詩“自然”“平淡”的美學評價》發表于《內蒙古大學學報》2002年第1 期,被《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2年第2 期摘要轉載。(2)《“以詩為文”始于陶淵明》發表于《內蒙古大學學報》2002年第4 期,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2年第11 期全文復印;尚永亮、劉磊在《中州學刊》2004年第5 期發表的《20世紀“以文為詩”研究述論》一文認為,在陶淵明研究史上,“以文為詩”始于陶淵明的觀點,是由高建新教授首先提出來的。龔斌、張影潔在《九江學院學報》2010年第4 期發表的《近十年陶淵明研究中幾個爭論問題略述》一文,將“以文為詩”始于陶淵明這一觀點列入近十年陶淵明研究中的幾個爭論問題之一,雖然“論斷還沒有得到研究者廣泛的響應,但不失為一個可以深入討論的問題。”(3)劉紹瑾、汪全剛在《湘潭大學學報》2006年第3 期發表的《陶淵明接受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學理反思》一文認為梳理和研究陶淵明接受用力最勤、成果最卓著的幾位學者是鐘優民、李劍鋒、劉中文和高建新等;“高建新探討了陶淵明在唐代、元明清及近代地位和影響的變遷史,將史的考察與歷史上的重要接受家王維、孟浩然、王國維、梁啟超等聯系起來”;“高建新從兩方面總結了陶淵明對中國古典詩歌美學做出的獨特貢獻:一是在詩歌審美視野上的開拓,二是‘開千古平淡之宗’。”(4)林方直在《前沿》2008年第2 期發表的《陶淵明研究的新進展——評高建新〈自然之子:陶淵明〉》一文認為《自然之子:陶淵明》“是著者多年來潛心于此領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全書系統、深入地探討了陶淵明的家世、生平、思想、創作、人格價值及其對后代的影響等重大理論問題,全面清理總結了前代有關陶淵明的研究成果,在充分搜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博采眾芳,廣鑒前賢,實事求是地評價陶淵明,重新發掘陶淵明的獨特價值,最終還陶淵明一個本來的面目”。(5)夏正亮在《九江學院學報》2010年第3 期發表的《近十年(1999―2009)陶淵明接受研究綜述》一文引述了筆者在《零陵學院學報》2003年第3 期發表的《陶淵明在元明清及近代的地位及影響》一文的主要觀點,即:元代是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廢止科舉考試七十余年,文人仕進無路,他們對自然美景的品賞,對藝術化生活的體味,對自己人格、精神追求的完全肯定,與陶淵明不謀而合。因此,元人文人大力推舉、稱頌陶詩。元人反對陶韋柳并稱,也反對陶謝并稱,正是因為元人發現了陶詩獨特的價值。我目前在研的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陶淵明文獻集成與研究”子課題“《陶淵明集》匯校匯注匯評”,也是得益于對陶淵明研究的持續關注與不斷有陶淵明研究論文的發表。近期,杜碧媛女士約我為《名作欣賞》“精神肖像”欄目撰寫關于陶淵明的文章。我結合這幾年的思考,寫成了《陶淵明:讓人景仰的偉大詩哲》一文,其中包含了我對陶淵明的最新思考。
我的山水文學研究也是如此,2018年7月應《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張清俐邀請,我談了對中國山水文學的看法:“先秦是中國山水文學的萌芽時期。‘人類與大自然在精神、情感等諸多方面的聯系在這個時期獲得了本質意義上的確立,由此建立的難以分割的聯系,不僅加深了人類對宇宙萬物的感知、認識,也映射出人類在追尋探索中所展示的真實心靈。’山水文學的誕生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志著中國文人山水審美意識覺醒,山水在生活中成為人們審美觀照的獨立對象。中國山水文學從魏晉時期走上獨立的發展階段,南朝謝靈運等文人的山水創作極具代表性,酈道元的《水經注》更是堪稱高峰。至于唐代,文學注重表現山水整體氣象、注重自然景物和生活感受的結合、注重創造詩境和多樣風格,柳宗元的系列游記將山水文學推向又一高峰。第三座高峰則是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13]近兩年,我仍有相關論文發表:《中國山水文學的歷史演進》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11月5日“文學”版、《江山若有靈,千載伸知己——中國山水文學的美學價值》發表于《光明日報》2019年3月11日13 版“文學遺產”專刊。
問學之路是一個不斷辨識自我、確證自我的過程,自證、他證,最后才能確證,要相信持續的努力終會獲得回報。我的最重要的三本著作——《自然之子:陶淵明》《詩心妙悟自然:中國山水文學研究》《中華生活經典·酒經》(中華書局2011年版),分別獲內蒙古自治區第二屆(2008年)、第三屆(2010年)、第四屆(2012年)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政府獎二等獎。《詩心妙悟自然:中國山水文學研究》同時獲內蒙古大學第五屆科學技術創新成果獎三等獎,雖然是三等,但2008年以來內蒙古大學再未頒發過此類獎項。我的經驗是,即使出版了專著,甚至獲了獎,也還要關注此領域的研究,評判此領域的研究成果。對已出的專著要不斷修訂、補充、完善。只要持續地關注與投入,就會有新的思考,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研究成果問世。《山水風景審美》一書,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5年增訂版、2011年第三版,字數也由初版的25 萬字增加到再版的35 萬字、三版的36.5 萬字。陶學研究專家、華東師范大學龔斌教授的《陶淵明集校箋》是目前國內整理得最好、水平最高的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6年初版,2011年修訂第二版,2018年再出典藏版,前后經歷了12年的時間,字數也由初版的41 萬字增加到了典藏版的51 萬字。今天治陶學者,沒有誰能離開龔斌教授整理的陶集。筆者從龔斌教授的學術成果以及治學精神中獲取過諸多啟發。
六
最后,還想說一點的是,即使是做科學研究,也需要較高的審美水平與較好的文學修養,特別是過硬的文字表達能力。其中,散文寫作是最好的基礎訓練。通過散文寫作提高語言表達水平,論文語言力求準確、洗練、生動、優美。散文寫作和論文一樣,同樣講究篇章結構、語言、文字。近代的學問大家,無不是文學大家,如魯迅、宗白華、朱光潛、錢鐘書、陳從周諸先生,無不是散文高手,如《野草》《朝花夕拾》《美學散步》《美學書簡》《寫在人生邊上》《說園》等,集哲理思索與散文之美于一體,令人一翻開就不忍釋卷,他們的古代文化與文學修養,讓我們這些多年從事所謂專業研究的教授自慚形穢,自愧弗如。
我自己在論文寫作之余,40年來發表了100 余篇散文,如《竹樓品傣味餐》(《光明日報》1993年5月10日)、《到西雙版納觀光》(《光明日報》1993年7月20日)、《紅月亮下的傣家樓》(《蘭州日報》1993年7月22日)、《曼斗村的“潑水節”——西雙版納“民俗旅游村”紀勝》(《光明日報》1993年9月27日)、《看云》(《內蒙古日報》1994年2月5日)、《不死的龍血樹》(《森林與人類》1994年第2 期)、《黃昏,在瀾滄江畔》(《內蒙古日報》1994年8月6日)、《等車》(《文化與生活》1996年第2 期)、《面對風景》(《內蒙古日報》1996年7月13日)、《永遠的誘惑》(《旅游時報》1996年9月29日)、《成都杜甫草堂》(《內蒙古日報》2009年8月17日)、《大興安嶺秋色》(《草原》2012年第1 期)、《燃燒的精靈——關于火的隨想》(《草原》2014年第4 期),等等。《“以人生為節日”與“詩意地棲居”》,2014年3月10日在《學習時報》發表之后,《人民日報》2014年3月28日第五版“評論”,以《以人生為節日》為題摘編了本文,“中國社會科學網”“人民網”“求是·理論網”“中國日報網”“人民論壇網”“鳳凰· 財經網”“鳳凰·資訊網”“中國民族宗教網”等轉載了此文。我試圖通過不間斷的散文寫作,加強自己對世界新鮮、敏銳的感受,避免文字表達的蒼白、枯索、單調。我的散文多寫風景,以此培養自己對山水自然的深厚感情,保持與功利的適當疏離,為理性的學術研究融入一些靈性的、感悟的東西。
愛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觀》中說:“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賴著別人的(包括生者和死者)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簡樸的生活。并且時常為發覺自己占用了同胞們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14]近40年的問學之路走到今天,我愈感到了此話的分量,我要求自己是懷抱著這樣的態度問學、治學的,多一份執著和責任,多一份莊重和神圣,我也愿意以此與青年學人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