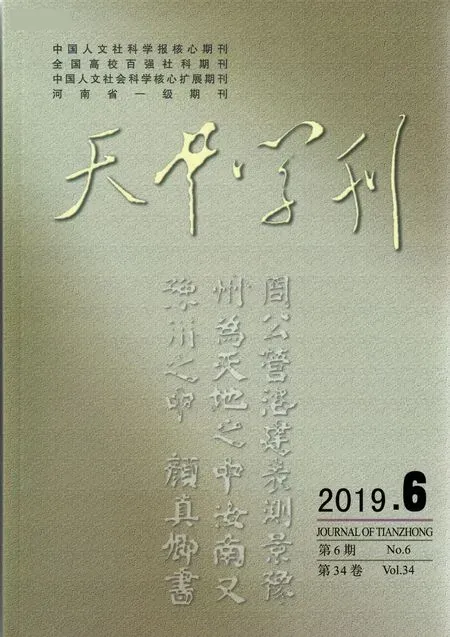朱子故事的流傳及文化內涵研究
閔 永 軍
(黃淮學院 文化傳媒學院,河南 駐馬店463000)
南宋朱熹不僅是一位理學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一位儒者的情懷,在勤于治政的同時,傳播思想,發展地方教育,興辦書院,廣收弟子,推行教化。朱熹因而被尊為朱子。南宋以后朱子得以配享孔廟,思想人格受到歷代尊崇。自元朝至明清,程朱理學被立為官方哲學,成為科舉功名的必考科目,程朱理學自上而下影響力非常之大。康熙帝稱道:“惟宋之朱子注明經史,皆明確有據,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字一句莫有論其可更正者,觀此則孔孟之后可謂有益于斯文,厥功偉矣。”[1]因其巨大的影響力,在相關正史中的記載之外,朱子傳說在文人筆記、小說家言及民間故事傳說等敘事文學領域傳播廣遠。從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研究角度出發,可以窺見朱子故事流傳的路徑及故事背后的文化蘊涵。從此項研究出發,窺斑知豹,也可以為古代文人故事類型敘事文化學研究提供一點借鑒和思考。
一、朱子故事的流傳演變
后世流傳的朱子故事主要集中在朱子彈劾唐仲友、朱子與妓女嚴蕊、朱子判案斷獄幾類上來。進行朱子故事演變的梳理,有必要從歷史真實的朱熹著手。
(一)歷史上朱熹其人與朱、唐交奏公案簡述
關于朱熹的生平事跡概況,今人已經整理詳盡,有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可以參看。原有的相關歷史資料主要集中在宋史本傳、朱熹文集、朱子語類等著作中。根據《宋史》本傳記載,朱熹少年天才、好學不輟,成年后治政有方、修建書院、講學教化、著書立說,并且剛正不阿、立身為民。朱熹弟子陳淳對其師治政功績有具體陳述,《郡齋錄后序》說:
先生在臨漳首尾僅見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慕而亦有愕然疑嘩然毀者。越半年后,人心方肅然以砭僚屬勵志節而不敢恣所欲,士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游于街衢而抄掠于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紊。良家子女從空門,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是豈不為可恨哉。[2]
朱熹知漳州僅一年的時間,政績斐然。可見朱熹不僅發明儒學思想功績赫然,而且在實際的治政中能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并有卓然成效。
關于朱熹與唐仲友一樁公案,以及牽涉妓女嚴蕊的一段史實,今人已經有了詳盡的考辨,史實基本清楚。如李致中《歷史上朱熹彈劾唐仲友公案》一文列舉并詳細分析了朱熹彈劾唐仲友六狀后認為:“綜觀朱熹彈劾唐仲友的罪狀,條款雖多,但最重要的當是他利用私刻會子版刷印官會而犯法發配來的犯人蔣輝,在他恐嚇之下繼續為自己再度私刻會版,刷印官會。這是知法犯法,罪不容誅。前述第六狀對此款情節已說得具體而入微,恕不贅述。”[3]唐仲友與嚴蕊事跡,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狀》中敘述得十分清楚:“追到嚴蕊,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蕊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千人,并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蕊逾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說與嚴蕊:‘如在彼處不好,卻來投奔我。’”[4]朱熹彈劾唐仲友罪責屬實,并無誣陷;彈劾唐仲友私通妓女嚴蕊一事也并無疑義。謝謙《朱熹與嚴蕊:從南宋流言到晚明小說》也認為朱熹彈劾唐仲友并非出于個人恩怨,而是職責范圍內對唐仲友不法行為的追訴,同時期朱熹還上書彈劾了其他人。由朱熹對唐仲友的彈劾為源頭,當時的宰相王淮對同鄉兼姻親的唐仲友有所庇護,把輿論的矛頭轉向學術之爭,轉向對朱熹道學的批判,由此開啟了慶元黨爭[5]。李鵬飛《論人與文的接受和傳播——以朱子形象為中心》也說:
束景南教授在《朱熹年譜長編》中指出,唐仲友是一個貪贓枉法的官吏,朱熹對其參劾合理。謝桃坊先生在《宋詞辨》中指出:“嚴蕊是一個貪婪奢侈、仗勢受賄、揮霍公款、詐騙錢財的歌妓,其人入獄是罪有應得的,不值得人們同情。”莫礪鋒先生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全面的證偽和總結后指出:“有些后人把唐仲友與嚴蕊視為一對忠于愛情的癡男怨女,從而為他們一灑同情之淚,并對棒打鴛鴦的朱熹百般辱罵,實在是受了小說家言的誤導。”[6]
(二)宋末及元明文人筆記中的朱子故事
筆記又可稱為筆記小說,它的特點就是兼有“筆記”和“小說”的特征,內容廣泛駁雜。古代文人筆記所記,既有積極的記人述事意義,又有隨意發揮、道聽途說、斑斕駁雜、經不起考辨的特點。
大致與朱子同時,已經出現了文人筆記對朱子故事的記述。最早的當屬洪邁《夷堅志》。《夷堅支庚》卷第十“吳淑姬嚴蕊”條:
又臺州官奴嚴蕊,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為守,頗屬目。朱元晦提舉浙東,按部發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為伍伯行杖輕,復押至會稽,再論決。蕊墮酷刑,而系樂籍如故。岳商卿提點刑獄,因疏決至臺,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身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即判從良。[7]
大略同時的俞文豹《吹劍錄·四錄》、陸游《四朝聞見錄》分別記錄了朱子彈劾唐仲友的緣由。稍后的吳子良《林下偶談》仍然亦記述了朱熹彈劾唐仲友一事。這幾人的記述較《夷堅志》簡略。
宋末元初周密《齊東野語》則分兩條記述了朱子與唐仲友、朱子與嚴蕊事件,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條: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臺,嘗狎籍妓,囑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
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臺,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8]383
卷二十“臺妓嚴蕊”條:
天臺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
唐與正守臺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
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
其后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臺,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為濫。系獄月余,蕊雖備受棰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
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蕊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臺故家云。)[8]386
周密《齊東野語》在《夷堅志》的基礎上增加了細節,所寫朱子故事更加繪形繪色:朱子彈劾唐仲友乃因受陳亮挑撥,唐仲友則小肚雞腸、胸襟狹隘,譏諷朱子不識字甚至無中生有構陷人。妓女嚴蕊才情俱佳,更兼俠義情懷。不過《齊東野語》在每一條結尾都注明了朱子故事從別處聽來,就有了道聽途說的嫌疑。
明萬歷時期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六十“朱熹(晦庵先生)”條記有朱子故事,所記嚴蕊、唐仲友事與《齊東野語》相同,當來自《齊東野語》,不同的是,還增加了朱子誕生的神跡以及朱子祝筆顯報應的傳說:“朱韋齋,晦庵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其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后生晦庵,果為大儒。”[9]
(三)晚明小說中的朱子故事
晚明凌濛初在前人筆記的基礎上創作了擬話本小說《硬勘案大儒爭閑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收錄在《初刻拍案驚奇》中。小說用細膩的筆觸寫了朱子錯斷案、朱子彈劾唐仲友、朱子與嚴蕊故事。故事情節與最近的筆記小說《堯山堂外紀》基本雷同,說明其顯然來自《堯山堂外紀》①。
小說從“文公為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后得地之家不昌。”一句敷衍開來,講述小民妄誣大姓祖墳一事。朱熹按照常理判斷小民不可能亦不敢誣陷大姓人家,因此把原屬于大姓的墳地斷給了無賴小民。而小民也正是摸準了朱子鋤強扶弱、愛護平民小戶的心思,把大姓的墳地平白占去。朱熹日后經過此地,詢問居民才得知小民妄誣大姓墳地一事,因此慚愧之下,對天祝告,上天顯靈,毀了墳地的風水。小說用這樣一件事作為擬話本正文的入話,著重點出朱子的成心偏見、狹隘偏執,鋪墊了下文處理唐仲友嚴蕊事件中,朱子“秀才爭閑氣”的狹隘自私、濫用刑罰、挾私報復。
《宋元學案說齋學案》敘述嚴蕊事與凌濛初擬話本小說相近,黃宗羲評價曰:“其(唐仲友)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為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功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明儒學案河東學案下呂涇野語錄》:“詔因辭謝久庵公,與論講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豈后學所敢輕試?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是太褊。’”上述兩書在客觀評價朱唐公案的基礎上,對朱子人品性格有一定判斷:“晦翁素多卞急”“太褊”,這樣的評價準確性有待確認,但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擬話本小說對朱子“成心”偏執的描述。
(四)今人整理的民間故事中的朱子故事
今人整理的民間故事中有大量的朱子故事,這些故事主要集中在閩學興盛的福建地區。那么這些民間故事的形成是在何時?本文認為它們中很大一部分應是受到凌濛初擬話本小說《硬勘案大儒爭閑氣》一文的影響而來,形成時間當在晚明以后的清及民初時期②。
現有閩中地區朱子民間故事,經過今人搜集整理,主要集中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地區相關的縣市民間傳說中:朱熹在漳州的傳說故事有《計除開元寺惡僧》《斷蛙池》《白云飛應》《石螺無尾蝦仔紅殼》《何有石》《塔口庵的來歷》《朱熹改詩》《朱熹點破蜈蚣穴》《青石碑》《(陳淳)畫月贈朱熹》《朱熹訪陳北溪》《朱熹點破蜈蚣穴》《朱熹錯判鐵環樹》《朱文公重建漳州府》《文昌魚的傳奇》;其他如《齊齊松》《茅筆鎮流》《葬大林谷鎮蟹精》《對天祝詞顯報應》等故事分散在閩地各處的民間傳說文本中。閩北和贛南鵝湖書院、白鹿洞書院地區的民間故事,大多涉及朱子與狐仙的感情故事:如《狐夫人》《鵝湖山朱熹遇怪》《狐貍墓》等。
比較閩北與閩南的朱子民間故事可以發現,“同為閩學重鎮的閩北與閩南卻存在著諸多不一樣的民間傳說……兩地區呈現出不一致的朱子形象,即朱子都具有奇異能力,但是朱子形象在閩北地區則偏向于書生形象,在閩南地區則偏向于儒家大學者與良吏形象。”[10]
還有一則獨特的故事,顯示了學者朱熹智慧淵博的人物特征。閩北地區流傳的《抓朱熹》(《中國民間故事集成· 福建卷》)故事講述朱熹“慶元黨爭”之際,被韓侂胄追趕抓捕,依靠自己的教書特長巧妙地避開。該故事顯示了朱熹具有淵博學識的特點。
二、朱子故事演變的文化內涵
從歷史史實到今天留存下來的民間故事,朱子故事經歷了長期的演化過程。從南宋洪邁的《夷堅志》開始,朱子故事里的朱子形象開始偏離歷史人物朱熹的本來面目。到晚明時期,筆記與小說中的朱子故事,更是把朱子塑造成了一個自私偏狹、固執迂腐的形象。在當代整理留存的民間故事中朱子形象更加多樣化。從歷史到傳說,朱子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發生了如此大的變異,那么探尋其變異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內涵,就是一件迫切且有意義的事情。
(一)朱子時期政治斗爭遺留的陰影
歷史上,南宋朱熹與洪邁的過節以及朱熹卷入慶元黨爭,是朱熹故事變異的源頭。如前文所述,宋人筆記中朱熹與唐仲友、嚴蕊的故事,是南宋黨爭的產物,是捕風捉影的流言,而非信史。洪邁是宋人筆記關于朱子故事的始作俑者。洪邁為何要制作朱熹與嚴蕊故事以誣朱熹,歷史原因復雜。《宋史》說洪邁“受知孝宗”,“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這受到朱熹尖銳的譴責:“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為不當取覿所紀云。”[11]此外,洪邁由于篡改周敦頤《太極圖說》首句,受到朱熹的責備[12],懷恨在心。洪邁在其晚年所著《夷堅志》第十卷“吳淑姬嚴蕊”條,炮制了“才妓作詞,岳霖判案”的凄美故事,以此詆毀朱熹政聲人品。洪邁筆記開其端,才有了后來以訛傳訛,至晚明凌濛初擬話本小說把朱熹惡名加以傳揚,流傳到民間,就有了各樣的朱子故事。閩北地區一則小故事《抓朱熹》則記錄了慶元黨爭之際,朱熹被韓侂胄追趕抓捕的歷史情景,正是當時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的再現。
(二)時代社會思潮的影響
明代中期王陽明心學崛起,隨著王學左派的極端影響,晚明時期個性解放思潮泛濫。個性解放思潮沖擊著代表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明史·儒林傳序》云:“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13]凌濛初在《硬勘案大儒爭閑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中,通過批判人人敬仰的道學先生朱熹,表達了對道學的質疑。凌濛初借機評論,立心正直的嚴蕊是真正講道學的,而不講人情人性、逞一己之私的大儒朱熹則是偽道學。通過考察晚明思潮解放的背景,細讀“二拍”文本,特別是《硬勘案大儒爭閑氣》,可以看出,凌濛初的道學觀就是發自本心的一種理想的道德狀態,而非克制正常人欲、扭曲人性的偽道學——理學。
從凌濛初創作“二拍”擬話本小說的動機來看,凌濛初作為一個書商,他明白讀者群的閱讀趣味和審美趣味,因此凌濛初不僅要刻印當時頗受歡迎的“三言”來售賣,而且他要親自動筆寫作,沿襲著擬話本小說貼近市民階層生活、重情近性的審美特點來創作。因此小說反對假道學、重視本心真性的傾向也是晚明時期的時代要求。
從閩北贛南民間故事關于朱子與狐仙傳說來看,“其中既有十分復雜的地域性差異,又是一個歷經長期演變的過程。它既是武夷山百姓對朱夫子之感情藉千古狐魂的理想泛化,也是明清時代怨女曠夫消解性寂寞的精神藥劑;既是宋元以降失意士人對科舉制度的情緒反彈,也是縱逸之輩放浪形骸的辯護談資;既是贛南萍鄉‘毛女洞’中山野之狐的轉換移植,又是人們深層婚姻文化心理及倫理價值取向的折射反射。”[14]
一方面是節烈牌坊依然存在,壓抑著社會中女性的身心,另一方面在朱子長期居住、講學的崇安縣,清初茶市漸興,娼妓亦至:“娼妓一業,明以前無可考見,清初茶市漸興,娼妓亦隨之至。清末赤石一隅多至七十余家。夕陽初下,鶯燕交飛,遍地笙歌,聲聞數里。可謂極一時之盛。然此輩均贛籍,茶市一過,則風流云散矣。”[15]總體上來看,晚明清初社會思潮漸趨于放松對人性的壓抑,縱情縱欲的人性解放潮流與這一時期艷情小說、猥褻小說的泛濫,提示著人們對于自我情感覺醒的要求,朱熹與狐精的感情故事揭示人們天理人欲之辨中大儒的符合普通人想象的情感需求。
(三)閩中地區民間崇儒重文的文化氛圍
閩地朱子學興盛,閩中地區崇儒尚文的文化氛圍不僅在上層士大夫圈,而且在民間也很有群眾基礎。從閩南地區的民間故事可以看出,理學大儒朱子十分受歡迎。如前所述,“朱熹是一個心系黎民的州官、循循善誘的儒師、神仙道人、江湖術士”,是一位儒家大學者和鋤強扶弱的清官。戴冠青所論最為肯綮:“在這些故事中,朱熹的能力已經被民眾無限擴大化,而且無一例外的是,他為民除害的武器都是神奇的朱筆或儒巾,朱筆和儒巾可是最能顯示其知識者本領或身份的用具呀!由此不難看出,朱熹在閩南民眾心目中多受敬重,閩南民眾崇儒尚文的心理有多執著。”[16]
閩南地區特別是漳州一帶朱子過化之后,士人學風興盛,從乾隆壬午《龍溪縣志》卷十“風俗”云“在宋為朱子之所過化,而民好儒……塾師巷南北皆有之,歲科應童子試額二千有奇,他邑弗及也。其魁壘者舉子業之外,旁及詩古文詞,往往有聞于世。世族多藏書……素封之家牙簽玉軸燦然英筒中”。朱子及弟子陳淳,到再傳弟子,早就從根本上奠定了閩漳地區的崇儒之風。
本文對朱子故事流傳演變進行梳理,分析了其背后的文化蘊涵。但朱子故事文本還不止于此,我們還可從朱子留下活動軌跡的各個地域的相關文人文獻、民間文獻入手,進行更加詳盡的鉤沉掘遺。研究中國敘事文化學,文人故事流傳及演變是一個重要的題材類型。本文旨在拋磚引玉,期待有更翔實的文本考辨、更深厚的資料積累、更深宏的理論研究出現。
注釋:
①參見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爭閑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②如《青石碑》《朱熹錯判鐵環樹》兩個故事主要情節都是小民利用朱熹鋤強扶弱、為民做主的一貫作風誣陷大姓故事,這個故事顯然來自《硬勘案大儒爭閑氣》;《對天祝詞顯報應》也從這篇擬話本小說中來。閩南地區大量的斷案故事,也可看做受擬話本的影響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