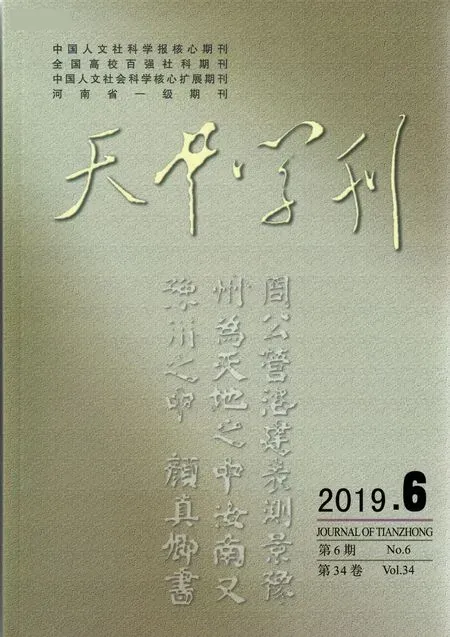梁祝故事的沖擊效應
——論求學情節對傳統教育習俗的悖逆與反抗
余 全 有
(黃淮學院 天中歷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駐馬店463000)
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的梁祝故事,勾勒出梁山伯和祝英臺與世俗眼光和要求存在明顯反差的形象,二人驚世駭俗的言行是傳統社會的人們想做而不敢做的,因而在大眾心目中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力。梁祝故事由求學、提親、哭墳三個主要情節構成,這些情節的不合常理,增強了梁祝故事的社會沖擊力,產生了強烈的感染力。其中,求學情節明顯具有對傳統教育習俗的悖逆與反抗色彩,“祝英臺化裝求學,是受誦詩習禮的束縛而進行的強烈反抗”[1]311。
一、求學情節沖擊了世俗社會教育觀念
在傳統社會,女子不能出外接受社會教育,即便文明開化、風氣日新的近代,也依然實行男女分校的教育方式。然而,在梁祝故事中,祝英臺不僅外出接受教育,而且還與男性一起讀書數年,更是與梁山伯長期親密相處,這在傳統社會中是令人無法想象的,也是不被允許的。正是這一情節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梁祝故事具有強烈的震撼和沖擊效應。
在傳統社會,無論是社會層面還是家庭層面,對待男性和女性接受教育的態度都截然不同。“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男教故重。則女訓亦未可輕。古今家國之際,有圣母即有圣子,有賢婦始有賢夫,政治之本,萬化之原,皆系乎此,其教固不重與?”[2]347從表面上看,似乎社會非常重視女性教育,但這也僅限于教女性如何相夫教子、持家奉食,至于學知識做事業則不關她們的事。由于女子識字后可能會接觸一些野史、小說、戲文之類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又常常被認為充斥著異端邪說,傳統社會便生出“婦人識字多誨淫”的思維,進而產生“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奇怪理論。這樣,女子應該讀什么書成為備受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于是,《女孝經》《女論語》《列女傳》《女訓》《女誡》成為女性接受教育的必讀之書。
傳統社會男性接受教育的目的一般是為了科場成名,光宗耀祖,家庭對男性求學之舉是積極支持的,如梁山伯的父親“一心想供養他上學,長大了取得功名”[3]105。而女性不能參與社會事務,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所以“女子之知書識字,達禮通經,名譽著乎當時,才美揚乎后世,亶其然哉”[2]343!也就是說,女性接受教育主要是為了成為所謂的“賢婦”“圣母”,即培養“婦德”。“婦德”的主要內容就是遵從傳統道德倫理,而傳統道德倫理的重中之重又是所謂“男女之大防”。“婦人之德,莫大于端己,端己之要,莫重于警戒。”[2]122在傳統社會,女子七歲便要約之以禮。《禮記·內則》即有“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的規條。《女論語》要求“內外各處,男女異群,莫窺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窺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2]80。女子輕易與別人接觸,會被視為行為輕薄,甚至上綱上線為道德敗壞,也就是民間通俗所講“不正經”。“嫁為人婦,恥辱門風……遭人指點,恥笑鄉中”[2]82。這樣的女子不僅會遭人輕蔑、唾棄,甚至其家庭乃至整個家族都會遭人恥笑。
傳統社會不允許女性參與社會事務,女性對任何社會和家庭事務均沒有發言權和決定權,她們只是從事家庭勞動的工具和生兒育女的機器,特別強調“凡為女子,須學女工……機車紡織,切莫匆匆,看蠶煮繭,曉夜相從”[2]81。如果一個女子的女工不精,她將會遭人恥笑。正規教育方面也根本沒有女性的一席之地,女性不僅不能與男性一樣進入學堂接受正規教育,而且統治者也沒有給女性進入社會預置任何通道,她們不能參加社會上任何考試,也不能接受任命承擔任何職務。只有在上流社會家庭中,家長才會聘請家庭教師教授家中的女子,但這種教育本身其實也并不是以提高女性的文化知識水平,使其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為目的的,而是為了更好地向她們灌輸封建倫理道德思想。“對于青春妙齡的女子來說,她們需要的是活潑的天性的滿足,是眼界的開闊,甚至于火熱情戀的激動。然而,‘十年不出’的幽禁式生活,無疑正與此相違。情竇初開、憧憬一切美好事物的青春少女,卻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4]祝英臺離開家鄉到學堂接受正規教育這一故事情節,在傳統社會中極具挑戰性,它所體現的是故事創作者和傳播者對傳統教育習俗的一種悖逆與反抗。“女扮男裝外出游學,當時雖是驚世駭俗,但實際上,正是廣大婦女潛在意識中希望獲得與男性具有同等學習權利的反映,也獲得了歷代開明文人的贊許。”[5]29這種挑戰性在民間產生的影響力正是梁祝故事得以廣泛流傳的社會心理基礎。
二、求學情節在教育內容和形式方面均對世俗觀念提出挑戰
在傳統社會,男女在接受教育的內容和形式上也同樣存在明顯區別。在“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理念引導下,傳統社會的正規教育主要讓男性攻讀圣賢之書,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成為統治階層合格的一員。當然,普通民眾家庭有生存技能教育,但那算不得正規教育,甚至根本算不上教育,只被視為雕蟲小技。按照“婦德”“婦容”“婦功”的要求,女性的教育主要集中于行為規范和家務勞動技能上,并將這些視為一個女性立足于家庭的基本要求,即“士勤于學,女勤于工……治絲執麻,以供衣服。冪酒漿,具菹醢,以供祭祀,女之職也”[2]117-118,“教女之道,猶甚于男。而正內之儀,宜先乎外也”[2]331。傳統社會的教育內容處處顯示出男尊女卑的思維模式和社會認知。“當寮事務,百樣該知;通文達義,應變隨機;揀柴執爨,煮茗焚香;補拆漿洗,繡鳳描凰;針線精致,裁剪審詳。”[2]350比如《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她首先學的是家庭勞動技能,誦詩書是放在后面的,紡織是必備的教育內容,而詩書只不過是點綴而已。司馬光曾說:“凡人,不學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也。于是乎有身為暴亂而不自知其非也,禍辱將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則為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6]1465他雖不完全反對女子讀書,但認為在內容上須有所選擇:“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讀《孝經》、《論語》及《詩》、《禮》,略通大義。其女功,則不過桑麻織績,制衣裳、為酒食而已。至于刺繡華巧,管弦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6]1466可見他主張女子學習主要以禮義規范和日常家務為主。據明代呂坤《閨范》載,司馬光還曾說過:“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7]1464《牡丹亭》中杜麗娘被父親訓斥道:“假如刺繡余閑,有架上圖書,可以寓目。他日到人家,知書知禮,父母光輝。”[8]231《溫氏母訓》則說得更直接:“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木蘭辭》中開始就是“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可見花木蘭在代父出征前的主要活動也就是在家中織布裁衣,從事家庭勞動。所以,很多文學作品常常將大家族女子居住的地方稱為“繡樓”,也即女子學習和從事紡織刺繡的地方,那里不僅是其日常起居之處,也是她們日常最主要的活動場所。而且,許多文學作品也都有大家閨秀在一起交流紡織刺繡技藝的情節,就連《紅樓夢》中的貴族女子也不能例外。
梁祝故事之所以成為民間傳奇,其中一“奇”,就是它塑造了祝英臺這樣一個在傳統社會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沖破家庭和社會阻力,到外面混跡于男性之中接受正規教育的女性形象。當然,關于祝英臺到外面接受正規教育的原因,不同版本有不同描述。常見的一種說法是祝英臺為了逃避皇帝在全國進行的選妃活動。“皇帝選妃傳全國,天下父母有憂色,惟恐女兒選入宮,從此骨肉兩相失”[9]1,“祝家有女名英臺,年輕美麗又多才,她想喬裝出門去,投師兼可免禍災”[9]2。另一種說法是梁祝兩家早有約定:如兩家生下的都是女孩就在一起學紡織刺繡,若都是男孩就一起讀書,一男一女就結為夫妻。后因梁家衰落,祝家企圖悔婚,才讓祝英臺扮成男裝,試圖蒙混過關。除此之外還有多種說法,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但是,無論何種說法,都有一些共同特點:一是祝英臺在出外讀書之前已經接受過傳統的家庭教育,有了一定的知識基礎,否則無法接受學堂里的正規教育;二是祝英臺外出讀書遇到了重重阻力。在外出讀書之前,她花費很多功夫做父親的思想工作,甚至扮成算命先生勸說父親,“怎奈父親老頑固,重男輕女不放行”[9]3。“閨女出門唯恐人議論,不去又怕遭災星”[9]8,即使在面臨遭受災禍與外出求學的選擇時,她的父親仍然對女兒出外求學表現出十分的不情愿,不愿松口放女兒出去。祝英臺在父親面前極力為自己出外讀書尋找借口:“祝府本是書香門第,孩兒遠去求學,為的是知書識禮,孩兒也曾聽爹爹說過,古時有曹大家、蔡文姬,都是一代才女,留名千古,難道孩兒就學不得她們么?”[10]9盡管祝英臺志向遠大,雄心勃勃,可父親卻潑下了一盆冷水:“你去不得,想你是裙釵之女,怎能拋頭露面,遠走杭城,要讀書,為父可請先生來府教讀……縱有名師,怎奈你是個女孩兒……祝府千金之女,遠去求學,有失體統。”[10]8他也并非完全反對女兒讀書,只是反對女兒遠去求學。所以,他提出一種折中方案,即請家庭教師在家里教女兒讀書,“就請了先生,在自己家里開館”[3]126。但隨著知識的積累,祝英臺感覺自己應該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也應該到外面開闊眼界,于是決定到當地頗有盛名的書院去求學。當她向家人說出自己外出求學的想法時,不僅父母反對,而且還遭到嫂嫂的公開嘲笑。很明顯,因為她是女娃,所以不能外出去書院求學。而這正是傳統社會女性接受教育的普遍形態,也是社會公眾普遍接受的一種女性教育方式和習俗。
三、求學情節與傳統教育習俗沖突所產生的文化效應
如前所言,正是求學情節與傳統教育習俗的沖突所產生的強烈文化效應使梁祝故事成為家喻戶曉的民間傳奇故事。可以說,求學情節對傳統教育習俗的顛覆性描述不亞于這一故事對婚姻習俗的沖擊。明代楊守祉曾在《碧鮮壇詩》中對祝英臺男裝出外讀書一事憤憤不平:“英臺亦何事,詭服違常經?班昭豈不學,何必男兒朋?”[11]9錢南揚也說:“祝英臺化裝出外求學,這種在封建社會中異乎尋常的壯舉,的確是驚世駭俗而寓意深遠。它的寓意,就在于反映了廣大婦女要求打破封建禮教,實現男女公開同窗共讀,希望取得和男子同樣的文化知識。這也可以說是封建社會婦女長期受壓迫和摧殘的潛在意識的爆發。”[1]304-305整個傳統社會對男女教育的態度、內容和形式均有明顯的區別,人們對這種區別的普遍認同和毫無疑義的接受又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它反過來又影響著教育習俗,從而使上述觀念逐漸固化和升級。正如謝無量所言:“世界之上,男女各居其半,其聰明材智未嘗不同,因于風俗習慣之相承,而處境不能無異。”[12]1但直到今天,這種觀念在許多人的頭腦中仍然時而浮現。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氛圍中,祝英臺卻“胸中有大志,要求學杭城”[10]5。在當時不可能有女子讀書的學堂中,祝英臺卻與眾多男性在一起讀書學習,這本身就是對當時社會習俗的一種顛覆和挑戰。祝英臺“懷著強烈的求知欲望,渴望有與男子一樣平等的讀書權利,女扮男裝外出游學,是梁祝傳說故事進一步延伸和展開的切入點,也是梁祝生死戀情節發展的起點”[5]28。所以,祝英臺外出求學又成為梁祝故事發展的重要契機和關鍵,也是梁祝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民國初年,男女教育仍然分立。‘男女相悅,總不免于私通’的觀念,在中國人觀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從社會輿論到政府學制,都是特講‘男女之大防’。直到1919年在‘五四’運動的沖擊下,北京大學才開女禁……婦女才得與男子同樣享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可見女子外出游學,正式求師,男女同學,在中國是‘五四’以后的事。可是梁祝故事卻把這種女子受教育、男女同學的強烈要求和實現,提前了1600 多年。這說明在民間,女子求知,和男子一樣受教育的愿望,并沒有因父權制的嚴酷統治和長期封建制度而泯滅。”[13]60祝英臺外出求學這一情節對社會公眾的思想沖擊和產生的社會文化效應絕非讀書識字那么簡單,它是對傳統社會中普遍流行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方式的徹底否定,也是對男女平等受教育權利的肯定與追求,進而沖擊了數千年來一直盛行的以男尊女卑為思想基礎的傳統教育觀念和教育制度。因為“梁祝故事不但開中國民間故事或小說史上女子以求知為第一要務之先河,反映了長期封建社會中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利的人類半數中的婦女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愿望,也歌頌了以文化知識結構為基礎的男女兩性平等、純潔的愛情,并因此而至于雙雙身殉。這種悲劇題材來自古代現實生活,給人們帶來的崇高感,絕非后世為尋夫、避難、當官而女扮男裝的大團圓故事所可比擬。它具有開啟民智,尋求人類(特別是婦女)自我解放,探求知識,追尋真理的自覺性和先進性”[13]62-63。也正因為祝英臺男扮女裝外出游學在當時是驚世駭俗之舉,直接反映了廣大婦女潛在意識中希望獲得與男性具有同等學習權利的訴求,這種訴求和抗爭又獲得了社會大眾普遍的贊許和認同。所以,求學情節也成為梁祝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的重要的文化和社會心理基礎。
四、結語
求學不僅是梁祝故事的主要內容和重要情節之一,也是梁祝故事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還是梁祝故事發展的重要鋪墊和切入點,它反映了故事的創作者和傳播者對傳統教育習俗的叛逆和反抗,體現了人們對男女平等接受教育權利的渴望與追求。這一情節產生了強烈的沖擊效應,使廣大民眾的心理受到強烈的激蕩和震撼。也正是這種對男女平等權利的向往和追求在民眾中產生了強烈共鳴,大大增強了梁祝故事在民間的感染力、震撼力、穿透力和輻射力,從而使它得到了長期而廣泛的傳播,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和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民間故事。
梁祝故事中求學情節對傳統觀念的否定和反抗,實際上是社會轉型在文學藝術創作方面的直接反映。明清之際,尤其是近代以來,商品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明顯改變,人們對舊傳統舊道德的抵觸情緒也日益強烈,期望擺脫舊倫理道德的束縛,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利。這種情緒從很多明清小說及近現代文學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與此同時,女性要求自身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呼聲也日益高漲,而其核心又是婚姻自主和受教育權利的平等。因此,梁祝故事自然也會受到這種社會思潮的影響和浸潤,而其對舊道德舊觀念的叛逆與反抗,又正好順應了社會觀念的變遷趨勢,使其得以更迅速和更廣泛的傳播。
此外,盡管梁祝是傳統社會中廣為流傳的一則民間故事,但它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社會已發生巨大變化,觀念得到明顯更新,但少部分人仍固守舊觀念、舊思想,在對待男女教育問題上仍堅持陳腐觀念,頭腦中仍殘留有女孩子讀書不讀書無所謂的觀念,梁祝故事無疑是對上述保守落后觀念的鞭笞與批判,對男女平等的頌揚與倡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