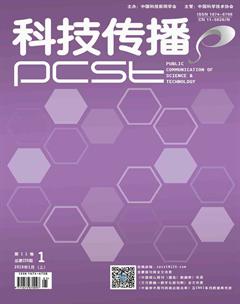傳播權在我國社會環境下的多維價值和發展路徑
陳燕
摘 要 在網絡時代,傳播技術的革新不斷影響著社會信息傳播的權利框架,傳播權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相比更具有開放、平等、自由的人權價值。傳播權作為一種社會權利和基本人權,從而使人人享有傳播權。文章探討了在我國社會環境下,傳播權的多維價值和發展現狀,明確發展傳播權應當以自由、包容、平等和多樣性參與作為基本原則,完善適應我國社情的規范、理性的傳播秩序。
關鍵詞 傳播權;道德權利;多維價值;言論自由;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9)226-0161-02
一直以來,我國的言論自由現狀就一直備受西方世界指責。一方面,我國一直以西方的言論自由理論研究作為我國發展言論自由的指向標;另一方面,全球并未在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和限制這一問題上達成合意。種種原因導致了我國目前在言論自由上面臨的窘境。
同時,言論自由逐漸發展成為人權的重要一部分,特別是言論自由中的傳播權。傳播權在未來將會備受矚目。網絡時代打破了傳統媒體作為信息把關人的角色,在幫助普通民眾更加無限制地獲取信息的同時,也讓研究者的目光轉移到如何更好地保護傳播權這一主題上。
1 傳播權在我國社會環境下的多維價值
傳播權是一項社會權利。其組成要素和各要素間的聯系還有待于統一認識,但作為一種新思潮,傳播權的支持者們正努力把它當作一項基本的人權來加以擬訂、解釋并發展。
1.1 傳播權延展了言論自由的內涵
言論自由是指不考慮出身、財富、智力等任何外在因素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平等且自由的擁有表達自由的權利。因為有了言論自由,人們才得以自由平等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辯駁對方的觀點,在這過程中又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可以說,傳播權充當了人們更好地享有言論自由權利的工具,幫助人們真實且有效的表達思想和感情,延展了言論自由的內涵。
1.2 傳播權填補了草根文化與精英文化間的罅隙
簡單地說,“草根文化”是指“草根群體”在生產、生活、交往活動中直接或是間接、自發或是自為地為適應和改造其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具有主體獨立意識又需要話語權實踐表達的文化體系[ 1 ]。而“精英文化”是一種由知識精英創造的、蘊涵著人文理想、體現著形而上價值、寄托著烏托邦理想的、在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優勢文化[ 1 ]。兩種文化長期處于一種對立或是敵視的狀態。
就如同東、西方世界之間不可忽視的溝通不足的問題。當人們想要以自由人的身份開始觀察兩個世界時,我們期待是有機會提出更為新鮮的觀點。這要得益于網絡時代,普通民眾可以通過各種社交媒介積極參與國家大事小情的建設,國家也積極保護民眾的正當權益。國家因此也產生調和通訊傳播社群間不平等的義務,從而避免主流傳播社群在文化差異上壓迫非主流通訊傳播社群。這也從側面表明在有機會的情況下,草根文化代表的群體是愿意傳播自己的觀點。
可以說,傳播權讓每個人對創建一個理性、正義的新國家和一個維護自身價值為基礎的新社會的前景頗為推崇,兩種文化開始正視彼此間的價值觀分歧,都避免被視為有偏見的觀察者,并且以全新視角去了解對方。
1.3 傳播權維護了民眾對民族國家認同感
和普通百姓一樣,國家也注意到了傳播積極信息對于穩定社會、凝固民心的重要性。這才有了近幾年政府在主流媒體上推出的各種以國家民族為主體的宣傳片,例如《中國的崛起》《舌尖上的中國》等。這些宣傳片、紀錄片不僅向其他國家和民族展示了我國泱泱大國的形象和深厚的歷史文化,也給了國人更多的民族自豪感和國家歸屬感。國家通過樹立自身的光輝且強大的形象,正在一步步強化民眾對于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這也恰恰是傳播權的價值之一。
2 傳播權在我國發展中的困境
目前,我國民眾對傳播權的態度仍然是一種無所謂或是輕視的態度。這與傳播權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實現有關。
除去受制傳統的社會文化形態,傳播權在我國發展面臨的有一個困境是農村和城市之間傳媒發展的不平衡。現代社會與過去相比的根本區別在于:在傳播者和接收者之間有一種或多種可供聯系的工具。因此,傳播權也可以被形象的稱為“騎在傳播工具上的權利。”
在目前的網絡社會,如何妥帖解決傳播工具占有的不平等是傳播權發展的新問題。如何減少甚至于消除人民因地理區域、資金、知識、技術等因素限制所導致的“信息落差”,促進社會中的每個群體都享有平等、充分的傳播權,共同分享網絡社會的好處,是我國人民大眾對傳播權提出的新要求。
除去傳統社會文化形態、傳播資源不平等這兩個阻礙因素外,我們見識到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導致的同質化信息的爆炸,以及權威話語權的缺失。這又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阻礙,即如何在新型傳播方式中進一步發展傳播權?
3 傳播權在我國社會環境下的發展路徑
考慮到我國傳播權目前的發展困境,很難想象如果不“順應人民天性”,人民何以能夠接受這種自由的權利理念,政府何以能夠實現鞏固權力屬于人民的理念,傳播權的現代化歷程如何完成?要“順應人民天性”就要從以下三方面保障傳播權的發展。
3.1 政府實施宏觀管控與各類傳播組織的微觀調控相結合
現代社會中,一般情況下統治階級及其執政黨對傳播權的控制采取單槍匹馬的宏觀管控的方式。但是,傳播權之于人類是非線性、動態的集合權利,單純的將其以法律形式去管控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潮流的。因此,政府的首要職責仍是從法律層面上完善對傳播權的保護和限制;其次,傳播的宏觀控制是絕對的,無所不在的,而微觀控制則具體意化在傳播宗旨到傳播技巧的各個環節,也是對傳播權宏觀控制的體現。
3.2 摒棄傳統社會文化形態下的“傳播無用論”心態
傳播權的行使方式與發展程度同樣取決于社會環境的接納與許可。遺憾的是,我國人民作為開展傳播活動和實現完整傳播權的主體,對此項權利的重視程度還不夠。所以,我們還要一步步破除人們對傳播權所持有的“無用論”心態。一方面,需要強化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主體地位,對傳播主體的傳播自由給予必要的中立和寬容,促進形成多元、開明和寬容的傳播環境,讓人們真正感受到傳播權與生活息息相關;另一方面,我們應該避免給一個重要的道德概念過多的功能,我們也應該避免不同概念之間不必要的功能重復[ 2 ]。
3.3 強化傳播多樣性原則和平等原則以填補“信息落差”
傳播權的核心精神在于人人平等,傳播主體不會因社會文化、經濟資源等外在因素的差異影響其行使傳播權利。傳播權不以同質化的社會環境、無文化的為前提。
簡單來說,傳播權是無論何時何地都由全體人類享有的道德權利,這項權利可以幫助人們打破傳播秩序中的隱形階級障礙,縮小信息傳播技術高速發展所帶來的“信息落差”,構建一個平等而理性的全新傳播秩序。
國家要提供的是能夠保障人們平等享有傳播權的機制和社會條件。這不僅意味著要在法律層面上確認和保護傳播權,還意味著全社會要為傳播權的充分實現提供文明、開放、創新的政治、文化環境等。
我們應以傳播權自由、包容、多樣與參與為基礎的四項原則為基礎,建立和健全符合我國國情的規范、理性的傳播秩序[3]。否則,除了依賴學術界對傳播權的紙上談兵外,無法真正做到人人享有傳播權,依然會給我國保護人權和構建法治社會造成阻礙。
4 結論
總的來說,僅僅對傳播權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是不夠的。社會文化觀念的限制、社會法律體系保護的不周全、農村與城市傳媒發展不平衡等,都是影響傳播權在我國發展的障礙。只有深入考察這些社會歷史、經濟和文化因素,才能探索到在我國范圍內沖破這些障礙,充分實現傳播權的積極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峻,張志偉.“草根文化”含義考[J].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1(1).
[2]吳妍.論“草根文化”的社會功能[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08.
[3]張永忠.淺析傳播法制的建構原則[J].法制與經濟,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