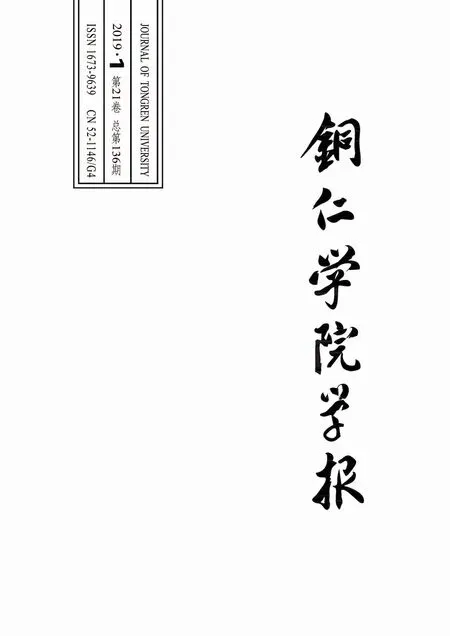索緒爾“語言學的對象”問題及其指導價值
顏景懿
?
索緒爾“語言學的對象”問題及其指導價值
顏景懿
(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 人文學院,貴州 畢節 551700)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回答了“語言學的對象”的問題,論述了若干具有深遠影響力的觀點:對“言語活動”、“語言”、“言語”三個概念的建立;對三者的區分以及三者之間關系的討論;對“語言”的界定,預見了符號學這個尚未誕生的科學,并且提出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間的關系等。現代語言學發展的不同流派圍繞“語言學的對象”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發展或者爭論,索緒爾明確了“語言學的對象”,為當今語言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針對其關于“語言”這一概念的形而上學性質,在語言教學中,應該對語言和言語的實質及其相互關系有一個新的認識,有的放矢地組織教學。
語言學的對象; 費迪南·德·索緒爾; 言語活動; 形而上學; 指導價值
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什么是語言、應該如何著手學習語言等等,這些關于其本質的根本性問題,一直是人們接觸語言和語言學后討論的常問常新的基本問題。事實上,關于語言的本質是什么,即“語言學的對象”的問題,亦是一個常問常新的問題,在當今也還值得作進一步深入思考。語言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非常激烈,經歷過一番歷史變遷。16世紀到18世紀,正音法和正字法范圍內的語音問題成為學者們討論和關注的核心問題,而18世紀科學的啟蒙,使學者開始更多地把人作為一種動物來研究,相應地把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放在人類語言的起源問題上。進入19世紀,由于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得到空前發展并獲得統治地位,語言學在研究對象上又重點關注一個連續不斷的、集中于語言學理論和實踐的專門領域。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下簡稱《教程》)中,首先提出語言與言語的區分,并重點討論了“語言學的對象”問題,認為現代語言學的任務就是探尋語言的構成規則和形式,而言語則是語言規則在實際使用中的具體體現,沒有科學分析的價值。至此,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似乎有了明確的答案。然而,“語言學的又完整又具體的對象是什么呢?這個問題特別難以回答。”[1]28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對索緒爾《教程》中關于“語言學的對象”部分的內容進行簡單的回顧和分析,并回答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同時,對語言學研究對象——語言這一概念的界定提出一些見解,并對索緒爾“語言學的對象”的指導價值做進一步思考。
一、語言的界定
語言的界定是確定語言學對象的出路。索緒爾在《教程》中沒有直接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即什么是語言學必要、具體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他只強調回答這個問題的困難并指出困難的原因所在。其他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既定的或事先確定的,然后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觀察這些對象,而語言學則不然。就語言研究來說,似乎觀點制造了對象。這意味著語言研究的對象是不清晰、不明確的,有待于研究者去選定。在索緒爾看來,沒有觀察視角即觀點的預先確定,有關語言的研究就理不清頭緒,就不可能從事科學的研究。
周流溪指出,普通語言學的重要任務之一,仍然是要繼續研究關于語言的性質和運作機制的理論,尤其是關于語言和言語的聯系和轉化的理論……只有加上語言的動態研究,從言語活動狀態中看到言語和語言的聯系和轉化,才能正確認識人類言語的性質。[2]312-313由于人類言語活動具有復雜、多重的屬性,人們在從事與此相關的研究時,不得不對其加以分析以選擇恰當的觀察角度。研究者的視角不同,所觀察、所研究的對象也不同。
索緒爾《教程》中關于“語言學的對象”分為三個部分,論述了若干具有深遠影響力的觀點。其中包括:對“言語活動”“語言”“言語”三個概念的建立;對三者的區分以及三者之間關系的討論;對“語言”的界定,預見了符號學這個尚未誕生的科學,并且提出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間的關系等。作者在文中列出了四個例子,來說明語言現象(言語活動)中包含著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兩面。言語活動當中的這種二重性給語言研究者造成兩難的境地:如果面面俱到,就得應對性質迥異、混雜不清的事物;如果只取其一,就會顧此失彼。因此,在他看來,言語活動不能成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作者接下來提出了語言是解決兩難境地的出路,回答了什么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并闡釋了什么是言語、什么是語言以及語言的性質和言語活動,著重強調了語言和言語的區別。
索緒爾在文中指出,言語活動(langage)具有多重屬性,或者說性質混雜,既有物理的、生理的,又有心理的;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可以成為若干科學的研究對象。語言(langue)自成一體(或者說是自足的整體),是言語活動的一個確定部分,屬于分類的原則。
二、語言是可以研究的
從語言的特性來看,語言是可以研究的。索緒爾《教程》構建了一個“言語循環”圖示來說明語言在言語活動事實中的位置,并把語言和言語活動區分開來。把“語言”和“言語”區分開來,“……闡明了任何科學程序所必需的抽象過程”,具有一般科學方法論的價值,對語言學研究對象和范圍的明確關系重大。索緒爾嚴格區分“語言”和“言語”的目的是為了凈化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這在科學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語言學的歷史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在《教程》中,作者用a,b,c三個二分法來分析言語循環:a)所謂的“外部”即圖中虛線所代表的,指語音傳播,是一種物理屬性,在作者看來它不屬于語言。b)“非心理部分”包括發聲器官的生理官能或具有生理性質工作或前面提到的屬于外部的物理活動。c)所謂的主動部分也包括生理的、心理的和物理的;而被動部分是指從聽者耳朵到頭腦(“聯想中心”)的部分,看來只能是生理和心理的。在這個“言語循環”過程中作者對言語的理解屬于哪個部分進行了簡單敘述。作者指出,言語活動中為集體所共享的核心或精髓部分即語言,就是索緒爾所說的“聯想調配官能”。隨后作者就將討論集中在“語言”和“言語”的辨析和比較上,指出語言是社會的,而言語是個體的或個別的;語言是主要的,而言語是從屬的。索緒爾在此強調了語言的重要性,他認為,語言由于其特性,應該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在這個意義上,言語是從屬的。但是如果就存在的意義而言,二者相互依存,甚至混為一體,難分輕重。
索緒爾接下來分四點對語言與言語的特點加以總結:(1)在多樣性的或異質的言語活動中,語言是界定得很清楚的一部分;(2)語言的社會屬性:它免受個別使用者隨意的臆造或改動,它好比一種契約,被所有同意它的使用者所遵守;(3)語言對于每個使用者來說都需要逐漸獲得;(4)一個人只要能聽懂語言符號,即便失去說話能力,仍然持有語言。說話和言語被排除在語言之外。最后作者強調語言是具體的,無非是要強調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語言不是似有似無、捉摸不定的,語言是可以研究的。
三、語言學研究對象的明確
在《教程》的緒論部分,索緒爾就明確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他將復雜的語言現象分成了三個層面,即語言(langue)、言語(parole)和言語活動(langage)。首先,他指出言語活動整體難以把握,因為它的性質是多方面的,跨越很多領域,不僅是個體,還有社會,身體,生理和心理,我們直接感受到每個人的言論活動很難掌握。接下來,他認為語言是個人被動地從社會接受并存儲在他們心中的系統。這是一種心理社會現象。它存在于個人意志之外,是社會的一部分言語活動,并且是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所共有的。口語是個人使用語言系統和個人詞性活動。語言和言語是彼此的先決條件,并且緊密相連。說話并讓人們理解,必須使用語言。與此同時,語言的存在必須體現在言語中。而且,它是使語言改變的言語。因此,語言不僅是言語的工具,也是言語的產物,但“這并不妨礙它們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因此,索緒爾認為,應該有兩個學科來學習語言和言語,一個是語言學,另一個是言語學。為了突出“語言”的系統性和同質性,索緒爾還提出了內部語言學與外部語言學的區別,其中與語言組織和系統直接相關的所有要素都屬于內部語言學的范疇。
關于語言學研究的定性,索緒爾在《教程》中寫道:“語言研究因此分為兩部分,最基本的部分以語言本身為研究對象,語言的本質是其社會性,獨立于社會使用個體。這是一種純粹的心理學研究。次要部分把語言的個人部分,即言語,包括發音,作為研究對象。這是一種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cal)研究”。[1]102索緒爾嚴格區分“語言”和“言語”的主要目的是純化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索緒爾指出,語言是一種表達思想的象征系統,表達為“概念與聲音形象的結合”,并建議“符號應該用來代表整體,并且應該使用能指和所指來代替概念和聲音形象。”具體來說,它是“能指”和“所指”的組合。“能指”和“所指”所結合而形成的符號,遵循的是所謂的“任意性原則”。
基于差別而建立起來的“能指”和“所指”,都必須存在于索緒爾所說的“語言系統”或“由形式構成的系統”之中。也就是說,語音必須形成一個系統才能將這個詞與那個詞區分開來;概念也必須位于一個概念系統中,其中只有意義和聲像的組合才是主要的。和語言(系統)相對的,則是言語。索緒爾用多種方式來描述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兩者總稱為language)的區別和聯系。例如,言語是從屬的、個人的、偶然的,語言是主要的、社會的等。從語言的角度來看,這兩個相差很遠的聲音形象是在說同一個詞,而從言語的角度來看,兩個人說同一個詞的聲音可能相差很遠。例如在語言中,張三、李四說“我”,“我”既不指張三也不指李四本人,而是指說話人,而在言語中,張三、李四說“我”則分別指張三、李四。句子(sentence)這個概念卻是屬于語言的,而說出一個句子(utterance)則是屬于言語的。大致可以概括地說,語言是語言共同體成員的語法系統,而言語是語言的體現,是依附于語法系統的說話行為,是人們平時所說的那些話。
語言學家必須面對復雜而無限的語言事實。要研究這些現象,我們必須從中抽象出一種語言系統,以便對這些語言事實作出合理的解釋。語言和言語之間的區別有助于我們澄清語言學的對象和范圍。它可以指導我們從特定的言語事實中抽象和概括有限的語言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緒爾認為必須區分語言和言語。他鼓勵語言學家擺脫傳統語言研究對經典考據或某些具體語言和現象的局限,從整體上掌握和認識語言,找到混沌和復雜語言現象背后的一般規律。
由上分析,語言學研究的是實際語言行為中所潛藏的形式系統。因此,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學的對象是語言,而不是言語。在《教程》中,索緒爾指出:“把語言和言語分開,我們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會的,什么是個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從屬的和偶然的分開來了。”[1]35作者所界定的語言不同于我們通常所說的語言,它是一個與“說話”或“言語”相對而言的、有具體內涵的、狹義的概念,與我們通常使用的、泛指的“語言”相對應的在《教程》里應該是“言語活動”。以上列舉的三個概念并不意味著三分法,事實是二分法。作者把言語活動分為語言和言語,并指出把言語從言語活動中去除就是語言。[3]77語言是隱藏在實際話語背后的形式系統,言語是實際的話語,是語言的運用。顯然,就概念的外延而言,“言語活動”就包含“語言”和“言語”。所以就這一點來說,三者的關系可用一個等式表示:言語活動=語言+言語。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表達方式容易造成誤解,似乎告訴人們在現實中存在著截然分明的兩個事物,二者相加便構成了言語活動。事實并非如此。雖然在理論上可以把語言和言語界定清楚并區分開來,但是在實際中二者的存在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語言存在于言語之中,是言語的抽象,同時又是言語得以實現的保證。不能錯誤地以為,語言和言語好像一部機器中的兩個相互連接的零件那樣存在著——那是一種簡單、明晰、機械的關系,用來描寫語言和言語是不恰當的。
在索緒爾看來,區分語言與言語的主要目的是純化語言研究的對象,即區分語言群體成員(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能力和實際的語言現象或材料。言語是一種可以直接觀察的語料,但語言學家真正的研究對象是語言群體的語言,即語言使用者在社會中通過學習獲得的、成為自己運用和理解這個語言的基礎的詞匯、語法和語音系統。[5]119
把語言和言語加以區分是作者提出的一個根本性的、富有開創意義的理論觀點。因為別人不曾做過,或尚未認識到,所以對此作者必然要給以詳盡、充分的論述。在作者看來,把語言和言語分開來研究是必須的,二者屬于兩條不同的路徑。如果不將二者分開,研究將無法進行。作者固然強調對前者的研究,但是并無偏頗,因為在區分語言和言語的同時,作者并沒有忽略二者的內在聯系。
四、索緒爾“語言學的對象”的發展與爭論
布龍菲爾德繼承了索緒爾“語言學應當以語言而不是言語作為自己研究對象”的觀點。他在評論卡斯柏森《語法哲學》(1927)時提出:“對于卡斯柏森來說,語言是一種表達方式;語言的形式表達說話人的思想和感情,這個過程是人類生活的直接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要符合人類生活的要求和變化。我的觀點與索緒爾的看法一致……這一切都是索緒爾所說的言語,它不是我們的科學所能研究的。我們很難預示某人在某個特定時刻是否要講話,或者講什么,或者用什么詞和什么語言形式來講。我們的科學只能研究索緒爾所說的語言的特征,這些特征對于社團的全部講話人都是一樣的——音位,語法范疇,詞匯等等。”[8]192
法蘭西學派的代表人物梅耶接受了索緒爾的思想,對語言學的任務做了新的表述:“語言是個本身具有獨立自足性的系統,因此我們必須從純語言學的角度去發現語言發展的普遍條件:這和解剖學上的條件、生理和心理條件一起,構成普通語言學的對象。”[5]128
索緒爾認為,如果把言語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很難得出集體意識中的語言規則。“我們沒法把它歸入任何一個人文事實的范疇,因為不知道怎樣去理出它的統一體。”[1]30馬丁內(André Martinet)提出了一個與索緒爾的主張相對立的觀點:“就人類言語活動、為人類言語活動而研究言語活動。”[6]132他所說的“言語活動”同時包括索緒爾所說的“言語”和“語言”。他認為,“科學研究首要的要求就是不能因為方法上的苛求而犧牲研究對象的完整性”[7]185,不能為了維護一種原則或方法而拋棄語言學的某些方面。語言學家不能只是局限于語言結構系統內部研究語言事實,而應該以言語活動為研究對象,通過功能的分析,從言語中歸納出語言系統,通過“功能篩選”,確定語言事實。[5]141索緒爾認為語言學無法把握言語帶有的主觀隨意性,他主張語言學應把具有穩定性的語言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是言語。他認為,語言科學正是沒有言語活動等其它要素摻雜在里面,才能夠建立起來。
哥本哈根學派在繼承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語言理論和純理語言的形式分析方法。在語言學的對象問題上,他們不像以往的語言學那樣,以語言物理的、心理的、邏輯的方面,或者社會和歷史的方面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是主要以語言單位之間的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
倫敦學派的創始人J·R·弗斯(Firth JR)不贊成索緒爾關于“言語”和“語言”的區分,更不同意索緒爾把語言學的對象局限于語言而排除言語的做法。他的語言理論是一種語言的社會學研究。在他看來,語言研究的對象是實際使用的語言,語言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有意義的語言成分,以建立語言因素與非語言因素之間的對應關系,因為人類的生活經歷決定了語言意義的形式。[5]301
新倫敦學派的代表人物韓禮德繼承了歐洲功能主義語言學的傳統,從社會角度研究語言,把語言作為社會文化語境的有機組成部分。系統功能語言學家把語篇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不再是傳統語言學強調的詞匯層面或句子層面,從語篇與情景語境或文化語境的互動關系中揭示語言的性質。他們重視功能的研究,研究語言是怎樣被使用的,建立語言使用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探索語言功能和語言系統的關系。
在索緒爾看來,語言是由社會集團建立的,只有在這一點上它才是社會的。他在提出語言的社會性問題之后,集中精力談論形式語言學,談論語言“本身和為其本身”,致力于建立語言的抽象模式。……這樣做的結果,導致了他的理論在有力地克服了19世紀語言學過分強調歷時研究而忽略共時描寫的局限性,并極大地推動了語言共時描寫分析全面展開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制約了語言學的全面發展,影響了語言研究朝著深層解釋方向的發展。[5]123-124
五、索緒爾“語言學的對象”的指導價值
(一)“語言”這一概念的形而上學性質
在討論“語言學的對象”和定義“語言”時,索緒爾強調了“形式”的概念。索緒爾所謂的“形式”應該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和中世紀哲學曾經使用的形而上學概念。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形式、質料和具體事物都是實體,有時甚至只有形式才是實體。“形式是能動的、現實的,質料是被動的、潛在的,只有接受了形式,(質料)才能現實地存在。”[4]1030而F·培根也使用了這個概念,并給了它新的內容指出事物的規律或內部結構。當索緒爾在他的《教程》中討論并描述了“語言(langue)”的概念時,他指出“語言這個對象在具體性上比之言語毫不遜色”[1]37,“語言的實體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聯系起來才能存在的”[1]146,“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質”[1]169,證明“語言”的“langue”定義具有亞里士多德和F·培根所定義的“形式”概念的形而上學本質。他定義了“形而上學的語言”,即“langue”,并強調語言獨立于“詞語的物質材料”,“詞語單位”是“其特征,而非其物質品質”構成,并且“思想的表達不需要物質符號”,“物質單位依賴于其意義和功能”。就像意義和功能需要一些物質形式的支持一樣。[1]10關于索緒爾“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的定義,至少應該注意兩點:
1.索緒爾對“語言(langue)”的定義應該是他理想的并要建立的語言學研究對象。索緒爾“語言(langue)”概念的最直接目的應該是建立一個理想的語言科學。語言科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語言成分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語言成分本身。事實上,這是為了引起語言學界對語言系統內部形而上學方面的關注,并追求語言形而上的描述。
2.索緒爾語言學要研究的具體對象的明確。“語言(langue)”是“言語活動(langage)”事實混雜總體中一個十分確定的對象(除了個人、社會的言語活動之外),是“言語活動(langage)”中人們可以區分出來并加以研究的對象,即“言語活動(langage)”排除了其他要素剩下的部分,“語言(langue)”是同質的,而“言語活動(langage)”則是異質的。也就是說,“語言(langue)”不等于“言語(parole)”、“言語活動(langage)”。
(二)把語言當成獨立的對象來研究的符號學意義
語言從言語活動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人文事實,它既是一種社會制度,同時又與政治的、法律的其他制度不同。為了闡明語言的性質,就必須考慮一種新的事實,即對符號學的研究。索緒爾在《教程》中明確提出,語言學僅是寬泛的或廣義的符號學的一部分或一個分支。他預見了符號學的存在,并明確地闡述道,語言學由于與符號學相聯系,才能獲得科學的地位。但是符號學還不存在。作者進一步說明為什么符號學沒有像其他科學那樣成為具有自己研究目標的、獨立的學科。其中的推理是,語言是理解符號問題的最佳基礎,由于語言沒有得到科學的研究,所以符號學就自然受到阻礙。作者進一步強調了語言學和符號學相互依賴的關系及語言對符號研究的重要意義。
(三)對語言教學的影響和指導價值
由于對兩種語言學元話語關鍵詞“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的理解不一致,所以語言教學領域也存在同樣的混淆,其中之一就是語言教學應該教“語言(langue)”還是教“言語(parole)”還是語體先行問題的討論。而且,當代語言學界對于究竟哪些屬于“語言(langue)”,哪些屬于“言語(parole)”仍然存在很大爭議。我們認為,語言教學的關鍵問題是對“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的本質及其關系有一個新的認識。索緒爾《教程》中關于“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的區分對語言教學至少有如下指導價值:
1.我們可以進一步確定或分解語言教學的目標:何時應該關注形而上學的“語言(langue)”,何時應該關注形而下的“語言(langue)”即“言語(parole)”開展語言教育和教學。
2.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診斷語言教學中的一些問題,了解和判斷學生是否具有形而上或形而下的語言能力,然后有針對性地組織語言教學。
六、結語
索緒爾嚴格區分語言和言語,明確了語言研究的對象,立足于從語言內部結構研究語言學。他的語言學理論幾乎構成了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基礎,現代語言學發展的不同流派實際上都在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不同角度的闡釋或者創新。隨著語言學的發展,其研究對象問題在當今也值得重加思考。由此,本文對“語言學的對象”和范圍提出以下兩點,與學界探討:
(1)“語言學的對象是語言”可表述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語言”。
(2)語言學應該包括語言語言學和言語語言學。語言語言學即以“語言(langue)”為研究對象的科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普通語言學,而言語語言學即以“言語(parole)”為研究對象的科學。
[1] 費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2]周流溪.語言研究與語言教學[M].香港:華人出版社,2001.
[3] Saussure,F.de.[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4]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5] 王遠新.語言理論與語言學方法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
[6] 馮志偉.現代語言學流派[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
[7] 周紹珩,譯.語言學譯叢:第一輯[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8] 劉潤清.西方語言學流派[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
Questions and Guiding Value of Saussure's "Linguistics Objects"
YAN Jingyi
( School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Bijie 551700, Guizhou, China )
Saussure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linguistics objects" in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and discusses several viewpoints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concepts of "speech activity", "language" and "speech"; distinction among the three concept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which foresees semiotics, a science that has not yet been born, and puts forw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Different schools of modern linguistics have developed or debated around the "linguistics objects" from different angles. Saussure has defined the "linguistics objects" which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nguistics and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According to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and speech and the mutual relation should be re-recognized in language teaching so as to organize teaching in a targeted way.
Linguistics objects, Ferdinand de Saussure, speech activity, metaphysics, guiding value
2018-12-15
201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中國新發現瀕危語言蔡家話參考語法研究”(15XYY023)。
顏景懿(1988-),男,山東濟寧人,講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電影學。
H0-0
A
1673-9639 (2019) 01-0122-07
(責任編輯 印有家)(責任校對 郭玲珍)(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