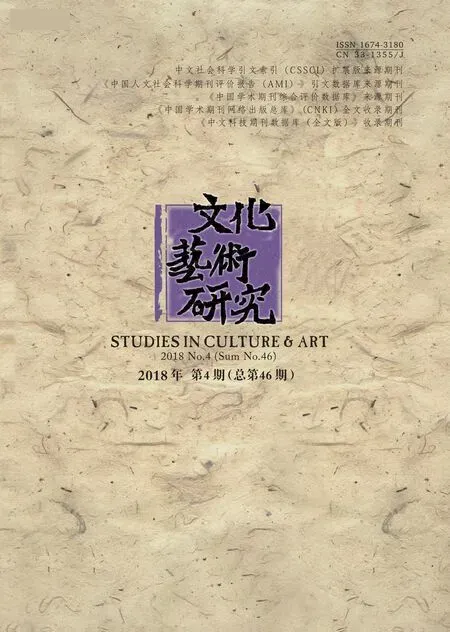清末上海學生演劇新論*
藍 凡
(上海大學 上海電影學院,上海 200072)
引 言
中國話劇是一種從外國移植來的新的舞臺表演形態,新劇和文明戲是對中國早期話劇的一種稱呼。學生演劇則是新劇的雛形,可稱為“學生新劇”。
學生演劇是指學校中的學生,為了教學課程和特定節慶所開展的一種演劇活動,早期對外作公演,一般是為了募捐賑災。
1907年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春柳社”,用華語演出翻譯劇《茶花女》和《黑奴吁天錄》之前,清末上海學生演劇,作為一種非演藝界的學生活動,對中國早期話劇的發生,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清末上海學生演劇,主要活動在外國人在中國辦的教會學校和國人自己創辦的新式學堂或學校中。
而學生的“演劇”,從舞臺表演的語言形態上講,基本上可分為兩類:用外國語(洋語)表演的學生演劇與用中國語(華語)表演的學生演劇,它導致了學生演劇在舞臺表演形態和性質上的不同。用外國語(洋語)表演的學生演劇,只發生在教會學校內,“學生新劇”——學生戲,則專指用中國語(華語)表演的學生演劇。
上海的學生演劇活動,最早起于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后來才在國人自辦的新式學堂或學校中展開。早期的上海學生演劇活動,僅朱雙云《新劇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徐半梅《話劇創始期回憶錄》和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等書刊文章有所記載,包括《申報》在內的新聞報刊都不見有任何報道,說明了學校的學生演劇活動并未社會化。至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前后,上海的學生演劇活動才漸趨活躍,尤其是隨著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和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文友會”與開明演劇會先后在上海成立,學生演劇活動開始走出校門,邁向了社會,才逐漸獲得社會的關注。特別是1907年后,中國留日學生大批返滬,從日本“新派劇”生發的舞臺表演新形態,一時風靡上海,成為了“學生演劇”向社會新劇的根本性轉折,上海的新劇(文明戲)運動開始繁盛。
一、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
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在晚清時期,用外國語表演的學生演劇——中國學生用外國語表演外文原劇,僅僅出現在滬上西方人所辦的教會學校中。
19世紀末,上海教會學校有圣約翰書院、徐匯公學、清心中學、中西書塾、格致書院等二十余所。作為語言教育,為了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和演說能力,經常組織學生在課堂教學中或節假日排演戲劇。這種學生演劇活動,實際上是學校課程教育的一部分,完全沒有演劇的社會性。
上海圣約翰書院的學生演劇活動,是西方人在中國所辦教會學校中,最早有演劇活動文獻記載出現的教會學校。
朱雙云在《新劇史》中說:“己亥冬十一月,上海基督教約翰書院剏始演劇,徐匯公學踵效之。”[1]45清光緒“己亥冬十一月”,即為公歷1899年12月24日的圣誕節。但據當時《北華捷報》的報道,至少從1896年7月開始,圣約翰書院就已經有了學生演劇活動。至1911年間,所搬演的劇目有《威尼斯商人》法庭判案一場,《愷撒大帝》廣場一場,《哈姆雷特》墓園一場,以及《馴悍記》和《仲夏夜之夢》等選段。[2]當然,極有可能,圣約翰書院的這種學生演劇,還要早于這一時間。不過從這些已見的報道和記載來看,這樣的學生演劇活動,帶有很大的特殊性——這是一種中國人用洋語演的洋戲,而且只限于校內和西方的宗教節假日,并不是社會性的演劇活動。
上海圣約翰書院a圣約翰書院,初由美國圣公會會長顏永京主持校務,1888年顏永京辭職,由湯森代理校務。繼由卜舫濟任校長。抗日戰爭期間及抗戰勝利后,先后由沈嗣良、涂羽卿任校長,學校行政由卜舫濟及其子卜其吉掌管。1906年正式成立大學后,設文理、神學、醫學三科。同年在美國立案,畢業生可直接升入美國大學研究院肄業,并取得學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根據1951年教育部頒行《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教會學校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指示》,圣約翰大學各個系分別合并入上海市的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第二醫學院、華東政法學院等有關高等學校。創建于1879年,是美國圣公會在中國設立的教會學校之一。由美國圣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將1865年設立的培雅書院和1866年設立的度恩書院兩院合并而成。1906年正式轉為圣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簡稱圣約翰、約大。地點在上海梵王渡。b梵王渡,現上海市萬航渡路靜安寺附近。教師多是美英傳教士。按照教會意圖,圣約翰為“高等學術機關,同時并為研究神學之中心”。初設國文、神學兩部,1880年和 1881年增設醫學部和英文部。分正科和預科。自1881年開始,學校所有課程包括校內生活,除了每星期僅一天的國學課用國語和上海方言授課外,全部使用英語。作為一所教會學校,直至1936年才開始招收女學生。上海圣約翰大學也是最早將西式教學風格引入中國的學校,除了極重視英語教學以外,也十分強調體育和課外活動。學校支持學生組織辯論會、演講會、體育會、科學會、繪畫會、攝影會、音樂會、青年會、同鄉會等各種社團組織,開展各種課外活動,學生演劇就是這種英語教學和課外活動的項目之一。c詳可參見徐以驊主編:《上海圣約翰大學(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圣約翰大學五十年史略出版委員會編:《圣約翰大學五十年史略(St. John's University,1879—1929)》,臺灣圣約翰大學同學會,1972年;熊月之、周武:《圣約翰大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而學生的演劇,全部是用英語演出的莎劇選段,就如朱雙云在《新劇史》中所說:“己亥冬十一月,約翰書院學生,于耶穌誕日,節取西哲之嘉言懿行,出之粉墨,為救主復活之紀念……然所演皆歐西故事。”[1]45可知,初期上海圣約翰書院學生演劇的特殊性在于:無論是夏季結業時的表演,還是圣誕晚會上的演劇,都是用英語演的英劇——用英語表演的莎士比亞戲劇選段,而且全部由男學生演出,屬課程教育和課外活動,不對外作公開演出,唯一的演劇活動時間是在西方的宗教習俗節假日——耶穌圣誕日舉辦,為學校的課程教育與教育實踐活動服務。
其后有同樣活動開展的教會學校是徐匯公學。“一時聞風踵效者,有土山灣之徐匯公學”[1]44,這里的“土山灣之徐匯公學”指的就是法國耶穌會教士在上海徐匯區建立的教會學校。d徐匯公學, 因奉耶穌會祖圣依納爵為主保,亦稱圣依納爵公學,清道光三十年(1850)由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南格祿創辦。吸收中國貧家子弟入學。徐匯公學使用耶穌會公學章程,學校專收男生,為寄宿制男子教會學校。民國以后,按中國新學制分為中學和小學,1930年增設高中部。1931年,教會向中國政府教育部門辦理立案,易名徐匯中學。校址在上海市漕溪北路徐鎮路。上海徐匯公學是比上海圣約翰書院建立更早的教會學校,以教授外語著稱,教員多為法國和意大利兩國的耶穌會神父,教育制度帶有法意色彩。教會學校設立的最大目的是為了傳教和培養神職人員。徐匯公學的外文學科分為法文、英文和拉丁文。法文開設最早,并且是必學語言。1859年開設拉丁文課,為有志于做神父的學生專設,被稱為“拉丁生”。至1904年才增設英文。徐匯公學初期僅設小學和中學,馬相伯入校僅十二歲,其弟馬建忠僅七歲。馬相伯與馬建忠,后來都是晚清學貫中西的文化名人。1891年,徐匯公學開設了“游藝演劇會”,增強了音樂和演劇等課外游戲娛樂活動。1900年還成立學校足球隊,以足球運動蜚聲上海。因在同等年齡段中找不到對手,只能年年與南洋公學作友誼賽,這為以后兩校的學生演劇交流創造了一定的條件。1904年,除了按學生年齡大小分成甲乙兩班外,還把教內生和教外生分為上院和中院。徐匯公學的學生演劇,也同樣是一種在中國的教會學校的學生,用外語來表演外國戲的活動。換句話說,學生在教會學校用外語(英語或法語)演西方人的戲劇原著,可以說是外國人在上海演外國戲的一種延伸,所以,徐半梅在《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記載道:“法國人在上海辦的天主教學校中,有一所徐匯公學。那學校中,在開招待學生家屬的懇親會的時候,常有演劇之舉。演的是操英語或法語的數出短劇,劇本相當有名,大半是他們平日上英語、法語課的課本,現在拿來實地登臺化裝表現罷了。觀眾除學生家屬外,還招待些教育界中人。那臺下觀劇的人雖并不能完全明白劇情,或聽得懂劇中人的對白;但學校中這樣公然提倡學生演劇,在當時很頑固的社會里,真是驚人的創舉。”[3]7雖然劇本由教員和學生自己選編和演出,但演出形式則與外國人演出——洋人演洋戲基本類同,而且一般都在校內演出,只招待家屬或者親友,所以朱雙云也說,這種學生演劇,“所操皆英法語言,茍非熟諳蟹行文字者,則相對茫然,莫名其妙也”[1]45。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圣約翰書院與徐匯公學的這種學生演劇,因為屬學校內的教育實踐,兩校相互之間并沒有任何交集。
在上海的教會學校,用中國語表演學生演劇——我們習稱“學生新劇”,最早有文獻記載的是上海圣約翰書院演出的《官場丑史》一劇,但這一記錄充滿了爭議。
現在普遍認為,上海圣約翰書院早在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耶穌圣誕日,就已經編演了《官場丑史》,是中國人自己第一個用中國話演出的“中國戲”——新劇,也是迄今為止有記載的上海學生演劇活動最早編演的戲劇作品。a陳白塵、董健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葛一虹主編的《中國話劇通史》,陳伯海、袁進的《上海近代文學史》,董每戡的《中國戲劇簡史》,董健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總目提要》以及《上海話劇志》等,均作如是觀。“文獻”的唯一依據是出于新劇藝人汪優游的自傳文章《我的俳優生活》一文:
有一年的冬季,同學們邀我到梵王渡圣約翰學校去參觀他們的慶祝耶穌圣誕節,聽說晚上還有學生扮演的新戲……我們吃了一餐晚飯,就擠到禮堂里去,在前排占了一個座位。
開幕演的好像是一出西洋戲。我因為聽不懂他們說些什么,沒有感到什么興趣。后來演的才是一出中國時裝戲。劇名有些模糊了,好像是《官場丑史》一類名稱。劇情卻記得很清楚……[4]313
《官場丑史》敘述一個目不識丁的土財主,到城中縉紳家拜壽,因排場闊綽,被弄得手足無措、洋相百出,鬧出許多笑話后,生發了“官迷”情結,納粟捐官,居然做了知縣。但他于官場禮節一竅不通,在判一奇案失敗后,被革職查辦,并當庭被剝袍服,受盡奚落。其實,這是一種用“三出舊戲湊合”成的、連汪優游自己都感到“劇名有些模糊了”的“中國時裝戲”。b但汪優游在《我的俳優生活》一文中,又說在后來“開明演劇會”的演出中,他將《官場丑史》改編成《官吏改良》演出:“我除了擔任幾出戲的配角以外,又把在圣約翰看見的《官場丑史》改名《官吏改良》,由我編成劇本,自任主角重演一次。此一出戲演得我非常得意,每一開口,就引得觀眾哈哈大笑。因此我的戲癮便中得更深了。”見參考文獻[4],第322頁。對于一所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以培養神職人員和教授英語為主的教會學校來說,讓其學生上演一出諷刺中國官場怪現狀的“時裝戲”,確實存在一定的悖論。
這是因為,其一,這一時期,圣約翰書院除了每星期僅一天的國學課用國語和上海方言授課外,無論是課內還是課外,全部只使用英語,所以不可能用國語演劇,更不可能還“編演”國語劇。其二,在耶穌圣誕節的慶祝活動上,一般而言,不可能出現如《官場丑史》這一類的華語劇,更何況,該劇情節顯然模仿了當時社會流行的黑幕譴責小說,與教會學校的圣誕節慶活動明顯相悖。其三,據當時目擊者汪優游的回憶,《官場丑史》的內容是根據中國的三出舊戲拼湊而成的,并且還模仿了舊劇《送親演禮》和昆曲《人獸關·演官》中的一些情節與噱頭,“這一場又是套的昆曲《人獸關》中的《演官》”,“這出戲雖是三出舊戲湊合成功的,里面的笑料卻是甚多”[4]314,對1899年的圣約翰書院來說,顯然也是不太現實的。作為以“研究神學之中心”的圣約翰書院,初期并不具備深諳舊劇和昆曲的師資力量。更何況,《送親演禮》一名《打牙巴骨》,是一出京劇鬧劇,梆子、徽劇都有此劇目。故事講述鄧九公之妻嫁女,因不諳婚時禮節,請儐相至家教習演禮。婚期,鄧妻至姻家,笑話百出,酒醉而歸。昆曲《人獸關》則是清初蘇州劇作家李玉的“一人永占”a“一人永占”,《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和《占花魁》的合稱。四個傳奇作品的一部,根據小說《警世通言》中的《桂員外途窮懺悔》改編,譴責桂員外的忘恩負義,與《中山狼》相近,但在舞臺上,流行程度不及《一捧雪》和《占花魁》。而其時,汪優游僅是一個欲報考中學的青年,在連“劇名有些模糊了”的情況下,其對戲的劇情也都可能懵懵懂懂,因此,在當時,他不可能對中國“舊戲”(京劇)了解非常清楚的情況下,這種言之鑿鑿的斷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有些學者認為,汪優游那天去圣約翰書院看到的學生演劇《官場丑史》,其實是1903年上海育材學校孔子圣誕日學生演劇的劇目b“事實上,育材此次演出才是汪優游首次看到的漢語學生劇活動,因為此前唯一一次漢語劇演出——南洋公學首演,校外人士不可能事先得知:鴻年和朱雙云都指出它是一次即興活動,‘知者絕鮮’。所以,汪優游發起民立中學演劇之前所看過的學生劇演出,僅有育材那一次。”詳見張軍:《子虛烏有的早期話劇開山之作:〈官場丑史〉——兼論以南洋公學為中心的上海初期學生劇活動》,《戲劇》2008年第3期。,但汪優游自己卻說,他這天去圣約翰書院看學生演劇,是“去參觀他們的慶祝耶穌圣誕節”,比起劇目的記憶,耶穌圣誕節與孔子圣誕日這兩者的區別更加不可能搞錯,所以無論《官場丑史》是否“子虛烏有”,還是汪優游看到的是育材學校的學生演劇,雖然至今仍是一樁公案,不過有一點是可以基本斷定的,在留日學生的春柳社公演《茶花女》之前,上海的教會學校圣約翰書院不可能已經有華語演劇。即使有史料記載,1906年12月27日圣約翰書院戲劇社參與過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為籌募會款而假座工部局議事廳演出新編戲《光緒四十二年之中國》之事[2],也僅說明了,作為教會學校的圣約翰書院的學生華語演劇,只是參與了華人辦新式學校的學生演劇活動,而且是在教會學校的校外進行的。
至于徐匯公學的學生演劇,因外語教育主要用的是法語和拉丁語,更不見有用中國話演外國翻譯劇或中國劇的任何文獻記載痕跡。
這說明了,至少在1907年前——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用華語公演《茶花女》和《黑奴吁天錄》之前,或王鐘聲在滬組織春陽社公演《黑奴吁天錄》之前,迄今為止,沒有發現上海教會學校的學生,用華語演劇的任何文獻,即使是課堂的演劇活動。c從《北華捷報》和鐘欣志的《清末上海圣約翰大學演劇活動及其對中國現代劇場的歷史意義》來看,上海圣約翰書院的莎劇演出,不管年代早晚,用的完全是英語,而鐘文認為,圣約翰書院“圣誕晚會上的中文創作”,除了因上海“大鬧會審公廨”案被迫取消的“中文戲劇社”的喜劇演出外,1907年12月24日在“同門廳”舉行的圣誕慶祝會上,戲劇社正館生演出的中文喜劇《怪新娘》(A Strange Bride)是最早有記錄的學生演出,“上半場洋人向縣官要人是十分當代的題材,也很有諷世的意味,下半場則可看到通俗文學常見的搶親情節”。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它至少表明了:在1907年上海新劇社會化之前,上海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活動,僅是為學校內的課程教育服務的,并非一種社會性的演劇活動,因此,作為外國語言教育,沒有必要用華語演劇。
另一方面,用外國語來表演翻譯成外文的中國劇,即將中國劇作或小說、故事,翻譯成外語演出,則更沒有這方面的任何文獻記錄,而且,由于教會學校辦學的目的和受師資力量的限制,用外國語上演翻譯成外文的中國劇,在晚清時期,完全沒有這種可能性。
由此可見,上海教會學校的這種學生演劇——用洋語演洋故事的演劇活動,并不是我們認可的“新劇”,a“中國之有大學生演劇,自圣約翰大學始”(見參考文獻[2]),正確地說,這種大學生演劇并非“新劇”的演出。所以鴻年在《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一文中說:“新劇發源之時代,蓋已二十余年。當圣約翰書院每年耶穌圣誕時,校中學生將泰西故事編演成劇,服式系用西裝,道白亦純操英語,年年舊規,習以為常。迨至今日,仍未廢止。是雖為一種新劇,而確與今日流行之新劇不同,不能指為文明新劇之鼻祖。”[2]28它至少表明了:上海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活動,是為學校內的課程教育服務的,并非一種社會性的演劇活動。所以非常清楚,中國人用外國語演外文原劇,并不是一種新的舞臺演劇形態——“文明新劇”。這是因為,上海教會學校的學生用洋語演洋戲,與外國僑民在上海用外語演外國戲,兩者的性質是一樣的。只不過前者用于學生的外國語教學,后者主要為了外國人自己的娛樂生活。
二、華人新辦學堂的學生演劇
開埠以后,隨著上海經濟的快速繁盛,由西方輸入的新教育思想和新教育方法,促生了一批華人自己創辦的新式學堂和學校。1900年前后,上海已經有了南洋公學、南洋中學、民立中學、愛國女學、經正女學等各種類型的新式學校。
教會學校的這種學生演劇之風,被華人新辦學堂的學生“聞風踵效”,逐漸推廣開來,上海的南洋公學、南洋中學、民立中學等,都出現了這種學生演劇活動。徐半梅在《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說:“這天主教學校中,每年總有這么一二次公開的演劇,招待校外人參觀,當然對于當時的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的。于是漸漸的使上海其它的學校,在開什么學藝會、游藝會、懇親會等的時候;也盛行拿演劇來助興了。”[3]8可見,用華語甚至地方方言表演的“學生新劇”,是繼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后,才在其他非教會學校中推廣開來的。
最早記載學生用華語演劇的是上海的南洋公學。

晚清時的上海南洋公學
朱雙云《新劇史》記載:“庚子冬十二月,上海南洋公學演劇一次。”庚子冬十二月為西歷1901年1月,“南洋公學中院二班諸生,亦聞風踵效,是年適丁拳亂,因年假余暇,私取六君子及義和團事,編成新劇,就課堂試演,草草登場,諸多簡陋,故知者絕鮮”[1]46。依朱雙云的說法,這種純粹的“課堂試演”,是由于受到圣約翰書院、徐匯公學的學生演劇影響,所以“南洋公學中院二班諸生,亦聞風踵效”[1]46,可以看作是對徐匯公學等教會學校學生演劇的“聞風踵效”的效仿,所以最后“草草登場,諸多簡陋,故知者絕鮮”[1]46。
上海南洋公學于光緒廿二年(1896)由盛宣懷創建于上海,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創辦的大學之一。因學堂地處南洋(當時稱江、浙、閩、廣等地為南洋),參考西方學堂經費“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為公學”,定名為南洋公學。學校地址設在徐家匯a今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與同設在土山灣的徐匯公學毗鄰,與設在梵王渡的圣約翰書院,也是一箭之遙,學生“聞風踵效”而嘗試演劇,是情有可能的。
但我們也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到,作為華人創辦的新式學校,南洋公學的這次學生演劇的劇目,有著強烈的反清民主傾向。朱雙云說:“越年年假,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上院諸生,聞風踵效,即就其禮堂演《六君子》及《義和團》二劇以資同樂。時劇本取材率尚時事,以是年之適丁庚子,故以義和團為題材。”[6]181參與這次演出的鴻年b鴻年,即羅鴻年,早年肄業南洋公學,學生演劇活動的主要骨干之一。后留學英國伯明翰大學。說得更為詳盡:
時為前清庚子年。是年年終考試早畢,而離放假之日有一星期,適中院二班生徒多戲迷者,乃就校舍中所懸粉板大書特書其向日所讀新聞報戲廣告之戲目。因之有人提議,不如即在校內演習,諸生均極贊成。即于是晚演六君子(《戊戌政變紀事》)。[5]228
朱雙云認為,演劇用“義和團為題材”,是恰逢庚子年,所以“劇本取材率尚時事”,而依照鴻年的說法,這類表現戊戌政變六君子的題材,是按照當時新聞報的戲目廣告“在校內演習”的,這表明了當時上海反清民主運動對南洋公學學生演劇的影響。查此時《新聞報》刊登的“時式新戲”廣告,丹桂茶園、天仙茶園、群仙茶園、天寶茶園等上演的《黨人碑》《瓜種蘭因》《中外通商》《鮑公十三功》《中外和約》《湘軍平逆傳》《捉拿客串》等,都是當時極受觀眾歡迎的新編各式新戲,而其中《捉拿客串》等演繹的正是“義和團”之事。
這一時期,上海實際上已成為革命黨人和知識分子的反清民主運動基地。南洋公學學生的這次用華語演劇活動,以義和團運動和戊戌政變六君子為題材,反映了上海學生演劇的發生與當時社會反清民主運動的密切聯系。學生演劇所表現出來的自由民主思想,可以看作是一年后發生的上海南洋公學退學風潮的事前反應之一。1902年10月,上海南洋公學因壓制學生言論自由,激起退學風潮,導致145名學生退學,以蔡元培為首的中國教育會,為此籌款在上海泥城橋(今西藏中路一帶)創辦愛國學社,接納退學學生。由蔡元培任總理,吳稚暉任學監,章炳麟、蔣維喬等當教員,實行學生自治,倡言革命。由此而培養了大批愛國的青年學生,許多更成為日后宣傳民主、倡導革命的骨干。
鴻年在《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中說:“中國式之新劇,如今日所演者,其發源之地,則為徐家匯之南洋公學。時為前清庚子年。”[5]228這里說的“中國式之新劇”,還不僅僅是舞臺形態上用華語演劇成為新劇之源,而與圣約翰書院等教會學校用外語演劇的區別,更在于國人創辦的新式學校中的這種“學生新劇”,從一開始就具備的革命性質。
而且,正是南洋公學的這種“學生新劇”,是裹挾在反清民主運動中開始的,所以很快就傳至非租界區域上海老城廂的新辦學校中。這其中,在南洋公學退學風潮中轉至其他華人創辦新式學校的演劇“積極分子”,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鴻年《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一文記載:“南洋公學二班生任家壁因事轉學至育材學校(即南洋中學),至翌年孔子圣誕日,任君發起演劇,因是素人演劇之風,遂日盛行。”又記載:“當時與南洋中學并立者厥惟民立中學校,校生亦皆選事者。聞鄰校演劇,不免見獵心喜,起而效尤,于孔子誕日舉行。該校運動家王蕙生、汪仲賢均為杰出演員,意亦天授也。”[5]228曾去南洋中學參加這次演劇的汪優游回憶說:“那天演的是兩出戲:一出是庚子聯軍占據北京城的故事;一出是江西教案,劇本比約翰稍有意識。”[4]315明確告知我們劇作對滿清政府的批判而顯現了“學生新劇”的鋒芒。
顯然,南洋中學和民立中學的學生演劇,可以說是上海學生華語演劇的濫觴,而具有了真正“學生新劇”的意義。
這是因為,上海南洋中學是上海最早由國人民間自辦的新式中學堂,初名育材書塾,1896年由松江秀野橋畔遷至上海城廂大東門內王氏家祠,1907年后才遷至龍華路日暉橋。上海民立中學則由祖籍福建的上海望族蘇氏兄弟于1903年創辦,秉承父輩“教育救國”和“為民而立”的辦學宗旨,屬民辦學校,校址設在上海的南市安仁里舊居。兩校的地點都在上海南市老城廂區內,而這一區域集中了這一時期大部分的上海戲曲演出場所——春仙茶園、天仙茶園、丹桂茶園等茶園式戲場。后來南市九畝地的戲曲改良重鎮“新舞臺”也設在附近。與南洋公學相比,兩校的演劇已經不是簡單地模仿報紙的戲目廣告,而是與附近茶園戲場的改良京戲發生了直接的聯系。
故而,一年后,上海南洋中學和上海民立中學舉辦的第一次學生合作演劇,成為了真正的“學生新劇”的標志。朱雙云《新劇史》記載:“甲辰秋七月,上海南洋中學及上海民立中學并演新劇。南洋民立二中學,每于孔子誕日,開會紀念。是歲則媵以自排新劇,代迎送神曲,演者觀者并興會飆發,為曠古未有之盛舉,然僅贈券懇親,無獵資者。”[1]48“甲辰秋”指的是清光緒三十年(1904)的初秋,演出的時間為孔子誕日,劇目為新編戲《科舉毒》和《林則徐》等。多年后,朱雙云再作《三十年前之學生演劇》一文道:“仲賢自觀劇于約翰書院以還,靡日不以相機演劇慫恿其同學。同學之好事者,都為之動,迭請于民立中學監院蘇穎杰師,卒得其可。乃于民國紀元前八年(公歷一九〇四年)之孔子誕日,演《科舉毒》《林則徐》諸劇于其課堂。”[6]181這樣的學生合作演劇,可以看作是打破校際之間封閉的演劇,展開了真正意義上的“學生新劇”的活動。
所謂真正意義上的“學生新劇”,因為“新編戲《科舉毒》和《林則徐》”,已經溢出了當時戲曲界的“時式新戲”的范圍,而完全是學校教師學生自己對“時事”進行的編創演出,“那時的編戲尚不懂得杜造故事,全是摭拾時事而成。共演三出戲,兩出都是教員編的:一為林則徐在廣東焚毀英商鴉片的故事,一為日本留學生監督的風流案件;我自己編的一出,乃根據日報所載”[4]315,其題材內容的反清民主傾向和強烈的針對性,明顯超出了當時“伶隱”汪笑儂演出的《黨人碑》和《瓜種蘭因》。
這種學生演劇活動的熱情,一時成為風氣后,逐漸被推向其他學校,依朱雙云的說法是:“自此以往,素人演劇之風日熾,二中學既習為常例,歲一舉行,更煽其余焰,傍及各界,一時募友立社,經營新劇者,皆其濫觴,幾成風雨。”[1]48
上海“文友會”的成立,就可以說是這種“幾成風雨”學生演劇的第一個高潮。“孔子圣誕每年只有一次。停三百六十日始過一次戲癮,實不足以滿足我戲迷的欲望。到了是年冬季,學校放了年假,身體得有空閑,便召集了幾個小朋友,發起一個空前的演戲團體,定名‘文友會’,預備在新年中過一次戲癮。”[4]316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冬,“文友會”由上海民立中學學生汪優游,聯合上海民立中學和其他學校的新劇愛好者組建而成。這是中國的第一個業余性質的新劇團體,也是中國晚清時期第一個由學生組建的業余演劇團體。所以汪優游說:“在專為演戲成立的團體,要算我們的‘文友會’創始第一個;并且那時學生演劇的風氣雖盛,但是脫離了學校,在外面組織劇團的,也要算‘文友會’第一個。”[4]316“文友會”的成立,標志了學生演劇開始走出校門,走上社會。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舊歷元宵節,“文友會”借用上海城內的晝錦牌坊陳氏私人宅院,舉行了首次公演。他們在院內搭了一個小戲臺,向外分送戲券,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等戲。“汪優游者,民立中學學生也。民立之演新劇,優游實聳成之。顧其愿猶未足,因藉年假余暇,創文友會于城東,節取時事之有裨社會、有益世道者,編纂新腳。越歲丙午元夜,假畫錦牌坊陳宅試演,觀者殊濟濟,實開今日各劇社之先聲,優游誠人杰哉。”[1]49
《捉拿安德海》講述清山東巡撫丁寶楨,在泰安縣捉拿慈禧總管大太監安德海的故事,汪優游說是演出根據《二十世紀大舞臺》雜志刊登的劇本,他自飾“總兵”,“‘文友會’演的三出戲:第一出是采用大舞臺雜志刊載的劇本《捉拿安德海》”[4]317。
《江西教案》系根據清同治年間江西民眾反對外國教會的斗爭史實編寫而成,揭露了法國傳教士在江西欺騙民眾,殘害婦女兒童的罪惡行徑。由上海育材學堂學生編劇并首演。文友會的公演,汪優游自飾劇中的糊涂知縣。“第二出是有一位曾經在育材學堂演過江西教案的朋友,他以為這出是他拿手好戲,竭力主張重演一次,要我扮演戲中的糊涂知縣,結果弄得一塌糊涂。”[4]317雖然《江西教案》“劇本沒有編好,弄得不能下臺,只好不了了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演的是當時的時事,且借機侮慢了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算是沾染了政治氣息”[7]。
兩出戲都強烈地表現了當時的反清民主思想。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12月,由朱雙云、汪優游等人發起組織的“開明演劇會”在上海成立,這是繼“文友會”之后,上海學生界演劇骨干的又一個聯合組織,也是繼“文友會”之后的學生演劇的又一個高潮。
“開明演劇會”的主要成員有汪優游、朱雙云、王幻身、瞿保年等。光緒三十三年(1907)二月,開明演劇會為給徐淮地區水災災民募捐,組織了一次大型義演。演出共五天,編演了六出“改良”新戲:反映清朝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政治改良戲,反映操練新兵的軍事改良戲,反映破除迷信的僧道改良戲,反映禁煙、禁賭的社會改良戲,誡勸盲婚的家庭改良戲和諷刺私塾的教育改良戲,統稱為“六大改良”劇。義演獲市民支持,紛紛慷慨解囊,捐助災民。至1908年,開明演劇會還演出過《新加官》《一劍憤》《訴哀鴻》《烈女傳》等劇。
“開明演劇會”雖然還是“假賑濟名義演劇”,“不算是專為演劇的團體”[4]324,仍然是學校的學生演劇性質,但在促使學生演劇的社會化——上海早期新劇的職業化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開明演劇會”已經不單是學生,教職員工也都參加了進來。a“會員不一定是學生,教員也有得參加的。當時上海著名體操教習張俊甫先生也高興地擔任登場表演。”見參考文獻[4],第321頁。其二是雖然還是打著“助賑”的名義,但“戲價每位四角,與當時戲園的正廳座價不相上下”,所以汪優游說:“‘開明演劇會’雖僻處城內出演,與上海話劇的發展卻影響甚大,由此造成了很多新戲迷。以后由客串而變成職業演員的上海人,大半是‘開明演劇會’的會員。”[4]322如朱雙云、周維新、王幻身等,前后都走上了職業新劇的道路。不僅如此,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為籌募會款,1906年12月27日假工部局議事廳演出新編戲《光緒四十二年之中國》,參與演出的許多是圣約翰大學的在校生。演出的《社會改良》《要求立憲》《內閣會議》和《陸軍會操》[8],與“開明演劇會”的“六大改良”劇極為相似,說明了這些劇目在學生演劇中的流行,連教會學校的學生都參與了進來。
“文友會”和“開明演劇會”的成立與演出活動,說明學生演劇已經走出校門,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從1906年開始,先后出現了上海滬學會演劇部、上海群眾學會演劇部、上海學生會演劇部、上海青年會演部和上海益友會等六七個學生演劇團體。此后,為了“藉劇籌賑”的學生演劇活動,“漸成市道”[1]51,如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冬十月,上海明德學校演劇籌款”;“是月a指1906年農歷十一月。,青年會組織演劇部”;“冬十二月,南翔鎮南翔小學演劇”[1]51;“美租界愛而琴路華童公學各學生因憫江北水災甚重,特于禮拜六(即本月初七日)在本校登場演劇,入場券每人銀洋五角,即以看資移助賑捐……”[8]“新馬路女子中西醫學堂經理張竹君女士及各女學生以淮徐海各屬水災頗重……女學生演劇……各學生不惜犧牲名譽賑救同胞,觀者無不感其誠而爭先捐助也”[10];“昨日,上海實業學堂及震旦學院學生假徐家匯李公祠合演中外古事,集捐賑濟淮海饑民”[11]; “日前,復旦公學及商部實業學堂學生曾假座李文公祠合演戲劇助賑水災,一時觀者無不同聲贊嘆”[12]等。依朱雙云的說法,“自此而降,學生演劇,幾成風尚。上海商會學堂、明德學校、基督教青年會、南翔鎮之南翔小學,均于是年之冬先后演出。是知今日話劇之所以炙手可熱者,非一朝一夕之功,其所由來漸矣”[6]。
可以這樣說,到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王鐘聲在上海成立“春陽社”后b“秋九月,王鐘聲來滬,立春陽社”,見參考文獻[1],第57頁。,次年在由日本歸國的任天知幫助下,合辦通鑒學校,招攬學員,以學校的名義排演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迦茵小傳》,再以“春陽社”的名義作社會公演,標志了清末上海的學生演劇,作為“新劇”的一個源頭,結束了其在早期新劇中的應有作用,而轉入其下一階段的存在。
三、清末上海學生戲的特征
清末上海學生演劇的“新劇”,亦被稱為“學生戲”,汪優游說:“此類表演,當時社會皆稱之為學生戲。”[4]319清末上海學生演劇活動中的這種“學生戲”——“學生新劇”,雖然前后時間不長,但卻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征。這就是:題材內容的激越性、表演風格的實用性、舞臺趣味的時尚性和演劇傳播的非社會性。
其一,題材內容的激越性。
清末上海的學生演劇,因從其發生起,就直接參與了當時的上海反清民主運動,因而其演劇在題材內容上,不但針對性強,而且表現得相當激越。鴻年在《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中說,第一次用華語演劇的南洋公學,上演的劇目,是根據小說《經國美談》c日本政治維新期間,在“新派劇”之前,對“歌舞伎”進行改良,推行“活歷史劇”運動,即將政治小說改編為戲劇搬上舞臺,《經國美談》就是根據矢野龍溪的小說改編。但目前沒有資料表明,南洋公學上演的《經國美談》,是否就是日本的“活歷史劇”《經國美談》。改編的,而且是由教員編寫,“適有一教員,將拳匪亂事始末編排成戲,囑諸生演習。諸生不敢重違教員之命,故均鼓舞精神,作第四次之演習”[5]228。如果說,早期學生演劇,包括日本留日學生演劇及后來的天津南開學生演劇,都有著“節取時事之有裨社會、有益世道者,編纂新劇”[1]49的傾向,那么,相比之下,清末上海學生演劇的針對性更強,態度更為激越,而且比當時汪笑儂等人的改良新戲“借助歷史,諷喻時弊”更為尖銳,將矛頭直指滿清政府,批判滿清政府的種種腐敗與反動。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上海南翔鎮南翔小學的學生演劇,“所演《黑龍江》新劇,慷慨激昂,全場多為感動”[1]52。而“文友會”的演出,“因為是空前盛舉,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我們那時受了《革命軍》(書名)的影響,腦中充滿了排滿思想,那出《捉拿安德海》的劇本,安德海第一個登場,在他的表白里就是許多侮辱慈禧太后的話。臺下有位老先生就奔到后臺來警告我們,勸我們不可演這種大逆不道的戲。我們當然不買他們的賬,反而滿奴滿賊地喊得格外清楚響亮些。”[4]317
正如汪優游回憶的,“在這年的暑假期中,上海發生了一個學生聯合會,假座寶善街春仙茶園開了一次游藝會……只記得演的是《沭陽女士》……表演時上海名伶小連生、汪笑儂、周鳳文、熊文通等都蒞場參觀。認為學生演戲頗有可觀。該劇情節曾被春仙茶園采用。以后上海戲園皆競演時事新戲,如《惠興女士》《黃勛伯》《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等等,造成一時風氣”[4]319。可見,清末上海學生演劇的這種反清民主的激越性,甚至直接影響了當時京劇界的戲曲改良運動。汪優游甚至這樣說,“開明會”去南京和無錫演出,因為上演的劇目問題,被懷疑成革命黨,最后被迫取消了演出。[4]325-327從這里也完全可以看出,上海學生演劇的強烈政治傾向和色彩,以及對當時上海反清民主運動的參與性。
唯其如此,徐半梅在《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所說的,學生演劇純粹是“幾個愛好戲劇的人,過過戲癮”[3]9,并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應該說,清末上海學生演劇帶有很強的政治訴求,是一批最早受到西方現代教育的“學子”,通過演劇的形式,來表達他們對晚清社會現狀的不滿和要求改良的迫切心情。而且,這種“學生戲”,已略見規模,是晚清社會動蕩和變革的直接反映。
其二,表演風格的實用性。
表演風格的實用性,指的是這種“學生戲”在表演上追求的是因地制宜和因陋就簡的“拿來主義”,只要能演戲——能表現題材內容的需要,一切為我所用。
其結果就是造成了在表演形態上的“不中不西”—— 表演上的混雜性,即有用“寫實”“對話”的方法表演,“這種穿時裝的戲劇,既無唱工,又無做工,不必下功夫練習,就能上臺去表演”[4]314;也大量存在“舊戲”(京劇)的程式表演,“戲臺設在一個大廳上,看客坐在天井里,臺上并無裝飾,只有兩個出將入相式的門簾。演員出場,仍用舊戲排場,念上場詩,通名字,都襲用舊戲形式;偶而也唱幾句皮黃”,“因為那時除了舊戲以外,并無別種戲劇可資仿效,自不能跳出舊劇的范圍”。[4]314用朱雙云的話來說,這種學生戲“鑼鼓之喧嘩”,并“不盡符于話劇體例”,而是“首以鑼鼓,雜諸話劇”。[6]182汪優游自己就認為:“‘開明會’……共演新戲十出……他們的戲名都取改良二字,如‘軍士改良’、‘官吏改良’、‘家庭改良’、‘教育改良’等等,隱然以改良風化自負。演出的方法,仍不能跳出舊劇的范圍,還是要去請教毛湘泉的場面來敲鑼打鼓。”[4]314徐半梅在《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也這樣認為,這種學生戲“可以說與京班戲院中所演的新戲,沒有什么兩樣;所差的,沒有鑼鼓,不用歌唱罷了。但也說不定內中有幾個會唱幾句皮簧的學生,在劇中加唱幾句搖板,弄得非驢非馬,也是常有的”[3]9。朱雙云甚至干脆將之稱為“新皮黃劇”。他說:“自紀元前五年,南洋公學創演新皮黃劇《冬青樹》(文天祥殉國事)后,流風所播。民立中學之《十族紅》(寫方孝孺抗不草詔事)、一社之《一劍憤》(詳后)、仁社之《小鏡子》(寫上海劉麗川反抗清廷事)、可社之《雙淚碑》(取材于當日時報所載之小說)、余時學會之《愛國精神》等(即以后上海新舞臺所演之二本《新茶花》),遂雜然并起矣。學生演劇之輒仿皮黃格調者,《冬青樹》實為厲階。”[6]188
這種有時甚至“用上海土白”表演的學生演戲活動,在戲劇的結構形態上,受到中國傳統戲曲的影響,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了戲曲的表演性——演員出場念上場詩,通報家門,偶爾夾唱幾句皮黃,臺上不設布景,只有出將入相的門簾,用分場方式,更以鑼鼓場面控制演出節奏,都是對上海當時非常流行的時式新戲(京劇)的一種“因陋就簡”的模仿和拼湊,因之被稱作“素人演劇”——一種非專業性的對“舊戲”的“為我所用”的模仿。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極具特殊性的、區別于“舊戲”的學生“新劇”。
其實,清末上海學生演劇的這種中西混雜性,是時勢所致,也是環境所致。譬如早期的學生演劇場所,一般都不是在茶園戲場,而是假課堂、私宅、會堂演出;穿自己的生活著裝登臺;向警察局借刀槍作道具,等等,為“學校”演劇的局限而表現出了充分的因地制宜和因陋就簡的舞臺形態實用性。a“文友會”的演出,“借會場是不要錢的,所用的男女服裝,也由會員到各處去借來;還到戲館里去借了幾件刀槍把子和假須等物。所費的只是布置會場之裝飾,和兩塊錢雇了一班鑼鼓,一共只花了十幾塊錢”。見參考文獻[4],第317頁。
朱雙云在《新劇史》中認為,清末上海學生演劇的這種用“舊劇”手法來演劇的做法,是因為非教會學校的師生不懂外語,只能“奉傳奇為圭臬”,用舊戲的手段來演新劇。b“猶憶《科舉毒》劇中之主角上場時曰:‘傴腰屈背假斯文,子曰詩云過一生。’其所以上場有詩,下(場)有對者,則以當時劇本,大抵出諸國文教員之手。國文教員頗多不嫻外國文字,既不能取異國,乃不得不奉傳奇為圭臬,時也,亦勢也。”見參考文獻[6],第182頁。但這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非教會學校,大部分都集中在上海的老城廂周圍,與主要演京劇的茶園式戲場毗鄰,因之而受到了當時甚為流行的、被稱為“文明新戲”“時式新戲”“時樣新戲”“應時新樣新戲”“海上奇聞新戲”“新式異樣新戲”“情節新戲”“奇巧新戲”“文武新戲”“連臺新戲”“燈彩新戲”等c詳見1900年至1906年的《新聞報》戲曲演出廣告詞。從1900年5月起,《申報》的戲目廣告中斷了四年半。改良京戲的很大影響和作用,因此而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地“拿來”為我所用。不僅如此,學生演劇的一些教職員工,平時本身就浸染于“舊戲”之中,如“開明會”成員之一的周維新,舊戲功底非常好,“因為他能唱孫調,能舞單刀”[4]322,儼然是個京劇孫派(孫菊仙)文武老生。“開明會”另一成員王幻身,是當時演劇的旦角臺柱,重要女性都由他扮演,后來加入“進化團”,仍為旦角臺柱。最后搭丹桂第一臺演舊戲,汪優游稱他為“新劇家搭舊戲班的第一人”[4]322。所以徐半梅要這么認為,學生戲的“戲劇的本身都是就近抄襲那京班戲院中所謂時裝新戲 ”[3]8。
當然,清末上海的這種學生戲,與當時京劇界的時式新戲并不是一回事,其最大區別在于,雖然學生演劇也唱皮黃,甚至“所演多《教子》《碰碑》等舊劇”[1]56,但畢竟是業余演出,學生和教師都不是專業的京劇演員,所以最多僅是“仿皮黃格調”,對專業的京劇表演而言,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依樣畫葫蘆”的“山寨”表演。這是因為,清末上海學生演劇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其政治訴求——學生介入晚清的反清民主運動的政治熱情的一種有意無意的行為表現,所以,對表演手法的借用是次要的,一切為了實用——能夠表達演劇訴求。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開明演劇會”與上海學生調查會聯合演劇于春仙劇園,這天上海戲曲改良的先驅,汪笑儂、潘月樵等都到場觀看,朱雙云在《新劇史》中記載,對學生演劇的題材內容和演劇激情,汪、潘都齊聲叫好,尤其是潘月樵,“潘尤傾倒”,并且說:“幸君等只諳表情,若略識皮黃,則吾輩將無瞰飯地。”[1]57言下之意,如果這些學生是京劇的專業演員,用這股激情演起革命戲,那他們自己倒要沒有演戲之地了。這也進一步證實了,清末上海學生演劇的“學生戲”,與清末上海京劇界的戲曲改良,在舊戲手法的運用上,完全不是一個性質的事,僅是一種“因陋就簡”的“拿”來所用。
但也正是這種“拿”來所用的學生戲,造成了清末上海學生演劇與留日學生演劇和南開學生演劇,在舞臺形態上的根本差異性。
其三,舞臺趣味的時尚性。
清末上海學生演劇,在表達政治訴求的同時,追求舞臺趣味的時尚性,這與當時上海流行的各式“時式”新戲,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這樣說,是學生戲對“時式”新戲的一種模仿。也就是“劇本取材率尚時事”[6]183。
雖然,因學生演劇的非職業性質,這種對“時式”的追求,還顯得比較稚嫩,但因學生戲的強烈政治性,求新和求變的舞臺趣味,就更容易得到社會的認可。譬如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冬,“文友會”在城內上演《捉拿安德海》,在劇名上,與當時茶園演戲的流行劇目,如桂仙茶園的《捉拿張桂卿》《捉拿小金子》《捉拿謠言大話》,丹桂茶園的《捉拿北京康八》《捉拿康九》《捉拿新臭蟲》和《捉拿客串》,群仙茶園的《捉拿吊膀子》,春仙茶園的《捉拿一枝蘭花》《捉拿自稱大好佬》等,名稱上完全類同,充滿了當時上海人喜歡的“新奇性”和招攬色彩,但這種“時式”捉拿,學生戲與“時式新戲”在劇目的內容上卻完全不同,《捉拿安德海》將矛頭直指滿清政府的腐敗,反映的是當時的反清民主思想,從而使得學生演劇的政治訴求,與時尚性的舞臺趣味黏合在了一起。
還值得一書的是,將當時上海本土的時尚“元素”和熱點,混雜進演劇之中,學生戲要比其時的“時式新戲”(時式京劇)還要有過之而不及。
學生演劇,不但借用舊劇,沿用“場面”a“場面”,戲曲里所用各種伴奏樂器的總稱。,甚至還將會唱上海本地小曲灘簧的非專業的一般小市民,也摻雜其間來打鼓,朱雙云就曾說:“有毛湘泉者,一箋扇店之店員,略諳‘灘簧’,因能打鼓,與會員汪君良諗,遂自薦焉。自之學生演劇幾非毛湘泉之‘場面’不可。”[6]183鴻年在《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一文中說:“其時有林瘦鶴者,善用小尺板唱小熱昏調,當開明學會演劇時,頗為觀者稱頌。有林步青等b似為“第”,但原文印刷為“等”。二之稱。”[5]232林步青、林瘦鶴等都是當時唱上海灘時興曲調“小熱昏”的藝人,學生演劇引入“灘簧”“小熱昏”等這種極其本土性的表演,不但“頗為觀者稱頌”,強化了“學生戲”的通俗性,充滿了“海上”風格,其對后來在上海流行的文明戲的“混雜”風格的風行,有著直接的關聯。早期學生戲甚至“用上海土白”表演c“不過中國人辦的學校中的演戲,往往不是學校當局所主張,而是學生們自己發動,要求學校當局讓他們參加,作為余興的。所演的戲,并不象那天主教學校用外國語,而是用上海土白的。”見參考文獻[3],第8頁。,它對若干年后中國影戲(早期電影)的表演和上海方言話劇的生成與時興,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其四,演劇傳播的非社會性。
演劇傳播的非社會性,是清末上海學生戲在自身生態上的一個重要特征。
清末上海學生演劇——上海華人辦新式學校的這種學生戲活動,基本上是學生的自發業余活動,與留日學生的演劇不同,與早期教會學校規定的作為教學用的外語演戲,也并不相同。其主要是募捐賑災,并且僅在“課堂”上表演,并不對外作社會性的公演。換句話說,這種學生戲基本上仍屬“學校”內娛樂活動,僅贈票給相關人員,“文友會”的演出,“戲券都是分送給人的”[4]317。并不賣票,“南洋民立二中學,每于孔子誕日,開會紀念。是歲則媵以自排新劇,代迎代迎送神曲,演者觀者并興會飆發,目為曠古未有之盛舉,然僅贈券懇親,無獵資者”[1]48。所以朱雙云在《初期職業話劇史料》又說:“中國之有話劇……創始者為上海約翰書院。風氣一開,于是徐匯公學、南洋公學、民立中學、南洋中學等各學校,紛紛繼起。但這一時期的話劇,只限于學校方面。”[13]有時候甚至還“謝絕參觀”,所以“外間絕鮮知者”。[1]57這可以說是清末上海學生演劇與留日學生演劇在演劇傳播和對外影響上的一個重大區別。
可以這樣說,清末上海學生戲是一種非職業、非專業的演出行為,即“素人演劇”,“素人演劇之風,當時不過學生逢場作戲,且必孔子誕日,或開游藝會時,乃一演之”[5]229,是一種學校內的教學性、節慶性和自娛性的藝術活動,其對外的購票看戲,基本上都是以賑災籌款的名義進行,而與其后新劇運動的專業性演出不同。這也造成了,學生演劇上演的劇目,不管是創作還是翻譯或改譯,都不見有劇目文本,即使是“幕表”文本,也不曾見有任何“留存”,正如鴻年在《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所記載的:“當時并無后臺化裝之室,更無預定腳本,即今日新劇所謂幕表者。”a即使在當時出版的最經典的幾本新劇類著述中,如朱雙云的《新劇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范石渠的《新劇考》和鄭正秋的《新劇考證百出》,也都不見有任何學生演劇的劇目文本。[5]228這也從“文學”角度表明了,在“學生戲”沒有社會化之前,它的“過渡”性質。
1907年前后,隨著“學生戲”后來的逐漸社會化,出現了為籌款而籌款的現象,演劇的傳播也出現了與“學生戲”相悖的情況。
譬如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冬十月,上海明德學校演劇籌款”,為了解決學校經費不足,“乃集該校職員,組織劇部”,由學校教職員工直接參與,所演劇目為京劇《化子拾金》,致使“售券之數頓減”,觀看人數大減,被批評為“徒沾沾于聲調,無裨益于風化”。[1]51《化子拾金》又名《拾黃金》,演繹乞丐范陶在街頭拾得黃金一錠,欣喜之余,載歌載舞。川劇、徽劇、湘劇、秦腔、河北梆子等地方戲均有此劇目。《化子拾金》沒有情節,也無固定演法,插科打諢,與當時流行的《戲迷傳》《十八扯》《丑表功》《瞎子逛燈》等,都屬戲中串戲,或作墊戲之用。上海明德學校為籌款而演此劇,被批評為“無裨益于風化”,說明了上海學生演劇后期,已經出現了當時上海茶園演戲“只為票房”的商業風氣。
清末上海學生演劇的特征,是與當時上海時式京劇相比較而言,也是與留日學生演劇和南開學生演劇相比較而言。顯然,清末上海學生戲的這種特征,是新式學校學生的屬性所致,也是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清末上海學生戲的這種特殊性,既說明了其在中國早期話劇發生和發展中的影響與作用,也表明了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后,上海學生演劇的這種特征在新劇的社會化中,有了延續的發展,在新劇的“甲寅中興”、愛美劇運動、左翼戲劇運動和抗戰戲劇運動中,都發揮了相應的作用。
結 語
中國的早期話劇——新劇,發端于晚清時期的學生演劇活動——“學生新劇”。
清末的學生演劇包括上海學生演劇、中國留日學生演劇和稍后的天津南開學生演劇,這是三種不同的舞臺演劇形態。換句話說,清末上海學生演劇活動中的這種“學生新劇”,俗稱“學生戲”,與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上演的、受日本“新派劇”影響的“學生新劇”,以及其后的天津南開演劇的“學生新劇”,可以說是三種并不完全相同類型的“新劇”。
清末上海的學生演劇,分為兩種:一種是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另一種是華人創辦的新式學校的學生演劇。
在時間上,發生最早的是上海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用外語演外語原劇。這種用外國語上演的外國劇,主要是作為學校的外語課程教育和課外活動,沒有演劇的社會性,與更早在上海出現的外國人演外國劇一樣,并非中國早期話劇——“新劇”意義上的學生演劇。
另一方面,至少在1907年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春柳社”,用華語演出改編劇《茶花女》和《黑奴吁天錄》之前,上海教會學校中并沒有學生用華語演劇的任何記載。
其后上海華人創辦的新式學校的學生演劇——被稱為“學生戲”的華語演劇,即中國學生用華語演自己編創或改編的華語劇,才可算是中國早期新劇的一種。
鴻年在《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中說:“中國式之新劇,如今日所演者,其發源之地,則為徐家匯之南洋公學。時為前清庚子年。”[5]228清末上海學生演劇是20世紀初發生在中國的一種特殊的演劇現象——“中國式之新劇”。作為新的演劇形態,學生演劇的生成基礎和屬性具有特殊性:這種編演的學生華語劇,呈現出明顯的題材內容激越性、表演風格實用性、舞臺趣味時尚性和演劇傳播的非社會性的特征。
“一九〇七年以前之上海學生演劇,雖未盡脫舊劇桎梏,然究為話劇型類。”[6]188但它又不完全是如留日學生演劇和稍后的南開學生演劇那樣的“話劇型類”。其題材內容上強烈鮮明的反清民主傾向和舞臺形態上極其特別的中西混雜呈現,構成了清末上海學生戲與留日學生演劇、南開學生演劇的最大差別。換句話說,清末上海的學生演劇,在劇目故事上,有著強烈的政治訴求,是當時反清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舞臺形態上,這種以人物對白為基礎的舞臺敘事藝術,既沒有“舊戲”嚴格的程式規范,穿時裝表演,顯出了與中國傳統“舊戲”表演形態上的異樣,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舊戲的舞臺形式,帶有不小的歌舞性和程式性的演劇體系成分,是對西劇和“舊戲”的一種不中不西和亦中亦西的“融合”,一種“西體仿用”和“中體西用”的雙重模仿和改良,表明了清末上海“學生戲”在戲劇觀念和形式上的“過渡性”——“新劇”社會化的準備和預演。

學生演劇示意圖
西方在上海租界內的特殊演劇活動和西方在中國設立的教會學校的特殊戲劇教學,在這兩大背景下發生的學生演劇活動,將中國的“舊戲”作為一種重要的參照對象,形成了一種“亦中亦西”的演劇新形態,從而成為中國話劇自發性的參照對象之一。但它與晚清戲曲改良運動中的改良新戲或時裝新戲,并不是一回事。晚清的戲曲改良運動,從內容到形式對“舊戲”的改良,其結果不可能衍化成一種完全依賴對白敘事的舞臺表演新形態,因為與西方的話劇相比較,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演劇體制,雖然改良新戲或時裝新戲當時也被稱作“新劇”或“文明戲”。
正如歐陽予倩所說:“最初上海的學校劇盡管說是受了教會學校神甫牧師們所介紹的宗教劇的影響,但是從那些戲的編排來看他們并不懂得分幕的方法,他們還是依照章回小說那樣,把一個戲分成若干回——其實就是場。”[14]98“分場”是當時京劇——舊戲最基本的戲曲結構形式,由此可見當時上海學校的學生演戲,在敘事結構上參照了傳統戲曲的舞臺結構形式,即使早期新劇(文明戲),也是“先學習了我們戲曲的編制方法,又接受了從日本間接傳來的歐洲話劇的分幕方法(前面說過春柳有所不同,它是先學會了分幕分場的編劇方法,回國以后又受了戲曲傳統的影響的)”[14]98。這里的早期新劇(文明戲),顯然就是在國內從學生演劇開始自身生發的一種演劇新形態,而與用歐洲話劇分幕方法來演劇的“春柳”不盡相同。
唯其如此,由于受到外國人演劇、教會學校學生演劇,特別是當時“時式京戲”的影響和作用,清末上海的這種學生演劇,對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后發生在上海的社會化的新劇(文明戲)運動,產生了非常復雜和多元的影響。我們今天將1907年留日學生演劇定為中國話劇的開端,是用一種完全西方話劇演劇體系作為衡量標準的結果。a至于這種在模仿和拼湊上海改良新戲基礎上的上海學生戲——“素人演劇”,由于帶有很濃重的“程式化”舞臺表演風格,在完全沒有外力的作用下,如1907年后“春柳系”和“天知戲”新派劇的影響,是否能自身轉化為以對白敘事為主的西方式舞臺表演藝術——話劇,留待另文與文明新戲一并加以討論。所以歐陽予倩說:“辛亥革命以前的學校演劇,還不具備話劇的雛型,就是春陽社所演的《黑奴吁天錄》,據看過的人所說既不象新戲又不象舊戲。”[14]49
清末上海的學生演劇活動,對中國早期話劇的影響和作用,主要發生在1907年之前。b1907年之后,隨著社會化的新劇(文明戲)運動的興起,上海學生戲在“屬性”上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4月13日至5月11日,上海南洋公學和徐匯公學假座李公祠,聯合演出古裝新劇《冬青引》,可以看作是中國學生演劇上演歷史劇的先聲;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通鑒學校在上海春仙茶園演出根據英國同名小說改編的《迦茵小傳》,可以看作是中國學生演劇演出根據小說改編舞臺劇的先聲;1912年5月,南洋大學學生假座新舞臺、大舞臺,上演了新劇《雙編針》《榴花血》,可以看作是中國學生演劇在戲曲新式劇場上演新劇的先聲;1913年1月7日至2月5日,上海城東女學在寒假期間舉行的游藝會上,演出了翻譯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而改稱《女律師》的新劇;同年6月2日,中國青年會演出了翻譯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而改稱《一磅人肉》的新劇,可以看作學生戲演翻譯劇的濫觴。
朱雙云說:“維時海上諸園,正競演新劇,春仙之《瓜種蘭因》,天仙之《鐵公雞》,丹桂之《查潘斗勝》,尤聲聞洋溢,為時盛稱,影響所及,遂至于此。”[6]182清末上海學生戲活動的一個重要意義正在于,晚清由改良派人士,包括梁啟超等人發起的改良戲曲創作,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革命,率先被上海華人創辦的新式學校的學生演劇所突破:走出了舊有的雜劇和傳奇的“案頭創作”而邁上了表演的舞臺,它與稍后的京劇界的戲曲改良運動糾纏交叉在一起,開啟了舞臺表演意義上的“戲界革命”,而與“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一起,成為晚清反清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