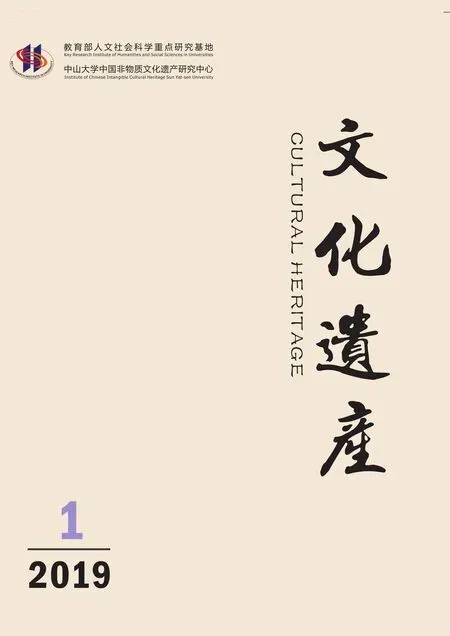趙琦美生平履歷考論
——紀念趙琦美抄校本古今雜劇發現80周年*
徐子方
趙琦美(1563-1624)又名開美,字玄度,又字如白,號仲朗,又號清常道人。幼聰好學,博聞強記,志在兼濟,藏書著述多所成就。著有《洪武圣政記》《偽吳雜記》《脈望館藏書目》等。校勘刊刻有《新唐書糾繆》《仲景全書》《周髀算經》《東坡先生志林》《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前集》《松石齋文集》《東坡雜著》《陳眉公雜錄》等。然科試無望,以蔭庇出仕,聲名不顯,生平資料闕如。2018年5月,乃趙琦美抄校本古今雜劇重現于滬上80周年,欲就所見,作一探考,以就正于學界朋友。
一、早年家居(1563-1599)
趙琦美嘉靖四十二年生于江蘇常熟。*趙琦美出生年月無確鑿記載,然據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六“墓表一”《刑部郎中趙君墓表》:“君以病沒于長安之邸舍,天啟四年之正月十八日也。” 天啟為明熹宗朱由校的年號,“天啟四年”乃1624年,由此上推,則琦美生于1563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具體時日,據《暨陽章卿趙氏宗譜》所記為六月二十五日,然譜系近人所撰,時間過晚,且前無其他資料支持,姑系于此。祖父趙承謙(1487-1568),字德光,號益齋,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授贛州府推官,擢南京吏部主事,官至廣東布政參議,著有《盛唐名家詩》。父為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趙用賢,著有《松石齋集》《趙用賢書目》等。兄弟三人,琦美為長,二弟祖美,國子監生,錢謙益《趙用賢墓志銘》稱其“倜儻有父風”,然祖美并未如父兄做官,而是將機會讓給了兒子。其父趙用賢故后,祖美子士履得蔭為中書舍人。三弟隆美(1581-1641),字文度,號季昌, 明熹宗天啟二年以蔭入仕,任職太常寺典簿,歷官至敘州知府,著有《趙敘州集》2卷。琦美另有姐妹七人,名不詳。
和一般士大夫子弟一樣,琦美幼年當在學讀書,為將來學而優則仕做準備。無名氏《太常續考》卷七一《太常寺·題名記·典簿》載:“趙琦美,直隸常熟人,官生。”*佚名:《太常續考》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99冊,第296頁。此處“官生”即國子監生,乃明清蔭監之一。但國子監生僅是一種身份象征,不必親到監讀書。趙用賢松石齋書房中萬冊藏書,為趙琦美幼年誦讀提供了先天優厚條件。他本人也注意購買喜愛的書,當時的蘇州為天下人文薈萃之地,也是琦美常去的地方。萬歷十六年,琦美26歲,他在蘇州地攤上以銖金購買了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十卷。與此同時,他還愛上了校書和刻書。萬歷十七年端陽后二日,琦美校五代杜光庭《錄異記》一書,并有跋:
……萬歷己丑端陽后二日,發故簏,偶見此書跋語,撫卷慨然。為校正二十一字。 趙清常記。[注]趙琦美:《錄異記跋》,杜光庭《錄異記》書后,《續修四庫全書》第1264冊,第509頁。
“萬歷己丑”即萬歷十七年,琦美27歲。稱“發故簏,偶見此書”,應是舊藏,但不見于其父《趙定宇書目》,可知也是趙琦美購置。
刻書方面,年輕的趙琦美也在積極參與并有所成就。萬歷二十三年(1595),校刻《東坡先生志林》五卷,其父趙用賢作序:
《東坡先生志林》五卷,……余友湯君云孫,博學好古,其文詞甚類長公,曾手錄是編,刻未盡而病卒。余子琦美因拾其遺,復梓而卒其業,且為校定訛謬,得數百言。庶幾湯君之志不孤,而坡翁之在當時,其趦趄于世途,鞿縛于窮愁者,亦可略見云。萬歷乙未海虞趙用賢撰。[注]趙用賢:《松石齋文集》,《刻東坡先生志林小敘》,《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41冊,第104頁。
很顯然,蘇軾此書在當時士大夫中頗受重視。趙用賢贊其“坡翁之在當時,其趦趄于世途,鞿縛于窮愁者,亦可略見”,似乎引為同調。《明史》本傳稱“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只為黨爭所陷,屢起屢蹶,對“趦趄于世途”之體會應較他人為深。對于此書,琦美父執湯云孫也曾花了一番功夫,將其全部抄錄,準備刊刻,然“未盡而病卒”,可謂赍志而歿。琦美繼其業,“拾其遺,復梓而卒其業,且為校定訛謬”,終于使得父輩的意愿得以實現。
是年,常熟及周邊地區癘疫大起,趙家亦多人患疾,幸得名醫沈南昉救治,未罹重大災難。目睹這一切的趙琦美對醫道救人感觸很深,在已致仕在家的趙用賢支持下,校刻出版有“醫圣”之稱的東漢醫學家張仲景《傷寒論》。趙琦美有序記其事:
歲乙未,吾邑疫癘大作,予家臧獲率六七就枕席。吾吳和緩明卿沈君南昉在海虞,藉其力而起死亡殆徧,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不知沈君操何術而若斯之神,因詢之。君曰:“予豈探龍藏秘典,剖青囊奧旨而神斯也哉?特于仲景之《傷寒論》窺一斑兩斑耳!”予曰:“吾聞是書于家大夫之日久矣,而書肆間絕不可得。”君曰:“予誠有之。”予讀而知其為成無己所解之書也。然而魚亥不可正,句讀不可離矣。已而購得數本,字為之正,句為之離,補其脫略,訂其舛錯。沈君曰:“是可謂完書,仲景之忠臣也。”予謝不敏。先大夫命之:“爾其板行,斯以惠厥同胞。”不肖孤曰:“唯唯。”沈君曰:“《金匱要略》,仲景治雜癥之秘也,盍并刻之,以見古人攻擊補瀉緩急調停之心法。”先大夫曰:“小子識之。”不肖孤曰:“敬哉。”既合刻,則名何從?先大夫曰:“可哉。”命之名《仲景全書》。既刻已,復得宋版《傷寒論》焉。[注]趙琦美:《刻仲景全書序》,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9頁。
文中稱校刻前原書“魚亥不可正,句讀不可離”,自己“字為之正,句為之離,補其脫略,訂其舛錯”,可見其工程量巨大。如果不是“先大夫”父親以“惠厥同胞”之使命感督促,琦美幾乎不可能承擔。而且事實上該書自校勘到刊刻花了四年功夫,直到萬歷二十八年三月方始完工。琦美在《序》的最后將醫人與醫國聯系起來,對父親的官場遭遇和日漸涼薄的世道人心發出這樣的感喟:“先大夫故嘗以奏疏醫父子之倫,醫朋黨之漸,醫東南之民瘼,以直言敢諫醫諂諛者之膏肓,故躓之日多,達之日少。而是書之刻也,其先大夫宣公之志歟!今先大夫歿垂四年而書成。先大夫處江湖退憂之心與居廟堂進憂之心同一無窮矣。”
要言之,早年家居時的這些讀書、校書和刻書經歷,為趙琦美一生成長無疑奠定了良好的的學識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獨立思考外,通過購書、校書和刻書,還可以發現青年趙琦美與眾不同的地方,這就是熱衷于雜學而對儒家正統的疏離。《錄異記》是中國古代神仙集,包含《鬼谷先生》等百余篇。前述琦美購置《酉陽雜俎》亦屬唐代小說。至于《東坡先生志林》,《四庫全書總目》以為“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后人裒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 同樣不脫筆記小說的范圍。由此可知,琦美年輕時即喜愛讀書和校書,而書的內容則多為神話小說,而與正統經義無關,這同樣極大地影響了他畢生思想及價值取向。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盡管當時的文壇領袖錢謙益稱贊琦美“天性穎發,博聞強記,落筆數千言”[注]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六“墓表一”《刑部郎中趙君墓表》,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36-1538頁。,卻無資料表明其通過科舉獲得功名,這只能說明趙琦美的知識結構與官方倡導并作為科舉考試內容的儒學正統存在著較大距離。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其父趙用賢官場地位的蔭庇,趙琦美很可能一輩子就是一個白衣秀士。
二、南京為官(1599-1610)
萬歷二十四年(1596),發生了導致趙琦美發生人生重大轉折的事件。這一年,父親趙用賢逝世。前已述及,用賢雖官至正三品吏部左侍郎,但過于剛直,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終陷朋黨爭斗,受政敵陷害,加之已絕姻親吳某乘隙誣告,遂移疾歸里,憂憤以死。有司依例撫恤,可以蔭子做官,琦美身為用賢長子,乃第一個受惠者,任職正八品的南京都察院照磨。當然,他也并非本年即前往履任。按禮制,他得在家服喪,三年終制,至萬歷二十七年方正式赴南京,就此踏上仕進之途。[注]參見金昱杉《趙琦美生平考》,《人文天下》2017 年 8 月刊。
明代南京為兩都之一,同樣設置政府六部,但管轄范圍僅限于周邊地區。趙琦美任南京都察院照磨。都察院由前代的御史臺發展而來,主掌監察、彈劾及建議。不僅可以對審判機關進行監督,還擁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斷”的權利,為最高監察機關。照磨,即“照刷磨勘”之簡稱,掌管磨勘和審計工作,事務原本繁巨,惟南京官制原本是個閑職,有的是時間,適合他喜愛讀書、校書和刻書的個性。也正因此,在南京11年中,沒有資料顯示他干了什么磨勘和審計的大事,倒是留下了校書和刻書的印記。
萬歷三十年(1602)四月,刻蘇軾《仇池筆記》成,并作序記其事:
《筆記》于《志林》表里書也,先大夫既已序《志林》而刻之矣。茲于曾公《類說》中復得此兩卷,其與《志林》并見者得三十六則。去其文而存其題,庶無復辭,亦不廢若原書,此余刻筆記意也。竊謂長公,才具七斗,游戲翰墨,皆成文章,故片紙只字,無非斷圭折璧,才既高而節復峻,此足以起忮矣。況復呶呶不勝其?睨一世則側目而揶揄之者,固將甘心焉。而相公廝壞殆以柄國者為鱉矣,士固可殺不可辱也。議新法未必傷柄人之心,然此等語不足以徹髓耶!夫荊公固士也,學雖僻而奈何辱之哉?烏臺之獄,豈盡人尤也乎。刻筆記。萬歷壬寅孟夏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注](宋)蘇軾:《仇池筆記》卷首,涵芬樓影印本。
由序文可以得知,趙琦美校刻此書,乃由于其與此前家居時和父親合作刊刻的《東坡志林》相表里,可互為參見。序文的更大價值還在于顯示出作者并非單純的刻書者,亦非單純的校勘者,而是對書中內容有過深入研究的思想者。比如作者雖然欽佩蘇東坡“才具七斗,游戲翰墨皆成文章”,承認王安石“學僻”,但對書中歪曲甚至詆毀王安石的文字則大不以為然,在引用古語“士固可殺不可辱”后直言:“荊公固士也,學雖僻而奈何辱之哉?”甚至聯系起歷史上蘇東坡的“烏臺詩案”冤獄,認為其被貶遭禍也有自己的原因:“烏臺之獄豈盡人尤也乎?”話雖說得很重,但也多少反映了趙琦美的真實思考。
萬歷三十三年(1605),琦美43歲,在官場結識浙江嘉禾(今嘉興)項群玉,得后者提供《酉陽雜俎》的數條軼文,頗為感奮。[注]趙琦美:《酉陽雜俎序》:“歲乙巳,嘉禾項群玉氏復以數條見示,又所未備也,復為續之。”按:“乙巳”即萬歷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前已述及,琦美在萬歷十六年于蘇州書攤購得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十卷,“喜甚,便攜之歸。開窗拂幾,較三、四過,其間錯誤,如數則合為一則者,輒分之;脫者,輒補之;魚亥者,就正之。不可勝屈指矣。”今得此數條增補,更覺錦上添花。次年,因公干赴京,居燕山龍驤邸。又得《洛陽伽藍記》舊刻本,續校并最終完成之。是書校勘前后歷經八載,至此方完成。琦美跋云:
丙午,又得舊刻本,校于燕山龍驤邸中,復改正五十余字。凡歷八載,始為完書。[注](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第57頁。
“丙午”即萬歷三十四年(1606)。文中“校于燕山龍驤邸中”一語曾引發爭議。孫楷第據以認為趙琦美此年已離開南京赴北京任職,其實這只是趙琦美的一次臨時出行。“燕山龍驤邸”并非琦美在京時官邸,而是都察院為赴京公干之官員安排的臨時旅邸,當然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為其父趙用賢生前任京官時所購置之住所遺存。原因非別,就在此后二年,琦美《酉陽雜俎》跋中自署頭銜仍為“迪功郎,南京都察院照磨所照磨”。文不長,引錄如下:
丁未,官留臺侍御內鄉李公,有士安、袁凱之癖,與美同好,自美案頭見之,欣然欲刻焉。美曰:“子不語怪,而《雜俎》所記多怪事,奈何先生廣《齊諧》也?”先生曰:“否,否!禹鑄九鼎而神奸別,周公序《山海經》而奇邪著,使人不逢不若焉。噫!世有頗行涼德者。”侍御既以章疏為鼎、為經以別之矣,乃茲刻又大著怪事而廣之。豈謂有若《尸穸》《諾皋》所記,存之于心,未見之于行事者,又章奏所不及攻而人所不及避也。藉此以誅其心,僇其意,使暗者、昧者皆趨朗日,不至煩白簡矣。是亦息人心奇瑰之一端云。迪功郎南京都察院照磨所照磨海虞趙琦美撰。
文中“丁未”即萬歷三十五年(1607),琦美45歲。與琦美同在南京都察院任職的侍御史李某,極力促成《酉陽雜俎》的刊刻。二人關于“子不語怪”的對話,實際上也道出了琦美自己的內心矛盾。都察院“以章疏為鼎、為經以別之”,本為王道,亦臺面上事,而“《雜俎》所記多怪事”,刊刻此書等于“廣《齊諧》”,難免有不務正業之嫌。這位李御史以“禹鑄九鼎而神奸別”和“周公序《山海經》而奇邪著”皆為王道解之,事實上也解開了趙琦美長期以來橫亙胸中的一塊心結。校勘刻印《酉陽雜俎》之類志怪筆記小說,“大著怪事而廣之”,能“藉此以誅其心,僇其意,使暗者、昧者皆趨朗日,不至煩白”,有何不可!
萬歷三十六年(1608),琦美46歲,仍在南京都察院任職。8月中,自友人孫唐卿處借得《文房四譜》錄校,至九月十三日甫畢。清人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五“文房四譜”條引該書琦美跋語云:
《文房四譜》四卷,戊申八月中,友人孫唐卿氏自家山來,奚囊中持此書,因借錄,并校其訛者無慮數十。續檢得《徐騎省集》中有是書之序,不知何年失去,今錄于前,可謂洛浦之遺矣。萬歷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海虞清常道人書于柏臺公署。[注](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屠友祥校注,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315頁。
“柏臺”即御史臺之別稱。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前代所設御史臺為都察院,琦美時任職南京都察院照磨,故云。《文房四譜》為宋代蘇易簡撰,共五卷,分為《筆譜》《紙譜》《墨譜》《硯譜》,是記載歷代筆、墨、紙、硯原委本末及其故實。書前有徐鉉序文,而琦美自友人孫唐卿處所借該書徐序缺損,賴徐鉉《徐騎省集》補之,是為全璧。校訂該書是目前所知趙琦美在南京任職期間進行的最后一項工作。
值得提出的是,琦美在南京任職期間也并非都是在做“不務正業”的事,也較好地履行了本職工作。據錢謙益《刑部郎中趙君墓表》記載:
(琦美)官南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廨,費約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將作營造式也。”[注](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六“墓表一”《刑部郎中趙君墓表》,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第1537頁。
都察院照磨掌管磨勘和審計工作,能夠做到“費約而工倍”,證明趙琦美并非只憑父親余蔭當官的貴介子弟,而是有其才干的能吏,但這種工作業績并不多見。由于陪都機構的備份性質,加之官職卑微,對于趙琦美來說,除了有時間讀書、校書和刻書外,能夠施展才華的機會實在少之又少。
三、任職京師(1610-1619)
錢謙益《刑部郎中趙君墓表》記載琦美所任第二個官職是太常寺典簿。《明史·職官志》:“太常,掌祭祀禮樂之事,總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于禮部。”至于典簿,屬太常寺典簿廳,時設典簿二人,正七品,主要從事掌奏文書的起稿校注。這個職位較之正八品的南京都察院照磨,品級上高了兩極,職責上似乎也更與文稿整理相關,對于非科舉出身的趙琦美來說,無論如何這都是官場人生的一件好事。
關于琦美入京任職的時間,學術界有不同看法。前已述及,孫楷第根據趙琦美《洛陽伽藍記跋》認為在萬歷三十四年,后來又據趙氏《文房四譜》跋作進一步推論:
丙午乃萬歷三十四年(1606),是時趙琦美已在北京。據謙益琦美墓表,琦美由南京都察院炤磨升太常寺典薄,則是時殆官太常寺也。三十六年在北京,為都察院都事。四十二年(1614)至四十五年(1617)在北京,為太仆寺丞。又文房四譜跋(《蕘圃藏書題識》卷五《文房四譜》條引)稱“戊申八月,友人孫唐卿(唐卿名允伽)自家山來,借錄此書,校其偽者。復從徐騎省集中錄出是書之序。”末署“萬歷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海虞清常道人書于柏臺公館。”柏臺乃御史臺別稱,則是時琦美已由太常寺典薄轉都察院都事也。[注]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年,第5頁。
萬歷三十四年,趙氏校書“燕山龍驤邸中”,“燕山”此處指代北京,“龍驤”即龍驤衛,琦美在京時寓所于此。孫氏據以推知其時琦美已在北京,似乎合乎情理,也不違背邏輯。然若就此認為趙琦美于萬歷三十四年已由南京都察院轉任北京太常寺則誤。證明這一點也容易,前述琦美于萬歷二十五年所撰《酉陽雜俎序》自署“迪功郎南京都察院照磨所照磨海虞趙琦美撰”,清楚表明其實仍在南京任職。如果說這還是孤證的話,今查《四庫全書·史部·職官類·官制之屬》所收《太常續考》卷七《太常寺·題名記·典簿》,即發現另有明確記載:
趙琦美,直隸常熟人,官生,萬歷三十八年任。
這就非常清楚地說明,趙琦美之任太常寺典簿,是在萬歷三十八年(1610)。《太常續考》八卷(江蘇巡撫采進本),不著撰人名氏。《四庫提要》謂該書“明崇禎時太常寺官屬所輯也。”“總括一代之掌故,則體貴簡要;專錄一官之職守,則義取博賅,言各有當,故詳略迥不同也。”書中所記應較可靠。琦美無科舉功名,本不可能做官,當時的身份是官生,其入太常寺任職時間由此可以確定。
明確了琦美赴京任職太常寺之年份,另一條史料仍需辨析。這就是琦美《故宮遺錄序》中的一段話:
故宮遺錄者,錄元之故宮也。洪武元年滅元,命大臣毀元氏宮殿,廬陵工部郎蕭洵實從事焉。因而記錄成帙。有松陵吳節為之序,予于萬歷三十六年間得于吳門書攤上。字畫故暗不可句,因為校錄一過,三十八年庚戌于金陵得張浙門墨本。為校正數十字,置之箓中。[注]佚名、蕭洵:《北平考·故宮遺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2頁。
文中除了交待《故宮遺錄》這部書的來龍去脈之外,還提供了兩條信息,一是在萬歷三十六年,琦美在南京任職期間曾回常熟老家探望,路過蘇州時還逛書攤買書;一是在萬歷三十八年,琦美仍在南京,購得《故宮遺錄》的張浙門墨寫抄本。前者猶可,無非豐富了趙琦美南京為官期間的經歷。后者則直接關系到琦美何時赴京任職的時間。有人也許會問,既然琦美在萬歷三十八年仍在南京,又如何能在同時任職于北京呢?其實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因為此二條史料均未注明月份,既然真實性均無問題,只能說明分別發生在上半年和下半年,二者之間并不矛盾。況且即使已在京師任職,也不能排除回常熟老家探望路過南京逗留之可能,畢竟11年在此為官,同事朋友肯定不會少。所有這些,皆不能作為質疑琦美于萬歷三十八年已入京供職之理由。
京師任職在趙琦美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時期,可以說決定他在藏書和校刻文化史上地位的幾件大事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首先當然是抄校內府本古今雜劇。萬歷四十年(1612)五月十四日,抄校于小谷本《女學士明講春秋》雜劇,是為趙琦美抄校古今雜劇之始。這一年,是趙琦美入京任職后的第二年,他50歲。今存趙氏抄校本古今雜劇《女學士明講春秋》劇末載有趙琦美跋:
于小谷本錄校。此必村學究之筆也。無足取,可去。四十年五月十四日,清常道人。[注]趙氏抄校本古今雜劇跋語俱附于《古本戲曲叢刊》第四集所收諸劇之后,此不一一注出,下同。
值得指出的是,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注意到此條,卻謂:“四十年疑誤”[注]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第104頁。,未說明理由。依筆者分析,當時由于本年只校此一本,別無其它,加之次年也無繼續抄校之記錄。以故孫先生認定趙氏抄校古今雜劇應自萬歷四十二年開始。然這樣推論主觀性太強,趙琦美抄校內府本和于小谷本雜劇,本人并非內廷人員,亦非收藏者,須打點關系或進行溝通方可落實,安能如自己藏書一樣方便。何況這兩年琦美還有其他更急迫的事要干,如編創《容臺小草》詩集,校刻出版《朝鮮史略》《皇佑新樂圖記》等書。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一下子全力投入抄校古今雜劇也是極有可能的事。故在沒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不宜輕易否定趙琦美跋文中的時間題署。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否定趙琦美自萬歷四十二年開始系統抄校古今雜劇的事實。這一年,琦美共抄校了《立功勛慶賞端陽》《望江亭中秋切膾旦》《看財奴買冤家債主》3本雜劇。次年,亦即萬歷四十三年,琦美一發不可收,抄校了息機子刊本《包待制智賺生金閣》和內府本《馬丹陽三度任風子》等67種雜劇。萬歷四十四年(1616),高峰已過,所抄校內府本《楚昭公疏者下船》《趙匡胤打董達》等7種。第四年是萬歷四十五年(1617),為有記錄的抄校古今雜劇的最后一年,當年校錄于小谷本《南極星度脫海棠仙》雜劇等18種。所有這些,當然都是根據明署抄校時間確定,另有大部分所藏古今雜劇沒有明確記載抄校時間,按照孫楷第的看法,都應該穿插在這幾年。所以可以肯定地說,趙琦美抄校古今雜劇,是這幾年頭等重要的大事。
除了抄校古今雜劇以外,任職京師的趙琦美所做比較重要的事應是《容臺小草》和《栢臺草》兩部詩集的創作編定。“容臺”,行禮之臺,亦為禮部之別稱。趙琦美官太常寺,太常屬禮部,故亦稱容臺。前面說過,萬歷三十八年趙琦美由南京都察院轉北京太常寺典簿。官品雖由八品升了一級,但太常典簿本冷官,枯寂無聊,遂和元人倪瓚《江南春》詞,陸續成六十闋,三年后完成,輯為《容臺小草》。該書今存浙江圖書館藏清五桂樓主人黃澄量所輯類書《今文類體》。[注]《今文類體》全書138冊,仿黃宗羲《明文海》體例分17類裝訂成冊,保存400多家原明刻本文集奏議,以明人編纂,故名今文,學術界亦作《明文類體》。琦美自序云:
癸丑,餉旋百逋交萃不保,先人之廬矣。舉頭今昔,乃迸跡于遺老莊吟,所謂《江南春》者,意未止于此。更續廿十葉,聊解窮愁,豈自多哉。”[注](明)趙琦美:《容臺小草》第11頁,明刻本,黃澄量《今文類體》纂輯。
“癸丑”乃萬歷四十一年,《容臺小草》結集于此年。琦美自萬歷三十八年調任太常寺典簿,冷官枯寂,開始寫詩打發時光。《容臺小草》為趙琦美留存于世的主要詩集,內容系和元人倪瓚《江南春》組詩,內容連貫,均為江南之美,首句以“筍”字開頭,末句以“營”字結尾,一韻到底。六十闕詞,六十種筍,無重復焉。
《栢臺草》為趙琦美的另一部詩集,今并存于浙江圖書館所藏清五桂樓主人黃澄量所輯類書《今文類體》,內容同為和倪瓚《江南春》,在三續《容臺小草》的基礎上續增四十闋,為四續和五續,實際上是《容臺小草》的續書。[注]參見童正倫:《滄海有遺珠——〈明文類體〉考釋》, 載《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3年第4期;金昱杉:《趙琦美著〈容臺小草〉的發現》,載《人文天下》2017年4月刊,總第94期。其所以另取書名,純粹由于創作地所由太常寺轉都察院之緣故。“栢臺”即柏臺,原指御史臺,明改都察院。琦美任太常寺典簿四年后,至萬歷四十二年又改都察院都事,品級相同,屬平調,但新職類似打雜,事冗繁劇。《栢臺草》自序這樣慨嘆:
容臺多暇,六日而吟成三續。秋間改栢臺,閱半歲,始得四續。
《江南春》原為唐人杜牧所作的一首七言絕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名聞遐邇。北宋寇準創為詞調,三十字,三平韻,中云:“江南春盡離腸斷,滿汀洲人未歸。”元代文人畫家倪瓚又以此題創作了七言詩三首,詩情及體式均較前人有所拓展。弘治十一年,倪詩原件收藏人許國用將其傳入吳中文士雅集,傳誦一時,唱和者云集,包括沈周、文征明、祝允明、唐寅、楊循吉、徐禎卿等江南名流。此后正德間,吳中又連續舉辦多次《江南春》詩的追和活動,并引發吳門諸畫家以《江南春》為題進行繪畫創作,成為明清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據今人統計,追和詞作竟達74家116首。[注]葉曄:《明詞中的次韻宋元名家詞現象——以蘇軾、崔與之、倪瓚詞的接受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嘉靖間有人將《江南春》追和之作編訂成集,萬歷間狀元朱之蕃又有所增補。而追和活動一直延至清光緒年間,金武祥所編《江南春詞集》乃集大成者。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與《江南春》詩的追和活動相關的人和事,皆與趙琦美無關。個中原因當然比較復雜,這里暫不擬深究。但可肯定絕非趙氏身份低微,詩作平庸,難入編選者法眼,因目前所存《江南春詞集》中百余首和詩,作者出身寒微不在少數,詩作大半平庸,即使名流亦莫能外。[注]可參見張仲謀:《論 〈江南春〉 唱和的體式及其文化意味》,《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趙琦美《容臺小草》追和倪瓚詩達60首,《栢臺草》40首,一共100首。總數超過明清諸版《江南春詞集》所收和詩全部,即使加上今人增補,總數也相距不遠。僅就數量而言,在倪作《江南春》的追和傳播史上也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
琦美京師任職期間還有一件關乎個人命運的重要活動,這就是面對后金頻頻入侵,明軍在東北迭遭敗績的形勢下,匹馬出關考察,歸后上書建言:

“神宗之末年”即萬歷四十七年(1619),這一年,琦美由正七品的都察院都事升轉正六品的太仆寺丞,這次升職大大激發了他的用世之心。明制,太仆寺掌牧馬之政令,以聽于兵部,即與軍事有關。琦美利用解馬公干的機會,獨自出山海關,周覽形勝要塞,遍訪當事,歸后則上書建言,冀于國事有所禆補。然由于人微言輕,不被重視,一腔熱血被澆了一盆冷水,強烈的挫敗之感使得他心灰意冷,失望至極,遂擲去烏紗,使事歸里。由此結束了將近十年的京師任職時期。
四、家居與客死任所(1619-1624)
離開京師后,趙琦美并未返回江蘇常熟的故里,而是去了浙江武康。這似乎匪夷所思,但卻是事實。武康是趙琦美晚年居住的別業。這方面直接資料仍舊來自錢謙益,他和趙琦美關系很近。眾所周知,琦美歿后,包括抄校本古今雜劇在內的全部藏書盡歸謙益所有,彼亦系趙氏抄校本古今雜劇的收藏者之一。錢謙益在應趙氏后人之請為趙琦美撰寫的墓表中有過這樣的敘述:
(琦美)默然不自得。以使事歸里,用久次,再遷刑部郎中。裴徊久之,過余而嘆曰:“已矣!世不復知我,而我亦無所用于世矣。生平好兵家之言,思以用世;好神仙之術,思以度世。今且老而無所成矣。武康之山,老屋數間,庋書數千卷,吾將老焉。子有事于宋以后四史,愿以生平所藏,供筆削之役。書成而與寓目焉,死不恨矣。”[注](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六“墓表一”《刑部郎中趙君墓表》,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第1536頁。
前已述及,趙琦美用世之心甚切,曾匹馬出關,考察形勢,上書建言,冀于國事有所禆補。然由于人微言輕,不被重視,失望之余,產生了歸鄉終老的念頭。這并不奇怪,明末政治混亂,君暗臣僻,上下閉塞,建言被輕視乃在意料之中。值得注意的倒是這段文字透露出琦美除了常熟祖宅之外的一處別業,位于“武康山中”。武康在今浙江湖州,屬德清縣管轄,距常熟一百七十多公里。由此可知琦美所居非止一處。“用久次”“老屋數間”表明琦美在此居住時間之長,“庋書數千卷”表明是其最終藏書所在。《墓表》不僅敘及錢、趙二人的密切關系,且在最后明確交代墓表是應逝者后人之請而作:
君生為貴公子,而布衣惡食,無綺紈膏粱之色。少年才氣橫騖,落落不可羈勒。而遇旅人羈客,煦嫗有恩禮。精強有心計,時致千金,緣手散去,盡損先人之田產,不以屑意也。尤深信佛氏法,所至以貝葉經自隨。正襟危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二。歸葬于武康之塋。而君之子某狀君之生平,屬余為傳。
《墓表》談到了趙琦美的平生秉性,及晚年篤信佛法的事實。于情于理,錢謙益此文內容的真實性無需懷疑。
武康作為趙琦美的終老及歸葬之地,在資料來源上并非孤證。清人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九收入琦美抄校元人張光弼詩集的跋語,中云:
元《張光弼詩集》二卷,……今見《丈園漫錄》,惜為刪去五十二章,惟存四十八章,錄作一家,亦備一代之遺事云。時天啟二年壬戌,書于武源山中。連陰雨二十日矣,尚未有晴意,恐復作元年連綿四五月也。清常道人書。[注](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屠友祥校注,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315頁。
天啟二年(1622),上距琦美“使事歸里”已有三年。文中可知琦美這一年在錄校元人張昱(字光弼)的詩集。地點為武源山中,今知“武源山中”,即武康山中。武康,有武康鎮武源街,“武康”“武源”一也。武康臨近太湖,水氣氤氳,山中多陰雨,琦美記載當時連陰雨二十日,又追記去年連綿四五月的陰雨天氣,可知其這幾年的確一直在此居住。也許正因為此處對于琦美晚年生活有特殊意義,至清初錢曾撰作《讀書敏求記》時竟出了靈異的色彩:
清常歿,書盡歸牧翁,武康山中,白晝鬼哭。[注](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楊衒之洛陽迦藍記”條,王云五主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排印本,第61頁。
鬼哭之事自然無稽,惟作者強調“清常歿,書盡歸牧翁”和“武康山中”值得注意,除了明確趙琦美藏書最終去向之外,還有一點同樣毫無疑問,在錢曾的心目中,死后葬于武康山中的趙琦美,獲知自己一生辛苦聚集起來的藏書,由于子孫不能保守而轉歸他人,遂致悲傷痛哭。《讀書敏求記》作于錢曾的晚年,上距趙琦美、錢謙益等當事人的故世已數十年,趙氏族人對錢謙益所撰墓表中關于琦美晚年別業和葬地的描述未有不同意見,由此更從側面證實了墓表本身的真實性和武康之于趙琦美一生行蹤的真實性和重要性。
但是,頗具悲劇意味的是,琦美并未能在武康老屋終老。就在錄校《張光弼詩集》的當年,他又接到擔任刑部貴州司郎中的朝命,雖然新職為正五品,較之此前擔任的正六品太仆寺丞又高了兩級,但心灰意冷、潛心佛法的趙琦美對仕途已失去了任何興趣,他“裴徊久之”,對心目中的至交錢謙益傾吐了自己懷才不遇的苦悶:“已矣!世不復知我,而我亦無所用于世矣。” 雖然朝命難違,他還是于當年八月奉命返京履職,但這種矛盾和苦悶極大地損害了他的身心。不到半年,琦美死于任所。錢謙益《刑部郎中趙君墓表》記得很明白:
明年,其家以訃音來,君以病沒于長安之邸舍,天啟四年之正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二。歸葬于武康之塋。
至此,趙琦美的生命終于劃上了句號,但有關他的悲劇并沒有結束。因舊絕姻家某氏作梗,死后的趙琦美遺骨幾不得還鄉。時人董其昌追記友人許微時提到有關琦美的一件事:
時趙玄度以秋官郎入都,公與握手道故,不勝感慨。未幾,玄度客死,姻家為難,旅梓幾不得還。公揮淚經紀喪事,復竭蹙御侮,歸其骨。[注](明)董其昌:《容臺文集》卷之八《封簡討少微許公墓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1冊,第494頁。
文中沒有指明對死后趙琦美尚且不放過的所謂姻家姓名,但大體可以推知是趙家已絕親家吳之彥,當年趙用賢有女許吳之子鎮。后因用賢得罪了權臣張居正,“之彥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撫福建。過里門,不為用賢禮,且坐鎮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怒,已察知其受居正黨王篆指,遂反幣告絕。”[注](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二九《趙用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001頁。從此結下仇隙。按道理已時過境遷,趙用賢已故多年,吳家不應該對趙家后代趕盡殺絕,但明代黨爭就是這樣殘酷,以致泯滅人性。幸虧友人許少微仗義幫忙,琦美方得魂歸故鄉,葬武康之塋。
綜觀趙琦美一生,自幼聰明穎悟,嗜書好學,博聞廣記,長成后熱心用世,志在兼濟,但由于生逢末造,科考不得意,懷才不遇,志不得舒,終于抑郁以死。在人生是一個悲劇,但他畢生勤奮好學,藏書、讀書、校書和刻書不斷,始終不渝,在藏書和文化傳播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一點尤值得我們今天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