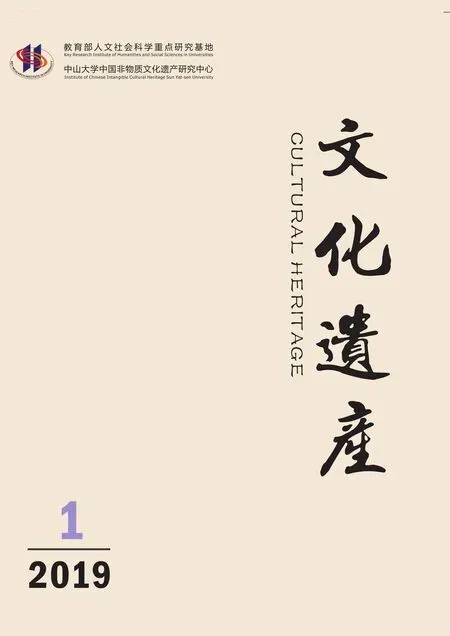論《山海經(jīng)》的色彩系統(tǒng)
李 牧
一、《山海經(jīng)》中被忽略的色彩
歷代學(xué)者對(duì)于《山海經(jīng)》的研究大體可分為兩部分:一是著眼于文字及文意考釋,二是探討有關(guān)“山海經(jīng)圖”的各類問(wèn)題*參見(jiàn)陳連山:《〈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一般而言,大多數(shù)學(xué)者肯定《山海經(jīng)》中《海經(jīng)》及《大荒經(jīng)》古本先圖后文、圖文并茂的特質(zhì)*除個(gè)別研究者如汪俊認(rèn)為《山海經(jīng)》無(wú)“古圖”外,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同《山海經(jīng)》古已有圖。參見(jiàn)汪俊:《〈山海經(jīng)〉無(wú)“古圖”說(shuō)》,《徐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2年第3期。,而認(rèn)為《山經(jīng)》并無(wú)“古圖”*參見(jiàn)陳連山:《〈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史考論》;劉宗迪:《失落的天書(shū)——〈山海經(jīng)〉》與古代華夏世界觀》,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6年。。劉宗迪在其《失落的天書(shū)——〈山海經(jīng)〉》與古代華夏世界觀》的附錄《〈山海經(jīng)〉》古本流變考》中指出,《山海經(jīng)》乃是由原先獨(dú)立成書(shū)及流傳,且內(nèi)容性質(zhì)與寫(xiě)作目的各異的《山經(jīng)》(或稱《山志》)與《海經(jīng)》(含《大荒經(jīng)》諸篇)合并而成。具體而言,《山經(jīng)》或可視為寫(xiě)實(shí)著作,而《海經(jīng)》則多基于先民想象。筆者大體同意學(xué)界此觀點(diǎn),但是,筆者以為,《山經(jīng)》所描述的山川地貌及動(dòng)植物,亦是時(shí)人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或想象世界的視覺(jué)反應(yīng),具有明顯的圖像性質(zhì)和細(xì)節(jié)。因此,本文中所謂“山海經(jīng)圖”包括實(shí)際存在過(guò)的“古圖”及非物質(zhì)性的主觀視覺(jué)呈現(xiàn)。另外,雖然劉宗迪對(duì)于《山海經(jīng)》古本源流的考證切實(shí)可信,但是,由于《山海經(jīng)》各部分之間成書(shū)目的和寫(xiě)作性質(zhì)的明顯不同,劉著未對(duì)古人將二者結(jié)集的內(nèi)在邏輯清晰呈現(xiàn)。筆者此文的初衷之一便是尋覓《山海經(jīng)》各部分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
一直以來(lái),學(xué)者們常試圖將“文”與“圖”兩方面綜合考察。郭璞在注釋《山海經(jīng)》之外又作《山海經(jīng)圖贊》,便可視為學(xué)界綜合考察《山海經(jīng)》的起點(diǎn)。但從目前研究看,學(xué)者在文字及文意考釋方面成果斐然,而關(guān)于圖像的研究則略顯單薄,大抵是由于圖像資料缺乏所造成的。《山海經(jīng)》文字所本之“古圖”*如所謂的“畏獸圖”或“禹鼎圖”。,以及中古張僧繇及舒雅所繪“山海經(jīng)圖”已經(jīng)散佚,而現(xiàn)今留存的明清時(shí)期的“山海經(jīng)圖”及其日本版本《怪奇鳥(niǎo)獸圖卷》,因?yàn)槟甏斫虿荒苷宫F(xiàn)《山海經(jīng)》的原初樣態(tài)。近年來(lái),在馬昌儀等學(xué)者的推動(dòng)下,學(xué)界日益重視“山海經(jīng)圖”的研究,關(guān)注圖像的流變、性質(zhì)、創(chuàng)作過(guò)程、“文圖關(guān)系”,特別是探尋今圖與“古圖”的外部區(qū)別和內(nèi)在聯(lián)系[注]參見(jiàn)馬昌儀:《山海經(jīng)圖:中國(guó)古文化珍品》,《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山海經(jīng)圖:尋找〈山海經(jīng)〉》的另一半》,《文學(xué)遺產(chǎn)》2000年第6期;《明刻山海經(jīng)圖探析》,《文藝研究》2001年第3期;《古本山海經(jīng)圖說(shuō)》,濟(jì)南:山東畫(huà)報(bào)出版社2001年;《明代中日山海經(jīng)圖比較——對(duì)日本〈怪奇鳥(niǎo)獸圖卷〉》的初步考察》,《中國(guó)歷史文物》2002年第2期;《全像山海經(jīng)圖比較》,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2003年;《從戰(zhàn)國(guó)圖畫(huà)中尋找失落了的山海經(jīng)古圖》,《藝術(shù)探索》2003年第4期;《明清山海經(jīng)圖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中日山海經(jīng)古圖之比較研究》,《中國(guó)東方文化研究會(huì)學(xué)術(shù)研究年會(huì)論文集》,2005年。其他“山海經(jīng)圖”的研究者還包括馮廣宏、過(guò)常寶、江林昌、沈海波、孫致中、張祝平、張華、朱玲玲、周恬逸、朱學(xué)良等。。針對(duì)現(xiàn)存“山海經(jīng)圖”與已佚“古圖”的承繼問(wèn)題,通過(guò)與出土戰(zhàn)國(guó)圖畫(huà)的比較,馬昌儀認(rèn)為,明清時(shí)代的“山海經(jīng)圖”雖然繪制時(shí)間較為晚近,但從圖像上看,畫(huà)風(fēng)簡(jiǎn)樸古拙,有古畫(huà)遺風(fēng),繪者極有可能是以“古圖”或以“古圖”為基礎(chǔ)的中古摹本為底本進(jìn)行直接臨摹或再加工創(chuàng)作[注]參見(jiàn)馬昌儀:《從戰(zhàn)國(guó)圖畫(huà)中尋找失落了的山海經(jīng)古圖》,《藝術(shù)探索》2003年第4期。。馬昌儀的判斷大體正確,但現(xiàn)存的明清“山海經(jīng)圖”即使能揭示“古圖”的某些特征,仍與后者存在較大差異。這一差異或源于《山海經(jīng)》文與圖的內(nèi)在關(guān)系。
馬昌儀、江林昌[注]江林昌:《圖與書(shū):先秦兩漢時(shí)期有關(guān)山川神怪類文獻(xiàn)的分析——以〈山海經(jīng)〉》、〈楚辭〉》、〈淮南子〉》為例》,《文學(xué)遺產(chǎn)》2008年第6期。等認(rèn)為,與湖南長(zhǎng)沙子彈庫(kù)出土戰(zhàn)國(guó)帛書(shū)“十二月神圖”(又名《月忌圖書(shū)》)相類,《山海經(jīng)》中許多內(nèi)容的記錄過(guò)程應(yīng)是先圖后文,即文字是對(duì)作為基礎(chǔ)和主導(dǎo)的圖像的補(bǔ)充和闡釋。由于圖是為文之基礎(chǔ),文本應(yīng)在內(nèi)容上與圖像對(duì)應(yīng),以體現(xiàn)二者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性和連貫性。而現(xiàn)今所存的明清“山海經(jīng)圖”在文圖結(jié)構(gòu)中并不具有主導(dǎo)性,實(shí)為依附文字存在的插圖,并且在數(shù)量上也不足以與文字內(nèi)容相合。因此,如要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山海經(jīng)圖”,尤其是《山海經(jīng)》中《海經(jīng)》與《大荒經(jīng)》所本“古圖”的樣貌,不應(yīng)僅限于考察現(xiàn)有的圖像資料,也應(yīng)從《山海經(jīng)》內(nèi)在固有“文圖關(guān)系”的角度,依托文字狀貌寫(xiě)形的功能,探究圖像形質(zhì)及其象征意義。筆者注意到,在過(guò)往“山海經(jīng)圖”或《山海經(jīng)》“文圖關(guān)系”研究中,由于現(xiàn)有圖像都是黑白印制,即墨色線條勾畫(huà)而不設(shè)他色,故鮮有學(xué)者討論《山海經(jīng)》及其“古圖”的顏色問(wèn)題。但是,從文本來(lái)看,《山海經(jīng)》中存在大量關(guān)于顏色的描述。以此推測(cè),或與出土帛畫(huà)及屈原所見(jiàn)楚先王宗廟和公卿祠堂壁畫(huà)類似,《山海經(jīng)》“古圖”極有可能是彩色的。王紅旗撰、孫曉琴繪的《經(jīng)典圖讀山海經(jīng)》意在嘗試通過(guò)現(xiàn)代繪畫(huà)技法還原《山海經(jīng)》“古圖”[注]王紅旗、孫曉琴:《經(jīng)典圖讀山海經(jīng)》,上海: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2003年。。但由于現(xiàn)代繪畫(huà)在技法、觀念以及用色等方面與遠(yuǎn)古時(shí)代的創(chuàng)制存在較大差別,因而,新圖或與古圖形制及時(shí)人的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風(fēng)格迥異。目前,學(xué)界鮮有從純文字角度進(jìn)行色彩考釋的論著。王懷義《論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與神話意象——以〈山海經(jīng)〉》為中心》一文對(duì)《山海經(jīng)》中的色彩稍有提及。他認(rèn)為,色彩對(duì)于揭示《山海經(jīng)》的敘事結(jié)構(gòu)和理解神話的象征意義具有重要作用:“在《山海經(jīng)》中,這種以顏色為基點(diǎn)的敘述模式,是其神話敘述的主要方式,那些五彩斑斕的動(dòng)植物形象一同構(gòu)成了《山海經(jīng)》中的神話意象群”[注]王懷義:《論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與神話意象——以〈山海經(jīng)〉》為中心》,《民族藝術(shù)》2014年第4期。。而肖世孟所著《先秦色彩研究》[注]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武漢大學(xué)2011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雖有使用《山海經(jīng)》的資料,但所涉內(nèi)容極少,僅關(guān)注其中所記有限的礦物顏料。
由于學(xué)界對(duì)于《山海經(jīng)》中色彩討論的不足,本文將首先梳理文本中出現(xiàn)的色彩,并從“文圖關(guān)系”的角度,探究各色之間可能存在的關(guān)系。再者,本文也將闡釋顏色在記述語(yǔ)境中作為文化符號(hào)的意義,為進(jìn)一步討論《山海經(jīng)》及其圖像中某些尚未被注意的特征,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方法論意義上,本文希望依托“文圖關(guān)系”研究這一范式,立足文獻(xiàn),特別是文字資料,探討非文字性的美術(shù)圖像及色彩觀念,為研究具有文字記錄而缺乏具體視覺(jué)資料的對(duì)象提供新的可能。最后,本文希望依托對(duì)于顏色的考察,提供《山海經(jīng)》文本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的一種可能解釋。
二、《山海經(jīng)》[注]本文的探討基于袁珂之《山海經(jīng)校注》,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4年。中的用色規(guī)律
《山海經(jīng)》大體可被視為一部上古時(shí)期的百科全書(shū),其主體部分《五藏山經(jīng)》主要是介紹各地風(fēng)貌及物產(chǎn),所涉神、怪、人、物眾多。在提及各類對(duì)象時(shí),顏色是重要的物性特征。本文將要探討的顏色來(lái)自文字直接的色彩描述,即文本中存在的、明確的色彩指示性詞匯,如“赤”“黑”“白”“青”“黃”等。在資料搜集過(guò)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文中存在兩類不同的色彩描述,即“細(xì)節(jié)性色彩”和“一般性色彩”。所謂“細(xì)節(jié)性色彩”,在文本中多用于描述該對(duì)象的細(xì)節(jié),是具有明確指向性的色彩描寫(xiě),如:

此處出現(xiàn)的“白”“青”“朱”“赤”“黃”等顏色即是細(xì)節(jié)性色彩。而“一般性色彩”在文本中相對(duì)應(yīng)的語(yǔ)詞,多為對(duì)象名稱中的一部分,是對(duì)該對(duì)象(往往是一個(gè)種類)的一般性介紹,而非具體的色彩敘述。如,《山海經(jīng)》中多處出現(xiàn)的“赤蛇”“黃蛇”“青蛇”“青雄黃”“白堊”等。與對(duì)象名稱相連的“一般性色彩”,并非專指某一特定事物的特定細(xì)節(jié),故可能會(huì)使顏色判定出現(xiàn)錯(cuò)誤。例如,《大荒西涇》記述:“有白鳥(niǎo),青翼,黃尾,玄喙”。此處,在討論“白鳥(niǎo)”的色彩時(shí),“白”的指向并不明確,很難判斷其描述的對(duì)象是鳥(niǎo)的“軀干”或是其他部分,抑或僅是作為類對(duì)象的名稱,并非實(shí)指,而其他色彩則有具體的對(duì)應(yīng)性說(shuō)明。相較而言,一般性色彩具有明顯的泛性特征,而細(xì)節(jié)性色彩則更具圖像性和畫(huà)面感。因此,本文在考察此例時(shí)更關(guān)注“青”“黃”“玄”等細(xì)節(jié)性色彩,而非作為一般性色彩的“白”。對(duì)細(xì)節(jié)性色彩的關(guān)注,或更有助于探究《山海經(jīng)》圖像的狀貌特征。當(dāng)然,本文的討論也會(huì)涉及一般性色彩。
據(jù)筆者統(tǒng)計(jì),《山海經(jīng)》中所提及的、施用細(xì)節(jié)性色彩介紹的對(duì)象共計(jì)176種,涵蓋神、獸、人、草、木以及無(wú)生命之物等不同類別。通過(guò)分析,《山海經(jīng)》中的顏色描寫(xiě)具有以下一些特點(diǎn):
(一)《山海經(jīng)》中所述顏色幾乎全為“正色”。
《山海經(jīng)》中最常出現(xiàn)的顏色詞為“赤”“黃”“青”“黑”及“白”,即后來(lái)與“陰陽(yáng)五行說(shuō)”相配的“五正色”。當(dāng)然,《山海經(jīng)》時(shí)代的“五色”或與今日色彩學(xué)意義下的“五色”在色相及色澤上有較大差異。肖世孟認(rèn)為,先秦“五色”在現(xiàn)代色譜中所涵蓋的范圍遠(yuǎn)大于當(dāng)今之“五色”,應(yīng)認(rèn)定為以“正色”為標(biāo)記的“五色”屬,而并非單一的顏色[注]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武漢大學(xué)2011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關(guān)于“五色”的記載,或最早出現(xiàn)于《西山經(jīng)》: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shí),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鐘山之陽(yáng)。瑾瑜之玉為良,堅(jiān)粟精密,濁澤有而色。五色發(fā)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御為祥。
雖未言明,依上下文看,此處所提之“五色”應(yīng)為“五正色”或“五正色”屬。除“赤”“黃”“青”“黑”“白”以外,《山海經(jīng)》中還有以下一些表示顏色的詞:“五采”[注]《南山經(jīng)》中“鳳皇”,《西山經(jīng)》中“鸞鳥(niǎo)”,《北山經(jīng)》中“鵸”“象蛇”,《中山經(jīng)》中“帝臺(tái)之棋”,《海內(nèi)北經(jīng)》中“騶吾”,《大荒東經(jīng)》中無(wú)名之“鳥(niǎo)”,《大荒西經(jīng)》中“狂鳥(niǎo)”“鳴鳥(niǎo)”及一無(wú)名之“鳥(niǎo)”,《海內(nèi)經(jīng)》中“翳鳥(niǎo)”。“蒼黑”[注]《西山經(jīng)》中“”,《海內(nèi)南經(jīng)》中“兕”。“赤黑”[注]《西山經(jīng)》中“鸓”。“蒼”[注]《西山經(jīng)》中“鰩魚(yú)”,《中山經(jīng)》中“犀渠”“牛傷”“魚(yú)”。“朱”[注]《中山經(jīng)》中“鴢”。“赤黃色”[注]《海外西經(jīng)》中無(wú)名之“鳥(niǎo)”。“青黃”[注]《海外西經(jīng)》中“鳥(niǎo)”“【詹鳥(niǎo)】鳥(niǎo)”,《海外北經(jīng)》中“天吳”。“素”[注]《海外北經(jīng)》中“蛩蛩”,《海內(nèi)經(jīng)》中“素矰”。“玄”[注]《海外北經(jīng)》中“玄股之國(guó)”,《大荒南經(jīng)》中“朱木”之“實(shí)”,《大荒西經(jīng)》中“白鳥(niǎo)”之“喙”,《海內(nèi)經(jīng)》中“建木”之“華”。“縞”[注]《海內(nèi)北經(jīng)》中“吉量”。“紫”[注]《海內(nèi)經(jīng)》中“建木”之“莖”,“延維”之“衣”。“旃”[注]《海內(nèi)經(jīng)》中“延維”之“冠”。“彤”[注]《海內(nèi)經(jīng)》中“彤弓”。。其中,“五采”是指兼具五色,即五色相雜;“蒼”可歸入“青”;“朱”“彤”和“旃”可歸入“赤”;“素”與“縞”為“白”色;而“玄”則可歸入“黑”類。因此,可能的“非正色”,即“間色”,大概只有“蒼黑”“赤黃色”“青黃”及“紫”。然而,通過(guò)對(duì)《尚書(shū)·禹貢》中“厥土青黎”的分析,肖世孟注意到,在先秦典籍中,當(dāng)顏色詞疊用時(shí),所表示的色相或可能指兩色相雜,而非兩色相間,在此例中即是,“其土黑中帶青綠色”[注]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武漢大學(xué)2011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62頁(yè)。。由是推之,《山海經(jīng)》中所謂“赤黑”“赤黃色”及“青黃”或有可能是“赤”與“黑”“赤”與“黃”及“青”與“黃”相雜,而非今日的“赭石色”“橙色”和“黃綠色”等色彩。“蒼黑”或?yàn)椴患兊暮谏瑥?qiáng)可視為“間色”,在《山海經(jīng)》中僅出現(xiàn)2次。而“紫”應(yīng)是《山海經(jīng)》中直接描述的唯一“間色”,在《山海經(jīng)》中僅出現(xiàn)2次。由此可見(jiàn),若《山海經(jīng)》之“文”與“圖”相應(yīng),其“古圖”應(yīng)是一份由“正色”色塊和線條組成的圖畫(huà)或套圖,而時(shí)人的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也應(yīng)與此色彩觀念相符。
(二)《山海經(jīng)》中“赤”色的主導(dǎo)性。
在《山海經(jīng)》中,“五色”的使用頻率是相異的。在所描述的176個(gè)對(duì)象中,“赤”色出現(xiàn)100次(如考慮被描述對(duì)象在不同部位的用色情況,“赤”則出現(xiàn)110次;類似差別在其他顏色的使用上并不顯著),“黃”色出現(xiàn)43次,“青”色出現(xiàn)44次,“黑”色出現(xiàn)44次,“白”色出現(xiàn)62次。而作為一般性色彩時(shí),“赤”色出現(xiàn)了62次,“赤”色屬“丹”出現(xiàn)29次,“朱”出現(xiàn)6次;相較而言,“白”色出現(xiàn)81次,“黃”色出現(xiàn)63次(其中“黃帝”之“黃”有10處),“青”色出現(xiàn)67次,“黑”色出現(xiàn)24次,“黑”色屬“玄”色出現(xiàn)20次。由此可見(jiàn),在《山海經(jīng)》所載之“五色”中,無(wú)論是作為細(xì)節(jié)性色彩抑或是一般性色彩,“赤”色屬出現(xiàn)頻率最高,其次為“白”色,而其余三色(除“黑”色作為一般性色彩時(shí)出現(xiàn)較少外)出現(xiàn)次數(shù)大體相同。另外,在“古圖”中,“赤”色色塊在面積上也應(yīng)大于其他顏色色塊,或者說(shuō),在人們基于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的觀察中,紅色是最為常見(jiàn)或最為醒目的顏色[注]除前引《西山經(jīng)》所描繪的大片“丹木”林外,還有“如猙”(《西山經(jīng)》)、“帝江”(《西山經(jīng)》)、“孟槐”(《北山經(jīng)》)、“窫窳”(《北山經(jīng)》)、“居暨”(《北山經(jīng)》)、“山膏”(《中山經(jīng)》)、“【犭戾】”(《中山經(jīng)》)、“燭陰”(《海外北經(jīng)》)、“育蛇”(《大荒南經(jīng)》)、“天犬”(《大荒西經(jīng)》)。。因此,可以推測(cè),“山海經(jīng)圖”應(yīng)是以“赤”色為主,而其他顏色為輔的圖像集合。當(dāng)然,在某些部分中,“赤”色則處于劣勢(shì)。如《中山經(jīng)》有:“又東三十五里,曰蔥聾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堊,黑、青、黃堊。”
(三)《山海經(jīng)》中的配色規(guī)律。
在本文中,所謂“配色”,是指《山海經(jīng)》在描述某一對(duì)象時(shí),所提及的多種色彩,在文字所描繪的“畫(huà)面”中,呈現(xiàn)的交互和共存狀態(tài)。在“赤”色主導(dǎo)的《山海經(jīng)》世界中,各色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看似雜亂無(wú)章,但其中也蘊(yùn)藏著一些配色規(guī)律:
首先,《山海經(jīng)》中任一對(duì)象所兼具的色彩都不超過(guò)五種,即“五采”。具備“五采”的造物(多為禽類)在上文已有提及,而具備四種色彩的事物有三:“巴蛇”(《海內(nèi)南經(jīng)》)[注]具“青”“黃”“赤”“黑”四色。、“甘柤”(《大荒南經(jīng)》)[注]具“赤”“黃”“白”“黑”四色。、“建木”(《海內(nèi)經(jīng)》)[注]具“青”“紫”“玄”“黃”四色。。身具三色者共計(jì)十有一,具二色者四十八,余下為單色。由此推測(cè),時(shí)人或已形成“色不過(guò)五”的配色觀念[注]《孫子·勢(shì)篇》中有“色不過(guò)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的觀點(diǎn),但《孫子》所言是指色彩的類別為五種,變化亦在五色之中,與本文關(guān)于顏色相配的“色不過(guò)五”不同。本文是就實(shí)際操作而言,并不討論顏色的屬性與變化。。在前段所引關(guān)于“五色”的“丹木神話”[注]王懷義:《論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與神話意象——以〈山海經(jīng)〉》為中心》,《民族藝術(shù)》2014年第4期。中,所涉及的顏色也僅有四種,即“赤”(及“丹”)、“黃”“白”以及“玄”。因此,雖論“五色”,其實(shí)只有“四色”,遵循 “色不過(guò)五”之原則。
其次,從色相看,基于現(xiàn)有材料,身具“四色”或“三色”者在顏色搭配上并未呈現(xiàn)明顯的規(guī)律性,或可認(rèn)為是任意配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三色”屬中,出自《西山經(jīng)》之“鵕鳥(niǎo)”“大鶚”“畢方”、有鳥(niǎo)翼而夜飛之“鰩魚(yú)”以及無(wú)名之“木”,都含有“赤”“白”兩色,或?yàn)椤段魃浇?jīng)》所出之“多彩”事物(“三色”及以上)的配色特征。而同出《大荒南經(jīng)》的“三色”屬“欒”及“朱木”則兼具“赤”“青”二色,或亦可視為此經(jīng)“多彩”事物之配色特征。另外,除“巴蛇”外,兼具“三色”或“四色”者,或?yàn)榍蓊悾驗(yàn)椤澳尽睂伲谠O(shè)色對(duì)象選擇上可能隱藏一定規(guī)則。
再次,在身具“二色”的對(duì)象處,可以發(fā)現(xiàn)較強(qiáng)的規(guī)律性:
表一:《山海經(jīng)》中身具“二色”的事物[注]此欄中白色用灰顏色標(biāo)示。
從上表可見(jiàn),“黑”與“青”、“黃”與“青”互不搭配。“黃”與“黑”之間的搭配,則僅有《中山經(jīng)》“帝休”一例;“黃”與“白”相配有兩例,即《北山經(jīng)》中“鵺”及《中山經(jīng)》中“聞【豕粦】”;“青”與“白”相配亦有兩例,即《中山經(jīng)》中“”及“青耕”。相較而言,“赤”與“白”相配最多,達(dá)14例,其次為“赤”與“黃”,10例;余為“赤”與“青”,8例;“赤”與“黑”,6例;“黑”與“白”,5例。由此,或可以得到以下“雙色”配色系統(tǒng)(見(jiàn)圖一),后文將進(jìn)一步讀解此系統(tǒng):
(四)《山海經(jīng)》中的單色
如前文所述,在《山海經(jīng)》中,施用細(xì)節(jié)性色彩介紹的對(duì)象共計(jì)176個(gè)。其中,施用兩種或兩種以上顏色的對(duì)象為74個(gè)。在單色的102個(gè)對(duì)象中,“赤”色共計(jì)39個(gè),“白”色21個(gè),“黑”色14個(gè),“黃”色9個(gè),“青”色12個(gè),余為其他顏色。而施用一般性色彩提及的對(duì)象則大部分為單色。可見(jiàn),《山海經(jīng)》中所提及的大部分事物在“山海經(jīng)圖”中應(yīng)是單色或無(wú)色的。一般而言,各色在“畫(huà)面”中的存在是相間相雜,并以“赤”為主導(dǎo)。但是,在某些區(qū)域,非“赤”色會(huì)取代“赤”色,而占據(jù)主導(dǎo)性地位,并出現(xiàn)排斥他色的現(xiàn)象。如: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其陰多鐵,其陽(yáng)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niǎo)多白雉、白翟。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是多白玉。……是多白金白玉。……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鳥(niǎo)獸盡白。(《西山經(jīng)》)
北海之內(nèi),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niǎo)、玄蛇、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國(guó)。(《海內(nèi)經(jīng)》)
可見(jiàn),《西山經(jīng)》中有一片“白”色的區(qū)域,而《海內(nèi)經(jīng)》中則有一塊“黑”色的領(lǐng)地。除“赤”色(如前述“丹木神話”)、“白”色與“黑”色外,《山海經(jīng)》中并未發(fā)現(xiàn)以其他色彩(如“黃”“青”)為中心的區(qū)域。這或許表明“赤”“白”“黑”三色較其他顏色在審美及其他功能上的不同。基于五行學(xué)說(shuō),西方屬金,尚白,而北方屬水,尚黑,因此,《西山經(jīng)》關(guān)于西方,以及《海內(nèi)經(jīng)》關(guān)于北方的敘述或反應(yīng)了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存在的五行觀念。然而,除此兩例外,《山海經(jīng)》文本的其它地方并未存在明顯的顏色與方位配對(duì)關(guān)系。
三、關(guān)于《山海經(jīng)》色彩敘述的討論
如前文所述,劉宗迪已考辯《山海經(jīng)》不同部分成書(shū)性質(zhì)不同,合編為一體的年代則更晚,但是,據(jù)筆者對(duì)于文本中顏色描述的綜合考察,無(wú)論《山經(jīng)》或者《海經(jīng)》,其顏色描述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一致性。顏色或許是表明《山海經(jīng)》各部分之間內(nèi)在聯(lián)系的重要標(biāo)志。因此,以下將綜而述之。
(一)《山海經(jīng)》色彩敘述的過(guò)渡性質(zhì)
陳彥青在《中國(guó)傳統(tǒng)色彩系統(tǒng)的觀念設(shè)計(jì)及其歷史敘事》中,所勾勒的中國(guó)古代早期人們對(duì)于色彩的認(rèn)識(shí)過(guò)程,以及色彩使用的發(fā)展歷史,如下:“1.渾然一色;2.二色劃分(陰陽(yáng)、黑白、純雜);3.三色觀(黑、白、赤);4.四色觀(黑、白、赤、黃);5.五色觀(黑、白、赤、黃、青);6.玄色統(tǒng)轄下的五色系統(tǒng)(玄黃——黑、白、赤、黃、青)及間色系統(tǒng)的產(chǎn)生”[注]陳彥青:《中國(guó)傳統(tǒng)色彩系統(tǒng)的觀念設(shè)計(jì)及其歷史敘事》,《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版)2013年第2期。。從現(xiàn)有版本看,《山海經(jīng)》中并未包含色彩認(rèn)知和使用過(guò)程中的第一(“渾然一色”)和第二(“二色劃分”)階段。而“三色觀”主要與《山海經(jīng)》中單色設(shè)色部分相關(guān),但是,從“赤”色在文本中所占據(jù)的絕對(duì)主導(dǎo)地位看,此項(xiàng)關(guān)聯(lián)已經(jīng)極度弱化。經(jīng)中隱約指涉的“三色觀”或僅為更古老觀念的遺存。再者,由于《山海經(jīng)》中所呈現(xiàn)的“五正色”共存現(xiàn)象,“四色觀”的表現(xiàn)也并不明顯。但從《山海經(jīng)》中的“雙色”配色系統(tǒng)可知,“青”實(shí)際上仍游離于其他四色之外。汪濤在《殷人的顏色觀念與五行說(shuō)的形成及發(fā)展》中提到,根據(jù)現(xiàn)有的甲骨文材料,在殷商前期,卜辭中提到的具體顏色有四種,即“赤”“白”“黑”“黃”,另外還有雜色,即“物(勿)”[注]載于艾蘭、汪濤、范毓周主編《中國(guó)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yáng)五行說(shuō)探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61-294頁(yè)。。在《山海經(jīng)》中,“勿”色或是存在的,即前述之“五采”。汪濤注意到,“青”在甲骨文中并不存在,只有在西周金文里,“青”字才被用作顏色詞,如西周晚期《墻盤》銘文中的“青幽高祖”一句便是一例,但這樣的用法十分少見(jiàn)[注]當(dāng)然,甲骨文及金文多為記錄祭祀的文字,并不能全面反映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生活中的實(shí)際用色情況。。然而,在《山海經(jīng)》中,“青”已然成為描述事物的重要色彩,因此,或可以推斷,《山海經(jīng)》的成書(shū)年代不可能早于西周中期。目前,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或成書(shū)于西周中后期[注]參見(jiàn)陳連山:《〈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中關(guān)于《山海經(jīng)》成書(shū)年代的討論,第18-27頁(yè)。。以色彩分析所得出的結(jié)論,與此判斷大體一致。另外,基于《山海經(jīng)》中同時(shí)存在的“青”的邊緣化和普遍性這一矛盾,《山海經(jīng)》極有可能成書(shū)于中國(guó)古人色彩認(rèn)識(shí)觀念從“四色觀”向“五色觀”過(guò)渡的時(shí)期。
《山海經(jīng)》的時(shí)代過(guò)渡性,也可從關(guān)于經(jīng)中主導(dǎo)色彩“赤”色的敘述中看出。先秦時(shí)期有所謂“殷人尚白”和“周人尚赤”的說(shuō)法。如《禮記·檀弓上》:“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從《山海經(jīng)》中的用色情況看,“赤”色是第一位的,而“白”色的數(shù)量雖遜于“赤”色,但出現(xiàn)頻率仍然很高,是第二位的色彩。汪濤認(rèn)為,從甲骨文的證據(jù)看,以“赤”色代替“白”色作為禮儀性主導(dǎo)色彩的傳統(tǒng),是從殷商晚期才逐漸興起的[注]載于艾蘭、汪濤、范毓周主編《中國(guó)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yáng)五行說(shuō)探源》,第276頁(yè)。。《山海經(jīng)》中的“赤”色與“白”色之間隱約可見(jiàn)的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透露出時(shí)代過(guò)渡的一些特征。另外,《山海經(jīng)》的時(shí)代過(guò)渡性,還體現(xiàn)在經(jīng)中所記“五色”,與后世“陰陽(yáng)五行說(shuō)”之間關(guān)系的模糊性上。多數(shù)研究者認(rè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的“五色”說(shuō)與先秦成型并流傳的“陰陽(yáng)五行”觀念關(guān)系密切[注]參見(jiàn)杜軍虎:《“方色”論析:由〈考工記·畫(huà)繢〉》之“五色”與“六色”并提談起》,《創(chuàng)意與設(shè)計(jì)》2011年第4期;吳愛(ài)琴:《先秦時(shí)期服飾色彩觀念探析》,《華夏考古》2015年第3期;許哲娜:《試論傳統(tǒng)五色帝文化》,《中國(guó)社會(huì)歷史評(píng)論》第十二卷,2011年;余雯蔚、周武忠:《五色觀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用色現(xiàn)象》,《藝術(shù)百家》2007年第5期;諏訪春雄:《五方五色觀念的變遷》,《民族藝術(shù)》1991年第2期。。在《禮記·月令》中,“五色”與“五行”“五帝”“五神”“五方”“五蟲(chóng)”“五音”“五味”“五臭”“五祀”“五臟”“五谷”“五畜”以及天干、數(shù)字和季節(jié)等相互對(duì)應(yīng),構(gòu)成了中國(guó)古代較為完整的知識(shí)體系。在前引《山海經(jīng)》所載“丹木神話”中,有“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的記錄。在此,“五色”與“五味”之間,或存在與《月令》所記類似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似可認(rèn)為是《山海經(jīng)》中關(guān)于“陰陽(yáng)五行”學(xué)說(shuō)較為明顯的論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陰陽(yáng)五行”學(xué)說(shuō)在《山海經(jīng)》成書(shū)的時(shí)期可能尚未成熟。原因有二:第一,《山海經(jīng)》中并無(wú)“五色”與“五行”及“五方”相配的切實(shí)證據(jù);第二,《山海經(jīng)》中保留了殷商時(shí)期流行的“四方風(fēng)”及“四方風(fēng)神”信仰,與后世“陰陽(yáng)五行”的“五方”系統(tǒng)有較大差異[注]參見(jiàn)胡厚宣:《釋殷代求年于四方及四方風(fēng)的郊祀》,《復(fù)旦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1956年第1期;陳連山:《〈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19頁(yè);劉宗迪:《失落的天書(shū)——〈山海經(jīng)〉》與古代華夏世界觀》,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6年。。這兩點(diǎn)說(shuō)明,《山海經(jīng)》中雖然蘊(yùn)含并可能影響了后世的“陰陽(yáng)五行”思想,但是,時(shí)人并未形成成熟和系統(tǒng)化的宇宙論和認(rèn)識(shí)論。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汪濤已有較完整的表述:“從甲骨文跟文獻(xiàn)材料的比較看來(lái),商代信仰體系和祭祀對(duì)后來(lái)五行說(shuō)形成直接發(fā)生了影響的是商人的宇宙觀。顏色作為宇宙觀的一個(gè)相關(guān)部分,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五行說(shuō);……當(dāng)然,這并不是說(shuō)五行說(shuō)是商代就創(chuàng)立了。后來(lái)文獻(xiàn)材料中所反映的五行說(shuō)是當(dāng)時(shí)的傳統(tǒng)和思想;沒(méi)有十分強(qiáng)硬的證據(jù)來(lái)證明在更早的商代晚期已經(jīng)存在了同樣的信仰。”[注]載于艾蘭、汪濤、范毓周主編《中國(guó)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yáng)五行說(shuō)探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89-290頁(yè)。據(jù)此,在《山海經(jīng)》的年代,“陰陽(yáng)五行”思想或許只是剛剛萌芽,其發(fā)展和最終流行大抵是由于后來(lái)時(shí)勢(shì)和思想界的推動(dòng)。
不過(guò),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山海經(jīng)》中出現(xiàn)了“間色”,即前文提到的“蒼黑”以及“紫”色,但并不能因此認(rèn)為《山海經(jīng)》處于由“五色觀”向陳彥青所謂的“第六階段”過(guò)渡的時(shí)期。主要原因在于無(wú)完整“間色”系統(tǒng)的存在。前引“赤黑”色、“赤黃色”及“青黃”色均為二色相雜,而非二色相間。另外,經(jīng)中并未出現(xiàn)“天地四方”所構(gòu)建的空間認(rèn)識(shí),因此,“紫”色等“間色”的存在或古已有之,但并未進(jìn)入時(shí)人的經(jīng)驗(yàn)“視界”,或者由于某些原因而被排斥在視域之外。據(jù)此推測(cè),經(jīng)中“無(wú)色”描述的對(duì)象極有可能具有“間色”色彩,但由于主流觀念的影響而被刻意回避和隱藏,造成了《山海經(jīng)》顏色描述的不完整性和選擇性。
(二)《山海經(jīng)》色彩敘述的選擇性
《山海經(jīng)》,特別是其中的《五藏山經(jīng)》部分,在行文中往往遵循較為固定的敘述模式。一般而言,首先介紹所要描述的“山”的地理位置以及此處的物產(chǎn),特別是礦產(chǎn)。在一般性介紹以后,文字便重點(diǎn)描述此地神異之物的特征,如形狀、顏色、物性以及聲音等。例如,《南山經(jīng)》這樣開(kāi)頭:
南山經(jīng)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饑。有木焉,其狀如榖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
就顏色而言,從此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作為描述對(duì)象特征的要素,“祝馀”之“華”之“青”,“迷榖”之“理”之“黑”,以及“狌狌”之“耳”之“白”等顏色在文本中被詳細(xì)記錄。但是,并非所有奇人、異物或神怪的顏色都會(huì)被提及。在許多情況下,色彩特征往往在敘述中被忽略。如:
又東三百里柢山。多水,無(wú)草木。有魚(yú)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復(fù)生。食之無(wú)腫疾。又東三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無(wú)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妒。(《南山經(jīng)》)
在這里,經(jīng)中對(duì)于“鯥”和“類”的形貌和特性有較為詳盡的描述,但是它們的顏色卻是“缺位”的。另外,從《南山經(jīng)》經(jīng)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山海經(jīng)》對(duì)于對(duì)象顏色的描繪并不是全方位的。例如,在介紹“祝馀”時(shí),“華”之外的部位,如“葉”和“莖”并未被提及;對(duì)于“狌狌”,也僅論及其“耳”,而略去余下的身體組成。此類描述的缺失現(xiàn)象在《山海經(jīng)》中普遍存在。
當(dāng)然,除受前文所述主流觀念影響外,關(guān)于顏色描述的不完整性大抵還有以下兩種可能的解釋:1.文字散佚;2.對(duì)于客觀世界的真實(shí)描述。從劉歆(劉秀)《上〈山海經(jīng)〉》表》看,此經(jīng)的錯(cuò)漏在漢代就十分嚴(yán)重,故而有文字散佚所造成顏色描述的缺失,是極有可能的。但是,從全書(shū)看,經(jīng)過(guò)歷代整理和修繕的《山海經(jīng)》在整體上仍然具有明顯的邏輯完整性,因此,文字散佚并不能解釋顏色缺失現(xiàn)象在整部著作中的普遍性。解釋2的依據(jù)源于學(xué)界對(duì)于《山海經(jīng)》性質(zhì)的認(rèn)定。在陳連山等學(xué)者看來(lái),《山海經(jīng)》是上古時(shí)期,“政府”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財(cái)力所編撰和修訂的一部記錄全國(guó)山川、物產(chǎn)的地理志[注]陳連山:《〈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12-16頁(yè)。。從地理志的性質(zhì)而言,其描述內(nèi)容應(yīng)是客觀的,而時(shí)人有限的認(rèn)知能力和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或造成了觀看與記錄的不完整。然而,就前引《南山經(jīng)》中關(guān)于“鯥”和“類”的描述可知,記錄者對(duì)于兩物并不陌生,或可認(rèn)為十分熟悉,故不應(yīng)缺乏對(duì)于二者明顯外部特征的認(rèn)知。因此,如果不是因?yàn)槲淖稚⒇斐傻奈谋救笔В蛴捎诂F(xiàn)實(shí)條件帶來(lái)的經(jīng)驗(yàn)局限,《山海經(jīng)》的記錄者在描述對(duì)象的特征,如顏色特征時(shí),有可能是嚴(yán)格依據(jù)“山海經(jīng)圖”中的圖像傳達(dá)(現(xiàn)實(shí)存在過(guò)的古圖或基于當(dāng)時(shí)知識(shí)體系的視覺(jué)想象)。而這些圖像是否被施以色彩,或者被施以何種色彩,很可能是經(jīng)過(guò)一定的規(guī)則進(jìn)行選擇的。在這些圖像中,無(wú)論是對(duì)“想象”或者“自然”之物的敘述或描繪,都可能具有強(qiáng)烈的意義指向性。《山海經(jīng)》對(duì)于色彩描繪的選擇性表明,時(shí)人可能已經(jīng)具備了較為全面的色彩知識(shí),并具有較強(qiáng)的實(shí)踐能力,可將自我對(duì)于世界的認(rèn)知,依據(jù)自身的信仰及當(dāng)時(shí)的審美觀念,進(jìn)行較為自如的運(yùn)用和發(fā)揮[注]這一點(diǎn)亦可以出土戰(zhàn)國(guó)帛畫(huà)等先秦文物作為旁證。。在這一意義上,《山海經(jīng)》的用色是具有規(guī)律性和目的性的人工活動(dòng)。
(三)《山海經(jīng)》色彩論述在先秦典籍中的獨(dú)特性
《山海經(jīng)》具有選擇性和建構(gòu)性的用色特點(diǎn),使其色彩系統(tǒng)在先秦諸典籍中十分獨(dú)特。除少量敘事成分外,此書(shū)的大部分內(nèi)容,是在介紹作者所聞見(jiàn),或所“想象”的各類珍禽異獸和神怪人物。據(jù)筆者考察,除四處外,《山海經(jīng)》中關(guān)于顏色的描述全部指向非人造之物。此四處分別是:1.《大荒北經(jīng)》:“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2.《大荒北經(jīng)》:“有鐘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xiàn)。”;3.《海內(nèi)經(jīng)》:“有神焉,人首蛇身,長(zhǎng)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4.《海內(nèi)經(jīng)》:“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guó),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在這幾處文字中,與人造之物“衣”“冠”“弓”及“矰”相聯(lián)系的是“非人”的“神”(黃帝女魃與赤水女子獻(xiàn)或?yàn)橐簧?[注]袁珂校注:《山海經(jīng)校注》,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365-366頁(yè)。,其人工痕跡因而被進(jìn)一步弱化和遮蔽。可見(jiàn),人造之物并非《山海經(jīng)》的中心對(duì)象,其敘事的中心是“人世”之外的,祛除了人為修飾的自然世界。
《山海經(jīng)》的這一敘事特點(diǎn)與之后出現(xiàn)的先秦其他典籍,如《詩(shī)經(jīng)》《楚辭》等,較為不同。在這些典籍中,除《天問(wèn)》指向未知世界外,“世間的生活”是作品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因此,大量的顏色詞匯被用于描述人造之物或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生活勞作之物,特別是服飾和牲畜;而且,許多標(biāo)志服飾色彩的“新詞”,如“纁”“黻”“緇”等,也因此而被創(chuàng)造,并被運(yùn)用于描述服飾之外的事物顏色[注]參見(jiàn)潘玉華、李順琴:《〈楚辭〉》顏色詞研究》,《語(yǔ)文學(xué)刊》2012年第2期;李炳海:《〈詩(shī)經(jīng)〉》女性的色彩描寫(xiě)》,《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1994年第6期;李琳:《〈詩(shī)經(jīng)〉》中的色彩運(yùn)用及其文化意蘊(yùn)》,河北大學(xué)2005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張春嬋:《〈詩(shī)經(jīng)〉》中的色彩世界》,《美與時(shí)代》2006年第2期;樓池蔚:《〈詩(shī)經(jīng)〉》的色彩描寫(xiě)及其審美意味》,《浙江海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年第4期;王楊軍:《〈詩(shī)經(jīng)〉》色彩詞研究》,西北師范大學(xué)2014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潘晨婧:《論顏色詞的文化內(nèi)顯義》,《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2016年第6期。。如《詩(shī)經(jīng)·邶風(fēng)·綠衣》中有“綠兮衣兮,綠衣黃里”;《詩(shī)經(jīng)·鄭風(fēng)·出其東門》中有“縞衣綦巾”“縞衣茹藘”;《詩(shī)經(jīng)·唐風(fēng)·揚(yáng)之水》中有“素衣朱襮”“素衣朱繡”;《詩(shī)經(jīng)·秦風(fēng)·終南》中有“黻衣繡裳”;《詩(shī)經(jīng)·小雅·都人士》中有“狐裘黃黃”“臺(tái)笠緇撮”;《楚辭·九章·思美人》中有“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以及《詩(shī)經(jīng)·魯頌·駉》中所提及的各色“馬”等等。可見(jiàn),先秦典籍中,除涵蓋包括間色(如“綠”)等豐富色彩外,還存在普遍的“物色合一”現(xiàn)象,即描述色彩的詞匯,同時(shí)意指某一特定事物。相較而言,在《山海經(jīng)》中,除鮮有提及“間色”外,此類“物色合一”的現(xiàn)象也十分少見(jiàn),僅有“騅”“縞”“素”及“旃”等少數(shù)幾例。而《周禮·冬官·考工記·畫(huà)繢》則更是從人工制作與技藝的角度討論“設(shè)色”的原則與技巧。篇中雖間雜“五行”等宇宙哲學(xué)觀念,但整體上仍以“人事”為中心,而“自然”及與之相關(guān)的“信仰”,則成為了人世生活的背景和點(diǎn)綴。
究其原因,《山海經(jīng)》或與上述典籍在時(shí)代和功能上存在較大差異。此書(shū)或意在通過(guò)“原生態(tài)敘事”模式,創(chuàng)造一個(gè)與后起詩(shī)騷等先秦經(jīng)典(特別是文學(xué)典籍)所描摹的“現(xiàn)實(shí)世界”有距離的、“非經(jīng)驗(yàn)”的、與早期巫文化相關(guān)的“神話世界”。“原生態(tài)敘事”是傅修延在其《中國(guó)敘事學(xué)》中提出的一個(gè)敘事類型,即將人類需要所指向和投射的“自然”作為觀照的焦點(diǎn),并同時(shí)將敘事的主體“人”隱去[注]傅修延:《中國(guó)敘事學(xué)》,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第38-64頁(yè)。。基于“原生態(tài)敘事”的視角,傅修延將《山海經(jīng)》所呈現(xiàn)的世界稱為“虛構(gòu)的世界”,屬于“可能的世界”之一[注]傅修延:《中國(guó)敘事學(xué)》,第50-51頁(yè)。。他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是古人探索‘可能的世界’的最初嘗試,真實(shí)世界提供的‘零部件’在這里被重新搭配,組合成許多‘可能的動(dòng)物’與‘可能的植物’。”[注]傅修延:《中國(guó)敘事學(xué)》,第51-52頁(yè)。在這一時(shí)人基于信仰所“想象”的“可能的世界”中,關(guān)于色彩的描述以及色彩之間的相互“搭配”也極有可能是主觀建構(gòu)和生成的。《山海經(jīng)》“非現(xiàn)實(shí)主義”意義上的建構(gòu)性,是理解其非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的色彩意象及“想象”“山海經(jīng)圖”的重要基礎(chǔ)。另外,從詩(shī)騷等作品中所廣泛運(yùn)用的“間色”看,古人對(duì)于色彩的認(rèn)識(shí)已經(jīng)發(fā)展到陳彥青所說(shuō)的“第六階段”,進(jìn)入色彩使用的成熟期。
四、結(jié)語(yǔ)
需要注意的是,《山海經(jīng)》及“山海經(jīng)圖”所映射的,或許并非當(dāng)時(shí)普通民眾的流行觀念和色彩意識(shí),而更可能是反映當(dāng)時(shí)政治掌權(quán)者或權(quán)力階層的主流觀念。如前文所述,陳連山認(rèn)為,在當(dāng)時(shí)篇幅巨大、或由眾人合力完成的《山海經(jīng)》應(yīng)是“遠(yuǎn)古時(shí)代極其重要的官方文獻(xiàn)”,是秘不示人的重要國(guó)家地理檔案[注]陳連山:《〈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20-27頁(yè)。。因此,與文字相配套的《山海經(jīng)》“古圖”也應(yīng)是僅有少數(shù)人創(chuàng)作,并只有少數(shù)人可以接觸的珍貴資料。而在過(guò)去的某些論述中,某些學(xué)者,如明代楊慎,以“禹鼎圖”為《山海經(jīng)》“古圖”,并強(qiáng)調(diào)“古圖”的“民用性”[注]陳連山:《〈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史考論》,第134-136頁(yè)。。持論的重要證據(jù)來(lái)自《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的一段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yuǎn)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xié)于上下,以承天休。”筆者以為,“禹鼎圖”并非《海經(jīng)》及《大荒經(jīng)》等所本之“古圖”,而且并非“民用”。證據(jù)之一是前論《山海經(jīng)》作為國(guó)家資料的重要性,證據(jù)之二來(lái)自于對(duì)《山海經(jīng)》中色彩的考量。基于圖文之間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山海經(jīng)》“古圖”應(yīng)是彩色的,而青銅古鼎則無(wú)疑是單色的。“禹鼎圖”到“山海經(jīng)圖”,再到《山海經(jīng)》應(yīng)該還經(jīng)歷過(guò)一個(gè)較為長(zhǎng)期的過(guò)程,其中或因由時(shí)代思潮的轉(zhuǎn)變(如色彩觀念的轉(zhuǎn)變),而發(fā)生過(guò)較大地變異。極有可能的是,《山海經(jīng)》“古圖”在《山海經(jīng)》成書(shū)之時(shí)已經(jīng)散佚,經(jīng)中所描述的或只是那個(gè)時(shí)代關(guān)于“古圖”(“禹鼎圖”?)的復(fù)原或轉(zhuǎn)述,因而才留下了當(dāng)時(shí)流行觀念的痕跡。
通過(guò)以上討論可以說(shuō)明,如果單純從顏色角度推斷而言(當(dāng)然,顏色僅為多重維度中的一維),《山海經(jīng)》的成書(shū)年代,大概是一個(gè)思想文化較為活躍的時(shí)期。各種思潮的興起影響了時(shí)人的色彩觀念。由于過(guò)渡時(shí)代的特點(diǎn),從文字描述看,《山海經(jīng)》中既殘留著“三色觀”的遺存,更體現(xiàn)著由“四色觀”向“五色觀”的轉(zhuǎn)變。因此,“山海經(jīng)圖”必定在再現(xiàn)“客觀”世界和個(gè)體主觀經(jīng)驗(yàn)的同時(shí),也真切地反映了其創(chuàng)作和書(shū)寫(xiě)時(shí)代的特色。在以“赤”色為主導(dǎo)的視界中,不論是“真實(shí)的世界”還是“可能的世界”,“五色”(或五“正色”)成為了構(gòu)筑時(shí)人視覺(jué)想象的色彩基礎(chǔ)。即是說(shuō),時(shí)人依據(jù)不同的理念,對(duì)“世界”進(jìn)行著不斷的建構(gòu)和闡釋,形成了想象的“視界”。因此,“山海經(jīng)圖”和《山海經(jīng)》均為某一時(shí)代的歷史創(chuàng)制,都深刻反映了該時(shí)代的觀念和特色。后世的圖像創(chuàng)作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前代的風(fēng)尚,但必定兼具本時(shí)代的烙印和對(duì)前代的“反抗”。在這一點(diǎn)上,依托“文圖關(guān)系”的對(duì)應(yīng)性進(jìn)行比對(duì)與分析,或許是更為有效和準(zhǔn)確的,理解特定時(shí)代創(chuàng)作的手段和方法。另外,《山海經(jīng)》中不同部分在色彩描述上的一致性,可以管窺古人在將《山經(jīng)》和《海經(jīng)》合為一書(shū)之時(shí)所本之內(nèi)在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