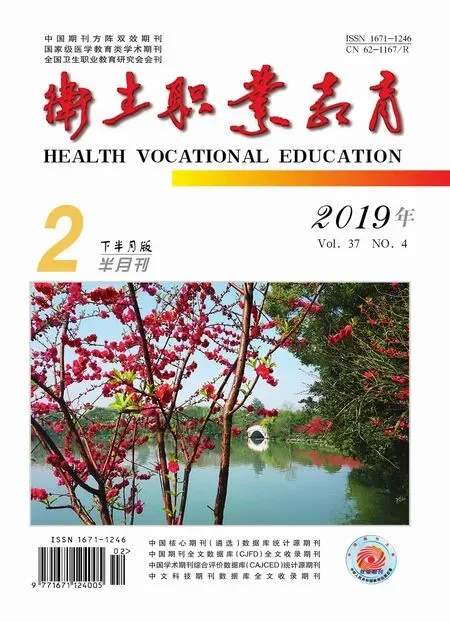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現況分析及對策
王慶華,趙曉敏,劉骙骙,張 瑜,楊 忠
(濱州醫學院,山東 濱州 256603)
2014年3月國務院頒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1]。生活滿意度是個人依照自己選擇標準對自己大部分時間或持續一定時期生活狀況的總體性認知評價,是衡量某一社會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參數。生活滿意度是多維概念,包括軀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支持、經濟狀況、自我效能、人際關系和社會保障等[2]。據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農民工總量達2.8億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不僅物質層面需要政策保障,而且精神層面需要人文關懷[3]。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缺乏系統研究,本課題探討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現況及對策,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18年3月1日至7月31日,采用整群抽樣法對濱州市濱城區448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其中女性194人,男性 254人;年齡 24~39歲,平均(27.5±6.5)歲。納入標準:(1)在城鎮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打工6個月以上,戶籍仍在農村的勞動者;(2)年齡在16周歲以上,40周歲以下;(3)研究對象身心健康,思維清晰,知情同意且自愿參加本研究。
1.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編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問卷進行調查,問卷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人口學資料,包括新生代農民工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經濟收入和家庭狀況等;第二部分為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問卷,包括社會支持(客觀支持和主觀支持)、職業培訓、經濟收入、生活狀態、身體健康、心理感受、自我效能、子女教育、法律援助、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共計12個條目,每個條目分為:非常滿意(85~100分)、一般滿意(65~84分)和不太滿意(≤64分)3個等級,進行自評,計算滿意度。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采用整群抽樣法、問卷調查法和焦點訪談法,以濱州市濱城區新生代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社區和企業作為研究場所,對調查員進行統一培訓,向研究對象介紹本研究的目的和意義,承諾匿名和保密,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利用周末或假期集中發放問卷和焦點訪談,自行擬訂訪談提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44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9.6%。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2.0軟件包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表示,均數間比較采用t檢驗或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率、構成比和χ2檢驗、多元回歸分析和Pearson相關分析等,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現況
滿意度=(非常滿意人數+一般滿意人數)/總人數×100%。包括生活狀態滿意度為67.86%,主觀支持滿意度為78.35%,經濟收入滿意度為55.58%,身體健康滿意度為79.47%,心理感受滿意度為58.71%,自我效能滿意度為74.78%,總體屬于中等偏上水平,見表1。

表1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現況[n(%)]
2.2 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與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的多元回歸分析(見表2)

表2 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與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的多元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現況
表1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目前生活狀態滿意度為67.86%,主觀支持滿意度為78.35%,經濟收入滿意度為55.58%,身體健康滿意度為79.47%,心理感受滿意度為58.71%,自我效能滿意度為74.78%,總體屬于中等偏上水平。表2顯示,主觀支持因素、自我效能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影響比較大(P<0.001),說明社會支持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有顯著影響。社會支持來源與新朋友、互動活動、情感支持、工作成就、歸屬感及社會制度等有關,個體獲取較多社會支持時,有助于其緩解壓力、克服困難、自我效能感增強[4]。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構建以同鄉關系、親戚關系和同事關系為核心的社會支持系統,對其生活滿意度具有積極作用。自我效能是衡量個體自信水平的重要指標,可影響其獲取知識能力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對此,鼓勵新生代農民工之間互相合作交流,及時給予肯定與鼓勵,使其獲得個人工作成功的經驗,增加自信,提高適應能力和生活滿意度。社會生活環境的改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致使新生代農民工開始追求自己的理想,努力實現人生價值,進城務工早已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5]。主觀上,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限制和小農意識影響,僅僅滿足傳統的消費需求,缺乏從整合好的信息中提煉自己所需知識的能力,勞動技能不高,只能從事低報酬的工作;客觀上,由于社會信息的不對稱分布、公共信息服務非均等化因素,自然就將這些信息弱勢群體邊緣化[6]。與城鎮居民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相關行業的行業環境、從業知識、勞動技能、競爭能力、駕馭市場能力都處于劣勢,在信息占有和資源使用方面存在差距[7],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和職業素養有待提高。
3.2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與社會支持、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
表2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支持各維度及自我效能與生活滿意度均呈顯著正相關(P<0.01或P<0.001)。把社會支持及其各因素、自我效能帶入逐步回歸方程,對生活滿意度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個體的自我效能、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預測作用,判定系數為0.360,回歸方程為Y(生活滿意度)=57.2+0.579X1(自我效能)+0.724X2(主觀支持)+1.695X3(對支持的利用度)。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高的社會支持和自我效能,有助于其更好地適應城鎮生活。社會支持是系列的社會互動,包括家庭成員、朋友、老鄉、同事及其他人提供的各種形式的援助和支持[8]。社會支持分為客觀支持和主觀支持,客觀支持也稱實際社會支持,包括物質上的直接援助和社會網絡、團體關系的直接存在及參與,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是人們賴以滿足他們社會、生理和心理需求的重要資源[9]。主觀支持也稱領悟社會支持,即個體所體驗到的情感支持,是個體在社會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而產生的情感體驗和滿意程度,與個體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對支持的利用度是個體對社會支持的利用情況,人與人之間的支持是相互的,支持別人的同時也為別人給自己提供幫助打下基礎。
4 建議與對策
4.1 城鎮社區建立農民工管理中心,改善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環境
管理中心負責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農民工群體的日常管理,如農民工在務工地落戶辦法的制訂及實施,居住、就醫、權益保障的落實與監管,隨遷子女的教育規劃和管理,信息系統建設等問題。同時,建立健全各級農民工行業協會,為農民工群體提供就業指導信息發布、法律咨詢及援助、職業教育和創業培訓等服務,加強各行業協會間的溝通協作,使之在勞務對接、信息共享、經驗交流等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通過雙向機制加強管理、完善服務,切實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提供保障和實際援助。用工企業以人為本,營造舒適的工作環境。管理者應創造讓員工感覺公平的工作環境,如公平的薪酬制度、公平的內部晉升渠道以及管理者觀念上的公平。企業應多管齊下,營造更加公平的軟環境,以提升員工的滿意度和工作績效。加強企業文化建設,結合企業自身實際狀況,凝練企業文化內涵和團隊向心力,提升員工的歸屬感。圍繞新生代農民工經常關心的事物主題及內容,如在社區層面推行法律援助、健康教育和心理輔導講座等服務,鼓勵新生代農民工主動參與社區活動,增加社區居民之間的人際互動,讓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鎮生活,不斷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和生活質量。
4.2 加大對“三農”的扶持力度,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提升農村生活幸福感,鼓勵更多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就業和創業,讓農民受到社會尊重與認可。大力開展新生代農民工的創業培訓、技能培訓,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素質與技能。加強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與應用,鼓勵和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組建職業農民隊伍。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健康問題,加強對該群體的健康投資,提高其身體健康水平[10]。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可以通過講座以及運用報紙、雜志、電視、互聯網等媒體加強對農民工身心健康重要性的認識以及如何改善健康狀況的宣傳教育,幫助他們確立科學的健康觀念和健康行為意識。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宣傳及實施,不斷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
在改革開放和城鎮化建設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發揮了建設者和主力軍作用,國家各級政府出臺惠農政策,進一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使新生代農民工思想觀念發生新變化,職業素養和職業技能不斷提高,積極融入城鎮化建設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總體屬于中等偏上水平,社會支持因素和自我效能因素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預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