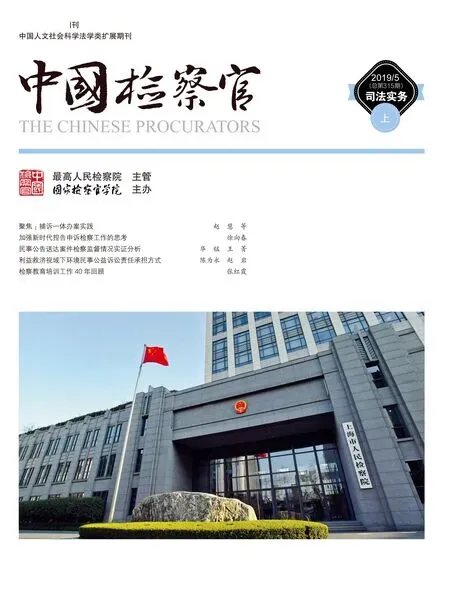民事賠償及對死刑限制適用的影響*
● 高恩澤*/文
一般認為,民事賠償可以緩解犯罪造成的實際損害,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減少,[1]體現了被告人的悔罪表現,表明其人身危險性有所降低;[2]民事賠償使得犯罪后果減輕,降低了處罰必要性。[3]但是,《刑法》第36條規定,犯罪行為致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既然行為人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是其法定義務,那么,履行義務的行為可以作為從寬處罰的根據,與“有損害就有賠償”的賠償本質屬性相悖。
一、民事賠償的含義
刑事法意義上的民事賠償,是指行為人的不法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經濟損失的彌補。民事賠償義務因不法行為而產生,不論填平損害時間早晚,所有彌補損害的行為都是賠償。但是,如果以賠償時間為標準,可以把賠償分為法院裁判前的賠償和法院裁判后根據裁判文書確定的賠償兩種,前者屬于刑事和解,后者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前者的賠償義務雖然同樣基于不法侵害行為而產生,但因被告人系基于悔罪而賠償,對其特殊預防必要性減少,對其從寬處罰符合法理。本文所指稱的民事賠償與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中的民事賠償不同,該種賠償形成于法院裁判之前,是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間的和解,可以成為法院裁量刑罰的根據。簡言之,雖然在廣義上,民事賠償和履行生效裁判文書明確的法定義務的民事賠償都是民事賠償,但能夠影響死刑限制適用的民事賠償,只限于前者。本文以及其他學者所討論包括對死刑限制適用在內的影響刑罰輕重的“民事賠償”,都只指判決生效前加害方對被害方的民事賠償。
以民事賠償的主體為標準,民事賠償可以分為加害人(被告人)的賠償和加害人的親友等人替代賠償。民事賠償本為案外因素,但司法實踐中卻可以對案件的量刑產生一定影響,這與“以犯罪事實為根據,以刑事法律為準繩”的定罪量刑原則存在一定程度的抵牾。如果是加害人親自賠償,特別是基于真誠悔罪,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確實表明被告人主觀惡性減小,從而對刑罰輕重產生影響,進而限制死刑適用,學界爭議不大。爭議較大的是被告人不是基于自己的意愿賠償被害人損失,而是由親友替代,被告人對此也并不消極反對時,被告人的主觀悔罪內心并不明顯,惡性并未減少,這能不能成為限制死刑適用的酌定情節,學界不無爭議。有觀點認為,親友替代賠償,既消除了被害人的報應感情,也緩解了社會的處罰感情。即使是親友的替代賠償,也向社會昭示不法侵害行為“得不償失”,會給行為人帶來不利后果,因而一般預防的必要性減少,可以成為減少預防刑的情節。[4]我們認為,對被告人親友替代賠償不可一概而論,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被羈押而失去自由和對家庭財產的實際支配、控制,只要被告人委托親友替代賠償的,就已經表明其主觀惡性減少。相反,不是出于被告人自己的意愿,而是親友越俎代庖替代民事賠償,被告人對此不聞不問的,雖然客觀上被害人的損失得以彌補,一般預防必要性一定程度上減少,但不宜過分夸大。因為這實際是鼓勵行為人可以任意行為,即使出事也有他人代勞,自己完全不用承擔責任的錯誤心理,無異于助長被告人對社會和親友不負責任的態度,也易成為他人效仿的榜樣。我們認為,并非只要有民事賠償就可以獲得從寬處罰的“獎勵”,只有那些確實體現被告人特殊預防必要性或者一般預防必要性減少的民事賠償才可以成為從輕處罰的酌定量刑情節。
二、民事“多”賠償的實踐定位
既然將民事賠償限定為法院生效裁判生效前,甚至是法院開庭審理之前,被告人對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積極賠償,其賠償數額往往成為被害人諒解與否的重要指標。如果等于甚至低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判決的數額,恐怕很難取得被害人的諒解。如,成都孫偉銘酒后駕車撞人案中,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雖然認定孫偉銘的親屬代為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11.4萬元,但仍判處其死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孫偉銘“積極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100萬元(不含先前賠償的11.4萬元),取得被害方一定程度的諒解”,因而改判其死緩。[5]兩級人民法院在認定事實和定罪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二審之所以改判死緩,主要根據可能在于多賠償了被害人經濟損失和取得了被害方諒解。可見,民事賠償和取得被害人諒解兩個因素的結合,才對死刑限制適用產生實際影響。而被害人的諒解,又往往建立在民事多賠償基礎之上。因此,“民事賠償可以死刑限制適用”的命題實際可以替換為“民事多賠償才可以限制死刑適用”。被害人諒解和民事多賠償,在此渾然一體化。
眾所周知,在侵權案件中,死亡和傷殘賠償金在全部賠償數額中所占比重非常之大,甚至可以達到賠償總額的四分之三。一般認為,舉輕可以明重,輕微的民事侵權案件中被害方尚可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和死亡、傷殘賠償金,對精神損害更加嚴重的刑事犯罪,當然也有權主張。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和《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規定,“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又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于是,無論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還是獨立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和死亡、傷殘賠償金的,都因與上述規定沖突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喪葬費、交通費等費用又微不足道,不足以滿足、平復被害人的情緒。如果被告人僅僅賠償醫療費、喪葬費等少額費用的,往往不能得到被害人的諒解。這就意味著,民事賠償實際是民事“多”賠償。但如果民事賠償數額過高,又有被害人利用刑罰相要挾“勒索”之嫌,這就決定了對民事“多”賠償須加以必要限制。我們認為,“多賠償”之“多”,不能漫無邊際,而是相較于法院依法判決可能確定的數額而言的。如果任由被害人“漫天要價”,法院又以被害人的態度為根據裁量刑罰,一定程度上被害人就實際掌握了死刑判決的決定權,這是不可思議的法治災難。我們認為,“多賠償”是指超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法”應當判決,但低于《民法總則》《侵權責任法》等所規定的包括死亡、傷殘賠償金在內的合理數額。當然,如果被告人基于對自己犯罪的悔恨和對被害人的同情等原因,自愿超出可能依法判決的數額的,不再此限。此外,被害人的諒解和“多賠償”之間并非絕對一致,在刑事和解理念的倡導下,當二者不一致時應以前者為根據。
三、民事賠償對死刑限制適用的影響
在我國,死刑有立即執行和緩期二年執行兩種適用方式,二者共稱死刑。有觀點認為,民事賠償既限制死刑立即執行,也限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適用,[6]只要這一酌定量刑情節發揮實質作用,那就只能判處無期徒刑。也有觀點認為死緩制度是酌定量刑情節適用的“用武之地”,[7]酌定量刑情節的作用只是限制死刑立即執行。有堅持死刑廢除論的學者呼吁“叫停死刑案件的立即執行”,同時主張“而代之以死刑緩期執行”,[8]實際上并不把死緩視為死刑。這兩種不同的死刑適用結果上距若天壤,后者不能視為生命刑。[9]
有學者認為,適用死緩的案件,既有“罪行極其嚴重”但“不是必須立即執行”而由死刑立即執行“降格”適用死緩的情況(減輕的死緩),也存在因有從重、加重處罰情節“升格”適用死緩的情況(加重的死緩),還包括案件既沒有從重處罰也沒有從寬處罰的特殊情節,法官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直接判處死緩的情況(本來的死緩)三種情況。[10]本文認為,死緩并非獨立刑種,是我國為了縮減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范圍而獨創的死刑的適用方式之一,其適用條件(對象)只能是“應當判處死刑”,但“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犯罪分子。如果通過犯罪情節來判斷罪行是否極其嚴重,那么就應該重點結合犯罪的手段、方法、危害結果等因素加以考量。簡言之,適用死緩的前提必須是“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對那些本不應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不應因有從重、加重處罰情節“升格”適用死緩,也不應直接根據案件情節判處死緩。換言之,認為死緩可以分為三種的觀點,實際是把死緩當成了獨立的刑種。因此,民事賠償對于死刑限制適用的影響有且僅有第一種情況。第二和第三種情況,被告人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害人是否諒解與被告人的生死無關。
注釋:
[1]參見于同志:《死刑裁量》,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頁。
[2]參見趙秉志、彭新林:《論民事賠償與死刑的限制適用》,《中國法學》2010年第5期。
[3]參見[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8-1069頁。
[4]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97頁。
[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審判參考》(2009年第6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6]參見蔡方方:《酌定量刑情節限制死刑適用問題研究》,《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7]參見彭新林:《酌定量刑情節限制死刑適用:價值、空間與路徑》,《法學》2014年第9期。
[8]參見韓瑞麗:《死刑制度的悲劇摭談》,《法學家》2007年第6期。
[9]參見于志剛:《死刑存廢之爭的三重沖突和解決之路》,《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6期。
[10]除積極賠償外,認罪態度較好、因民間矛盾激化、自首等情形也是適用死緩較多的因素。參見于志剛:《死刑存廢之爭的三重沖突和解決之路》,《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