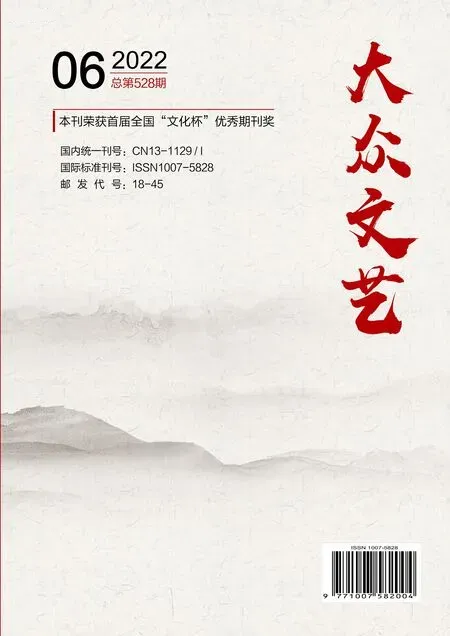對柏拉圖《會飲篇》中泡賽尼阿斯頌辭的解讀
(浙江大學 310011)
《會飲篇》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所著的一部對話體作品,約在公元前385年后完成。它是一部探討愛的本質(zhì)的對話錄,整篇作品主要由六篇對愛神愛若斯的頌辭組成,其中收錄了修辭學家斐德羅、喜劇家阿里斯托芬、哲學家蘇格拉底等人的觀點。本文在參考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公元1899年—1973年)所著《論柏拉圖的〈會飲〉》的基礎上,試對泡賽尼阿斯頌辭作比較系統(tǒng)的解讀。
在《會飲篇》中,泡賽尼阿斯的頌辭緊接著斐德若的講辭,斐德若認為只存在一個愛若斯,泡賽尼阿斯首先反駁了這個觀點,他認為愛若斯有兩個,分別是是屬天的和屬民的。隨后他給出了論證的大前提:“所有行為就其所為本身來說,并沒有美丑可言。……美不美,惟有如何行事的方式才顯得出來。做得美做得當,所做的就美;做得不當,所做的就丑。”1泡賽尼阿斯認為,區(qū)分兩類愛若斯的著眼點在于追求愛若斯的行事方式,即做得美、做得當?shù)膼廴羲咕褪菍偬斓膼廴羲梗龅貌划數(shù)膼廴羲贡闶菍倜竦膼廴羲埂_@個邏輯當然值得辯難,難道所有的行為,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區(qū)分善惡與美丑的嗎?即使我們能同意或部分接受他的觀點(至少在“愛若斯”問題上),那么我們還需要往下繼續(xù)辨析泡賽尼阿斯在區(qū)分“當”與“不當”問題上采用的標準何如,而對于這個標準的探討將會貫穿頌辭全文。
泡賽尼阿斯認為沉湎于“屬民的”愛若斯的“這類人在愛的時候不是愛女人就是愛男孩,而且,愛的更多的是他們的身體而非靈魂”。而鐘情于“屬天的”愛若斯的人則不同,“因為這性感神的血緣中沒有女性,只有男性,所以這情愛只是對少男的情愛”。正如施特勞斯所言,“泡賽尼阿斯追求的是對男童戀的辯護”,但是并非所有指向于男性的愛若斯都是“屬天的”,換言之,區(qū)分“屬天的”還是“屬民的”標準不在于性別,而是所指向的目的,即屬民的指向于身體或性的享受,而屬天的則指向于強壯或理智。
為什么泡賽尼阿斯認為屬天的性感神的血緣中沒有女性,只有男性?他自己做了馬虎的辯護,“屬天的性感神年紀較長,不至于浴火中燒”,我們或許可以這么理解,對于少男的愛戀中有部分是可以剝離掉性愛的,而對于女人的愛戀,這種剝離是不可思議、絕無可能的,從中我們也可以品位出那個時代的哲人對于男女本性的潛在意識。
我們再去探討這個指向動作的主語(或發(fā)起人),那么毫無疑問,泡賽尼阿斯是站在“有情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的,就他本人而言,他不正是那個愛戀于阿伽通的“有情人”嗎?有趣的是,泡賽尼阿斯第一次提到,應該有禁止愛小男孩這樣的法律時,他給出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免得人們(注:指有情人)在尚未定型的人身上浪費太多精力”。施特勞斯一針見血地指出:“他關注的是有情人的私利”,“出于有情人的這種私利,那么好人(good men)強加給自己一種法律”,畢竟這種法律是對有情人的一種保護,泡賽尼阿斯也承認“規(guī)矩男人都自愿訂出這樣的法律來約束自己”。
隨后泡賽尼阿斯將話題引入了頌辭的核心部分,即探討法律和情愛之間的關系。他先列舉了兩個極端的例子,以與走中間路線的雅典和斯巴達做對比:在厄利斯和玻俄提亞這樣的未開化(不善言辭)的希臘人中,法律允許人們?nèi)我馇髿g;而在僭政治下和蠻夷治下,“愛少男、愛智識、愛體育,都屬于不正派行為”。雅典人則在慎重考慮后答應求歡,雅典和斯巴達關于情愛的法律在泡賽尼阿斯這里得到了贊許。然而,吊詭之處在于當時的雅典法制對于同性戀的問題似乎并不那么寬容,施特勞斯對這點看得很明白,他說“但這不是一個完全公正無私的人的講辭。這席講辭出自這樣一個人之口:他想為自己的行為爭取自由,他說這些行為是合法的,但我們在后面將看到,這些行為并不合法。他整篇講辭以對雅典禮法的贊頌為幌子,其實都是在暗示如何改進雅典禮法。”2
根據(jù)施特勞斯的觀點,這篇頌辭在本質(zhì)上是一篇“協(xié)商講辭”,是受作者的私利激發(fā)而闡述的有特定目的之言論。3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分別對比斐德若和泡賽尼阿斯對愛若斯的贊頌:斐德若說,為情伴去死,尤其為有情人去死,會得到諸神的高度獎賞,不去死則會受到諸神的嚴厲懲罰。泡賽尼阿斯在頌辭中歷數(shù)了雅典法律給予有情人的令人驚詫的自由,正如他所言,不僅“為了奪得所愛的人,有情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要他想得出來,法律完全不予限制,還會加以表彰”,甚至連情人發(fā)的誓言不算數(shù)也能得到神的原諒。“有情人在哪里都收到鼓勵,從不會被認為在做不正派的事情”,任何的“百般殷勤、苦苦央求、發(fā)各種誓、睡門檻,做些連奴隸都不屑做的添肥事兒”,在泡賽尼阿斯的開門見山的大前提下(“所有行為就其所為本身來說,并沒有美丑可言”),便都可以接受了。
盡管如此,泡賽尼阿斯在創(chuàng)作這篇頌辭的時候,當下的雅典法律畢竟沒有實現(xiàn)他的目的,他想要確證的是有情人追求情伴和情伴答應有情人這個雙向的過程都是高貴的,因此可以為法律所接納。當我們再次回溯泡賽尼阿斯這篇頌辭,不禁發(fā)現(xiàn)泡賽尼阿斯在論述如何區(qū)分“屬天的”愛若斯和“屬民的”愛若斯,這種度量標準已被悄然轉(zhuǎn)移。在頌辭開頭,對照于“屬民的”愛若斯,前者有如下的特征:1.愛的是靈魂(理智)而身體(性的享受);2.愛的是男性而非女性(只有對男性的愛才可能剝離出性愛的成分);3.愛的是少男而非小男孩(小男孩的理智尚未萌發(fā))。4這三個特征歸結(jié)起來有一個主導性的原則:就是對理智的追求,但這個原則明顯存在一個悖論:泡賽尼阿斯無法說明的是,為什么有情人對于少男的愛要優(yōu)于對成年男子的愛和對女人的愛,畢竟少男的理智才剛剛“萌芽”。如果情伴對有情人的接受是出于一種對理智的追求,那么有情人對情伴的愛慕又是何動機呢? 僅僅是對青春年少的青年男子的“向往”嗎?
泡賽尼阿斯還需要創(chuàng)造另一個概念,在頌辭的最后部分他談到:“有個人委身于自己的有情人是因為他人好,以為同他建立愛的情誼會使自己變得更好,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完全搞錯,那人其實很壞,沒有一點美德,即使受了如此蒙騙,仍是好事。因為,這讓大家看到,他這人為了美德和上進才如此,雖然受到蒙騙,沒有什么事情比這更美好的了。總之,為了美德而委身,再怎么也是件好事。這種情愛與屬天的阿佛洛狄忒結(jié)伴,本身也是屬天的……”5追求“美德”的少年可能會落入只是假裝有美德的成年男子之手,但這無有大礙。他不需要去確證這個有情人真有美德與否,便可以用這種方式接受任何人的求歡,只要相信對方有德行就行了。對于有情人而言,少男這種對于“美德”的追求不正是“美德”的一種表現(xiàn)嗎?泡賽尼阿斯也證言:為了美德而委身,哪怕受到蒙騙,沒有什么事情比這更美好的了。于是,有情人對于少年的追求也就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美德。在有情人對情伴的追求和情伴對有情人的接受的雙向過程間,泡賽尼阿斯建立了令人信服的同質(zhì)性,我們也應該承認,泡賽尼阿斯達成了論證的目的。
在《會飲篇》中,斐德若的立場有著某種模棱兩可,但泡賽尼阿斯、厄利克希馬庫斯和阿里斯托芬都是男童戀的支持者。泡賽尼阿斯的頌辭尤其具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在柏拉圖對話中,它是唯一一篇協(xié)商講辭,這意味著它不僅要捍衛(wèi)現(xiàn)有法律中對自己的權益有利的方面,也在提倡其中尚未能滿足自己主張的要求,客觀公正當然不是它所追求的目的。我們剖析這個文本的關鍵應該放在對泡賽尼阿斯身份的雙重性的認識上:他既是愛戀阿伽通的有情人,又是致力于推動修改法律的立法者之一,他是這雙重身份的混合體,然后才會有這樣一篇復雜的文本。
*注:古希臘的同性戀關系中,并非兩個年齡相若的成熟男人之間,而是成年男子與少男之間的戀情:成年男子甜言蜜語追求少男,少男被恭維、贊美打動后接受追求。在劉小楓的譯本中,主動一方的成年男子被譯作“有情人”,被動一方的少男相應譯作“情伴”。
注釋:
1.劉小楓.《柏拉圖的〈會飲〉》[M].華夏出版社,2003:63.
2.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論柏拉圖的〈會飲〉》[M].華夏出版社,2012:94.
3.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論柏拉圖的〈會飲〉》[M].華夏出版社,2012:112.
4.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論柏拉圖的〈會飲〉》[M].華夏出版社,2012:109.
5.劉小楓.《柏拉圖的〈會飲〉》[M].華夏出版社,20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