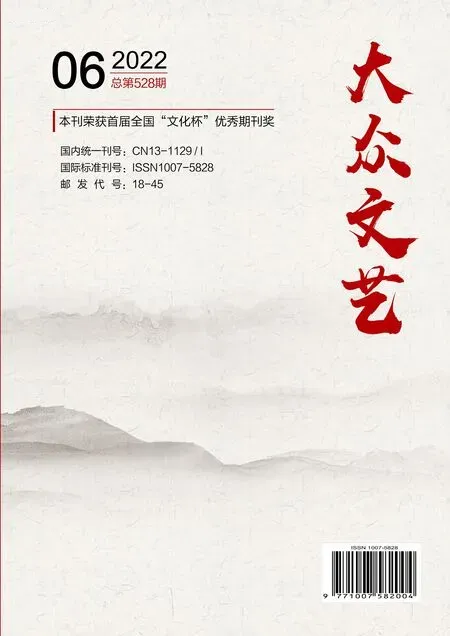生態之美,心之所向
——淺談賈平凹文學作品的自然生態美學意蘊
(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210000)
賈平凹是我國文壇史上較早觸及生態美學創作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學創作中體現出的生態思想旨在通過描摹自然的原生態美感來展示生態環境的原始生命力。賈平凹深受老莊美學思想的影響,畢生追尋“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從而使得“世間萬物的同一性”成為賈平凹塑造“和諧”藝術世界的宗旨。追溯作者的文學創作生涯,首先源自其深受古樸的“商州”文化浸染,其次是受古代傳統宇宙意識——老莊思想的影響;同時,他抨擊“工業文明”社會之下的物欲橫流,無限膨脹的物質欲望將人類帶入“自掘墳墓”的險境。在其作品中,賈平凹以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的相關理論為指導,以此探討在人與自然關系逐漸疏遠、淡漠的時代,如何保持關心自然、關注生態的赤子情懷和博愛之心。
賈平凹的生態文學作品凝聚了生態之美。在《月跡》中:“月光是玉玉的,銀銀的,灑在院里、沙灘上,滿世界都柔柔和和得像水面一樣。”在《冬景》中則是寧靜與空靈的景象:“雪下得好大,雪天里有太陽的紅光,有一樹的小鳥,更有樹下的賞雪人——他在做一首冬的詩。” 在這類散文作品中,自然是美好安寧的。而這種本質,是大自然與生俱來的,也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美的饋贈。但是,大自然也有另一面:譬如“秦嶺深處的大洼地更是像死亡一般寂靜”……在這類文字中,自然仿佛是上帝的化身,令人望而生畏,獨特的生命體驗由此而生。在《張良廟記》等文中,自然總是以深林險峭的面貌出現,《荒野地》中描寫的時間則是亙古的洪荒,在《讀山》中,“山風森森,竟幾次不知了這山中的石頭就是我呢,還是我就是這山中的一塊石頭?”頗具莊周夢蝶的意味。在這類作品中,可謂是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然而在近現代思想史上,人們曾一度認為人類能夠征服自然,顯然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正如諾曼·卡曾斯說:我們違背大自然的結果是:我們破壞了自然景觀的美,自然動態的美和天籟的美。賈平凹始終持有來自生命深處的覺悟,也因此,他總是大篇幅地運用擬人的修辭手法進行創作,使自然具有人的思想和情感——安寧如慈母的大地,挺拔如偉岸丈夫的山脈……這類描寫源于作家對自然具有人格化的肯定,他把對自然生態的熱愛,都灌注到文學創作中,自然生態是他文學精神世界的港灣。
一、詩畫意境的審美創造
生態自然美學一直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的萬物空靈境界總讓人心馳神往。然而,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大自然很悲哀地從人類的“詩畫意境”變為人類攫取財富的寶庫。賈平凹的生態文學重新激發了人類對自然的審美情趣,引導我們運用多種感官世界去認知自然之美。其返璞歸真的景物描寫無不令人心曠神怡、如癡如醉。《懷念狼》中有這樣一段景物描寫:“河面并不寬,流水卻急,繞著對面山根下來,沿著河灘蒼蒼茫茫的野蘆葦和蒲草,有路繞過一叢河柳,河柳下系著只船。”作者運用白描的藝術手法只言片語就生動形象地為讀者展示了鄉村的寧靜美好和純澈無暇,這大概是大自然無需加工就天生麗質的美,也是大自然形象勾勒出的詩畫意境美。再如小說《浮躁》里的人們生活于竹林蒼榆之間,這些深居簡出的人們,曾心無旁騖,自由愜意的生活于滋養他們的廣博的土地上,和鱗次櫛比的高樓都市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詩意棲居的審美創造巧妙地奠定了生態美的藝術氛圍。
二、對神秘自然的憂患意識
賈平凹的文學作品中還經常出現大量的神話故事,它們看似荒誕不經,形成一種現實和幻想混雜在一起無法分清界限的世界,可見對神秘自然的憂患意識是賈平凹文學創作中又一突出特征。從敬畏、保護生態的角度出發,小說《懷念狼》就集中體現了這一特征,這是關于一個“離鄉與返鄉”的文學題材,它被賈平凹重新放置于當代生態危機的背景之下。小說講述了一個關于尋找15只瀕臨滅絕的狼的故事,情節跌宕起伏、離奇神秘。眾所周知,狼在我國北方民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象征地位,狼以其強大的力量威懾著人,但在關鍵時刻也庇佑著人類,因此北方人民把狼視為神一般的存在。《懷念狼》表現出人性和狼性間的互相幻化,構成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隱喻——人與狼互相依賴,缺失一方,都將會打破整個生物鏈的平衡。賈平凹在小說結尾中借“我”這一都市人形象在沒有狼的世界中痛苦吶喊的悲劇表達了他對人類濫殺狼群、破壞自然的強烈控訴,強調了人與自然中所有的物種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賴的關系。狼的消失,使得人們陷入到一種精神空虛之中,生態鏈的斷裂終將帶來生存欲望的渙散。賈平凹說:“人是在與狼的斗爭中成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恐懼、孤獨、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懷念狼是懷念著勃發的生命,懷念著世界的平衡”。由此可見,只有人與自然之間相互和解、共生,社會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愿景。
三、探求和諧自然的生態倫理
人與自然的和諧是生態文學追求的理想境界,遠古時代的人們視自然為“皇天后土”,即遵循了天地間的法則,才可以國泰民安,這種遵循生態倫理的理念是賈平凹生態文學的內在核心。在小說《天狗》中,山民對 “天狗吞月”現象視為一個具有神秘色彩的象征儀式。文中的山民們還過著一種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所謂“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種寧靜閑適的生活方式和現代人形成鮮明的對比:反觀當下,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物欲,無休止地展開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和掠奪,殊不知,心靈的安穩在于安貧樂道,只有把欲物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人與自然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賈平凹大力提倡極簡主義,節制欲望返歸自然從而獲得精神的升華。小說《懷念狼》中的“我”在就曾親眼見證過一位老道人為狼治病的場景,狼離開時用前爪跪地的方式向恩人道謝。當老道人死去,狼群悲傷地來送葬的場景使讀者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它蹲在了門口先是嗚嗚了一陣,緊接著嗚嗚聲很濁,像刮過一陣小風,定睛看時,就在土場邊的柏樹叢里閃動著五六對綠瑩瑩的光點:那是一群狼在那里”。人與狼之間深沉的情誼,靈魂洗禮與救贖。這里,賈平凹將以“我”為代表的人類和以“狼”為代表的自然生命之間夢幻般的憧憬展露無遺。倘若人類能節制欲望,以一顆博愛、仁慈的心去看待世間萬物,探求和諧的生態倫理,那么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愿望就將指日可待了。
四、結語
隨著社會的發展,大自然曾經安寧的湖水被攪渾,和諧的凈土變成了昔日黃花,人類為了發展經濟不惜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這種現狀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賈平凹的文學作品不僅表達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憧憬,而且深刻地控訴了人類中心主義指導下,破壞自然、鄉村巨變等社會現實,表現了人類終將回歸自然的歷史宿命。心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學史觀體現了賈平凹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歷史使命。通過反思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意識,人也從自然中獲得啟迪,達到彼此間的融合,促使我們去反省物我關系的生態哲學觀,所謂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此為賈平凹進行生態美學研究的現實意義所在。正是這樣一種和諧的自然生態倫理觀,使得賈平凹的文學作品在當代文壇中熠熠生輝、常青不衰,向世人證實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內涵,總是在持之以恒地追求自然宇宙與社會人生的無我合一的境界,其中流露出人道主義情懷和社會責任感更加富有時代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