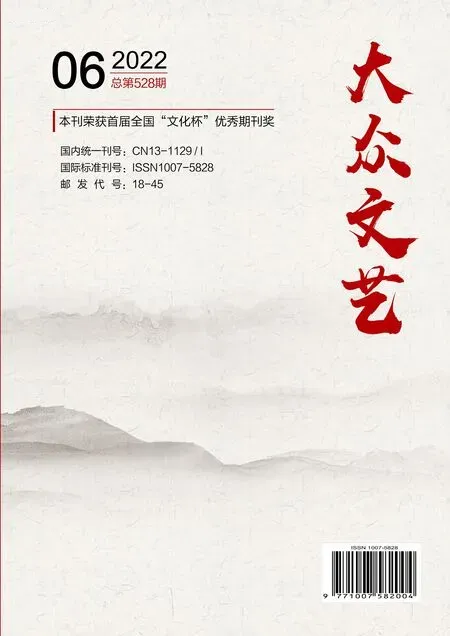從本質生成到異質共在
——試論賽博格對海德格爾生存觀的一種解構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511400)
一、海德格爾生存觀的本質蘊涵
毋庸置疑,海德格爾是堅決反對傳統形而上學的邏輯定義法,批判造成人與世界疏離的主體性原則。回溯《存在與時間》,“存在(sein)”不應該被理解為一個靜止狀態的名詞,即無法給予固定的概念,而趨向于納入動詞的范疇考究,即一個持續波動、變化的動作或狀態。海德格爾用“此在(Dasein)”表示人的存在,由德文da與sein兩個部分組成,da為定冠詞,表示特定的時空或狀態。Dasein特指人這種超出自身的存在者,是此純緣境(Da)或純構成,它沒有自己的現成本質,而只在讓世界顯現的方式中獲得自身。由此,把思維主體當作存在者甚至妄圖把握存在者的存在,這一種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關系面臨著土崩瓦解的危機。進而,海德格爾把人的“生命”等同于“此在”,即存在的在此,它經歷著在。如何經歷呢?此在與能在相伴相生,能在指的是對自身生存的狀態與方向進行籌劃,同時通過將此在所囊括的各種偶然性、可能性一一拋于此在面前,使此在得以領悟自身,即體悟“為何之故(Worumwillen)”,使人的存在得以窺見本質。換言之,此在的生存就是一個實現能在的過程。
正如他在《給查理森的信》中所言道:“《存在與時間》的首要任務是摒除主體性。”“此在”等系列概念的提出從源始性上告別了傳統形而上學的解釋或任何形式的主體性規定,把人的本質的定義權利返還給了自身。
二、賽博格理論的異質隱喻
“隱喻”的希臘語metaphora,據字源釋義meta與pherein的意義分別是“在…之后”、“轉換”。語言學上,“隱喻”特指具有相近特征、屬性的兩個事物由其一來指代另一個事情的演進或變化過程。
“賽博格”一詞源于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科學家弗雷德和內森從“控制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 ”中構造了“賽博格(cyborg) ”這個專有名詞。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唐娜·哈拉維雖是堅定地站在后現代女性主義的立場上發表了膾炙人口的“賽博格宣言”,筆者認為,其更不容忽視的理論建樹在于如何定義現實世界乃至如何定義人的本質的問題探詢,而不僅僅針對女性。在論文集《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中,存在于無限空間密集的賽博格意象是一個巨大的隱喻。超越普遍性和總體化概念的以太空間,像一個“神話的時代”;而每一個行走其間的賽博格,都叫做“喀邁拉(chimera) ”。這時,人類變成了理論上虛構的機器和生物體的混合物,男性與女性、肉身與非肉身、自然與非自然、有機物與無機物甚至日常生活與虛幻擬像的界限已然被模糊、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動態的社會現實和身體現實,人的生成與現狀,均存在于異質的賽博格之中。誠然,“賽博格成了我們新的本體論”。
三、主體的置換:此在之體悟與共在之沉淪
海德格爾說:“正因為此在是通過‘為何之故’——生存論的首要法則而構建,人類社會等一切事物才擁有可能。”此在的主體性,指向的是生存活動具有“為何之故”的特性與規定上。換言之,只有當人的一切活動都朝向此在,同時處于一切生存活動的“為何之故”的可能性之中,此在才能在領會自身的可能中實現、選擇、籌劃自身。同時,藉由此在“為何之故”的豐富內涵,“在—世界—中—存在”的結構才具有普遍性與合法性。反過來,要實現對世界與存在的把握,我們必須要對“為何之故”進行體察和領悟,即深刻地認識到此在這個主體(尤其內容的能在),并對能在驅使此在積極地謀劃、籌備、獲取自身的趨勢了然于胸。在海德格爾那里,此在是掙脫了傳統人類本體論的沉重枷鎖,純粹依靠本己舉步維艱地走向冠冕的。
然而焊接的火光、眩惑的數字,攘奪了此在的領地,擁賽博格為王。存在的主體不再是在特定境遇中靜靜地關注自身、思考自身,而是通過世界這一異己的媒介來領會,甚至領會的本能機制都摻雜了賽博格元素,表現為海德格爾所說的“一種日常沉淪的存在方式”。此在沉淪于這種賽博格日常中,自我的本真狀態被鎖閉和排擠,人不能瞥見和正視生存的本己性與此在的本質性,只好從俯拾即是的世界層面來理解生命的瞬間,以期領會存在。此時,此在作為主體的實現形式,仍然靜穆、嚴肅地關注自身,承擔起生命沉重的負擔和無定的風險,保持決然、內省的姿態。無疑這是困難的。當此在來到賽博格世界,異于本質的元素參與了人的肉身肌理、甚至思維系統的建構,重新定義了生存的本質——異質共在,此在便輕易地陷入沉淪。沉淪意味著一個布滿可能性、意向性和權能性假象的狀態。人們采取了不同于體悟、內省以實現主體的路徑,結果是失去了自身。此在作為存在的主體,早已在電光火石間被擊碎,轉而置換成沉淪狀態中的異質共在。
四、結語
當人與動物、人與機器、物質與非物質等界限被突破與取消,現代世界趨向于由異質共在的動態現實所構成,海德格爾生存觀由此陷入了理論的泥潭。我們不得不承認,賽博格思想是對傳統存在觀主體的一場解構性實踐。人何去何從,仍然是一個不斷被追問、解釋與反駁的永恒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