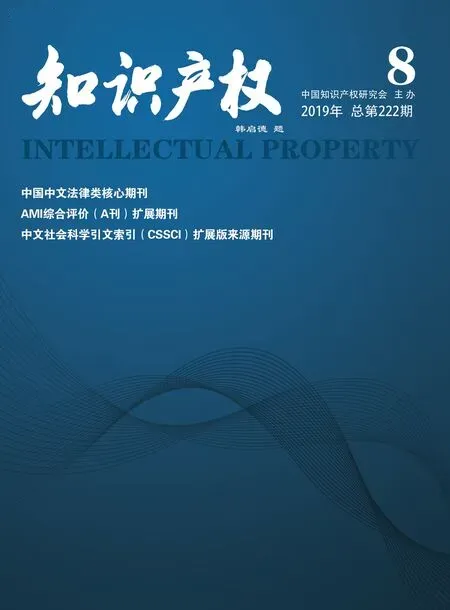限制注冊商標權:商標先用權制度的改革路徑
馮術杰
內容提要:2013年,我國在修改商標法時引入商標先用權制度,嘗試平衡商標在先使用人與在后注冊人之間的利益,以加強對于未注冊商標的保護。但這一制度設計未能從體系上對商標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關系作出合理安排,導致在先商標使用人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權益被忽略,并損害到相關公眾的利益。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摒棄注冊商標權絕對的觀念,按照尊重在先權益的原則,承認在先使用人在其商譽所及范圍內的排他性權益,并承認這種權益可以對抗在后的注冊商標。在該制度的設計和運行上,對于在先標識的權益保護應以其具有較高知名度為條件,避免走向商標使用取得制度。
盡管商標注冊制度是現代商標法的主流和基本制度,但未注冊標志的保護仍是各國法律中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以實行注冊制度的歐盟國家為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丹麥、英國及其他北歐國家都對未注冊商標給予不同程度的保護。①See Annette Kur ffamp; Martin Senftleben, European Trade Mark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p.90; Verena von Bomhard ffamp; Artur Geier,Unregistered Trademarks in EU Trademark Law, The Trademark Reporter, Vol. 107, Issue 3 (May-June 2017), pp. 677-700.正是為了加強對于未注冊商標的保護,我國在2013年修改商標法時確立了商標
先用權制度:商標注冊人申請商標注冊前,他人已經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先于商標注冊人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的,注冊商標專用權人無權禁止該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圍內繼續使用該商標,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適當區別標識。②《商標法》第59 條第3 款。一般認為,商標先用權的適用條件為:在先的商標使用為善意,商標在先使用早于在后注冊商標的申請日或初審公告日和使用日,在先使用的商標有一定的影響,在先使用人在原有范圍內繼續使用其商標,商標注冊人可以要求在先商標使用人附加適當的區別標志。參見杜穎:《商標先使用權解讀——商標法第59 條第3 款的理解與適用》,載《中外法學》2014 年第5期,第1358-1373 頁;蔣利瑋:《論商標在先使用抗辯——對新〈商標法〉第59 條第3 款的理解和適用》,載《中華商標》2013 年第11期,第33-38 頁;芮松艷、陳錦川:《〈商標法〉第59 條第3 款的理解與適用——以啟航案為視角》,載《知識產權》2016 年第6 期,第28-33 頁;馮術杰、李楠楠:《商標在先使用抗辯條款的適用條件》,載《中華商標》2017 年第8 期,第51-54 頁。該條款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于保護商標使用人的利益和應對商標搶注:對于法律上有明文規定的并且實踐中可以證明的商標惡意搶注行為,其注冊可以經由異議或無效程序而被阻卻;但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也未被司法實踐認可的“惡意搶注”行為或者有明文規定但無法證明的惡意搶注行為,則異議或無效程序無能為力;而且,還存在異議期或無效宣告請求期已過的情形,惡意搶注的商標也就效力既定了。此時,如果實際上的惡意搶注人在獲得商標注冊之后對在先的善意使用人提起侵權之訴,這種對于“實質正義”的顛覆是立法者和司法者所不能接受的。③參見馮術杰、李楠楠:《商標在先使用抗辯條款的適用條件》,載《中華商標》2017 年第8 期,第51-52 頁。當然,在不涉及搶注的情形,即在后的相同或近似商標被第三人善意注冊的情形,在先使用的商標也仍可以按照先用權制度繼續使用。一般認為,從法律性質上來看,《商標法》該條款是為商標在先使用人創設了一項針對注冊商標權的例外。④李揚:《商標在先使用抗辯研究》,載《知識產權》2016 年第10 期,第4 頁。盡管這并沒有為在先商標使用人創設一項排他性或獨占性民事權利,但仍然是一個有利于在先商標使用人的制度安排。
但是,如果從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角度看,事情剛好相反。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第(二)項(以下簡稱反假冒條款)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被認為是對未注冊的商業標志提供保護,這其中就包括未注冊商標。⑤理論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證了未注冊標識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對象的理由。黃暉:《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未注冊商標的保護》,載《中華商標》2007 年第4 期,第20 頁;張鵬:《我國未注冊商標效力的體系化解讀》,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5 期,第139 頁。參見馮術杰:《未注冊商標的權利產生機制與保護模式》,載《法學》2013 年第7 期,第39-47 頁。盡管由于法條用語的局限性,法院很多時候需要把商標認定為商品名稱或裝潢。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監字第15-1 號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監字第37-1 號民事裁定書。2017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對于該條款所適用的標志的范圍作了擴展,但其保護具有知名度的未注冊標志的理論基礎沒有改變。⑥孔祥俊著:《反不正當競爭法新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年版,第329-330 頁;王太平:《我國知名商品特有名稱法律保護制度之完善——基于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 條第2 項的分析》,載《法商研究》2015 年第6 期,第185 頁;姚鶴徽:《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反不正當競爭保護制度辯證與完善——兼評〈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送審稿) 〉》,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3 期,第131 頁。實踐中,只要相關商業標志在一定地域內持續使用一段時間,具有較高的商譽,就形成了受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正當利益。⑦根據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 條第1 款的規定,在認定商品知名度時,要求商品要在“中國境內”有一定知名度。但此處的“在中國境內”并不要求商品在全國境內知名。而“特有”主要是指商業標識具有顯著性,能夠在特定商品與服務之間形成固定聯系,起到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在山東心連心酒業有限公司與山東濟寧心心酒業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糾紛案中,心心公司提交的使用證據局限于山東省,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心心公司通過多種方式對產品進行了宣傳,在山東省特別是濟寧地區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知悉,認定為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并無不當。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62 號民事裁定書。因此,商標法上的先用權客體也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所保護的未注冊標志。從這個角度看,商標法允許在后注冊商標與在先使用標志的共存,這是一個有利于在后注冊商標的例外,但卻構成對在先使用人反不正當競爭權益的限制。
這就存在注冊商標權與反不正當競爭權益的協調問題。⑧陳紅:《商標權與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稱沖突問題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04 年第6 期,第70 頁;馮術杰:《知識產權條約視角下新型競爭行為的規制》,載《知識產權》2018 年12 期,第3-13 頁。這種利益沖突具體體現在:如果商標在先使用人援引反不正當競爭法禁止在后的商標注冊人使用其注冊商標,商標注冊人能否以商標有效注冊為由進行對抗?在在先使用商標的知名度所覆蓋的地域范圍內,如果第三人未經許可使用相同或近似的標識從而容易導致消費者混淆,這是侵犯了在先使用人的利益還是商標注冊人的權利?第三人應向商標在先使用人還是向在后注冊人承擔賠償責任?在商標先用權制度的設計和運行中,這些問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本文即從商標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關系角度對商標先用權制度進行分析,以期對其完善提出建議。
一、商標先用權制度的困境
《商標法》第59條第3款協調商標在先使用人與在后注冊人之間利益沖突的方法是:通過讓在先使用人附加區別標志的方式避免在先使用商標與在后注冊商標之間的混淆,以實現商標共存。但這種制度安排只是在法律層面讓沖突雙方做出某種妥協,而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或減少混淆可能性的發生。正如有學者所指出,“允許注冊商標權人毫無障礙地進入在先使用商標已經具有知名度和信用的營業圈進行經營,由于兩商標使用的商品以及商標本身相同或近似,即使先使用人附加了區別性標記,也難免發生注冊商標搭取在先使用商標知名度和信用、導致相關公眾混淆的現象”。⑨李揚:《商標在先使用抗辯研究》,載《知識產權》2016 年第10 期,第16 頁。因此,商標在先使用人的正當權益以及相關公眾不被混淆誤導的利益都將在這一制度安排中受到損害。⑩杜穎:《商標法律制度的失衡及其理性回歸》,載《中國法學》2015 年第3 期,第120 頁。
《商標法》第59條第3款只是設置了商標共存制度,但沒有明確規定共存商標在禁止權與損害求償權方面的沖突處理。在商標法的框架內,未注冊商標只有在是馳名商標的情況下才能禁止他人使用。這也就排除了在先使用人享有商標法上的請求權基礎的可能,而商標先用權作為注冊商標權的例外的性質,也就更表明其請求權基礎的缺失。實際上,當第三人未經許可在在先使用人商譽覆蓋的范圍內使用相同或近似的標識從而容易導致混淆,商標注冊人可以依據商標法起訴第三人求償,而在先使用人也可以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起訴第三人求償。商標法上的禁止權基于法律的擬制,其范圍覆蓋整個法域;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禁止權基于法律對于實際存在的商譽的承認,其僅存在于其知名度所及的范圍。但在事實層面,在后注冊商標很可能未在該地域內建立商譽。對于消費者來說,第三人使用的商標只能與在先使用的商標而非在后注冊的商標發生混淆,故第三人只可能侵害在先商標使用人的實際利益,造成與后者的混淆并利用其商譽。這種情況下,基于注冊制度而擬制的商標權就與基于使用制度而承認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益發生了沖突。
從橫向的制度比較來看,先用權制度廣泛存在于各國的專利法之中,但商標先用權制度尚屬少見。?參見我國《專利法》第69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二)在專利申請日前已經制造相同產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經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準備,并且僅在原有范圍內繼續制造、使用的。究其原因,雖然商標法與專利法設置先用權制度的目的都在于平衡在先使用人與在后知識產權所有人之間的利益,但該制度在專利法與商標法中所引發的利益格局卻是明顯不同的。在專利法中,允許在先使用人在原有范圍內繼續使用自己研發取得的技術成果,僅涉及在后專利權人與在先使用人之間的利益分配,對消費者利益不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在此情形下,消費者購買相關產品是著眼于產品的技術特征,無論產品來自專利權人還是在先使用人,其所依賴的技術是相同的。專利權人的產品提供好比一條大河,先用權人的產品提供好比一條小溪,任何第三人的侵權產品提供都損害專利權人的利益從而應歸入大河,大河與小溪兩者共同構成完整的市場貨源,利益劃分清晰。但在商標法上,先用權制度卻不能在在先使用人與商標注冊人之間實現利益的清晰劃分。與專利通過控制產品的提供來源來實現利益分配的機制不同,商標通過對標志的使用范圍控制來實現利益劃分,并以此保護消費者不對產品提供者產生混淆誤認這一第三方利益。在商標法的框架內,我國的商標先用權制度無法真正實現在先使用人與在后注冊人之間的標志使用范圍的劃分。首先,前述商標先用權在性質上是一種抗辯權,而注冊商標權是一種獨占權。這意味著,注冊商標權的效力是無所不在的,商標注冊人不僅可以在其“大河”內使用商標,也有權在在先使用人的“小溪”內使用其注冊商標,還有權對“小溪”內第三人的商標侵權行為主張權益。其次,且不論“小溪”與“大河”之間很可能存在聯通性,單是“小溪”內的兩個商標共存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消費者的混淆誤認。因此,先用權的設置對以商標權注冊取得為基礎的商標法形成了很大的沖擊,而在專利法領域并不存在上述問題。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實行商標使用取得制度的美國一直允許商標之間的共存,但其允許的是不同地域范圍內的相同或近似商標之間的共存。就兩個未注冊商標之間的沖突而言,普通法主要考慮商標使用的“時間先后性”與“地域性”,而“時間先后性”受制于“地域性”。這意味,因使用產生的商標權利效力僅及于商譽存在的地域范圍,且在該地域內以商標使用的時間先后確定權利歸屬,不同地域內商標權的產生不受時間的限制,即在不同地域內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可以同時產生商標權。就在先使用商標與在后注冊商標之間的沖突而言,美國法院的解決方案為,未注冊商標的使用人可以主張“限制地域”抗辯,即未注冊方得以在注冊方提出申請之前一直連續使用的地區內主張優先權,但同時該未注冊商標當事人的商標權會被“凍結”在該地區。?參見羅伯特·P.墨杰斯、彼特·S.邁乃爾、馬克·A.萊姆利等著:《新技術時代的知識產權法》,齊筠、張清、彭霞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468 頁。在In Re Beatrice Food Co案?參見李明德著:《美國知識產權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536 頁。中,美國法院指出,如果在先使用者在狹隘的商業地域使用,而在后使用者積極拓展商業范圍,并且首先提出了注冊申請,則在后使用者可以獲得在后的全國范圍內有效的注冊,但不包括在先使用者的商業區域。由此可見,商標先用人基于使用而獲得的在其使用范圍內的商標權優先于在后的注冊商標權,后者不能進入前者的地域范圍。
當然,這并不是說同一地域范圍內的商標共存總是被法律所禁止。基于當事人之間合意的商標共存是多數國家的法律所允許的,盡管相關公眾的利益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害。這是因為,商標權在性質上是一種私權,因而允許當事人依其意志進行處分。?參見《TRIPS 協議》前言。商標法將相關公眾的利益和商標權人的利益都列為保護對象,當兩者發生沖突的時候,就需要做出協調。同時,由于商標權人在共存的機制中是最直接的利益相關方,理論上可以推定他們不會作出有害于自身利益的安排,即如果兩個商標權人可以接受共存關系,就可以認定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的可能性是較小的,否則商標權人也同樣會是受害者。但是,法律硬性規定的商標共存與基于當事人合意的商標共存是迥然不同的,因為立法者難以像身處利害關系之中的商標權人那樣根據具體商業態勢決定共處格局,也就難以借助當事人的妥協安排實現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點。換個角度看,立法者硬性規定的商標共存制度,也就是對某個商標權設置限制或例外,因而要遵守對私權進行限制的一般原則:具有正當合理的目的并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就我國的商標先用權制度而言,保護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可以構成對注冊商標權限制的正當合理的目的,但問題在于,目前的制度安排不符合比例原則:不僅相關公眾通過商標識別商品來源和降低搜索成本的利益沒有得到保障,而且在先使用人的商譽及反不正當競爭的權益更是受到嚴重損害。究其原因,乃是立法者對注冊商標權的保護水平過高。因此,應當在商標先用權的制度中進一步增加對注冊商標權的限制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使得該制度更加公平和高效。
二、限制在后注冊商標權的合理性
要增強對在先使用商標的保護,就必須保障在先使用人基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享有的權益。首要問題就是,如果在先商標的使用人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其商譽所及的范圍內對在后的注冊商標主張禁止權,商標注冊人能否以注冊商標合法有效為由作為抗辯?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有學者認為,“當注冊商標專用權與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稱權發生沖突時,應重點保護注冊商標專用權”?孔祥俊著:《商標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原理和判例》,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365 頁。。實務界對該問題有過類似解讀。在瀘州千年酒業有限公司等與四川江口醇酒業(集團)有限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參見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長中民三初字第359 號民事判決書;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6)湘高法民三終字第30號民事判決書。中,瀘州酒業公司起訴江口醇公司侵害其注冊商標“諸葛亮”,江口醇公司反訴瀘州酒業公司侵害其知名商品特有名稱,一審與二審法院在審理兩者權利沖突時認為,注冊商標尚在有效期內,瀘州酒業依法享有商標專用權,商標權人正確、合法地使用注冊商標不構成對江口醇公司知名商品特有名稱的侵害。由此可見,法院認為注冊商標可以是反假冒訴訟的有效抗辯理由。從我國目前對于商標先用權制度的理解來看,也是認為注冊商標權的效力優先于在先使用人的權益,這就間接表明商標注冊能夠作為反假冒訴訟的抗辯理由。
從比較法上的經驗來看,歐盟商標制度中對在后注冊商標與在先權益之間的沖突也作了相關安排。首先,《歐盟商標條例》第9.2條在規定注冊商標權的同時也規定,歐盟注冊商標權不能損害他人在先取得的權利,這與《TRIPS協議》第16.1條的規定一致。?Regulation (EU) 2017/100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June 2017 on the 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旨在協調成員國國內法的《歐盟商標指令》第14.3條也規定,如果成員國法律承認在先使用的標志在局部地區的權利,則在后的商標注冊人無權禁止該標志在其權利被承認的區域內的繼續使用,比如商號權。?Directive (EU) 2015/243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15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 See Annette Kur and Martin Senftleben, op.cit.,p.435.其次,《歐盟商標指令》在其第XI章(成員國法律的效力)第2節(適用國內法以禁止歐盟商標的使用)中規定,如果成員國法律允許,效力僅及于局部地區的在先權益的所有人可以禁止在后的歐盟注冊商標在該地區的使用。?Article 138 of Regulation (EU) 2017/100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June 2017 on the 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這表明,歐盟商標法上對于僅存在于局部地區的在先權益,一方面允許其在在后歐盟商標注冊之后仍在原范圍內繼續使用,另一方面,在先權益人可以根據法律規定禁止在后歐盟商標在其權益所及地域范圍內的使用。?Charles Gielen and Verena von Bomhard (edit.), Concise European Trade Mark and Design Law,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7,pp.416-418.
日本與我國具有相同的法律體系與規則,《日本商標法》第32條同樣規定了商標在先使用權。日本國內對于商標注冊能否作為不正當競爭防止法仿冒的抗辯理由也存在爭議,不過,日本學者指出,雖然《日本商標法》第32條的規定與注冊商標不能作為競爭防止法抗辯理由的觀點存在抵觸之處,但在司法實踐中,日本法院在反不正當競爭訴訟中通常根據權利濫用法理認定被告的商標獲得注冊這一理由不能構成反不正當競爭之訴中的有效抗辯。?參見李艷:《論商標注冊能否作為仿冒訴訟的抗辯理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編:《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回顧與展望》,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6-238 頁。日本雖是大陸法系國家,但在解決注冊商標使用權與在先使用人禁止權的沖突問題上,與英國采取了同樣保護在先權益的做法。英國采用商標注冊主義與反假冒相結合的商業標志保護模式。在未注冊商標使用人依據反假冒之訴起訴商標注冊人時,商標注冊人能否以商標注冊抗辯,英國上訴法院在Inter Lotto (UK) Ltd v. Camelot Group plc案?See Inter Lotto(UK)Ltd v.Camelot Group plc.[2003]L.L.R.699,para. 31.中對該問題作出了明確闡述。法官認為如果原告沒有形成可受保護的商譽,則原告依據仿冒訴訟主張的權利得不到支持。如果原告形成了可受保護的商譽,則被告無權限制原告的權利。被告主張,其在商標法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高于且優先于原告在反仿冒法上的權利,即使反仿冒法上形成的權利優先于商標的注冊。被告的此種主張被法院否定。法院認為注冊商標權僅在反仿冒法上的權利產生于商標注冊之后,才優先于反仿冒法上的權利,在商標注冊申請日之前產生的反仿冒法上的權利優先于注冊商標權。此外,1994年《英國商標法》也明確規定,申請注冊的商標在英國的使用可以因為違反保護未注冊標志的法律而被禁止。?UK Trade Marks Act 1994,sec.5,cl.4.因此,在英國法律框架下,商標注冊不是對抗在先使用人反假冒法上權利的抗辯理由,在先使用人在反假冒法上的權利構成注冊商標權的限制,注冊商標所有人的商標權只能在該地域之外的范圍內行使。澳大利亞商標法也有相同規定,只是,在后商標的注冊可以成為免除無過錯的侵權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的理由。?Australian Trade Marks Act 1995, s 230(2). Robert Burrell ffamp; Michael Handler,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Registered and Unregistered Trade Marks, 35 Fed. L. Rev. 375 (2007), pp.375-397.
在反假冒訴訟中,商標在后注冊人能否以商標注冊抗辯還涉及注冊商標權的權利屬性問題。有學者指出,注冊商標權包括對商標的專用權和禁止權,前者是一種積極權能,后者是一種消極權能。實際上,使用商標(無論未注冊商標還是注冊商標)是一種自由,不需要法律的授權。這種自由的邊界就是他人的權利。?參見馮術杰著:《商標法原理與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78-179 頁。商標自愿注冊原則意味著即使商標不被注冊,市場主體仍具有使用某種商業標識的自由。1994年《英國商標法》第9部分第1款規定,商標所有人在商業標識上享有排他性的權利,未經他人允許使用該商標是侵權行為。英國上訴法院在Inter Lotto (UK) Ltd v. Camelot Group plc案?Wim Alberts, The (Positive) Right to Use a Trade Mark:The Kurt Geiger Case, Stellenbosch Law Review, Vol. 21, Issue 3, 2010,p.482.中指出,該規定并不意味著商標法賦予商標注冊人使用商標的權利,而是賦予其排除他人使用商標的權利。《TRIPS協議》第16條第1款將商標權的內容規定為:注冊商標所有人有權阻止第三方未經其同意而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標志,如果該使用容易導致混淆誤認。該規定也是從禁止權的角度界定商標權。因此,商標權的本質只是排除他人將相同或類似標志作為商標使用的禁止權。?Rush Annand ffamp;Helen Norman, Trade Mark Act 1994,Blackstone Press,1998,p.11.商標專用權是對其他市場主體的影響而言的,注冊人是否有權使用商標,取決于其他法律對他人權利保護的規定。?比如,甲是一個未注冊馳名商標的使用人,乙將該商標申請注冊了,不能認為商標注冊賦予了乙使用該商標的權利;甲將乙享有著作權的logo 申請注冊為商標,不能認為商標注冊賦予了甲使用乙的作品的權利;甲使用著乙的知名商品名稱,后來甲把乙的商品名稱申請注冊為了商標,不能因此認為商標注冊賦予了甲使用該標志的權利。因此,從注冊商標權的屬性來看,在先使用人禁止在后的商標注冊人對其商標的使用也不具有理論障礙。
此外,從商標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譽的保護來看,即使在商標權注冊取得制度下,商標上所承載的商譽也是商標法保護商標的基礎,這一點從商標法對描述性標志的保護可見一斑。《商標法》第11條規定,通用標識、描述性標識等其他缺乏顯著性的標志不能作為商標注冊,但同時又允許通過使用取得顯著特征的商標可以獲得注冊。將涉及到同行業競爭者普遍利益的描述性標志劃歸到某個經營者的名下,這種利益妥協揭示了商標法的價值追求——保護商譽。這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商譽的法理是一致的,只是前者賦予了使用者在整個法域的排他權而后者賦予使用者在局部地區的排他權。商標注冊制度是為宏觀效率的目的而建立商標使用秩序,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為保護真實商譽而確立商業標志使用秩序,當前者破壞了后者,鑒于商譽保護在商標法上的重要地位,效率目的的價值追求必須為商譽保護做出足夠的妥協。這就要求,在后商標注冊人在在先使用人建立商譽的地域內不僅不能使用其商標,也不應享有請求權,該地域范圍內的排他權應被完整地賦予在先使用人。為此,必須打破注冊商標權絕對的觀念,重視商標使用和商譽在商標法中的應有地位,反不正當競爭法賦予在先商標使用人的請求權不能被商標法取消。?王蓮峰:《我國商標權限制制度的構建——兼談〈商標法〉的第三次修訂》,載《法學》2006 年第 11 期,第126 頁。這種制度安排,不僅符合商標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之間的平等關系,也有著堅實的條約基礎。
三、限制在后注冊商標權的條約基礎
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在注冊商標權的保護方面規定了保護在先權益的義務,也為按照尊重在先權益的原則處理注冊商標權與在先權益關系的制度安排留下了足夠的空間。《TRIPS協議》第16條第1款,一方面規定了商標注冊人的排他性權利,另一方面規定了注冊商標權不應損害任何在先權利,并明確注冊商標權不影響WTO成員方規定權利可以基于使用取得。《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10條之二第1款規定了締約國有義務為國民提供反不正當競爭的有效保護,其第3款所列舉的不正當行為的類型就包括混淆行為:即以任何手段與競爭者的營業場所、商品或工商業活動造成混淆的行為。因此,商標在先使用人基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享有的禁止他人混淆行為的權益構成可以對抗在后注冊商標的在先性權益。
此外,根據《TRIPS協議》第17條,WTO成員方可以對商標權規定有限的例外,條件是這些例外考慮到商標所有人和第三人的正當利益。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分別針對歐盟發起的地理標志WTO爭端解決案件?See WT/DS 174/R, WT/DS/290/R. 參見馮術杰:《歐盟地理標志法律制度述評——寫在DS174、DS290 兩案裁決之后》,載馮術杰著:《知識產權法:國際的視野與本土的適用》,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中,專家組對這一條款作了解釋和適用。該案中,歐盟的地理標志保護條例規定,在先的注冊商標可以與在后的地理標志共存。這看似是在地理標志的保護制度中為商標權人的利益而設置的對地理標志權的例外,但美國和澳大利亞認為:從商標權保護的角度看,這是為地理標志權人的利益而對商標權設置的例外。美國和澳大利亞認為這違反了《TRIPS協議》第16條關于注冊商標權利內容的規定。歐盟則認為,這盡管對商標權作出了限制,但該限制符合《TRIPS協議》第17條針對商標權例外的規定,因此是條約所允許的。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在裁定中認定,歐盟為地理標志注冊人的利益設置的對商標權的例外符合《TRIPS協議》第17條規定的條件。其一,這一例外是有限的,因為,地理標志產品的產區、生產者、產品數量都是有限的,因而地理標志相關的農產品都必須符合相關的產品品質和管理規則;其二,這一例外考慮到了商標權人的利益,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條約要求的是“考慮到”而不是充分保護,而且歐盟另有關于產品標簽等方面的規定有助于區分商標與地理標志產品;其三,這一例外也考慮到了第三方的利益,這里主要涉及地理標志產品生產者的正當利益(作為特色農產品的生產者,他們有正當利益使用地理標志于其產品上)和相關公眾的利益(他們有權通過地理標志識別特色農產品)。允許在先商標使用人在其商譽所及的范圍內享有完整的排他權,這無疑構成在后注冊商標權的例外,但這種例外以在先使用人的商譽范圍為約束因而是有限的。這是在公平原則基礎上兼顧比例原則的利益平衡方式,考慮了注冊商標權人的利益和相關公眾的利益。?參見劉麗娟:《我國商標注冊制度的問題和完善》,載《電子知識產權》2016 年第4 期,第75 頁。此外,與《TRIPS協議》就著作權和專利權的限制所作出的規定相比,其就商標權的限制所設置的條件是最為寬松的,因為對于前兩者的限制不能與著作權或專利權的正常實施發生沖突,而對于商標權的限制沒有這個要求。?See Annette Kur and Martin Senftleben, op.cit.,pp.53-55.因此,承認在先使用人在其商譽所及范圍內的排他權,這種對注冊商標權的例外設置符合《TRIPS協議》第17條的規定。
在我國,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注冊商標、企業名稱與在先權利沖突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在先權利包括著作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企業名稱權等,該條非窮盡性的列舉沒有明確將《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意義上的權益納入其中,但也沒有明確排除。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16條規定,《專利法》第23條所稱的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包括:商標權、著作權、企業名稱權、肖像權、知名商品特有包裝和裝潢使用權等。類比商標法,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所保護的未注冊標志沒有理由不能構成相對于注冊商標的在先權益。因此,我們應摒棄注冊商標權絕對的觀念,將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先用人權益與注冊商標權同等看待,按照保護在先權益的原則處理兩者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完善商標先用權制度。?實行商標注冊制度的歐盟,就是按照保護在先權益的原則平等地處理注冊商標與未注冊商標之間的關系,而沒有在兩者之間建立效力等級關系。Verena von Bomhard and Artur Geier, supra note 1.
四、商標先用權制度的完善
2013年商標法修改中引入的商標先用權制度,盡管從商標法的角度看是對注冊商標權設置了例外而對在先使用人賦予了一定的權益,但根本上仍是維護在后注冊商標權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它允許在后注冊商標與在先使用商標在同一范圍內共存;另一方面,它將共存范圍內的排他性權益賦予了在后商標注冊人。這實際上造成了對在先使用商標商譽的侵害甚至剝奪,并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該制度將商標法的位階置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之上,將注冊商標權的位階置于反不正當競爭權益之上,抹殺了商標在先使用人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權益。
要解決這一制度困境以實現注冊商標與未注冊商業標識的公平保護,就要采取更徹底而明確的改革方案:承認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標識在其商譽所及范圍內的排他性權益,否定在后注冊商標在該范圍內的效力。這就要求摒棄注冊商標權絕對的觀念,充分重視保護正當商譽的重要性,按照尊重在先權益的原則確立未注冊標識相對于注冊商標的優先性。這一解決方案可以有效保護正當的在先權益,保護相關公眾不就商品來源和品質被誤導的利益,從而也維持固有的競爭秩序與消費者認知秩序。這種解決方案的確對注冊商標權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這種限制是有限的,具有正當合理的目的,并考慮到了商標注冊人的利益和相關公眾利益,并符合比例原則。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一方面,應當在《商標法》中明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的保護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另一方面,應當明確在后注冊商標的權利范圍不包括在先使用商標的知名度所及的范圍。《商標法》第59條第3款關于在先使用人有義務附加識別標志的規定也就當然應當刪除。根據上述方案完善后的商標先用權制度,其在設計和運行上都應堅持對于在先標識的知名度要求。這樣就可以避免走向商標權使用取得制度,避免與鼓勵商標注冊的效率目標相違背,也避免對注冊商標權的不當限制。
就保護未注冊商標與維護商標注冊制度的關系而言,我國長期以來實行商標權注冊取得制度,鼓勵商標注冊,這有利于保障商標使用的宏觀秩序從而提高商標制度的效率。如果為未注冊商標提供完善、全面的保護則會顛覆商標權注冊取得制度。因此,我國應將反不正當競爭法所保護的未注冊商業標志的范圍僅限于具有一定影響或商譽的標志,這樣就不會產生與鼓勵商標注冊相反的后果。因為盡管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未注冊商標可以獲得保護,但這種保護完全依賴于商標使用的證據。未注冊商標的使用人每次主張權益都必須對商標使用的存在、范圍、存續等提供證據,而一旦商標使用有減退或證據保存不善,其權益就得不到支持。?英國的反假冒之訴中,原告必須證明在起訴之前存在必要的商譽,盡管商譽是根據個案確定的事實問題,但通常要考慮兩個方面的問題:(1)地域問題,原告必須證明在主張權利的管轄區內存在商譽;(2)區別性問題,爭議商標必須具有足夠的區別性,使其能夠表明特定原告的商譽。See Rembert Meyer-Rochow, Passing Off-Past, Present and Future, 84 Trademark Rep. 38, 63 (1994),pp.45-46.相比之下,商標注冊人的權利行使只需一張商標注冊證。因此,商標注冊仍然會是商業標志保護的最高效途徑。2017年修改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仍堅持對于受保護標志的知名度要求,也這充分體現了立法者維持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商標注冊制度之間體系化關系的意圖。
對于商標先用權制度中“有一定影響”這個條件的理解,理論和實踐中還存在一定分歧。有觀點認為,在《商標法》第32條的適用中,如果某商標遭他人惡意搶注,則該事實本身即說明該未注冊商標具有一定影響,因而該條款對知名度的要求具有彈性;第59條第3款中的“有一定影響”這個條件對知名度的要求也應當具有彈性。?參見曹新明:《商標先用權研究—— 兼論我國〈商標法〉第三次修正案》,載《法治研究》2014 年第9 期,第22 頁。對商標法的這兩個條款確需作體系化解釋,但值得注意的是,《商標法》第32條和第59條第3款的理論基礎和規范目的并不相同。前者的目的在于防止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被他人搶注。因此,“具有一定知名度”就是該條款適用的必要條件。但司法實踐中,為了有效打擊惡意的商標搶注,誠實信用原則被有意無意地納入到了該條款的解釋中,在能夠證明搶注者有違誠信的情況下,立法者所設定的知名度要求也就被降低了。?比如“家家酒”案,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6)高行抗終字第474 號行政判決書。因此,《商標法》第32條在司法實踐中有兩個理論基礎:阻止在先使用并有較高商譽的商標被搶注,阻止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商標搶注。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商標先用權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護已經形成較高商譽的商標得以繼續使用并得以禁止他人的假冒,因此,唯具有較高的知名度的標志才能成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客體,對在后注冊商標權形成限制。所以,在商標先用權制度的實施中,必須堅持知名度的門檻,避免走向商標權使用取得制度與反不正當競爭法適用的泛道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