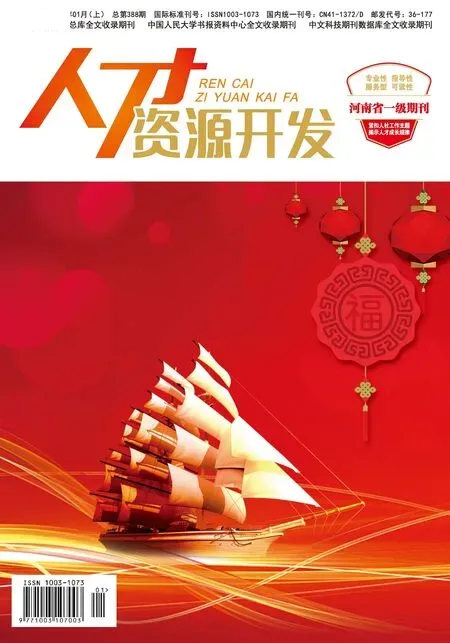父親的金盞菊
□侯德云
我有兩個家。早年跟父母兄弟在一起,是一個家;現在跟妻子女兒在一起,又是一個家。
我有兩個家,三個庭院。
我喜歡庭院。我在鄉村長大。在鄉村,庭院是“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從沒見過誰家沒有庭院。沒有庭院,在哪兒養豬呢?在哪兒養雞、養鴨、養狗、養貓呢?
從出生到12歲,我的家,由三間土房和一個狹長的庭院組成,很簡陋。院里有豬圈,有雞窩,有露天廁所,還有一個長方形的菜窖。菜窖是活窖。活窯的意思是可以打開蓋子,鉆到里邊去,像地窨子一樣。入冬以前,菜窖里裝滿了蔬菜,白菜、蘿卜、胡蘿卜、土豆等。它們是菜也是糧。
冬天的雪后,我把菜窖頂上的雪掃干凈,撒上一把高粱,用籮筐捉麻雀。魯迅先生小時候也干過這事。對魯迅先生而言,可能是個游戲,對我卻不是。我希望能多捉幾只麻雀,大小也是一口肉啊。
看三三兩兩的麻雀在籮筐邊上蹦跳,我那不爭氣的肚子,一陣陣嘰里咕嚕。
好日子終于來了。1979年,在明媚的陽光下面,我家蓋了四間新房。新房是磚石平房,有一個接近正方形的庭院,院墻也是磚石的。院子里依舊有豬圈、雞窩和廁所,都在西側。東側是菜園。父親種了兩畦黃瓜和一畦西紅柿,也有蔥、辣椒和茄子。鄉村人家大多把黃瓜和西紅柿當水果吃,自然要種得多些。讓我感到奇怪的是,父親還在菜畦的邊緣種了一溜兒草本花卉。春天和夏天,院子里總有盛開的花朵,各種顏色,黃色、紅色、粉色、紫色。我不認識那些植物,只是覺得好看。現在知道了,其實只有三個品種,金盞菊、百日草和紫茉莉。
種得最多的是金盞菊。要是父親能活到現在,我一定會問他,為什么要種那么多金盞菊?是不是喜歡它金燦燦的顏色?是不是喜歡它開呀開呀開呀總也開不敗的花期?
搬到新房之后,父親再也不為全家人的吃飯問題發愁,再也不為幾個哥哥的婚事發愁。大概就是這個原因,父親才有了種花的閑心,才種了好多金盞菊。父親心中是不是藏了一個金燦燦的心愿?
鄉村習俗,夏天,家家戶戶都喜歡在庭院里吃晚飯,主要是圖個涼快。
我還記得,父親吃飯的座位永遠不變,坐北向南,他一抬頭就能看見花朵和蔬菜。夕陽的余暉把天際涂成金盞菊的顏色。父親話不多,但臉上的表情,總是笑瞇瞇的。
搬進新房那年,父親69歲,在我眼里,已經是很老很老的老人。現在我才想到,父親的笑瞇瞇,便是書面語中的“慈祥”。
很多年以后,我對植物學深度癡迷,木本、藤本、草本,都有“研究”,對父親的“最愛”,自然也了解頗深。到這時我才知道,金盞菊有很強的自播能力,它能自己照顧自己,你種它一回,它便一年一年又一年,向你綻開笑臉。

父親在內心深處,是不是也期待他的兒女,能像金盞菊那樣“好養活”呢?
我喜歡有花的庭院。金盞菊盛開的季節,我的心情也金燦燦。
那時候我不會想到,30年后,我在瓦城擁有了一方自己的庭院。庭院不大,70多平方米的樣子,有矮墻,有涂成灰白色的鑄鐵柵欄。為了這方庭院,我前后設計過五種方案,還研讀過明代造園家計成的大作《園冶》。最后確定的方案是,院中設木制茶座,有半圓和橢圓形的花池,有沿墻舒展的灌木和喬木。
我在庭院內外栽下不少木本、藤本和多年生草本植物,有古典園林常見的白玉蘭、貼梗海棠、毛竹、牡丹、紫藤,還有櫻花、楓樹、龍爪槐、香花槐、薔薇、鳶尾、蜀葵等。
我的庭院應該叫花園才對。閑暇時,我常在花園里澆水、施肥、剪枝。從春到秋,我喜歡在黃昏時分,到花園里坐坐。喝茶,讀書,或者跟來訪的朋友聊天。我覺得這樣的生活才有滋味。
為紀念改革開放30年,我寫過一篇小文,叫《庭院》。寫的是父親的兩個庭院和我的花園。前者說得詳細,后者寥寥幾筆。
有一個細節,《庭院》里沒寫。現在該寫了。
我在花園一角,種植了一大叢金盞菊。我像父親一樣“瀟灑”,種了就種了,以后是不是長得好,是不是開得好,全靠它自己。
轉眼十年,金盞菊年年長得好也開得好。
我有時會在晚霞滿天的瞬間,在金盞菊旁邊小坐片刻,一朵朵看它。
我對身邊的妻子說:“金盞菊,別名金盞花、黃金盞等。原產歐洲西部、地中海沿岸、北非和西亞。頭狀花序,單生莖頂。舌狀花,一輪或多輪,平展或卷瓣,金黃或橘黃。花蕊多為褐色,也有深紫色和綠色。一年或越年生草本,喜光照,耐瘠薄……”
我是在背誦植物書上的金盞菊條目,腦子里卻浮現出父親慈祥的面容,活生生,每條皺紋,每根胡須,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那天上的父親,你知道嗎?你最小的兒子,為你種了十年金盞菊。
父親你知道嗎?像你期待的那樣,我終于把自己也變成了一棵金盞菊:“喜陽光,耐瘠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