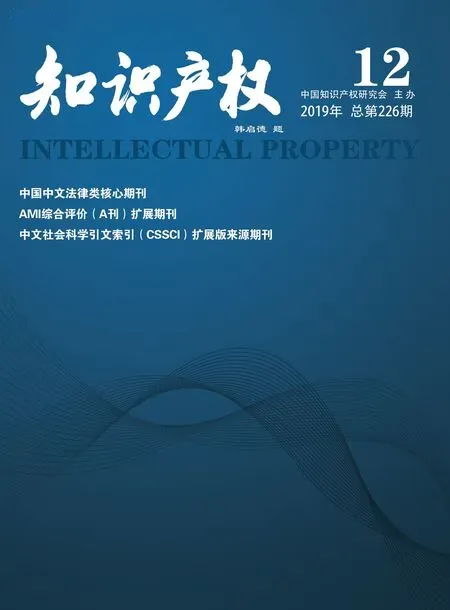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制度檢視及完善
——以《TRIPS協議》義務的澄清為視角
賀志軍
內容提要:“入世”時我國為“接軌”而修改有關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規則,其中對《TRIPS協議》義務的解讀在今天看來,體現出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有必要進行澄清和重新進行制度檢視。在實體救濟上,《TRIPS協議》并非禁止行政裁決作出“責令賠償損失”的決定,人為地撕裂“責令停止侵權”與“賠償損失”兩類實體救濟為不同程序,勢必使行政裁決的“分流閥”功能先天不足,故對行政裁決武裝“賦能”勢在必行。在行權程序上,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程序“遵守實質相當原則”之《TRIPS協議》義務履行長期被忽略,急需推動其司法化改造進程。在司法審查上,《TRIPS協議》的義務設定具有履約“彈性”,我國需引入“當事人選擇權”這一新變量,建立對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差異化司法審查制度。
一、問題的提出
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制度是我國行政執法與司法雙軌保護的重要組成內容,現階段面臨著重大的制度發展契機。2018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對商標、專利行政執法體制進行從“管執合一”向“管執分離”的重大改革,把“商標、專利執法職責”交由新組建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隊伍”承擔,而國家知識產權局“負責商標、專利、原產地地理標志的注冊登記和行政裁決,指導商標、專利執法工作……”。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健全行政裁決制度加強行政裁決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要重點做好“知識產權侵權糾紛和補償爭議”等方面的行政裁決工作,并部署“要適時推進行政裁決統一立法,以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形式對行政裁決制度進行規范”及“健全行政裁決救濟程序的銜接機制”。①《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健全行政裁決制度加強行政裁決工作的意見〉》,載http://www.gov.cn/xinwen/2019-06/02/content_5396932.htm.,最后訪問日期:2019 年12 月1 日。在這一全新的背景下,檢視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制度所存在的問題,無疑是當下值得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
“行政裁決”概念在理論上曾有過多種不同的表述界定,②參見王小紅著:《行政裁決制度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 頁。《意見》將其定義為“行政機關根據當事人申請,根據法律法規授權,居中對與行政管理活動密切相關的民事糾紛進行裁處的行為”。學界對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制度有過不少研究,議題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關于其正當性的研究。如有論者從行政裁決是“司法機關解決侵權民事糾紛的一種補充”③參見魏瑋:《知識產權侵權糾紛行政裁決若干問題研究》,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7 年第4 期,第51-60 頁。角度來為其辯護,而有的論者則展開批駁解構并提出由“有權社會機構裁決”來取代。④參見陳錦波:《我國行政裁決制度之批判——兼論以有權社會機構裁決替代行政裁決》,載《行政法學研究》2015 年第6 期,第86-98 頁。二是關于其程序設計的研究。針對目前行政裁決與司法救濟程序之關系較為混亂的現象,有論者指出,只有對行政裁決的設定進行徹底改革,行政裁決糾紛的訴訟選擇問題才會得到根本解決;⑤參見韓思陽:《行政裁決糾紛的訴訟選擇》,載《政法論叢》2014 年第4 期,第97-104 頁。有論者關注專利侵權行政裁決及其司法審查、確認不侵權訴訟三種程序之間的銜接;⑥參見夏淑萍:《專利侵權糾紛行政裁決的程序協調及相關問題之解構——以蘋果公司訴北京市知識產權局及其關聯案件為例》,載《知識產權》2017 年第5 期,第52-60 頁。還有論者就商標行政裁決“循環訴訟”怪相主張對行政裁決施以合理性司法審查強度。⑦參見彭情寶:《論司法審查行政裁決的強度——基于商標行政裁決“循環訴訟”的分析》,載《學術論壇》2014 年第9 期,第93-96 頁。三是關于其適用與實效的研究。有論者提出了行政裁決制度的存亡律與活躍度理論,指出行政裁決設定領域退縮存在主觀上行政主體避免遭行政訴訟和客觀上適應避免公權過度干預私權領域及行政權過度擠壓司法空間的發展趨勢之雙重原因。⑧參見葉必豐等:《行政裁決:地方政府的制度推力》,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2 期,第5-18 頁。在實踐層面,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適用呈萎縮趨勢;實務界對此存在迥異的態度,如來自法院的觀點多主張“專利侵權糾紛應當以統一的司法保護取代行政保護,只保留行政調解的糾紛解決職能”,⑨崔寧:《〈專利法〉第四次修改中的專利行政執法相關問題研究》,載《中國知識產權》2017 年第3 期,第48-51 頁。這里的行政保護無疑包括行政裁決在內;來自行政部門的觀點則主張維護專利侵權行政裁決制度。通觀現有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發現,有關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一些基本問題尚未得到清楚、有力的闡釋。比如,行政裁決在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究竟該扮演何種角色?其角色到底是該強化還是弱化?對行政裁決程序如何進行法律規制?對行政裁決又該如何進行司法救濟與銜接?等等。現有研究成果更是鮮見有以《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以下簡稱《TRIPS協議》)相關執法義務為約束條件來探討的,如該協議第41.4條對行政執法程序設定的司法審查義務,第49條和第50.8條對涉及裁決“民事救濟”或“臨時措施”之行政執法程序所設定的遵守與司法程序“實質相當原則”之義務。作為WTO成員,《TRIPS協議》關于“知識產權執法”的義務規定是檢視和完善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制度的國際基準。因此,結合前述問題,本文擬將《TRIPS協議》相關義務的澄清及約束作為主要的分析視角,就如何進一步優化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制度展開探究。
二、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實體救濟
(一)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中的民事責任類型
“行政行為”概念的外延主要有兩種劃分法:“二分法”將其分為“行政立法”和“行政執法”;而“三分法”則將其中的“行政執法”再一分為二,即把行政裁決性質的行為獨立為一類稱為“行政司法”,剩余的仍稱為“行政執法”。⑩參見馬懷德主編:《法律的實施與保障》,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128-130 頁。很明顯,“二分法”采廣義的“行政執法”概念而“三分法”則采狹義的概念。通常所說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保護,其法益性質實際上存在著到底是公法益還是私法益的根本差異,故采用“三分法”以區分“行政執法”與“行政司法”這兩個子概念更為準確,前者保護知識產權公法益而后者保護知識產權私法益。?2018 年3 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對知識產權綜合執法作出了頂層改革規定,不僅實現了知識產權管理“二合一”,而且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管執分離”:國家知識產權局作為管理機關主要職責包括負責商標、專利、原產地地理標志的注冊登記和行政裁決,指導商標、專利執法工作等;“指導”而不再“實施”專利、商標行政執法,商標、專利執法職責交由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隊伍承擔重新組建。在這種架構下,行政執法與行政裁決保護知識產權法益的公私屬性有了明顯的分化與區別。從本質上說,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正是通過“行政司法”程序來實現對侵權之民事責任救濟,相應的實體救濟便是指依制度規范所能為權利人提供的實體意義上的救濟形式,即具體的民事責任形式。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如何選擇合適的民事責任形式?學界提出的“知識產權請求權”理論對此可提供很大啟發。
知識產權請求權是指在知識產權被侵害或者有被侵害之虞時,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基礎性權利,請求相對人為或不為一定行為,從而保障其合法權益的一種實體救濟權;其內容可“類型化”為三種具體的請求權,即防衛請求權(停止侵害危險請求權)、保全請求權(停止侵害請求權)與補救請求權。?參見李揚著:《知識產權法基本原理(1):基礎理論、標識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08 頁。這種“三分法”類型系依據侵權與救濟的時間關系(救濟是在侵權之前、之中還是之后)來劃分的;與之對應,如果行使這三種請求權仍不能實現民事義務的履行,則在雙軌保護框架下“可以起訴或請求行政處理”,從而轉化為具有國家強制力的“三分法”民事責任。防衛責任是針對知識產權有遭受侵害之虞時可以要求他人承擔的責任,主要體現在臨時禁令上;保全責任是為通過制止“實際侵權”行為而實現對知識產權的權利保全,體現在民事司法“判決停止侵害”和行政機關“責令停止侵權行為”上;補救責任源于相對人承擔由知識產權原義務所派生出來的新義務,主要體現在賠償損失上(有時還包括不當得利返還或使用費支付)。
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對“三分法”民事責任形式有不同的選擇。其中,鑒于防衛責任系面向未來之“未然”侵權,其適用較保全、補救責任更為嚴格方稱得上“正當”;為了不給他人的行動自由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保障臨時禁令頒行標準的嚴格和統一是必要的,故即使在“雙軌”保護模式下,也只有司法“單軌”被依法賦予適用防衛責任的決定權。就民事保全責任來說,《商標法》第60條、《專利法》第60條和《著作權法》第48條均有行政“責令停止侵權行為”的規定,但決定主體的受羈束性抑或享有裁量性差異則體現出法律對不同知識產權領域的行政裁決在“賦權”上的有別。就民事補救責任而言,現行法上賠償損失之適用卻“逸出”了行政裁決程序而進入相關的“行政調解”程序之中;對此,頗值得從理論上深入探討。
(二)民事補救責任之實現:賠償行政裁決抑或賠償行政調解
1.與《TRIPS 協議》“接軌”驅動下知識產權侵權賠償規范變動述評
“入世”前,《專利法》就專利侵權糾紛規定專利權人或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商標法》就注冊商標侵權糾紛規定商標注冊人或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且均有“責令賠償損失”規定。這里法律規范上的“處理”當然地屬于“行政處理”;因其具有主體的行政性、對象的特定性(系與行政管理活動密切相關的知識產權侵權糾紛和補償爭議這一特定的民事糾紛)和結果的非終局性,實質上正是《意見》所說的“行政裁決”,?值得說明的是,2019 年《關于健全行政裁決制度加強行政裁決工作的意見》提出“嚴格規范制度表述”的措施,即起草、修改法律法規時,對行政機關通過行政裁決化解民事糾紛事項作出規定的,應當明確使用“作出行政裁決”的表述,不能使用“作出處理”“作出決定”“作出裁定”“作出裁處”等模糊表述,以免在實踐中產生歧義和混淆。其可以像民事司法那樣來獨立自主地實現損害賠償的補救責任。但是,“入世”時出于“接軌”驅動的原因,分別都取消了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對專利侵權、工商管理機關對商標侵權“責令賠償損失”的規定;相應地修改為關于賠償“行政調解”,即在“行政處理”(實為“行政裁決”)的同時,只能根據當事人請求另行就賠償數額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可提起“民事訴訟”。需要提及的是,在《專利法》第四次修正過程中,國家知識產權局于2012年8月9日公布的“征求意見稿”草案中曾提出“回到過去”的思路,即“擬規定授予專利行政執法機關損害賠償判定權”;但2018年12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公布和公開征求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正案(草案)》?《專利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見》,載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2019-01/04/content_2070155.htm,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1 月10 日。,否定了這一修正思路。
由上可見,損害賠償規則以“入世”為分水嶺,呈現出由行政裁決與司法?通常意義上,行政執法與司法構成知識產權的雙軌保護,這里的行政執法是廣義的;在狹義的行政執法概念意義上,就知識產侵權的民事糾紛而言,其“雙軌”則應是指行政裁決與司法。“雙軌”救濟走向實質意義上的司法“單軌”救濟(輔以損害賠償的“行政調解”);這種轉型背后的直接原因是《TRIPS協議》第45條的“損害賠償”規定使然。然而,本文認為,我國當時修法的初衷是“認為”將損害賠償判斷權還給司法機關才是與WTO要求接軌的,事實卻是我國對該條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誤讀。《TRIPS協議》第45條只是對司法機關“賦權”,亦即“應當有權責令賠償損失”(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order……damages),其本身并未強調是“排他性”的“賦權”;行政裁決中“責令賠償損失”作為對民事責任的一種實現方式,本來是《TRIPS協議》并未專門調整和設定義務的,甚至是其第49條所預設允許的,充其量也只有這種行政裁決的程序應當相對于民事司法程序來說“遵守實質相當原則”的義務要求而已。而反觀我國立法修改在行政裁決的實體救濟上對“責令停止侵權行為”與“責令賠償損失”的態度差異,以及新一輪修法過程中就要不要賦予行政機關在行政裁決中“責令賠償損失”權猶豫不決,足見某種程度上我國在雙軌保護的責任規則設置上的立場不一致和理論不自覺。
2.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責令賠償損失”的合理性
《意見》指出,行政裁決“具有效率高、成本低、專業性強、程序簡便的特點”,有利于促成矛盾糾紛的快速解決,發揮化解民事糾紛的“分流閥”作用。現行的損害賠償司法“單軌”救濟這種法律制度安排亦是“利弊兼有”:“利”是有助于實現“司法權威定價”?參見孔祥俊:《積極打造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升級版”——經濟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的新思考》,載《知識產權》2014 年第2 期,第3-16 頁。,在實踐中當事人進行談判或發警告函等過程中運用先例判決的情形并不鮮見;?參見謝曉堯:《著作權的行政救濟之道——反思與批判》,載《知識產權》2015 年第11 期,第3-16 頁。“弊”是造成行政之“軌”在補救責任救濟上制度性“先天無力”,即就損害賠償替代性地進行所謂“行政調解”,難以發揮行政管理機關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應有的救濟作用。從應然意義上而言,行政裁決必須具有在結果意義上解決所涉糾紛的基本功能,如此方能體現其存在的價值;為此,必須從法律規范層面對其充分“賦能”,即讓其有權提供實現糾紛解決所必需的實體救濟手段。賠償損失無疑是“民事責任”實現的重要方式之一(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方式);基于法律責任的內容“通約性”特點,賠償損失在現行法的民事、行政、刑事三類責任的實現中均受到很大關注。
在刑法上,存在“判處賠償經濟損失”和“責令賠償損失”的不同制度。《刑法》第36條第1款規定判處賠償經濟損失制度,即法院在依法給予犯罪分子刑事處罰之外,就被害人所遭受的經濟損失“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第37條規定責令賠償損失制度,即對于犯罪情節輕微而免予刑事處罰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據案件不同情況給予包括賠償損失在內的非刑罰措施處理。這里“判處賠償經濟損失”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結果,只是民事責任實現的方式。“責令賠償損失”并不以被害人提起民事訴訟為前提,而是以免除刑罰為前提;實際上不只是民事責任的實現方式,同時也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637 頁。還有學者認為,這里的“責令賠償損失是承擔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蔡雅奇:《責令賠償損失也是承擔刑責的一種形式》,載《檢察日報》2012 年12 月10 日第6 版。
在行政法上,“責令賠償損失”既有一般法上的存在空間,又有特別法上的具體制度規定,但總體上呈逐漸式微的特點。《行政處罰法》第7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因違法受到行政處罰,其違法行為對他人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這里“民事責任”的“依法承擔”取決于“法”的設計與具體規定,當然包括那些存在規定有“責令賠償損失”的行政法律規范。以《檔案法》為例:該法于1987年制定及經過1996年、2016年兩次修正,一直都規定有“責令賠償損失”。學界對其法律性質一直存在爭議,分歧觀點有:民事法律責任說;具體行政行為說;行政處罰說;綜合說(認為根據責任的不同可能存在民事法律責任和行政處罰兩種責任);表述不當說(認為應表述為“檔案所有人有權要求造成損失的一方予以賠償”以還原其民事法律責任的本意)。?參見張世林:《關于〈檔案法〉中“責令賠償損失”的法律性質認定探討》,載《檔案學通訊》2003 年第2 期,第42-44 頁。然而,2016年修訂的《檔案法》第24條第2款仍有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責令賠償損失”的規定,2017年國務院修訂的《檔案法實施辦法》第28條也有類似規定。
現行的專利和商標侵權行政裁決在實體救濟上存在內在的“悖論”:一方面,本質上它應是民事責任實現的一個完整手段;另一方面,形式上它卻被現有規則生硬地分裂為行政裁決行為和行政調解行為兩個性質不同、救濟殊途且常常分離存在的“子程序”。行政裁決行為系依“權利人請求”而為,對此可以有行政訴訟;行政調解行為則必須是權利人與侵權人“雙方合意”才能進行,對不愿調解或調解不成的就無權處理,即使賠償調解達成協議但之后卻不履行的仍需要通過民事訴訟來解決。從侵權救濟的相對完整解決看,侵權之行政判定與行政救濟之間分離脫節,導致救濟不足;此時的行政裁決程序只能構成“半軌”,導致對“權利人請求”的“內容實現”在程序處理上只能達到“一半”的半成品狀態。這種在單純的民事責任之行政裁決意義上的所謂“雙軌保護”(或許稱之為“一根半軌道保護”更符合實際)其設計偏離了“雙軌”保護的初衷。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立法者將專利和商標侵權行政裁決誤解為是知識產權公法益保護意義上的狹義“行政執法”行為,因而對行政權介入單純的私法益(知識產權是私權利)持有內在的“顧忌”;殊不知,這種理解不當地忽略了此類行政裁決行為所具有的“行政司法”的特殊屬性。
學界亦不乏有將“責令賠償損失”權力排除在“行政執法權”之外的觀點。?參見李玉香:《完善專利行政執法權之再思考》,載《知識產權》2013 年第4 期,第69-72 頁。本文認為,這種觀點并未關注到“行政執法”概念的廣義與狹義之區分,實際上應當排除“責令賠償損失”的只是為保護公法益的狹義“行政執法權”情形。如果維持真正的“雙軌”保護,那么在應然意義上,法律特別授權的“行政裁決”完全可作為與司法相對獨立的、國家行使公權力的糾紛解決方式,將其全面“武裝”起來,發揮其優勢;相應地,行政“責令賠償損失”可以納入知識產權保護規則設計之中。理由是:其一,這是實現權利人要求的民事責任所需。現行法上的“行政處理”是“應權利人請求”而啟動程序的,卻依法只能處理保全責任(即責令停止侵權)這一半的“請求”內容,而將“補救責任”(即賠償損失)從“請求”中剝離;雖然這種制度設計在客觀上有利于通過案件審理來實現賠償數額的“司法定價”,卻根本談不上有效率,對請求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其問題解決上的不徹底性乃是制度設計帶來的固有弊端。其二,這是行政權這一公權力在知識產權民事爭議的行政裁決中完整、有效行使所需。現行法的“雙軌”保護設計已經視行政救濟具有與司法救濟在權能上的“相當性”;如果賦予某“軌”處理民事責任和提供相應民事救濟,就應當在“認定侵權”基礎上,同時賦予該“軌”相應的確定合適的“責任方式”的權力,做到“既許之,則授之”,理論上保全、補救、防衛“三類型”的責任內容都應當可處理。即使為了防范行政裁決對賠償損失這一補救責任的不當處理,也不如先讓行政裁決可以責令賠償、再通過允許后續提起訴訟來進行事后的司法監督。實踐中,出現既想要保持行政權行使的克制而又伸手處理侵權糾紛,還有“專利行政調解司法確認機制”等改革試點,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立法不允許專利和商標侵權行政裁決進行補救責任處理所造成的。
三、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行權程序
(一)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程序“遵守實質相當原則”之《TRIPS 協議》義務
我國現行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提供“責令停止侵權行為”的救濟,相當于《TRIPS協議》第44條意義上的“禁令”(injunction),實質上屬于保全責任的民事救濟形式。這種行政裁決落入了《TRIPS協議》第49條及第50.8條所規定的涉及“民事救濟”情形之范疇,需要在行權程序上履行相應的條約義務。《TRIPS協議》第49條規定,如由于行政程序對案件是非曲直的裁決而導致責令進行任何民事救濟,則此類程序應符合與本節所列原則實質相當的原則。第50.8條規定,在作為行政程序的結果可責令采取任何臨時措施的限度內,此類程序應符合與本節所列原則實質相當的原則。可見,該協定對與民事救濟有關的行政程序和與臨時措施有關的行政程序,以“民事程序與行政程序交叉重合的規定方式”從程序公正上設置了相應的“遵守實質相當原則”義務。
《TRIPS協議》第三部分各節標題及條文中采用“程序”(procedures)與“措施”(measures)兩個概念,兩者分屬于不同層面:采取“procedures”的只有民事程序、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三類基本“執法程序”(enforcement procedures);采取“measures”的有“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視情況而定可能分別屬于民事程序或行政程序(其本身一般不太可能是刑事程序),即只是某一類“執法程序”中下位的“執法措施”(enforcement measures)。相應地,該協議第49條及第50.8條所表述的“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指的應是廣義的“行政執法”之“程序”,即可以包括狹義行政執法和行政司法意義上的行政裁決。不過,該協議并非是從“名義”上看系采取行政程序或是司法程序來確定義務要求的;相反,是從程序運行“結果”所涉及的“救濟”方式來設定應滿足的“程序義務”要求的,并也只以此為限。如果有任何“民事救濟”或“臨時措施”是由“行政程序”所最終作出的(ordered as a result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則其程序規則相應地應當符合協議關于民事程序及其臨時措施的實質性原則要求;對與民事救濟或臨時措施無關的其他“行政程序”,則并無此類義務要求與規定。這里所謂的“民事救濟”主要體現在《TRIPS協議》第44條禁令、第45條賠償損失、第46條清除出商業渠道或銷毀;“臨時措施”則主要體現在第50條第1款行為保全和證據保全上;同時,在規范設計上,《TRIPS協議》就“執法程序”設定了程序公正的內在義務,該協定第三章不少條文都是關于這方面的規定。以《TRIPS協議》民事程序為例,其義務大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程序參與方面,從信息、代理、訴求、證據等方面進行了義務設定;二是民事救濟方面,包括賠償損失、禁令、侵權品處理、信息披露、補償(程序錯誤的)等義務規定。由此,“遵守實質相當原則”義務也就要求從時間、費用、形式、信息、機會等方面來確保行政裁決程序的公正及效率。
(二)司法化改造: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程序之《TRIPS 協議》義務履行
學界主流觀點認為,一般性的行政裁決應強調其“司法性”。有學者認為,司法程序遵循當事人舉證、雙方辯論等不同于行政執法程序的正當程序原則,是為了確保公平、公正;同樣,行政裁決所具有的“準司法”行為屬性,決定了在行政裁決中行政主體的思維方式和裁決程序都應區別于其他行政行為,包括準用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限制行政機關調查取證權等。?參見胡建淼、吳恩玉:《行政主體責令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屬性》,載《中國法學》2009 年第1 期,第77-87 頁。還有學者指出,行政裁決權由專門的裁決機構行使,在外國已經被制度化了,故建議我國應該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行政裁決機構。?參見張樹義主編:《糾紛的行政解決機制研究:以行政裁決為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30 頁。從《TRIPS協議》義務履行角度而言,實現民事責任的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程序需要參照民事司法程序來落實“遵循實質相當原則”,由此相關行政裁決的程序“司法化”便成為該制度在法治框架內運行的約束條件和必然要求。
這里以專利侵權行政裁決為例來進行說明。其行政裁決程序的“司法化”改造可考慮在法律規則層面設立“準司法的行政裁決”機構和程序,具體宜從案件性質、裁決管轄與程序規則等方面來構建:其一,專利行政裁決的案件性質需要進行“變性”,即從現行法上的行政爭議改變為民事爭議。這種行政裁決具有私權的行政救濟性、侵權糾紛解決的準司法性和非終局性,同時也具有專業性、效率性、經濟性、政策形成性優勢等特點。其二,裁決管轄到底是基于權利人的單方申請還是雙方合意申請?法律特別賦予行政機關民事糾紛的裁決權,乃因行政機關這一主體維護公益的職責所在,故裁決程序可采取“類司法”的基于權利人的單方申請即可啟動,現行法也正是這樣設計的。其三,裁決程序規則在我國法律上并無具體設計甚至無原則性規定,只是在部門規章層面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彌補。2015年國家知識產權局修改的《專利行政執法辦法》對“專利侵權糾紛的處理”進行專章規定,從第10條到第21條涉及請求人、請求書、立案受理、送達、答辯書、調解、口頭審理、處理決定書、期限等內容,足以顯示“準司法程序”特點。該辦法在裁決程序方面“突出行政執法效率”,如第21條規定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時限是“自立案之日起3個月內結案”(修改前的舊辦法是4個月),案件特別復雜的,經批準延長的期限最多不超過1個月(案件處理過程中的公告、鑒定、中止等時間不計入案件辦理期限)。雖然學理上不乏主張適用“準司法程序”來處理行政裁決侵權案件,但在法律層面仍規則不明;“遵守實質相當原則”義務之履約尚需要引起重視,裁決程序規則有必要由效力層次較低的部門規章上升為行政法規乃至法律規則。至少《專利法》第60條應當原則性地規定,專利行政機關處理專利侵權糾紛時,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程序的規定,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類似地,商標侵權行政裁決也應當履行《TRIPS協議》所要求的“遵循實質相當原則”義務。在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的基礎上,2018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重新頒行了《市場監督管理行政處罰程序暫行規定》,對包括商標侵權在內的市場監管違法行為實施行政處罰的程序進行了全面規定。從該部門規章文本看,雖然立足于“行政主體—行政相對人”關系,對商標侵權人有足夠的程序保護,但一定程度上對被侵權的商標權人(第三人)卻存在保護不夠之嫌。2019年12月,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了《商標侵權判斷標準(征求意見稿)》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主要涉及侵權認定實體規則,但幾乎未涉及侵權處理的程序規則。由于商標侵權領域的“管執分離”改革,在國內法律規則層面上尚亟待進行相應的商標侵權行政裁決程序建構。
與行權程序之公正性相關聯而國內學界探討甚少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止侵權”的行政裁決,但在后來的行政訴訟中被認定為“錯誤”,那么對行政相對人造成損失的該如何賠償呢?國內學界對行政裁決出現錯誤情形下如何履行救濟義務鮮有探討。《TRIPS協議》第48條對此規定了兩類救濟規則:第1款規定“濫用”程序的當事人之賠償責任,即對基于申請的、“濫用執法程序”(abuse of enforcement procedures)的一方當事人,司法機關有權責令其承擔充分賠償責任,以彌補因受到錯誤禁止或限制的對方當事人因此所受損害(包括適當的律師費)。第2款規定,在實施知識產權法律過程中,只有當公共機構及其官員(public authorities and officials)所采取或擬采取的行動是出于“善意”時,方可被免除采取適當救濟措施的責任;對此,有論者指出,該款的宗旨在于確保執法程序被濫用情形下非“善意”的公共機構及其官員應承擔責任。?See Carlos Correa,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 Commentary on the TRIPS Agree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31.由此,《TRIPS協議》要求請求人不得“濫用執法程序”,否則應承擔充分賠償責任;結合第49條的“行政程序”而言,行政裁決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就可能錯誤的行政裁決之免責也僅限于“善意履職”范圍內。在某種意義上,這也與行政裁決“遵循實質相當原則”的義務相關聯,故《TRIPS協議》該條所確立的原則要求也有待在國內法律規則層面上進行相應建構。
四、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司法審查
(一)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司法審查”之《TRIPS 協議》義務檢視
《TRIPS協議》第41.4條在較宏觀層面上就所有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決定均規定了“司法審查”義務。我國官方譯本將該條款翻譯為:“訴訟當事方應有機會要求司法機關對最終行政裁定進行審查,并在遵守一成員法律中有關案件重要性的司法管轄權規定的前提下,至少對案件是非的初步司法裁決的法律方面進行審查。但是,對刑事案件中的無罪判決無義務提供審查機會。”?法律出版社法規中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全書(含司法解釋)》,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634 頁。
仔細對照協議英文版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41.4 條英文文本規定如下:“Parties to a proceeding shall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review by a judicial authority of 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nd,subject to jurisdictional provisions in a Member's law concerning the importance of a case,of at least the legal aspects of initial judicial decisions on the merits of a case. However,there shall be no obligation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review of acquittals in criminal cases.”可發現,該官方中譯本存在一些不妥之處,尤其是容易使人誤認為“最終行政裁定”需接受司法審查、再是“初步司法裁決”接受法律審查,儼然變成一個專門調整“行政裁定”的條款。具而言之:其一,就司法審查程序而言,在“條約義務”的意義上英文版本所采用的“review by a judicial authority”可以是甚至主要是上訴審理意義上的司法審查。從語法上看,該條款第1句對此的結構表述為“review of……and of ……”,系將“行政決定的最終結果”(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和“一審裁判”(initial judicial decisions)并列作為“司法審查”的對象;該條款第2句仍采“review of……”的結構,只不過對象是“刑事案件中的無罪判決”(acquittals in criminal cases)。其中,對“一審判決”和“無罪判決”情形均明確只是上訴審理意義上的司法審查;那么,對“行政決定的最終結果”的司法審查究竟只是在上訴審理還是“初審—上訴審”意義都具有條約義務?至少作準文本并無明確規定,成員對此具有國內實施的選擇權。其二,就司法審查對象而言,英文版本所用的“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并非“最終行政裁定”,只是“行政決定的最終結果”之義。這里的“administrative decisions”范圍遠遠廣于《意見》意義上的“行政裁定”,因為除此之外還包含狹義“行政執法”所作出的“決定”;同時,這里的“final”是相對于“preliminary”而言的,不是《行政訴訟法》第13條第(四)項無可訴性(“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行政行為”)意義上的決定。我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立法中,就專利(只針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商標授權和確權糾紛,都規定由行政機關作出“終局裁決”,“入世”時為履行協議第62.5條類似規定的“司法審查”義務,我國修改取消上述關于授權和確權的行政終局裁決規定,使涉及知識產權的所有糾紛都具有了可訴性;至于對知識產權侵權違法等行政處罰執法,則一直都提供司法審查的監督。
基于以上分析,該第41.4條宜翻譯為:“執法程序當事人應有機會就下列情形獲得司法機關的審查:對行政決定的最終結果;根據一成員有關案件重要性的司法管轄的法律規定,至少從法律方面,對涉及案件是非的一審裁判。但是,對刑事案件中的無罪裁判無義務提供審查機會。”這里作為條約義務的“review”的含義極為關鍵,從文理解釋上存在靈活履約的可能空間。其一,這里的“review”完全可以是“上訴”意義上的“司法審查”,當然意味著對行政程序所作出的行政決定可以只給予司法上的上訴復審。至少就《TRIPS協議》已要求“遵守民事程序的實質性原則”的那部分“行政裁決”所作出的“行政決定”而言,由于該類行政裁決已經扮演民事司法同樣的權力功能,允許對其上訴復審僅僅是程序公正的要求。對此的一個印證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等特定的聯邦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裁決后,當事人不服的可以直接“上訴”至“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如果再不服還可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the U.S.Supreme Court)去申訴。其二,這里的“review”也不限定對行政決定的最終結果只能進行司法上訴審理。換言之,隨著“of”后面的賓語不同,其既可能是從司法“一審”到“二審”的“復審”,也可能是從“行政決定”到司法“二審”的“復審”,還可能是從行政決定到司法“一審二審”的“復審”(對《TRIPS協議》未作程序義務規定的行政處罰等決定,就應當采這種理解更為妥當)。其三,該條中的“review”并未限定是何種程序的“司法審查”,即根據具體情況可能是民事的或行政的或刑事的司法審查。因此,協議中“review”一語所蘊含的履約靈活性決定國內實施轉化時需要進行區別性的“自我選擇”。
(二)當事人選擇權: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類型化司法審查
我國現行法上對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司法審查”義務的履行,主要體現在對裁決不服可提起“行政訴訟”上,即依照《行政訴訟法》后續進行“兩級”司法訴訟。雖然我國提供了更多的司法監督,但這不是《TRIPS協議》義務所要求的;這種“高成本”的“一刀切”式制度設計,額外地帶來審理周期長等頑疾。這與“入世”修法時對《TRIPS協議》第41.4條“司法審查”義務理解存在偏差、無視其內在彈性空間直接相關,與我國沒有對“行政執法”行為與“行政裁決”行為進行差異化的司法審查制度有關。
行政裁決的性質厘定不能只看行權主體的行政機關身份,更要看裁決權力本身的屬性。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核心在于民事責任,在“行政行為”外延上屬于“行政司法”行為,本質上是由法律特別委任給知識產權行政機關行使的“司法權”或是“委任司法權”,具有鮮明的“準司法”(quasi-judicial)性。對已經履行《TRIPS協議》“遵守實質相當原則”義務的行政裁決來說,在“司法審查”義務下的后續程序中再從頭重走一遍“民事司法程序”,勢必具有一定的“同質性”。由于后續的司法審查也必須以解決民事侵權糾紛為落腳點,故“司法審查”的具體程序需進行“理性改造”,尤其應當對其訴訟程序與司法審級進行特別考慮。
日本行政法上“二分法”的“當事人訴訟”制度對此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日本2004年修改的《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4條將“當事人訴訟”界定為,“關于確認或者形成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的處分或者裁決、根據法令規定以該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為被告的訴訟,關于公法上的法律關系的確認訴訟及其他關于公法上的法律關系的訴訟”。學術上以行政機關在訴訟中的主體身份為標準,稱前者為“形式當事人訴訟”,即一方當事人根據特別法律規定以行政裁決的對方當事人為被告提起訴訟;稱后者為“實質當事人訴訟”即當事人以公法上的法律關系為對象提起訴訟。有學者提出,我國擴容借鑒建立行政裁決“形式當事人訴訟”模式,并對停止執行、司法變更、行政審理和民事證據、不得另行民事訴訟以及限制相應的行政考核等方面提出建議。27參見沈世娟:《著作權行政保護的完善》,載《知識產權》2013 年第4 期,第64-68 頁。但也有學者認為,在行政裁決方面引進日本當事人訴訟制度并不可行,理由是被告從行政機關變更為對方當事人而不符合邏輯,還會引發權力運作的混亂及執行困境。28參見陳錦波:《我國行政裁決制度之批判——兼論以有權社會機構裁決替代行政裁決》,載《行政法學研究》2015 年第6 期,第86-98 頁。應當說,從行政機關的主體身份入手來構建司法審查制度的做法,可資在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司法審查法律規則設計中予以借鑒。
我國行政法學界主流觀點對行政裁決爭議的“性質可轉化”特點也漸成共識,認為當事人對行政機關不具有完全管轄權的民事爭議裁決不服而向法院起訴的,若以行政機關為被告而請求法院對行政裁決進行司法審查,則該爭議轉化為行政爭議;若仍以原爭議的對方當事人為被告來請求法院裁決而將之前的行政裁決擱置一旁,則仍屬于民事爭議。29參見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編寫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2 頁。這種“性質轉化”發生與否取決于當事人的選擇,即仍然起訴對方或者是轉而起訴行政機關。由此,本文認為,就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司法救濟,可考慮賦予當事人對該裁決作出“司法審查”類型的“當事人選擇權”,即從新的行政訴訟或者后續的民事上訴中選擇一種(且一經行使即不能再行重新選擇):一種是選擇“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當事人認為行政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不當而將行政機關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一審),該侵權民事爭議轉化為行政爭議;同時,依2014年《行政訴訟法》第61條規定,在涉及行政機關對民事爭議所作的裁決的行政訴訟中,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申請“一并審理”解決相關民事爭議。由于這種做法與現行的知識產權單行法律規定存在較大契合性,故在學界得到較多支持;其適用有限定條件,如對于行政裁決“責令賠償損失”重大不當的,也可判決變更賠償數額,也可以要求行政機關重新作出行政行為。另一種是選擇“民事上訴”的方式。根據前文關于《TRIPS協議》第41.4條“司法審查”義務的澄清,可得出我國應當對狹義“行政執法”行為與“行政裁決”行為進行差異化司法審查制度的結論;實行不同的司法審查類型及審級是實行差異化的重要思路。不過,這需要刪除現行知識產權法律對侵權行政裁決“一元化”行政訴訟的相關規定,并宜改造成“民事上訴審理”模式。原來的行政裁決將在實質上視為“準司法”的民事一審;在后續司法審查程序中,實際上只是收回了委托出去的司法判斷權,僅僅只是對初審的一種繼續復審。30參見江必新:《司法審查強度問題研究》,載《法治研究》2012 年第10 期,第3-9 頁。鑒于這種行政裁決適用的是民事訴訟程序或實質相當的類似程序,法院對相關行政裁決所作決定的“復審”不在于其行政程序本身是否合法,而是行政機關作出決定是否遵循了準民事訴訟程序、侵權認定及給予的法律救濟是否合法。同時,以對方當事人為被告向該行政機關所在地的民事二審管轄法院提出上訴,更符合效率價值。
在某種意義上,上述“當事人選擇權”的行使可為不服行政裁決爭議的“性質轉化”提供必要的正當性。從對現行規則的變動幅度看,“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屬于改良型的做法,基本在現行規則框架內就可實現。對權利人而言,這種“合一”處理機制帶來了“搭便車”效果;在證據收集和運用“完善民事爭議和行政爭議交叉的處理機制”以及侵權事實認定上都同時為民事責任的實現提供了便利,從而在知識產權領域將有利于最終解決侵權糾紛和實現訴訟效率。“民事上訴”屬于規則再造式的做法。就知識產權單行法律發展動向看,《商標法》早在2013年修改時就商標民事爭議行政裁決的規定修改第60條第2款時刪去了舊法中“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規定,2019年修改時對此予以了維持。可以預見的是,民行交叉爭議的新規定將對《專利法》第四次修改形成“示范效應”,從而為行政訴訟抑或民事訴訟的選擇預留出法律上的空間。
結語
隨著2019年有關行政裁決制度的《意見》頒行,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制度迎來發展的春天。相關回顧表明,“入世”時我國為“接軌”而就有關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規則進行修法,不乏對《TRIPS協議》執法義務進行了某些在今天看來帶有歷史局限性的解讀,對此實有必要進行澄清。在實體救濟上,《TRIPS協議》并非禁止行政裁決作出“責令賠償損失”的決定,只是要求其作出程序應當參照民事司法程序那樣“遵守實質相當原則”;相反,人為地撕裂“責令停止侵權”與“賠償損失”兩類實體救濟為不同程序,勢必使行政裁決的“分流閥”功能先天不足,難逃之前在適用上逐年萎縮的厄運,故對行政裁決“賦能”勢在必行。在行權程序上,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程序“遵守實質相當原則”之《TRIPS協議》義務履行,長期被理論界與實務界所忽略,急需以公正及效率為導向通過相關立法來推動其司法化改造進程。在司法審查上,《TRIPS協議》的義務設定具有履約“彈性”;我國迄今運行“一刀切”行政訴訟之司法審查模式成本高昂、痼疾不少,需區分“行政執法”與“行政司法”屬性差異并引入“當事人選擇權”這一新變量,從而建立對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的差異化司法審查制度。可以說,《意見》是對行政裁決制度的正本清源,只有加緊研究知識產權侵權行政裁決制度的優化與落實,才能真正發揮其在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化解民事糾紛的‘分流閥’”的角色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