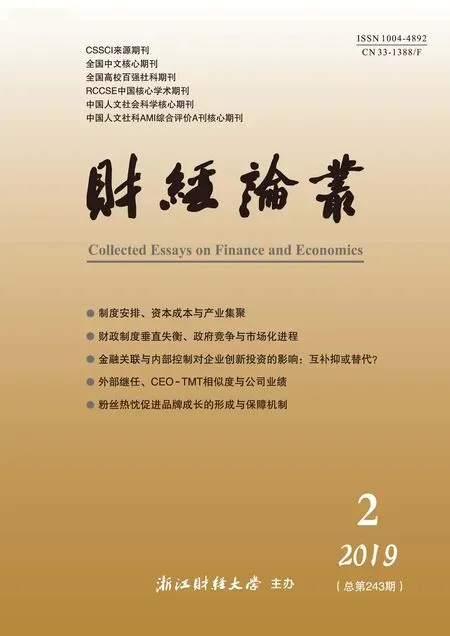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下的銀行風險承擔:主觀偏好還是被動選擇
張 澄,沈 悅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事實上,在構建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體系的同時,我們首先需要準確判定我國面臨的金融風險有哪些。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內部風險的萌生、積聚和擴散已經成為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要爆發源。在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以及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商業銀行內部風險是否集中凸顯以及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等問題已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高度重視。資產價格與宏觀經濟的波動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的視角來研究銀行風險承擔問題將會愈來愈受到重視。
一、相關文獻回顧
近年來,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問題備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并涌現出了一批關于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渠道(Risk-taking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的研究[1][2][3][4],這無疑為關于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行為方面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角。基于此,已有文獻還分別從宏觀和微觀的不同角度分析了影響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幾類因素:市場結構與競爭因素[5]、銀行個體特征因素[6]以及宏觀經濟波動因素[7]等。
關于房地產價格和銀行風險承擔。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關于房地產價格在宏觀經濟波動中的作用。而如今,嵌入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分析才可以更好地闡釋銀行體系在資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中的重要性。方意(2015)分析了貨幣政策和房地產價格沖擊對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的異質性影響,認為上漲的房地產價格對銀行主動風險承擔的影響更大,并進一步指出,在上行的經濟周期中更需要關注房地產市場的泡沫[8]。還有部分學者在檢驗貨幣政策的銀行風險承擔渠道時,進行了關于資產價格波動對銀行風險承擔作用機制的輔助性檢驗。徐明東和陳學彬(2012)認為,資產價格上漲會使銀行風險承擔增加,即存在“寬松的貨幣政策—房地產價格上漲—銀行風險承擔增加”的傳導機制[9]。相反,牛曉健和裘翔(2013)指出,房地產市場的景氣程度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10]。還有學者基于銀行風險承擔與房地產信貸政策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強調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與房地產信貸政策之間存在協同或拮抗作用[11]。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我們發現學者們對于宏觀經濟波動與銀行風險承擔的關系莫衷一是。一種觀點認為,宏觀經濟波動與銀行風險承擔負相關。宏觀經濟的上行周期會通過抵押物升值、企業違約率降低等因素而使銀行風險承擔降低;而當宏觀經濟處于下行周期時,企業因經營不善而導致違約率增加,銀行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比如潘敏和張依茹(2012)指出,宏觀經濟波動的正向沖擊會使銀行風險承擔降低,即二者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性[5]。劉生福和李成(2014)也認為,較快的經濟增長會使銀行風險承擔降低[12]。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宏觀經濟波動與銀行風險承擔正相關。主要是由于銀行風險偏好會在不同的經濟周期內發生改變。在經濟擴張時期,銀行為了追求高收益而選擇去承擔更大的風險;在經濟蕭條期,銀行的風險偏好行為更加謹慎,因此整體風險承擔水平下降。比如徐明東和陳學彬(2012)認為,良好的宏觀經濟走勢會使企業凈值得到改善,違約風險因此而降低,進而導致銀行風險承擔增加[9]。Angeloni等(2015)同樣發現,在經濟擴張時期,利率水平的降低會刺激銀行體系中資產回報率的減少,基于“追逐收益”路徑,銀行將選擇承擔更大的風險[13]。
總體來看,目前關于宏觀經濟波動和銀行風險承擔之間關系的研究較為豐富,且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但卻鮮有關于房地產價格、宏觀經濟波動和銀行風險承擔三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且多數文獻并未將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進行劃分。那么,三者之間究竟存在何種作用機制?是否存在銀行風險承擔“主觀偏好”與“被動選擇”的差異性?是否存在系統重要性銀行風險承擔與非系統重要性銀行風險承擔的異質性?本文試圖針對這一系列問題展開論述。
由是,本文基于我國40家商業銀行2005~2015年間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數據,從行為視角將銀行風險承擔劃分為“主動”和“被動”,實證考察了房地產價格、宏觀經濟波動和銀行風險承擔三者之間的影響關系,并基于宏觀審慎監管的思想,實證分析了系統重要性差異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異質作用。這對認清我國銀行風險承擔問題,做好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工作等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理論分析
2008年美國次貸金融風暴之后,涌現出了很多有關銀行風險承擔視角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這些研究都認為,貨幣政策的變化會影響金融中介的風險容忍度,進而影響其內部的資產定價、資產組合風險水平等。事實上,資產價格、宏觀經濟波動以及預期等因素都會對銀行的風險感知能力產生影響,進而影響我國經濟金融體系的安全。
關于房地產價格和銀行風險承擔的關系,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上漲的房地產價格會提升銀行持有的抵押物價值,進而優化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最終表現為銀行主動承擔房地產價格上漲帶來的風險,我們稱之為“房地產抵押”路徑[11]。房地產市場的繁榮發展促使房地產企業開發貸款和個人按揭貸款的增加,誘發銀行對高風險、高收益資產的需求大幅增長,而一旦“非理性繁榮”市場的泡沫破裂,不良貸款率上升,最終表現為銀行被動風險增加,我們稱之為“追逐收益”路徑[14]。基于“大而不倒”的經營思想,我國商業銀行在面臨經濟下行、房地產行業市場蕭條以及流動性不足等危機局面時,中央銀行會通過再貸款等方式對其進行“救市”,進而提高商業銀行的風險感知能力,我們稱之為“央行保障”路徑[15]。
關于宏觀經濟波動和銀行風險承擔的關系,一種解釋認為,宏觀經濟環境的好壞可能會與銀行風險承擔正相關,即銀行風險承擔的“順周期”效應[16],主要表現為:寬松的貨幣環境將減輕實體企業的債務負擔,并促使抵押物升值,銀行為了追求高收益而選擇承擔更大的風險。此外,銀行往往在上行的經濟周期中表現更為樂觀,進而提高自己的風險容忍度;在經濟蕭條時期,銀行為了規避風險而變得十分謹慎,此時風險承擔水平下降。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宏觀經濟波動可能與銀行風險承擔負相關,主要表現為:在宏觀經濟的上行周期中,抵押物增值會使企業違約率降低,進而促使銀行風險承擔降低;當宏觀經濟處于下行周期時,已經發放的貸款由于受到宏觀經濟中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促使企業違約率增加,不良貸款的增加最終會導致銀行被動風險承擔增加。
可以看出,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都會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產生影響。盡管已有的研究未得出一致結論,但學者們在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會影響銀行風險承擔這一問題上存在共識。進一步,如果宏觀經濟波動顯著地影響銀行風險承擔,那么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是否會對二者之間的關系產生某種促進或者是抑制作用?在不同的影響路徑和作用機制中,是否存在銀行風險承擔“主觀偏好”或者是“被動選擇”的差異?因此,我們將在下面的實證分析中考察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對銀行風險承擔影響的異質性。這不僅有利于拓展現有關于銀行風險承擔的研究,同時也有助于分析我國銀行體系在面臨當前復雜宏觀經濟環境變化背景下的風險問題。
三、實證模型
(一)銀行風險承擔的基準模型
首先,我們通過構建如下基準計量模型來反映房地產價格、宏觀經濟波動和銀行風險承擔三者之間關系:
Riskit=α0+α1Riski,t-1+α2Gapt+α3HPt+α4Controlsit+ui+εit
(1)
式(1)中,被解釋變量Riskit為商業銀行i在t期的風險承擔水平(存在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兩種情況),GAPt為t期的宏觀經濟波動水平,HPt為t期的房地產價格水平,Controlsit代表系列控制變量,ui為個體效應,εit為誤差項。考慮到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對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的反應存在明顯的滯后性,我們引入風險承擔的滯后一期變量作為模型的內生變量。如果GAPt的估計系數為正,表明宏觀經濟的上行周期會使銀行風險承擔水平提高,而下行周期則會降低銀行風險承擔水平。如果HPt的估計系數為正,則反映上漲的房地產價格會導致銀行風險承擔增加,而下跌的房地產價格則會導致銀行風險承擔減少。
(二)基于系統重要性差異的模型拓展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讓學術界和實務界充分認識到了宏觀審慎管理的重要性。宏觀審慎思想對金融機構的系統重要性進行了劃分,認為金融機構的系統重要性差異對系統性風險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結合宏觀審慎監管思想,充分考慮系統重要性差異對銀行風險承擔的異質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2]。根據不同商業銀行在我國金融機構中的相對作用,傳統的研究將中、農、工、建、交五家銀行劃分為我國系統重要性銀行。但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7年第4號工作論文[17]表明,目前我國部分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樣應當被識別為國內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如招商銀行、浦發銀行和興業銀行等。因此,我們在檢驗傳統五大國有銀行系統重要性的同時,也需要考慮納入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進行檢驗[注]本文選取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民生銀行和光大銀行。。
我們在基準計量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虛擬變量Sysi和GAPt、HPt的交互項GAPt*Sysi、HPt*Sysi,實證檢驗基于系統重要性差異的拓展模型,即計量模型(2):
Riskit=β0+β1Riski,t-1+β2Gapt+β3HPt+β4Gapt*Sysi+β5HPt*Sysi+
β6Controlsit+ui+εit
(2)
式(2)中,Sysi為商業銀行i的類型,當Sysi=1時,認為所選擇的樣本銀行為系統重要性銀行;當Sysi=0時,則認為所選擇的樣本銀行為非系統重要性銀行;交互項GAPt*Sysi以及HPt*Sysi,用來檢驗在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下,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是否會呈現出異質性表現。
(三)引入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交互項的模型拓展
為了檢驗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是否會對宏觀經濟波動與銀行風險承擔之間的關系產生顯著性影響,我們在基準計量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交互項Gap*HP,得到計量模型(3):
Riskit=γ0+γ1Riski,t-1+γ2Gapt+γ3HPt+γ4Gapt*HPt+γ5Controlsit+ui+εit
(3)
由于式(1)、式(2)和式(3)的解釋變量均包含了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這極可能引起內生性的問題。傳統的估計方法將得到有偏的估計結果,得到變量之間的經濟學解釋也必然不科學。相較而言,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動態面板系統廣義矩估計法(SYSGMM)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參數估計值[18][19]。由是,本文將在實證檢驗中采用動態面板系統廣義矩估計的方法進行估計。
(四)變量定義與數據說明
根據已掌握的文獻[20][21][22][4],目前常用的銀行風險承擔指標有預期違約概率(EDF)、Z值(Z-Score)、風險加權資產比例、凈貸款占總資產的比重以及不良貸款率等。同時,參考方意(2015)對商業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的劃分[8],本文分別選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Risk_A)和不良貸款率(Risk_P)作為商業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商業銀行被動風險承擔的代理變量。其中,風險加權資產比例由風險加權資產值對總資產的比率獲得[注]風險加權資產值由總資本對資本充足率的比率獲得。;不良貸款率由不良貸款對貸款總額的比率獲得。
我們選取風險加權資產比例來衡量商業銀行的主動風險承擔。文中的銀行主動風險承擔是基于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而提出,意味著較低的利率水平迫使銀行的風險容忍度發生改變,進而銀行在發放新貸款時主動放寬信貸標準,導致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增加。具體而言,銀行在發放新貸款時(事前)的行為,我們將其定義為銀行的“主觀偏好”。由于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是從風險的視角對資產進行加權處理,很好地描述了銀行內部高風險資產所占比例,且該比例在銀行發放新貸款時即可確定,具有前瞻性。風險加權資產占比越高,表明銀行購買風險資產的主觀傾向性越強。因此,銀行主動風險承擔水平與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正相關。
我們選取不良貸款率來度量商業銀行的被動風險承擔。文中的銀行被動風險承擔是在銀行自身風險容忍度未發生改變的前提下,其已發放的貸款(事后)在受到各種不利宏觀因素的沖擊后出現違約,進而導致銀行被動承擔過度風險,我們將其定義為銀行的“被動選擇”。由于不良貸款率刻畫了銀行內部出現違約貸款的比重,且該比重的改變說明已發放貸款的風險發生改變,不良貸款的占比越高,表明商業銀行被動選擇承擔更大的風險。因此,銀行被動風險承擔水平與不良貸款率正相關。
需要說明的是,文中的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的主要區別在于:新發放的貸款和已發放的貸款(遭受違約)之間存在時滯[8]。為了更清楚地闡釋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基于對我國5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數據分析,我們繪制了5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風險加權資產比例和不良貸款率的對比圖(見圖1)進行進一步描述。觀察圖1發現,樣本期內我國5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波動較平緩,而不良貸款率波幅較大。也就是說,由于受到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的沖擊,我國商業銀行因風險感知能力發生改變而影響主動風險承擔的變化并不明顯,但因違約企業數量增多等外部因素而導致被動風險承擔的變化較大。下面我們將具體分析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對銀行主動風險承擔與銀行被動風險承擔的影響。

圖1 我國5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風險加權資產比例和不良貸款率
我們選取國房景氣指數(HP_1)、產出缺口(GAP_1)分別作為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的代理變量。同時為了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選取我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增長率(HP_2)、GDP的對數增長率(GAP_2)分別作為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的替代變量進行估計。對于銀行層面的控制變量,我們選取資本充足率(CAR)表示銀行資本結構,資產收益率(ROA)描述銀行盈利能力,銀行資產的自然對數(Size)刻畫銀行規模,成本收入比指標(Effi)反映銀行效率水平。對于宏觀層面的控制變量,我們選取1年期定期存款實際利率(MP)作為貨幣政策的代理變量,以此來檢驗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在貨幣政策的沖擊下是否存在差異性。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樣本為我國40家商業銀行2005~2015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數據。樣本銀行包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5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和浦發銀行等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北京銀行、上海銀行和江蘇銀行等23家城市商業銀行[注]5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包括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包括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廣發銀行、平安銀行、恒豐銀行、渤海銀行和浙商銀行;23家城市商業銀行包括北京銀行、上海銀行、江蘇銀行、南京銀行、寧波銀行、盛京銀行、徽商銀行、杭州銀行、天津銀行、哈爾濱銀行、長安銀行、廣州銀行、包商銀行、成都銀行、重慶銀行、長沙銀行、吉林銀行、鄭州銀行、大連銀行、河北銀行、蘇州銀行、溫州銀行和湖北銀行。。樣本銀行的相關數據由BankScope數據庫和各大商業銀行年度報表整理得到。房地產價格、國房景氣指數、國內生產總值以及貨幣政策變量等宏觀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以及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等。為了避免長期趨勢的影響,我們對房地產價格的相關指標進行HP濾波處理。還進一步對銀行個體特征層面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均為平穩序列。表1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模型
表2報告了基準計量模型(1)的估計結果。列(1)至列(3)是以風險加權資產比例作為商業銀行主動風險承擔的代理變量進行估計,列(4)至列(6)是以不良貸款率作為商業銀行被動風險承擔的代理變量進行估計。

表2 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
注:*、** 和*** 分別表示z統計量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各變量的估計系數下方括號中的數字為對應的標準誤差;模型檢驗下方括號中的數字為對應的P值;回歸結果省略了常數項。下同。
表2中的AR(2)統計量和Sargan統計量顯示,在我們設定的基準計量模型中殘差項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工具變量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因此,可以認為基準計量模型的設定是合理的。具體來看,首先L.Risk_A和L.Risk_p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存在滯后一期的持續性。其次,以風險加權資產比例作為被解釋變量時,GAP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而HP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以列(1)的估計結果為例進行說明:1單位正向宏觀經濟波動沖擊對銀行主動風險承擔的影響為1.0908,1單位正向房地產價格沖擊對銀行主動風險承擔的影響為-1.4503;以不良貸款率作為被解釋變量時,GAP和HP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以列(4)的估計結果為例進行說明:1單位正向宏觀經濟波動沖擊對銀行被動風險承擔的影響為0.3835,1單位正向房地產價格沖擊對銀行被動風險承擔的影響為0.0336。對比可知,各項外部沖擊對銀行主動風險承擔的影響更大。
總體來看,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都會影響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上行的經濟周期會使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同時增加,并呈現“順周期”的特征[7]。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導致銀行的風險加權資產比例下降,即銀行主動風險承擔減少。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是抵押物升值使實體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得到改善,一方面刺激銀行信貸規模又增加了銀行的盈利水平,從整體上降低了銀行內部資產的風險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銀行并未過度主動吸收風險權重高的資產。再加上貨幣當局對銀行體系的信貸監管加強[12],這一系列因素影響著銀行主動風險承擔,使其并未出現風險承擔的“主觀偏好”現象;相反,上漲的房地產價格和良好的宏觀經濟走勢會導致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上升,即銀行被動風險承擔增加,當受到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時,多數資信較差的企業獲得貸款而最終出現違約,從而導致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使其出現風險承擔的“被動選擇”現象。
貨幣政策變量(MP)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值,這與經典文獻的結論一致。意味著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銀行不僅會改變現有的風險容忍度,主動去承擔過度風險,同時也會因為銀行不良貸款的增多而被動承擔過度風險。從銀行個體特征層面的控制變量來看,資本充足率(CAR)的系數均為負,表明資本充足率越高的銀行風險承擔水平較低,同時也意味著資本不足的銀行相對資本充足的銀行來說更加偏好風險,也會采取更加冒險的行為[9]。銀行規模(Size)與風險承擔水平呈負相關,說明資產規模越小的銀行更傾向于風險承擔行為。銀行盈利能力(ROA)和效率水平(Effi)與主動風險承擔正相關,與被動風險承擔負相關,表明高收益、高效率的商業銀行更加傾向于主動承擔過度風險。
(三)基于系統重要性差異的模型拓展
表3列示了計量模型(2)的估計結果。列(7)和列(8)僅考慮將中、農、工、建、交五家銀行劃分為我國系統重要性銀行,列(9)和列(10)則納入了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進行檢驗。此外,我們以剔除系統重要性銀行后的29家商業銀行為研究樣本,進一步估計計量模型(2),結果分別報告于列(11)和列(12)。
從表3的估計結果可知,納入部分股份制銀行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受到房地產價格上漲或下跌的影響更大。因此,從宏觀審慎監管的思想來看,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也應被考慮納入我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中。綜合來講,在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下,系統重要性銀行與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存在差異。系統重要性銀行會削弱銀行被動風險承擔的“順周期”效應;在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系統重要性銀行會比非系統重要性銀行被動承擔更多的風險,而主動風險承擔將被削弱。可能的原因在于:系統重要性銀行資產規模大并且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相對重要,普遍受到更加嚴厲的金融監管,內部風險管理能力相對較強[23],所以系統重要性銀行的主動風險承擔行為略顯遲緩,而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則相對激進[24]。同時我們發現加入交互項以后,GAP和HP估計系數的符號均與基準模型一致,再一次證實了前述的研究結論。

表3 基于系統重要性差異的模型估計結果
(四)引入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交互項的模型拓展
表4展示了計量模型(3),即加入交互項GAP*HP的估計結果。列(13)和列(14)以風險加權資產比例作為商業銀行主動風險承擔的代理變量,并選取房地產價格增長率和GDP的對數增長率進行穩健性檢驗;列(15)和列(16)以不良貸款率作為商業銀行被動風險承擔的代理變量,并選取房地產價格增長率和GDP的對數增長率進行穩健性檢驗。

表4 引入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交互項的模型估計結果
表4中的各項檢驗結果均表明我們的估計結果具備合理性。可以看出,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會影響宏觀經濟波動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的關系。無論是以風險加權資產比例還是以不良貸款率作為被解釋變量,GAP*HP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擴大宏觀經濟波動對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的影響,即銀行風險承擔將表現為更強的“順周期”特征。同樣,加入交互項GAP*HP以后,GAP和HP估計系數的顯著性水平和符號并未發生顯著變化。為了進一步確保本實證研究的穩健性,我們對5%水平下Winsor縮尾處理后的樣本進行檢驗,其估計結果顯示交互項GAP*HP的系數仍顯著為正,且系列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均未發生顯著變化[注]限于篇幅,未列出結果,作者備索。,表明本文的實證結果并不會因各變量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同時也充分證實了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會對宏觀經濟波動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立足于宏觀審慎監管的思想,結合我國40家商業銀行2005~2015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數據,通過系統廣義矩估計的方法研究了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下的銀行風險承擔問題,從行為視角綜合研判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是“主觀偏好”還是“被動選擇”,并進一步考察了系統重要性差異對銀行風險承擔的異質作用。實證結果顯示:(1)上行的經濟周期會使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同時增加,而上漲的房地產價格會降低銀行主動風險承擔,相反則會導致銀行被動風險承擔的增加;(2)在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下,系統重要性差異的確會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產生異質作用;(3)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擴大宏觀經濟波動對銀行主動風險承擔和被動風險承擔的影響。目前,我國房地產業的資金來源過度依賴于銀行體系,一旦房地產價格出現劇烈波動,整個銀行體系必然受到牽連。認清宏觀因素沖擊下的我國銀行風險承擔問題是我們做好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的首要前提。因此,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首先,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會對銀行風險承擔產生顯著影響,監管當局應當密切關注銀行市場與宏觀政策的協調,在經濟“穩增長”的同時加強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警惕房地產價格上漲過程中,銀行風險承擔“順周期”效應的增加,有效防范由于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過度波動而誘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其次,監管當局應針對不同類型的銀行實施差異化的監管策略,尤其是加大對中小型商業銀行的風險監管,合理避免因其更加冒險和激進的風險承擔行為而產生銀行內部風險積聚和擴散的現象。最后,政策當局應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納入宏觀經濟的分析框架中,更好地解釋我國房地產價格、宏觀經濟波動與銀行風險之間存在的相互影響的作用機制,從而維護我國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