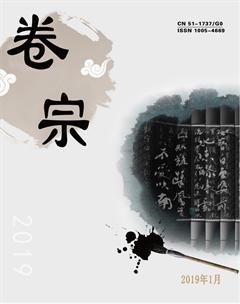人工智能犯罪的幫助行為正犯化探析
羅艷芳 葉沛春
摘 要: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人工智能技術(shù)越來越廣泛地應(yīng)用于社會的各個方面,給人類帶來了新的生活體驗。同時,也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帶來一系列風(fēng)險,甚至誘發(fā)犯罪。在人工智能犯罪問題上,基于人工智能電子人格屬性,對人工智能犯罪中幫助行為正犯化進行研究,以期對這種新型犯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式。
關(guān)鍵詞:人工智能正犯化;幫助行為
人工智能犯罪是指人工智能技術(shù)所可能帶來的犯罪類型。幫助行為正犯化,是指刑法將原本屬于刑法分則條文規(guī)定的正犯行為的幫助行為,直接規(guī)定為正犯行為,并設(shè)置獨立法定刑的一種立法模式。是否將人工智能犯罪中幫助行為正犯化,這種必要性應(yīng)該從兩點出發(fā):其一,人工智能犯罪是否具有獨立性,即是否需要將其作為獨立犯罪種類予以考量;其二,如果人工智能犯罪可以作為獨立犯罪,那么是否有必要將幫助行為獨立予以考量。
1 人工智能犯罪的獨立性
將人工智能技術(shù)運用于犯罪中,變現(xiàn)方式多種多樣。從主客觀相互聯(lián)系的角度,可以將人工智能犯罪分為四類型:
1)犯罪人故意利用無意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實現(xiàn)犯罪。所謂的無意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是指良好的、普通的、合法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技術(shù)的開發(fā)和運用本意是服務(wù)社會,但犯罪分子將其視為犯罪工具,利用其潛在的社會風(fēng)險性形成犯罪。犯罪分子利用這種不可控的社會風(fēng)險為犯罪工具加以利用,只能以犯罪人的故意犯罪予以確定罪名。這些罪名,大體上可以通過目前的刑法體系予以確定,因此判斷難度并不大。2)犯罪人過失利用無意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實現(xiàn)犯罪。例如,由于操作不當(dāng)誤使人工智能機器人傷害其他人。這種類型也是基于人工智能技術(shù)所帶來的潛在社會風(fēng)險,以傳統(tǒng)的過失犯罪予以判斷即可。3)犯罪人故意利用有意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實現(xiàn)犯罪。所謂的有意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是指不良的、特殊的、非法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例如,制造具備后臺記憶存儲的智能家具,從而收集犯罪所必須具備的數(shù)據(jù);制造所謂的“殺人機器人”,實現(xiàn)犯罪目的。這種有意的行為,本身從研發(fā)階段就具備了社會危害性,具備典型危險犯的特征。這種類型的犯罪,既可能涉及到傳統(tǒng)罪名,但可能獨立成為新的罪名。4)犯罪人過失利用有意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實現(xiàn)犯罪。這種類型是對上述第三種類型的過失化處理。基于“深度學(xué)習(xí)”的可能性,犯罪人可能在制造出其難以預(yù)測的社會危害性,提前犯和結(jié)果加重犯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超脫于犯罪人自身帶來的社會危險性,刑法自然要予以適當(dāng)關(guān)注和譴責(zé)。
上述第1、2種類型,人工智能技術(shù)導(dǎo)致的結(jié)果為實害結(jié)果,人工智能成為了犯罪工具;但是其并未超過目前的刑法罪名體系,通過傳統(tǒng)犯罪的規(guī)制就能判斷這些犯罪是否成立。第3、4種類型,使得人工智能犯罪具有了獨立性。人工智能不在是簡單工具,而可能是屬于違禁犯罪的產(chǎn)品。基于這種違禁的性質(zhì),人工智能犯罪在研發(fā)或者制作過程中就可能產(chǎn)生社會危險性,侵害社會法益。為此,獨立定罪成為了必要,人工智能犯罪的獨立性就顯而易見了。
2 人工智能犯罪幫助行為正犯化的必要性
人工智能犯罪幫助犯行為正犯化的必要性,主要考察其社會危害性和立法目的。人工智能犯罪中,幫助行為本身就具有較強的社會危害性;基于預(yù)防犯罪的必要性,刑事政策應(yīng)該對幫助行為進行積極預(yù)防;同時,人工智能犯罪的幫助行為較為明確,可進行類型化的歸類,這也使得幫助行為正犯化成為了可能。
2.1 幫助行為具有較強的社會危害性
在高科技面前,人類的風(fēng)險總可能被肆意擴大。信息技術(shù)所帶來的隱蔽性和溝通的便利性,使得科學(xué)技術(shù)一旦被運用在犯罪之中,所帶來的社會風(fēng)險極易以成倍的效果顯現(xiàn)。規(guī)制這種潛在的社會風(fēng)險,提前預(yù)防和規(guī)避風(fēng)險提供了兩種途徑。提前預(yù)防可以達到較好的防范效果,但是對于預(yù)備行為的正犯化卻是對其行為的徹底否認。例如,對于恐怖主義犯罪,預(yù)備行為的正犯化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階級的徹底否認;這種否認,實際上是對某一類犯罪行為法益危害性的判斷,甚至出現(xiàn)了“敵人刑法”的效果。但對于人工智能犯罪,如果從預(yù)備階段就予以否認,以“敵人刑法”的角度思考人工智能技術(shù),將不利于該技術(shù)的發(fā)展及推廣;研發(fā)人員在高度刑法壓制的情況下可能為了規(guī)避風(fēng)險而選擇不開發(fā)、不制造,這對于人工智能的發(fā)展來說極為不利。規(guī)避風(fēng)險則是另一種風(fēng)險的預(yù)防措施。在無法避免法益受到進一步侵害的情況下,規(guī)避一定的風(fēng)險既可以減輕法益侵害,也可以起到良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對于人工智能犯罪,新型技術(shù)和傳統(tǒng)犯罪的結(jié)合可能帶來更大的危害,如果能夠針對幫助行為予以譴責(zé),從而及時有效阻止犯罪的進行,這將更好的保護法益。因此,從社會侵害性的角度上看,幫助行為正犯化有利于更好的保護法益。
2.2 符合刑法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則
人工智能犯罪作為高科技犯罪的一類,其影響將在兩方面擴張:第一,技術(shù)的研發(fā)過程本身就可能導(dǎo)致多元化運用,例如讓無人機加裝偽基站,就需要讓偽基站小型設(shè)備化,一旦這個技術(shù)實現(xiàn)附加地可能使其他高科技犯罪工具設(shè)備小型化;再如,開發(fā)用于竊取個人信息的虹膜識別技術(shù),這本身可以運用在其他犯罪(如盜竊)中。第二,技術(shù)的運用過程又可能導(dǎo)致多用途化犯罪,例如開發(fā)自爆機器人,本身可以利用其殺人,也可利用其破拆他人合法財產(chǎn)。為了預(yù)防這種連鎖的犯罪效果,就需要在刑事政策上做到真正的預(yù)防:既要預(yù)防犯罪結(jié)果的發(fā)生,更要斬斷這種犯罪鏈的存在可能性。因而,將其幫助行為正犯化有利于遏制潛在風(fēng)險擴大化的可能性,也有利于加大打擊人工智能犯罪,實現(xiàn)警示和教育的政策功能。
3 人工智能犯罪幫助行為正犯化的類型
綜上所述,有必要將人工智能幫助行為正犯化,的幫助行為也有類型化的可能。這種可能性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1)提供人工智能犯罪技術(shù),例如研制開發(fā)人工智能程序用于犯罪。2)提供人工智能犯罪工具,例如殺人機器人等。3)將二者予以結(jié)合,即研發(fā)技術(shù)和設(shè)備。具體分析,實際上只有一種可能,即第三種情況。這是因為,人工智能的概念是“深度學(xué)習(xí)+智能機器”的結(jié)合,單純的技術(shù)和單純的實物都不符合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礎(chǔ)上,人工智能犯罪實際上是一種提供犯罪工具的幫助行為;這種幫助行為,需要技術(shù)與實物相互結(jié)合,從而才是真正的幫助行為。傳統(tǒng)理論認為,幫助行為正犯化不排除預(yù)備的可能,也不排除為幫助行為提供幫助行為的可能。提供單純的技術(shù)支持或者是提供單純的實物配件,可能認為是幫助行為的預(yù)備形態(tài)或者是幫助行為。但是,這一切有賴于人工智能犯罪幫助行為的正犯化。對此,基于人工智能犯罪的獨立性和幫助行為正犯化的必要性,有必要將人工智能幫助行為的入罪化。
參考文獻
[1]王愛鮮.幫助行為正犯化視角下的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罪研究[J],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7(02)。
[2]董榮華、白海戎.論幫助行為正犯化的正當(dāng)性——以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為視角[J],思想政治與法律研究,2016(06)。
[3]劉春麗.幫助行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為切入點》[J],福建警察學(xué)院學(xué)報,2017(01)。
[4]劉長斌.幫助行為的“正犯化”研究[D],華東政法大學(xué)碩士畢業(yè)論文,2016:20—25。
[5]于沖.幫助行為正犯化的類型研究與入罪化思路[J],政法論壇,2016(07)。
作者簡介
羅艷芳(1986-),女,湖南瀏陽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刑法。
葉沛春(1988-),男,福建漳州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犯罪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