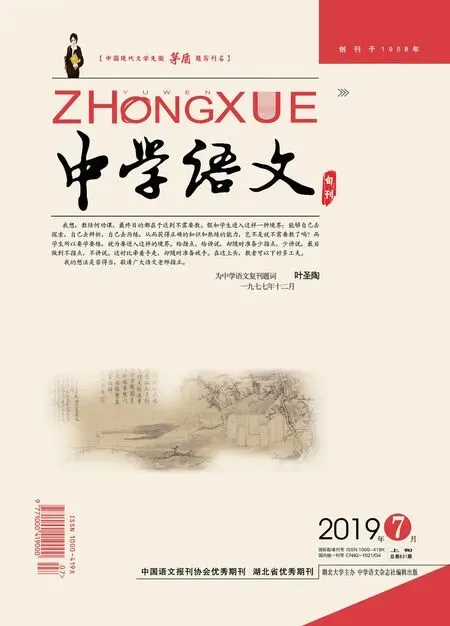敘事散文的“抒情間離”及其教學(xué)運(yùn)用
郭躍輝
一、敘事散文的“抒情間離”
敘事散文,也被稱(chēng)為“寫(xiě)人敘事散文”“敘事抒情性散文”等。這也暗示出,記敘、抒情、描寫(xiě)、議論等多種表達(dá)方式共同存在于這類(lèi)散文中,而且它們呈現(xiàn)出水乳交融的狀態(tài)。記人記事、景物描寫(xiě)、情感抒發(fā)、人物及事件評(píng)論,本來(lái)就是敘事散文的必備要素。作者寫(xiě)作散文的事件,定會(huì)滯后于散文中發(fā)生的事件,畢竟作者不可能邊經(jīng)歷事件,邊創(chuàng)作散文。或者說(shuō),這兩個(gè)事件之間存在著“時(shí)間差”,此種“時(shí)間差”在回憶性散文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像魯迅的散文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shū)屋》《阿長(zhǎng)與 〈山海經(jīng)〉》等,都存在著兩個(gè)“我”,一個(gè)是經(jīng)歷當(dāng)時(shí)事件的“童年之我”,一個(gè)是記述事件、反思事件的“成年之我”。統(tǒng)編教材七年級(jí)上冊(cè)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shū)屋》課文后的“積累拓展”第五題,將這兩個(gè)“我”稱(chēng)為“小魯迅”和“‘大’魯迅”;七年級(jí)下冊(cè)的《阿長(zhǎng)與〈山海經(jīng)〉》課文后的“思考探究”第二題,將這兩個(gè)“我”稱(chēng)為“成年的我”和“童年的我”。而且,“成年之我”往往是與原初事件間隔了較長(zhǎng)時(shí)間的距離之后,對(duì)事件進(jìn)行“再經(jīng)歷”,并且用理性的審慎目光去觀照、反思當(dāng)時(shí)的事件。這就是筆者所說(shuō)的“抒情間離”。
“間離”,原是德國(guó)戲劇家布萊希特提出的史詩(shī)劇的創(chuàng)作特點(diǎn)。他認(rèn)為:“史詩(shī)劇的基本要點(diǎn)是更注重訴諸觀眾的理性,而不是觀眾的感情。觀眾不是分享經(jīng)驗(yàn),而是去領(lǐng)悟那些事情。”①布萊希特所說(shuō)的“間離化”是有意識(shí)地在演員與所演的戲劇事件、角色之間,觀眾與所看演出的戲劇事件、角色之間制造出一種距離或障礙,使演員和觀眾都能跳出單純的情境幻覺(jué)、情感體驗(yàn)或共鳴,以“旁觀者”的目光審視劇中人物、事件,運(yùn)用理智進(jìn)行思考和評(píng)判。②而筆者借用布萊希特的“間離”概念,并將其轉(zhuǎn)化為“抒情間離”。如上所述,寫(xiě)作散文時(shí)的抒情主人公、事件的敘述者,在相隔一段時(shí)間后對(duì)事件進(jìn)行敘述以及“再體驗(yàn)”與“再經(jīng)歷”,從而用一種理性的眼光觀照當(dāng)時(shí)的事件。經(jīng)歷事件時(shí)的情感狀態(tài),與寫(xiě)作事件時(shí)的情感狀態(tài),是有距離的,此即為“抒情間離”。我們可以根據(jù)原初事件與寫(xiě)作事件的距離,將“抒情間離”分為三種:一種是較長(zhǎng)時(shí)間的“長(zhǎng)久間離”,例如回憶童年事件的散文,時(shí)間距離可能達(dá)到二三十年甚至更長(zhǎng);一種是相隔幾年之后,再去寫(xiě)作當(dāng)時(shí)的事件,此為“中度間離”,例如朱自清的《背影》、史鐵生的《秋天的懷念》、楊絳的《老王》等;一種是原初事件與寫(xiě)作事件的時(shí)間比較模糊的,或者說(shuō)是相隔時(shí)間不長(zhǎng)的,例如莫懷戚的散文《散步》,文章第一句話(huà)就是“我們?cè)谔镆吧仙⒉健保坪踉跏录c寫(xiě)作事件是同時(shí)發(fā)生的,此為“即時(shí)間離”。本文要分析的,是“中度間離”的文章與案例。
例如朱自清的《背影》,不少教師認(rèn)為散文寫(xiě)的是“父愛(ài)”,也有的專(zhuān)家認(rèn)為寫(xiě)的是“生命意識(shí)”。“父愛(ài)”是一種情感,是事件發(fā)生時(shí)的“我”和父親的情感狀態(tài),那么,作者在1925年寫(xiě)作《背影》時(shí)對(duì)“父愛(ài)”的態(tài)度和父親買(mǎi)橘子時(shí)的態(tài)度,究竟有沒(méi)有區(qū)別?黃厚江老師執(zhí)教《背影》,就是從這種“抒情間離”入手的。父親翻越月臺(tái)去買(mǎi)橘子的時(shí)間和寫(xiě)作《背影》的時(shí)間存在著差距,這一點(diǎn)也是“抒情間離”效果產(chǎn)生的原因。前者更多側(cè)重于父親對(duì)兒子的愛(ài),以及兒子的感動(dòng)之情,后者則側(cè)重于兒子對(duì)父愛(ài)的理解。而“背影”的作用在于:正是這樣一個(gè)艱難的、“不容易”的“背影”喚醒了作者對(duì)父親的關(guān)注,也才有了多年后“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發(fā)之于外”對(duì)父親深深的理解。黃老師得出的結(jié)論是:“我們認(rèn)為《背影》主要表達(dá)的并不是父親對(duì)兒女的關(guān)愛(ài),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父子之情,而是一個(gè)兒子對(duì)父親的艱難和不容易的理解過(guò)程。”③這樣的解讀,更符合散文創(chuàng)作的實(shí)際狀況。
二、教學(xué)運(yùn)用之一:基于情感體驗(yàn)的教學(xué)落點(diǎn)的選擇
王榮生教授認(rèn)為:“散文的精妙處,閱讀散文的動(dòng)人處,在于細(xì)膩,在于豐富,唯有通過(guò)個(gè)性化的語(yǔ)句章法,我們才能感受、體認(rèn)、分享它所傳達(dá)的豐富而細(xì)膩的人生經(jīng)驗(yàn)。”④敘事散文自然也離不開(kāi)情感的抒發(fā)與書(shū)寫(xiě)。因此,“散文教學(xué)應(yīng)注重學(xué)生審美、情感的體驗(yàn),讓學(xué)生沉浸在人物的感情當(dāng)中,體悟情感、洞察人性、豐富心靈、涵養(yǎng)人格。”⑤問(wèn)題是,一篇散文中的情感脈絡(luò)是多元的,情感類(lèi)型是多樣的,教師的教學(xué)著力點(diǎn)究竟應(yīng)置于何處呢?這就需要從“抒情間離”的角度進(jìn)行分析。
史鐵生的《秋天的懷念》一文出現(xiàn)了“我”、母親和妹妹三個(gè)主要人物,引導(dǎo)學(xué)生體驗(yàn)、分享人物的情感,應(yīng)該是重要的教學(xué)內(nèi)容之一。但教學(xué)落點(diǎn)是母愛(ài)呢,還是“我”對(duì)母親的懷念以及痛悔之情呢?有的教師在分析第一段時(shí),止步于“母愛(ài)的偉大”,這其實(shí)是沒(méi)有從“抒情間離”的角度進(jìn)行進(jìn)一步思考與探究。文章寫(xiě)于母親去世七年之后,文章流露出的不僅有深切的懷念,還有一種悔恨。例如第一段中作者用到了幾個(gè)疊詞和動(dòng)詞,即“悄悄地躲出去”“偷偷地聽(tīng)著我的動(dòng)靜”“悄悄地進(jìn)來(lái)”“眼邊兒紅紅的”。按照常理,在兒子發(fā)脾氣摔東西時(shí),母親應(yīng)該立即過(guò)來(lái)安慰,這是人之常情,但文中的母親卻“躲”了出去,看似不合情理,實(shí)際上恰恰是母親照顧到雙腿癱瘓的兒子的自尊心,希望給“我”一個(gè)獨(dú)處的空間,這是一種理解。同時(shí),母親內(nèi)心又十分痛苦,十分憐惜自己的兒子,這一點(diǎn)從“偷偷地聽(tīng)”“悄悄地進(jìn)來(lái)”可以看出。當(dāng)“我”看到母親“眼邊兒紅紅的”時(shí),按照常理應(yīng)該能夠體會(huì)到母親的痛苦,但“我”依然“視而不見(jiàn)”。作者七年之前看到母親“眼邊兒紅紅的”時(shí)的情感,和寫(xiě)作本文時(shí)回想當(dāng)時(shí)的情形,對(duì)母親“眼邊兒紅紅的”的情形進(jìn)行“再體驗(yàn)”時(shí)的情感,是不一致的。拉開(kāi)了一定時(shí)間距離之后,特別是當(dāng)母親去世之后,再來(lái)寫(xiě)這個(gè)片段,流露出來(lái)的就是一種懷念之情、痛悔之情,一種“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的深深的遺憾。因此,教學(xué)落點(diǎn)應(yīng)該是“我”寫(xiě)作本文時(shí)的情感狀態(tài)。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教師在“情感體驗(yàn)”的基礎(chǔ)上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價(jià)值觀教育”,不自覺(jué)地史鐵生筆下的“母愛(ài)”泛化為普遍的母愛(ài),教育學(xué)生要愛(ài)自己的母親,或者就是抓住“好好兒活”等反復(fù)出現(xiàn)的句子,教育學(xué)生要珍惜生命。從“抒情間離”的角度看,筆者認(rèn)為這個(gè)教學(xué)落點(diǎn)也不準(zhǔn)確。將個(gè)人化的情感抽象化并將其“占有”而非“分享”,這是散文教學(xué)常見(jiàn)的偏差。實(shí)際上,對(duì)于《秋天的懷念》中的情感,教師要在“體驗(yàn)分享”的基礎(chǔ)之上,引導(dǎo)學(xué)生用理性的甚至是“隔離”的眼光對(duì)散文的情感進(jìn)行審視。那就是:作者并未一味沉浸在對(duì)母親的懷念以及深深的痛悔之中,而是能夠重新看待生命的價(jià)值,重新燃起對(duì)生活的希望之火。如果說(shuō)第一段中的“好好兒活”讓人情不自禁熱淚盈眶的話(huà),最后一段中的“好好兒活”應(yīng)該引起讀者對(duì)生命的思考。這個(gè)教學(xué)落點(diǎn)的切入,教師可以引導(dǎo)學(xué)生圍繞教材插圖進(jìn)行思考。教材插圖中的史鐵生,雙臂抱胸,目光自信,而且笑得十分爽朗,這與整篇文章的情感基調(diào)一致嗎?插圖中史鐵生的笑容,是將那種失去母親的遺憾、對(duì)母親的痛悔以及對(duì)自己的生命缺憾轉(zhuǎn)化為樂(lè)觀、堅(jiān)強(qiáng)的生命態(tài)度之后的必然反映。這才是本文“情感教學(xué)”的最終落點(diǎn)。
三、教學(xué)運(yùn)用之二:基于認(rèn)知沖突的問(wèn)題設(shè)置與探究
所謂認(rèn)知沖突,指的是人在認(rèn)知發(fā)展過(guò)程中,原有認(rèn)知圖式與新的情境矛盾時(shí)在心理上所產(chǎn)生的沖突。教師在進(jìn)行散文教學(xué)時(shí),也要從學(xué)生易產(chǎn)生認(rèn)知沖突的地方切入,設(shè)置問(wèn)題,引發(fā)學(xué)生的思考與探究,從而達(dá)到“思維發(fā)展與提升”的學(xué)科核心素養(yǎng)目標(biāo)。從認(rèn)知沖突到建立新的認(rèn)知協(xié)調(diào)與平衡,本身就是思維訓(xùn)練的過(guò)程。散文中的“抒情間離”的存在往往會(huì)讓人產(chǎn)生認(rèn)知沖突,教師要善于從這些點(diǎn)入手,通過(guò)問(wèn)題設(shè)置、探究、討論,達(dá)成一定的教學(xué)目標(biāo)。
對(duì)于楊絳的《老王》,幾乎所有的教師都會(huì)抓住最后一句話(huà)“幾年過(guò)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gè)幸運(yùn)的人對(duì)一個(gè)不幸者的愧怍”,指導(dǎo)學(xué)生分析“愧怍”的表現(xiàn)及原因。其實(shí),“愧怍”產(chǎn)生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是“現(xiàn)在”,“幾年過(guò)去了”意味著作者是在拉開(kāi)了與原初事件的時(shí)間距離之后寫(xiě)作本文的。那么,“愧怍”就不是一種“即時(shí)間離”而是“中度間離”的表現(xiàn)。圍繞這個(gè)點(diǎn),我們?cè)賮?lái)解讀文中的某些細(xì)節(jié),例如“我們當(dāng)然不要他減半收費(fèi)”,作者為什么要用“當(dāng)然”這個(gè)詞?一般的理解是:這里表明作者一家之前幫助老王是誠(chéng)心誠(chéng)意的,并不要求老王回報(bào)。作者一家也很同情老王的貧苦生活,從來(lái)沒(méi)有占便宜的念頭。這種理解無(wú)可厚非,但沒(méi)有聯(lián)系“愧怍”進(jìn)行分析。有論者指出這句話(huà)“展示了知識(shí)分子與底層勞動(dòng)大眾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境遇落差和難以彌合的心理距離”⑥,這也是“愧怍”的根本原因。教師只要請(qǐng)學(xué)生反復(fù)閱讀“當(dāng)然”這個(gè)詞,并結(jié)合文中其他細(xì)節(jié)進(jìn)行分析,學(xué)生是可以把握到這層含義的。如果我們考慮到“抒情間離”的因素,就會(huì)繼續(xù)追問(wèn)如下問(wèn)題:
楊絳在寫(xiě)這篇文章用到“當(dāng)然”一詞時(shí),究竟有沒(méi)有知識(shí)分子的那種優(yōu)越感?如果沒(méi)有,作者為什么要“愧怍”?如果有,難道她不清楚用到這個(gè)詞之后會(huì)暴露自己的“人格缺陷”嗎?
這樣的問(wèn)題就是建立在“認(rèn)知沖突”的基礎(chǔ)之上的。按照一般人的心理,自己不太光彩的一面、容易引起誤解的一面,寫(xiě)入文章時(shí),要么會(huì)避免出現(xiàn),要么會(huì)“文過(guò)飾非”,不可能冒著被人指責(zé)的風(fēng)險(xiǎn)直接袒露真實(shí)的想法。而楊絳明知用“當(dāng)然”會(huì)引來(lái)指責(zé),為何不直接說(shuō)“我們不要他減半收費(fèi)”?如果這樣的追問(wèn)有點(diǎn)牽強(qiáng)的話(huà),我們還可以抓住老王去世之后,作者與老李對(duì)話(huà)完畢之后的“我也不懂,沒(méi)多問(wèn)”一句進(jìn)行思考:
老王把畢生積蓄送給了楊絳一家,楊絳一家明知與老王家相距不遠(yuǎn),卻沒(méi)有去看望病危的他,而且當(dāng)別人告知老王的死訊時(shí),作者居然說(shuō)“我也不懂,沒(méi)多問(wèn)”,這豈不是太冷漠了嗎?作者在寫(xiě)這篇文章時(shí),知不知道用“我也不懂,沒(méi)多問(wèn)”的句子會(huì)讓人感到她的冷漠?如果知道,為什么還要用這些詞句?
這其實(shí)就是一種認(rèn)知沖突,需要學(xué)生在理解作者的情感世界的基礎(chǔ)上,建立新的認(rèn)知平衡。建立新的認(rèn)知平衡,需要有“雙重觀照”的視點(diǎn)。一是作者“觀照”老王,這些句子表達(dá)的恰恰是幾年之中“我”內(nèi)心深處揮之不去的“愧怍”,真誠(chéng)袒露自己的內(nèi)心,才能襯托出“愧怍”的深切;二是讀者“觀照”作者,作者在文中真誠(chéng)地剖析自己的靈魂,不正表明了知識(shí)分子的良知以及人身上的那種善良的人道主義情懷嗎?這一點(diǎn)與巴金在《小狗包弟》中的自我反思與批判的邏輯是很相似的。
總之,“抒情間離”的存在,啟發(fā)教師不僅要關(guān)注原初事件的過(guò)程、狀態(tài)以及人物心理,更要關(guān)注作者創(chuàng)作散文時(shí)的心理狀態(tài)與情感傾向;不僅要對(duì)抒情對(duì)象及其情感進(jìn)行體驗(yàn),更要對(duì)抒情主體的情感與態(tài)度進(jìn)行理性觀照。
- 中學(xué)語(yǔ)文的其它文章
- 群文閱讀:從占有、會(huì)通走向存在
——景慧穎《伶官傳序》教學(xué)實(shí)錄評(píng)析 - 核心素養(yǎng)視角下的《拿來(lái)主義》教學(xué)構(gòu)想
- 設(shè)計(jì)“學(xué)的活動(dòng)”,促成思維延拓
——戴望舒《雨巷》深度教學(xué)探究 - “腳手架”:為論述文寫(xiě)作引路
——由歐陽(yáng)煒的作文課《論辯的針對(duì)性》引發(fā)的思考 - 高中記敘文“語(yǔ)言建構(gòu)與運(yùn)用”素養(yǎng)現(xiàn)狀調(diào)查與改進(jìn)建議
- 《史記》“整本書(shū)閱讀與研討”的思考與實(shí)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