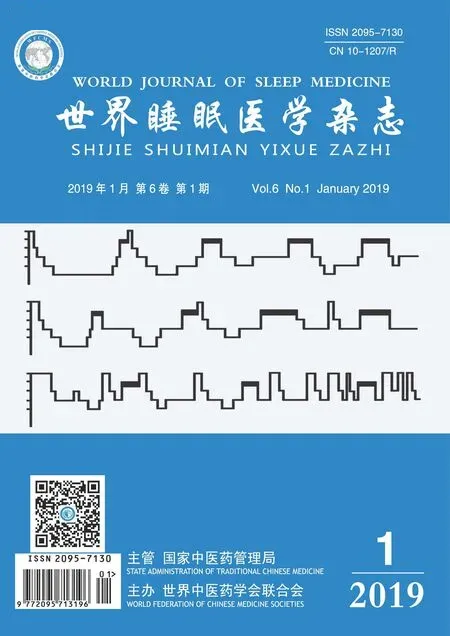以脾胃為樞扭結合五臟治療失眠案例分析
王渙群 卞煒( 重慶永川區中醫院腦病科,重慶,4060; 重慶永川區中醫院康復科,重慶,4060)
失眠為陰陽失調,陽不入陰,陰陽失交所致[1-2]。睡眠的生理基礎[3]是陰陽交和、平衡,陰陽失交,陽不入陰,陰不斂陽,致使魂不守舍,故而發為失眠。該病多由情志過極、勞逸失度、久病體虛、飲食不節等引起,陰陽失調、陽不入陰所致。《靈樞·口問》云:“衛氣晝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主臥……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詳細闡述了睡眠的生理基礎,即衛氣的正常運轉、陰陽交替是睡眠正常的根本保證。若衛氣運行失常,營衛失和,必然會影響睡眠甚至失眠。人的精神白天向外,夜間精神要回向內才能達到好的睡眠,如果向內的精神不能收斂,就會失眠。陰陽失交致失眠分為3類[4]:一為陰虛,因陰液虧虛不足以收斂陽氣,導致衛氣常行于外,故而失眠;二為陽盛,為陽氣太盛致陰氣相對不足,導致陽氣浮越于外而致失眠。三為邪阻,所謂邪阻,就是人體的病理產物或病理狀態阻礙了“陽入于陰”的道路。
1 病例詳情
某,女,29歲,護士。
一診:從小失眠,不易入睡,睡后易醒,心慌多夢,反復糾結,控制不住思考,經常頭暈,食欲二便調。舌質淡白,苔中下部薄黃微膩;脈象:右寸關弦大,右尺沉細無力;左寸細數,尺脈沉細無力。BP:98/56 mmHg。MTL 214.87 pg/mL。
中藥5劑,1劑/d,水煎500 mL,口服:麩炒白術30 g、首烏藤30 g、北沙參30 g、山茱萸30 g、黃芩片5 g、干石斛30 g、鉤藤30 g(后下)、郁金20 g、白芍20 g、干姜3 g、敗醬草10 g、桂枝10 g、煅磁石10 g、黃芪30 g、麥冬10 g、炒酸棗仁30 g。
二診:患者失眠稍有改善,仍易醒,反復糾結,控制不住思考,經常頭暈,食欲二便調。舌質淡白,苔中下部薄黃微膩;脈象:右寸關弦大,右尺沉細無力;左寸細數,尺脈沉細無力。BP:102/56 mmHg。MTL 222.82 pg/mL。
上方去桂枝10 g、煅磁石10 g、黃芪30 g、麥冬10 g、炒酸棗仁30 g、加焦山楂30 g、連翹10 g、柴胡12 g、川牛膝10 g、赤芍10 g、疏肝和胃解郁熱。
中藥5劑,1劑/d,水煎500 mL,口服:白術30 g、首烏藤30 g、北沙參30 g、山茱萸30 g、黃芩片5 g、干石斛30 g、鉤藤30 g(后下)、郁金20 g、白芍20 g、干姜3 g、敗醬草10 g、焦山楂30 g、連翹10 g、柴胡12 g、川牛膝10 g、赤芍10 g。
但患者訴療效不佳。使用艾司唑侖治療失眠,睡眠時好時壞。
三診:患者不易入睡,睡后易醒,心慌多夢,因長期上夜班近半年失眠病情加重,月經量少,稍推后,舌質淡白苔薄稍膩脈細數滑,重按稍差,右寸關滑,尺稍弱。MTL 211.43 pg/mL。
中藥4劑,1劑/d,水煎300 mL,口服:黨參片20 g、白術20 g、琥珀10 g(沖服)、山藥20 g、醋鱉甲10 g(先煎),大棗10 g、制何首烏10 g、升麻10 g、淡豆豉10 g、炒金櫻子肉10 g、當歸20 g、天冬10 g、茯神木20 g、法半夏10 g、薏苡仁10 g。
四診:患者心悸失眠加重,平躺時可聽到心跳聲,心率100次/min左右,予以美托洛樂12.5 mg/bid后心悸癥狀稍有減少,心率減為80次/min左右,失眠,整夜無法入睡,舌質淡白苔薄稍膩脈細數滑,重按稍差,右寸關滑,尺稍弱。MTL 202.14 pg/mL。
中藥4劑,1劑/d,水煎500 mL,口服:鉤藤30 g(后下),麥冬10 g、五味子10 g、麩炒白術20 g、白芍20 g、龍骨20 g、黃芩片5 g、敗醬草10 g、干石斛30 g、北沙參30 g、首烏藤30 g、桑葉30 g、山茱萸30 g、炒酸棗仁30 g、法半夏10 g。
五診:患者睡眠可,夢多,舌質淡白苔薄稍膩脈細數滑,重按稍差,右寸關滑,尺稍弱。
中藥5劑,1劑/d,水煎500 mL,口服:麥冬10 g、桑葉30 g、法半夏10 g、敗醬草10 g、五味子10 g、首烏藤30 g、龍骨20 g、黃芩片5 g、山茱萸30 g、炒酸棗仁30 g、北沙參30 g、鉤藤30 g(后下)、白芍20 g、麩炒白術30 g、干石斛20 g MTL 243.15 pg/mL。
患者失眠明顯緩解,無心慌胸悶,次日精神可。近半年來未再復發。
2 討論
該患者長期慢性失眠,心肝血虛,久病及腎則心腎不交出現不易入睡,睡后易醒,心慌多夢,反復糾結,控制不住思考,食欲二便調。舌質淡白,苔中下部薄黃微膩;脈象:右寸關弦大,左寸浮細,尺脈沉細無力。五行之中,各有陰陽,陰生五臟,陽生六腑。陰陽通過升降出入,升降有度,肝氣上升肺金斂降,腎水下降心火上升,臟腑周流,升是為了更好的降,降是為了更好的升,升降協調運動,臟腑氣血周流起來,保持著正常的衛氣運行。
上述病例中,一診、二診、四診有相同的藥物:麩炒白術、首烏藤、北沙參、山茱萸、黃芩、干石斛、鉤藤、郁金、白芍,補肝腎解郁降肺,肝藏血,肺藏氣,而氣原于胃,血本于脾。雖然脾胃為氣血生化之源,并未用大量補脾藥物,氣血由脾胃生化而來,不等于要大量健脾藥物,基本方以升肝降肺來調理脾胃,患者明顯右寸脈弦大,說明肺氣不降,氣統于肺,凡臟腑經絡之氣,皆肺氣之所宣布也,所以通過降肺氣來升肝,肝升則不郁,心火可以下滋腎,腎水可以升木,陰陽升降平衡則安然入眠;二診中加入焦山楂、連翹、柴胡、川牛膝、赤芍解郁清肝熱,肝升不起來更加重了失眠;三診中大量升麻、淡豆豉、炒金櫻子肉、當歸、天冬、茯神木、法半夏補肺氣,肺氣不降則肝氣不升,心脈受阻則心跳加快。在四診、五診中通過降肺金升肝木睡眠改善明顯。故諸多經典的失眠學說,如“陰陽說”“神主說”“氣血說”“營衛說”與中醫的“胃”都有密切的聯系[5]。如陰精的虧損,封藏力差,肝膽疏泄失常,脾運化失常,生血之力差影響睡眠,其他臟腑功能改變對脾土的氣化產生變化都會對睡眠產生影響,失眠的問題是陰陽的升降出入出了問題,在升降出入的過程中脾胃發揮著重要的樞紐作用,失眠輕重與腦腸肽相關性,胃腸是人的第二大腦[6](腹腦或腸腦),它是腸神經系統,脫離了中樞神經系統支配的獨立活動系統,幾乎所有中樞神經系統中的遞質和調質均存在于腸神經系統中,大腦[7]通過交感或副交感神經的傳入或傳出調節腸神經系統活動,而腦腸肽作為神經遞質在神經的傳導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