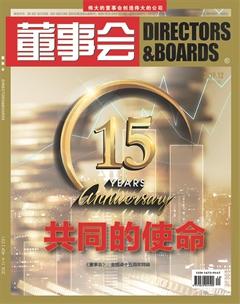本質思維
王勇華
九方皋相馬
唐代韓愈《馬說》中有“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名句傳承至今,廣為熟悉。很多人也因此知道了有伯樂這個相馬大師的存在。其實,歷史上與伯樂齊名的還有另一個重要人物:九方皋。可以說,今天大多數人都知道有伯樂而不知道有九方皋。北宋著名文學家黃庭堅就曾感嘆過“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皋”,這句話簡直就是“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翻版,由此可見,九方皋與伯樂一樣,都極為稀有。
九方皋的寓言故事記載于《列子?說符》。《列子》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是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列子后學著作的匯編。全書共八篇,一百四十章,由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話故事、歷史故事組成。《列子》屬于諸家學派著作,基本上是以寓言形式來表達精微的哲理,是一部智慧之書,它能開啟人們心智,給人以啟示,給人以智慧。
九方皋的故事大致如下。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pin)而黃。”使人往取之,牡(mu)而驪(li)。穆公不說(同“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九方皋的故事很簡單,秦穆公認為一個連馬的性別和顏色都看不準的人,怎么能識別千里馬呢?伯樂則不以為然,認為九方皋“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因而能觀“天機”,尋得天下最好的千里馬,而事實也證明了伯樂的判斷和九方皋的見識的確高明。
九方皋的故事中大致蘊含著以下幾個層面的智慧:一是看問題時要有所舍棄才能有所專注并產生重大發現;二是選人用人要求其大節,而不苛責小事,要從根本看問題,抓住主要特征,不以偏概全;三是做事情要將獲得的感性材料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這樣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質。
九方皋的故事固然充滿傳奇感,但其背后所隱喻的哲理卻充滿了辯證性。例如,所謂通過專注于重點,舍棄次級要素的方式獲得發現的方法論,必將面臨“管中窺豹”“一葉知秋”“見微知著”等方法論的挑戰。再如,所謂選人用人舍小節,求大節,不以偏概全的做法,就會面臨“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錙銖必較”“深思遠慮”“無微不至”等做法的責難。還如,“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的工作方式是否會陷入絕對主觀主義,唯心主義,剛愎自用,一意孤行?
寓言故事畢竟只是故事而已,九方皋的故事所要表達的無非是一種觀點和態度。只要其具有某個角度和層面的智識啟發意義就足夠了,不必苛求故事背后的邏輯和原理完全周延和正確。
九方皋故事中所表達的相馬的方法論也許有所爭議,但其中所表達的無論顏色、性別等如何,不能只看表面筋骨,關鍵是要識別出千里馬,即看穿馬的本質特征的認識論則是極其珍貴的。即建立本質思維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思維方式,認清事物的本質既可能是生活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尚未認清事物本質時),也可能是指導生活持續開展的基本規則和依托(已經認清事物本質時)。
忽視的后果
現實經濟生活中有很多忽視本質思維的案例,有些事例的后果往往非常嚴重,教訓極其深刻。

例如,前幾年風靡全國的P2P網貸平臺,曾經如火如荼般瘋狂發展,成為熱點經濟金融現象。然而,近些年多個網貸平臺項目或與之相關的金融產品“爆雷”乃至“老板跑路”,引發監管層開始對網貸平臺及其產品進行嚴格篩查清理和整頓,甚至當前幾個重點省份已經徹底取締網貸平臺。稍微懂得一些金融知識的理性投資者都知道,多數P2P網貸平臺的商業模式,其本質就是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然而,廣大普通投資人或許完全抱著賭徒心理,沖著超高額回報一擁而上。他們根本就不考慮自己的資金借出后的用途,根本不考慮項目穿透后的“底層資產”究竟是什么,根本不考慮高超額回報(有的甚至高達40%的年化投資回報)是如何產生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看穿這些問題,也就看穿了網貸平臺的本質,就可以理性決定自己的投資取舍了。可惜的是,廣大普通投資人或許就像九方皋相馬一樣,只“見其所見(短期高額回報),不見其所不見(商業模式的可靠性、底層資產的真實性)”,只“視其所視(高回報),而遺其所不視(高風險)”,所以也就難以識別投資的成色和效果了。
再如,信托行業前些年一直高聲呼吁要“回歸本源”,成為監管政策和行業從業主體的“普遍共識”。然而,沒有人真正能夠說清什么是信托行業的本源。如果回顧歷史,信托制度產生于英國中世紀衡平法院判例創設的用益(use)制度,初衷是為了解決家族財富傳承中的法律規避問題。從域外信托制度發達的英美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并沒有專門的信托行業和信托行業從業主體,更強調的是通過信托法律關系中的信義義務(fiduciary duty)來調整投資人和資產管理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試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家信托行業和信托制度的“本源”是什么?其實,號召信托行業回歸本源是很好的本質思維的運用模式,但效果卻不得彰顯,究其原因在于并沒有認識到我國信托行業的本質究竟是什么,所以,相關導向性改革意見是虛無縹緲的,或者說是沒有目標的導向。
還如,當前金融界有時將金融產品大類區分為“標品”與“非標品”。通常來說,標品與非標的主要區分在于是否具有較好的流動性,以及存續期能否進行適時估值。標品因其具有較好的流動性和估值連續性等特征,當不能按期兌付或損失時,投資人一般不會向管理人追責。但是,非標產品因為缺乏適時估值機制且因流動性不足,當不能按期兌付或損失時,投資人往往要求管理人“剛兌”或追究管理人的管理責任。根據最基礎的金融產品運行邏輯,因為非標產品存在流動性差和缺乏實時估值機制,其風險原則上相對標品而言更高,管理人需要履行更高程度的謹慎管理義務甚至承擔“剛兌”責任,相應的,根據風險與收益匹配規則,管理人應該收取更高的管理費才有可能覆蓋風險成本。然而,當前金融市場中卻大量存在高風險非標產品管理人所收取的管理費甚至不如銀行存放款息差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廣泛存在,究竟是什么外在因素扭曲了非標產品管理費市場的正常定價機制,還是非標管理主體根本就沒有看清自己所管理的產品的風險本質呢?
九方皋相馬的寓言故事看似簡單,但故事背后的啟發意義,啟發意義的辯證性,尤其是其中所蘊含的對本質思維的強烈推崇,著實對社會現實有著深深的指導意義。如果看不穿事物的本質,或者僅僅浮于表象不去深入追尋事物本質,掌握不了認識事物的辯證方法,那就只能如“股神”巴菲特所言:只有在潮水退去時,你才會知道誰一直在裸泳!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