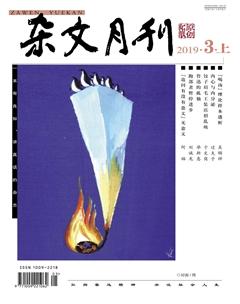“出于本能”又出于什么?
鄭殿興
讀1月4日《新京報》通訊《旅行團異國遇襲兩中國男子擊退劫匪》——特別是朱川“出于本能”那句話,讓我頓時眼前一亮,激情揮毫了。
2018年12月20日,圣彼得堡,一個來自中國的36人旅行團,凌晨5時20分遭遇了3名歹徒搶劫,就在不少游客“嚇得不知所措時”,同是游客的朱川卻一下子“沖上去,將搶包的那個男子猛地撂倒按在地上……那名搶包的男子被控制后,另外倆人(同伙)變得很憤怒”“開始做掏兜的動作,準備攻擊朱川”“這時,已經在車上的趙文勇飛快下來,將一名站立的男子踹倒。隨后,全車人都下來立刻震懾住了三名男子”,三人趕緊落荒而逃了……接著便是:“所有的游客包括俄羅斯司機……都為他倆鼓掌。”
鼓掌、叫好、點贊、稱妙……在這些該有的表現之外,還應發出這樣的一問:為啥他倆敢出手?
朱川本人的回答是:“出手完全出于本能。”
“出于本能”?
此言,似不很“響亮”,不很“高大上”……但我看,這話其實是句大實話。
本能,有先天的,如孩子一生下來,就會哭、會吃奶;有后天的,譬如一遇到“刺激”,人便會無意識地做出反應,拒絕、挺身或退縮、躲避……“旅行團異國遇襲”時,朱川、趙文勇的“出手”及不少人嚇得不知所措,便屬這類反應。只不過,前一種可稱之“正義本能”,大可稱道;后一種呢,乃“自然本能”,雖多可理解,稱道肯定談不上了。
“出于本能”的“正義本能”,哪兒來的?不是遺傳,更非神靈賦予,只能是人在成長、生活實踐中,有意識地磨煉、培育出來。“正義本能”能量積蓄、儲備多了,在需要顯現時,便會無意識地釋放出來——“該出手時就出手”,決用不著誰來督促、下命令。仍以朱川為例:“幾年前在廣州,一位女士的耳環被搶,我追了那個搶匪好幾條街,他當時還拿著刀,最后把他制伏,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引文同上)再如,身為輔警的趙文勇,如此的自覺磨煉肯定少不了……所以,他才會從車上跑下來助力朱川,一腳踹趴下搶匪。
由“正義本能”,聯想到了華中科大的“宿管阿姨”金林君“告別信走紅網絡”事:在金林君退休離校的最后一天,“學生圍著她,和她擁抱、告別”。“畢業生回校送我,抱頭痛哭”……為什么?因為她心里有學生——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愛他們,幫他們:多次幫貧困生找兼職、做勤工儉學;曾為一名沒錢買車票的學生,“掏了1000塊”;經常給兩個貧困生帶來飯菜,讓他們“感受到家的溫暖”。所以,這兩個“做勤工儉學的孩子,每年國慶假期,都會回來看我,2018年10月5日,帶著孩子來看我,特別感動”。(2019年1月3日《新京報》對話版《華中科大一宿管阿姨退休 告別信走紅網絡》)
金林君如此愛學生,也可視為一種本能——“善良本能”的反應。這樣的善行,因無作秀、功利因素,才會如此長久,讓人們感嘆連連。
朱川、趙文勇的“正義本能”,表現的是扶危——見義勇為、挺身而出;金林君的“善良本能”,表現的是濟困——見難就幫、樂于助人。如此本能,委實是中華民族扶危濟困美德在現實的繼承與光大:如此扶危即見義勇為的“大善”和如此樂于助人即助困的“小善”,都是“讓世界充滿愛”的感人畫面!
至此,對“出于本能”又出于什么之問,就可這樣作結了:本人主動、自覺地磨煉、培養,讓“善”的本能能量不斷積蓄、積累……就會在“善”的本能需要進發之時,迅猛地迸發出來!
此答,是就個體而言——要讓“出于本能”之“善”多一些放大效應,決離不開好的社會環境譬如好的輿論環境!幾年前,《雜文月刊》、北京市雜文學會和《人民日報》文藝部等單位聯合舉辦的雜文征文“善行民族風”,就是對“出于本能”之“善”——“大善”“小善”送上的“鮮花”“掌聲”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