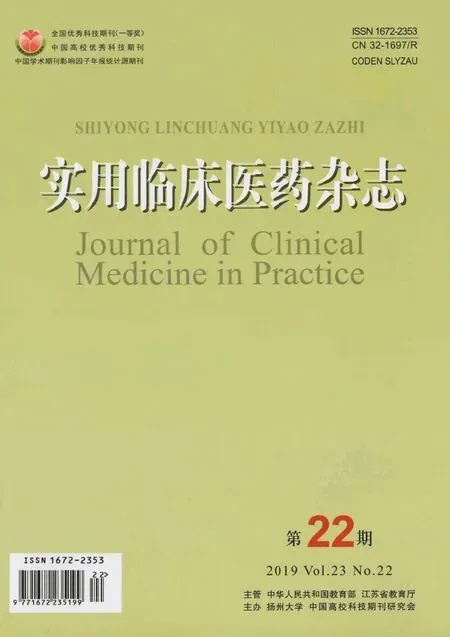1, 25-二羥維生素D3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作用研究進展
張夏霞, 李校天, 李 沙, 黃紅洽, 劉 雨
(1. 河北工程大學臨床醫學院, 河北 邯鄲, 056004; 2. 河北工程大學附屬醫院 消化內科, 河北 邯鄲, 056004;3. 河北工程大學 醫學院, 河北 邯鄲, 056004)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一類多系統疾病,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生活習慣的改變,其發病率逐漸上升,最終可進展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硬化,甚至肝癌。1, 25-二羥維生素D3[1, 25-(OH)2D3]是人體內維生素D的最終活性形式,正常人群的維生素D缺乏(VDD)具有廣泛性,而NAFLD患者體內的維生素D水平則更低。現將1, 25-(OH)2D3對NAFLD的作用的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概 述
NAFLD是一類無過量飲酒史(無飲酒史,或飲酒折合乙醇量男性<30 g/d, 女性<20 g/d)[1]并排除藥物或其他導致脂肪肝等干擾因素的臨床綜合征,分為非酒精性脂肪肝、NASH、NASH肝硬化、NASH相關性肝細胞癌等組織學類型[2]。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亞洲地區NAFLD的發病率可達25%[3], 有研究[4]匯總各國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也顯示發病率不同程度上升,并且這種趨勢一直在加劇,嚴重影響了人類的健康。目前已明確肥胖、2型糖尿病、血脂異常、代謝綜合征等會增加NAFLD發病風險,同時NAFLD患者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慢性腎臟疾病等的患病風險也會增加[5]。NAFLD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以肝臟甘油三酯蓄積為主要特點,是機體內多種信號通路及復雜調控失衡的結果,目前指南推薦以改變膳食結構及增強鍛煉為主要干預方式,但仍缺乏明確推薦的藥物治療方法。1, 25-(OH)2D3是維生素D的活性形式,除具有抗氧化、調節鈣磷代謝等作用外,其對糖尿病[6-7]、肺病[8-10]、腫瘤[11-12]、免疫類疾病[13-15]等均有影響。一些前期的動物和體外實驗[16]發現1, 25-(OH)2D3可通過抑制肝星狀細胞的增殖來延緩肝纖維化進展。近來大量研究表明,活性維生素D參與NAFLD的發生與發展,可緩解NAFLD的疾病進程。
2 NAFLD與VDD
維生素D參與人體多種生理過程,除通過食物獲得外,也通過太陽光照催化皮膚中7-脫氫膽固醇(7-DHC)轉化為前維生素D3, 在血液中與維生素D結合蛋白(DBP)結合,在肝臟維生素D-25-羥化酶作用下轉化為25-羥基維生素D3[25-(OH)D3], 最終在腎臟轉化為1, 25-(OH)2D3[17]。久坐、長時間室內工作以及高脂高糖飲食導致VDD普遍存在。Holick M F[18]綜合多個國家的調查結果,表明了VDD的廣泛性。
少數研究表明維生素D與NAFLD之間并無相關性, Jaruvongvanich V等[19]在一項涉及974例NAFLD患者的臨床薈萃分析中,發現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活動度積分(NAS)及纖維化評分的高低與血清25-(OH)D3的水平無顯著相關性。Patel Y A等[20]檢測維生素D代謝基因(CYP24A1, CYP27, CYP2R1, CYP3A4, VDR)的肝臟表達后,發現這些基因的表達與NAFLD嚴重程度之間沒有任何關系,證明NAFLD的組織學特征與維生素D水平之間缺乏關聯。
目前多數研究結果支持維生素D和NAFLD之間具有相關性, Roth C L等[21]在動物實驗中發現高脂高糖飲食合并VDD的SD大鼠相比低脂組及高脂伴維生素D含量正常組的大鼠,肝臟炎性因子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和白介素-1β(IL-1β)表達上調更明顯,同時提出VDD通過脂多糖(LPS)結合CD14/LBP增敏系統激活Toll樣受體(TLR)2和TLR4的信號通路,刺激下游炎癥信號分子導致脂肪變性和炎癥,推動NAFLD的進一步發展。Sharma等[22]發現母體鈣和維生素D的缺乏會使雌性后代脂質代謝異常,導致肝臟脂肪變性。
Beilfuss A等[23]對106例NAFLD患者的肝臟活檢標本進行分析,發現NAFLD患者血清維生素D水平降低,肝組織中的維生素D受體(VDR)基因表達增加。敲減VDR基因表達后會增加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誘導的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A)的表達。Nelson等[24]將190例經組織學檢查確定為NASH的患者按血清維生素D水平分類,其中55%患者有VDD(<20 ng/mL), 在調整年齡、性別、種族、體質量指數(BMI)、谷丙轉氨酶(ALT)和糖尿病狀態后,表明VDD與NASH獨立相關。韓國學者[25]的一項橫斷面研究發現,在調整代謝綜合征和內臟脂肪后,男性VDD與NAFLD之間存在顯著關系。中國一項包含2 960名參與者的大樣本臨床實驗中,調整年齡、吸煙、檢查季節、血清鈣、甲狀旁腺激素和所有可能的混雜因素,單變量相關分析顯示男性血清25-(OH)D3與肝臟脂肪含量顯著相關,女則性不然[26]。Targher G等[27]收集冬季門診確診NAFLD的60例患者與60名正常志愿者的整體參數比較,前者血清25-(OH)D3濃度顯著降低,并發現25-(OH)D3與NAFLD組織病理學之間是線性相關的。另外,國外學者[28]發現25例NASH患者、36例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的肝穿刺組織中VDR表達與NASH和CHC患者的肝組織學嚴重程度呈負相關,血清25(OH)D3水平與活檢證實的NASH患者的肝細胞損傷程度成反比, NASH患者膽管細胞VDR表達與脂肪變性嚴重程度、小葉炎癥、NAS評分呈負相關。VDD不僅體現在成年NAFLD患者中,有研究[29]還發現了兒童NAFLD患者的血清低維生素D水平。Manco M等[30]發現64例NAFLD患兒中伴隨纖維化的血清25-(OH)D3水平更低,發現肝組織纖維化及炎癥程度與血清25-(OH)D3水平相關(P<0.01)。Kim H S等[31]篩選了1988—1994年4 015例確診NAFLD的患者并進行長達19年的隨訪,發現維生素D水平與肝臟脂肪變性程度呈顯著負相關(P<0.01), 并提出VDD增大了NAFLD患者糖尿病和阿爾茲海默癥的相關死亡風險。
3 1, 25-(OH)2D3對NAFLD治療作用
3.1 NAFLD的發病機制
1998年由DAY最早提出的“二次打擊”學說,被廣大學者所認可[32]。第一次打擊是高脂飲食、肥胖和胰島素抵抗等導致的肝臟脂質積聚。NAFLD最直接的病因是肝臟脂代謝異常,大量游離脂肪酸及甘油三酯在肝細胞內蓄積。體內正常脂質代謝有以下4種途徑: ① 膳食脂質吸收[33]; ② 脂肪動員; ③ 肝臟從頭合成; ④ 脂肪酸β氧化。第二次打擊是活性氧激發肝實質細胞的炎癥級聯反應和纖維化。隨著研究深度及廣度的拓展,“多重打擊學說”認為除“二次打擊”外,環境、遺傳因素和腸道微生物的變化共同作用于遺傳易感者誘導NAFLD, 腸道菌群改變導致腸內脂肪酸進一步產生,激活炎癥途徑和釋放促炎因子,炎癥細胞因子加重肝臟炎癥反應及脂質蓄積,形成腸道-肝臟軸惡性循環[34]。因此,以上任何一個途徑出現問題都會導致NAFLD的發生和發展,且這些問題通常是共同存在的。
3.2 1, 25-(OH)2D3改善NAFLD的基礎研究
在脂質代謝方面,對高脂飲食(HFD)建立的NAFLD小鼠的研究[35]發現,其肝臟過氧化物酶體增殖劑激活受體(PPAR)-α的表達減少平行于PPAR-γ的表達增加。Borges C C等[36]在喂養HFD及VDD的小鼠肝臟中發現PPAR-γ、甾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1(SREBP1c)、碳水化合物反應元件結合蛋白(ChREBP)和脂肪酸合成酶(FAS)增加以及β-氧化減少,這些都是導致肝臟脂肪堆積的重要因素,而1, 25-(OH)2D3劑量依賴性地抑制3T3-L1前脂肪細胞分化后細胞內脂滴的形成,抑制分化早期轉錄因子PPAR-γ、轉錄因子α(C/EBPα)[37]、脂蛋白脂酶(LPL)、SREBP1c 和FAS的表達[38]。
在氧化應激及炎癥反應方面,中國學者[39]以HFD及HFD+VDD構建小鼠NAFLD模型,并連續6周進行5 ng/g的1, 25-(OH)2D3肌注,發現1, 25-(OH)2D3可降低模型鼠的肝甘油三酯、炎癥因子TNF-α、IL-6的水平。有研究[40]發現, 1, 25-(OH)2D3通過降低丙二醛(MDA)減弱氧化應激,誘導轉錄因子NRF2核轉位和上調編碼抗氧化酶的基因的表達來保護免受HFD誘導的NAFLD。Jahn D等[41]在高脂高糖飲食的小鼠飼料中加入不同劑量的維生素D,發現高劑量(10 000 IU維生素D3)的維生素D可明顯改善肝臟脂質堆積情況,降低炎癥基因趨化因子(CCL2)的表達,同時發現維生素D治療后回腸TLR4、TNF-α和IL-1β促炎基因的下調。一項對膽堿缺乏飲食誘導的NASH大鼠的研究[42]發現,補充1, 25-(OH)2D3提高了大鼠血清中25-(OH)D3的水平,降低了谷草轉氨酶(AST)、ALT的表達量,并且提高肝臟VDR的表達,提示活性維生素D3對NASH的緩解作用。
3.3 1, 25-(OH)2D3改善NAFLD的臨床研究
大量基于人群的臨床試驗也支持維生素D對NAFLD的治療作用。Foroughi等[43]研究表明,維生素D補充治療可降低NAFLD患者空腹血糖,減輕NAFLD患者胰島素抵抗(IR)程度,增強胰島素敏感性。Sharifi N等[44]發現改善NAFLD患者維生素D狀態可改善血清高敏C反應蛋白和MDA水平。Kitson M T等[45]對12例經活檢證實無肝纖維化的NASH患者給予大劑量維生素D(25 000 IU/周)口服24周,發現肝組織學及血清肝酶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同時提出,在人群治療中,維生素D效果體現可能24周時間相對較短。因此,國外學者[46]對48例組織學確定為NASH的患者進行了一項雙盲隨機對照實驗,發現給予2 100 IU維生素D治療48周后,治療組血清ALT水平較安慰劑組顯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