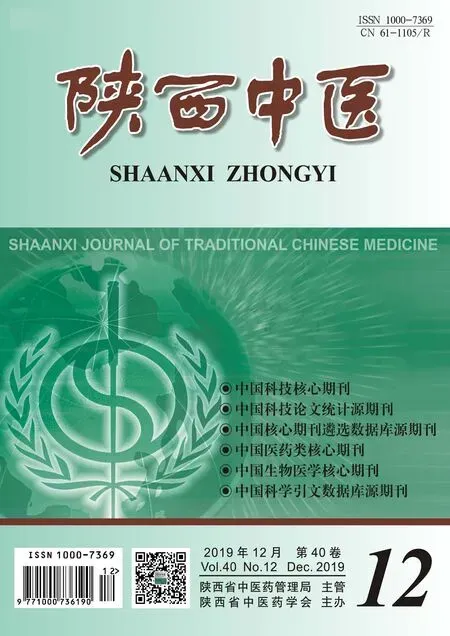穴位埋線治療支氣管哮喘的實驗研究探討*
唐徐韻,陳盼碧
貴州中醫藥大學針灸骨傷學院(貴陽 550025)
支氣管哮喘(簡稱哮喘)是目前臨床上較為常見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相關報道表明隨著如今生態環境的惡化,因哮喘而失去生命的人數正在逐年增長。據世界衛生組織2017年的相關數據顯示,全球患有哮喘的人數達到了2.35億人,其中我國是目前世界上哮喘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1]。近年來,雖然西醫在治療哮喘的相關研究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西醫治療哮喘仍以應用激素為主要的治療方法[2],此方法雖見效較快,但會誘發一系列藥物副作用,長期使用可能會引起咽部的不適、聲音嘶啞或念珠菌感染等[3],影響患者身體的早日康復。大量臨床研究發現,中醫針灸尤其是穴位埋線在治療哮喘方面療效顯著,且具有副作用小、操作簡便、療效持久,患者易于接受等特點[4]。筆者通過閱讀整理大量相關文獻后,現將近十年穴位埋線治療哮喘相關的實驗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穴位埋線對哮喘炎癥調控的實驗研究
多種炎性細胞參與引起的慢性氣道炎癥反應是哮喘主要的發病機制,其本質就是一種氣道炎癥反應[5],近年來關于穴位埋線治療哮喘炎癥調控的實驗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相關炎性細胞、細胞因子和其他炎性介質等方面。
1.1 對炎性細胞的影響 有研究表明,相關炎性細胞在肺組織中募集浸潤的過程可受到穴位埋線治療的干預,從而減少出現氣道變異性炎癥的可能[6],其中哮喘炎性反應的主要效應細胞是嗜酸性粒細胞(Eosinophil,EOS)。在哮喘的發病機制中,EOS浸潤是哮喘氣道炎癥區別于其他炎癥性疾病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病理過程包括EOS向炎癥部位的趨化、募集,由于EOS在哮喘發生的病理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減少EOS的浸潤來治療哮喘已成為了近年來的一個研究熱點。
凌黎明等[7]將哮喘模型大鼠分組并用不同的治療方法干預,觀察其癥狀和EOS數量的變化情況,結果發現穴位埋線組哮喘大鼠腹腔動脈血液中EOS的數量明顯減少。周君[8]觀察過敏性哮喘大鼠經穴位埋線治療后肺泡灌洗液中EOS計數的變化,發現經埋線治療后的哮喘大鼠肺泡灌洗液中的EOS數量顯著減少,推測哮喘的炎性癥狀可經穴位埋線減少EOS的募集浸潤而得到抑制。孫宗鼎[9]采用不同的治療方法干預過敏性哮喘豚鼠,結果發現穴位埋線組和地塞米松組豚鼠肺組織中的EOS均有減少,提示這兩種方法均可有效改善哮喘的炎性反應。以上研究均可表明,穴位埋線可有效減少EOS向炎癥部位的移行趨化,調節EOS介導的哮喘炎性反應,抑制哮喘炎癥反應的發作,減少組織的損傷,從而達到治療目的。
1.2 對細胞因子的影響 常見的哮喘氣道疾病是特異性哮喘,是由Th2過敏反應驅動的,當哮喘發生時EOS和細胞因子水平的升高是導致氣道炎癥發生、氣道重塑以及氣道高反應性(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AHR)的主要原因。因此哮喘的炎性反應不僅受到炎性細胞的影響,同樣也受到相關細胞因子的影響,尤其是Th2型細胞因子的高表達。據相關研究表明,穴位埋線可能是通過對相關細胞因子,例如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s,ILs)、干擾素(Interferon,IFN)、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s,TGFs)等的調控來緩解哮喘炎癥反應的。
賴新生等[10]通過觀察穴位埋線干預后哮喘豚鼠血清中IL-4含量的變化,發現哮喘豚鼠血清IL-4的水平經治療后有所降低,推測穴位埋線可通過影響IL-4的含量以緩解哮喘發作時支氣管收縮的情況。張琳[11]觀察穴位埋線干預后哮喘模型大鼠血清中IL-4和IFN-γ的水平變化,發現大鼠血清中IL-4和IFN-γ的水平可受穴位埋線的調節,進而推測穴位埋線可以調節失衡的Th亞群的水平,以改善哮喘大鼠的炎癥反應。張貴峰等[12]分別檢測哮喘豚鼠治療前后肺組織中細胞因子的情況,結果發現穴位埋線可以有效降低哮喘豚鼠肺組織中內皮素-1(Endothelin,ET-1)、TGF-β1、基質金屬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MMP-9)、核轉錄因子-κB( 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κB,NF-κB) 、細胞間黏附分子-1(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 表達的陽性細胞指數,推測哮喘的治療可以通過穴位埋線調控上述細胞因子的水平來實現。賴火特等[13]用不同的方法干預哮喘模型豚鼠,觀察治療前后哮喘豚鼠血清中相關細胞因子含量的變化,發現穴位埋線可以有效降低哮喘模型豚鼠血清中TNF-α的含量,緩解哮喘發作時的癥狀反應。付明舉等[14]用穴位埋線干預哮喘豚鼠后觀察其病理形態學改變和支氣管肺組織TGF-β1蛋白表達,發現穴位埋線可下調豚鼠支氣管肺組織中TGF-β1蛋白的表達,干預氣道重構。賴火特[15]發現穴位埋線可以抑制哮喘豚鼠TGF-β1的蛋白表達,還可下調哮喘豚鼠血清中IL-4和TNF-α的水平,從而抑制氣道炎癥的發生,減輕氣道壁的損傷。
近年來,穴位埋線通過對細胞因子的調控治療哮喘相關實驗研究的文獻結果均可表明穴位埋線可通過調控相關細胞因子的表達,調節失衡的Th亞群水平,來抑制哮喘炎癥反應的發生。
1.3 對其他炎性介質的影響 黏附分子可以介導相關炎性細胞的聚集,促進炎性介質的釋放從而引起氣道炎癥,與哮喘的發病密切相關,而細胞核內相關炎性介質基因的轉錄則受到NF-κB的影響,因此穴位埋線對哮喘的炎癥反應可以通過調節相關炎性介質的水平來達到治療目的。崔瑾等[16]用穴位埋線治療哮喘模型大鼠后觀察其肺組織中NF-κB和ICAM-1的變化,發現肺組織中NF-κB和ICAM-1的表達受到抑制,進而影響肺組織中炎性細胞的募集浸潤,以減輕哮喘大鼠哮喘癥狀的發作程度,使哮喘大鼠肺、支氣管的病理變化得到明顯的改善。在此實驗的基礎上,陳盼碧等[17]選用不同穴位埋線組方干預哮喘模型大鼠后觀察ICAM-1和NF-κB在肺組織中的表達情況,結果發現肺俞膻中腎俞組肺組織中ICAM-1、NF-κB的表達均低于腎俞組和肺俞膻中組,推測標本兼治的肺俞膻中腎俞埋線組的防治效果要明顯好于治標的肺俞膻中埋線組,以及治本的腎俞埋線組,為臨床穴位埋線治療哮喘的選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實驗依據。孟越[18]研究發現穴位埋線可能是通過kB抑制蛋白α(Inhibitory subunit of NF-kB,IkBα)對NF-κB起反饋調節作用,抑制NF-κB的激活,減少炎性介質基因進入細胞核的轉錄,從而緩解哮喘的慢性氣道炎癥的發生。以上相關研究說明,穴位埋線治療哮喘可能是通過調節細胞間黏附分子或核轉錄因子等相關炎性介質的表達,從而抑制氣道炎癥的發生,達到治療目。
2 穴位埋線對哮喘免疫調節的實驗研究
目前臨床上西醫首選激素治療哮喘,雖然激素治療可明顯緩解氣道的炎癥反應,但對機體本身免疫功能的調節則不是十分理想,而且長期使用激素治療容易產生耐藥和不良反應。另有研究表明,穴位埋線治療哮喘的遠期療效是優于西藥的,并且在調節機體的免疫功能方面也確有優勢[19]。筆者通過查閱文獻發現,穴位埋線從提高免疫功能的角度治療哮喘的實驗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免疫球蛋白和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這兩個方面來闡述其作用機制。
2.1 對免疫球蛋白的影響 哮喘的發生離不開免疫功能的失調,是一種由免疫功能失調所引起的變態反應性疾病,當疾病發生時,抗原的入侵會使機體產生一種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而IgE的產生可以加速機體進入致敏狀態,因此可以通過調控IgE的水平來治療哮喘。凌黎明[20]用不同的方法干預哮喘模型大鼠,并觀察大鼠的癥狀、外周血中EOS數量,以及血清IL-4和IgE的變化情況,并將治療前后穴位埋線組和針刺組大鼠血清IgE的水平進行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推測常規針刺降低IgE的水平、改善哮喘癥狀的效果不如穴位埋線。劉敏[21]用穴位埋線干預變應性鼻炎大鼠,發現穴位埋線可以下調大鼠血清中IgE和鼻黏膜中IL-4、IL-17、TGF-β1、P物質的含量,以及升高IFN-γ含量,來調節大鼠的免疫平衡,緩解炎性癥狀,且效果優于西藥組。孫小靜[22]研究發現穴位埋線可以下調哮喘大鼠外周血中IgE和IL-4的水平,推測穴位埋線可能是通過影響IL-4水平進而調控IgE含量的。以上實驗研究均可表明,穴位埋線主要可通過降低機體內IgE的含量,以調節機體自身的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治療哮喘的目的。
2.2 對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的影響 人體所有正常的功能都有賴于免疫系統和神經內分泌系統的共同參與和調節,因此機體要維持一個穩定的內環境必然有賴于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穴位埋線可通過神經-內分泌-網絡與免疫系統的相互協同作用,增強特異性IgE抗體的表達,促進相關炎性細胞在氣道聚集浸潤、誘導其釋放炎癥介質、調節免疫應答的平衡,從而提高機體免疫功能。蔣詩超[23]用穴位埋線治療哮喘豚鼠,觀察哮喘豚鼠的癥狀、氣道炎性細胞、支氣管氣道病理等變化,以及肺組織神經生長因子、血清嗜酸性粒細胞陽離子蛋白、下丘腦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三個指標水平的變化,結果發現穴位埋線治療哮喘的作用機制是通過下調哮喘豚鼠機體中NGF、ECP、CRH的水平,以緩解哮喘豚鼠EOS性炎癥,從而達到治療目的。進而說明穴位埋線是可以對機體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產生一定調節作用的,從而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治療哮喘。
3 小結與展望
穴位埋線對哮喘炎癥反應的調控,主要是通過對炎性細胞、細胞因子和其他炎性介質的影響,從而改善氣道的炎性反應。而穴位埋線對哮喘免疫功能的調節,則主要可通過對免疫球蛋白和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的調節兩條途徑來實現。盡管如此,穴位埋線治療哮喘的機制研究還存在許多不足,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其作用機制缺乏深入的研究,上述實驗研究大多將指標含量的升降作為分析其作用機理的條件,但并沒有深入探討指標變化的機理,例如許多研究表明穴位埋線可以降低哮喘大鼠EOS的水平,但卻很少有分析影響EOS水平的機制。第二,實驗方案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同的實驗選取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穴位以及不同的觀察指標,難以對相關實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例如有的實驗選取的是定喘、肺俞、足三里和豐隆穴處進行埋線治療,而有的則選取的是肺俞、定喘、足三里和尺澤穴,選穴配穴方法不同,其作用機理之間本身就存在差異。第三,目前與炎癥相關的研究較多,而與免疫相關的機制研究較少,但哮喘的發病機制與免疫失調密切相關,提示今后的研究也可直接從免疫角度進行探討。另外,大量研究表明穴位埋線治療哮喘確有優勢,但目前相關作用機制的研究并不多,也沒有一個準確、統一的認識,因此還有待進行深入的探究,以期為臨床哮喘的治療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