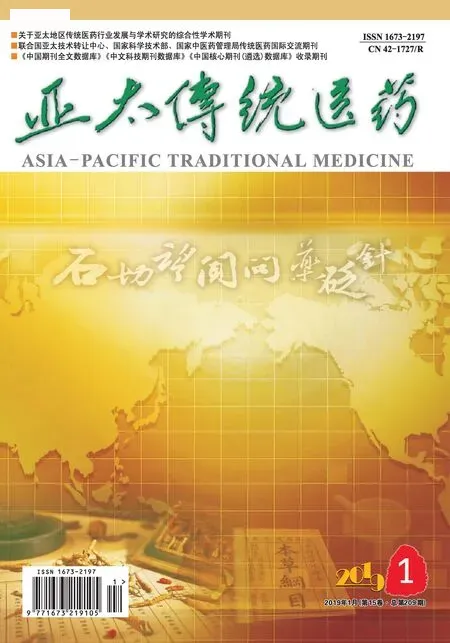柴芍清肝湯治療甲狀腺功能亢進癥47例臨床觀察
,
(1.安徽中醫藥大學,安徽 合肥 230038;2.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安徽 合肥 230031)
甲狀腺功能亢進癥(甲亢)是臨床上較為常見的、可由多種因素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甲亢即甲狀腺分泌過多的甲狀腺激素,主要表現為循環、消化系統的高代謝證候與體征[1]。目前甲亢的治療手段主要有抗甲狀腺藥物治療、放射碘治療、手術治療,以抗甲狀腺藥物口服治療最為常用;但由于藥物治療易產生肝細胞損傷、白細胞計數減少等副作用,常限制了藥物的選擇[2]。甲狀腺功能亢進癥在中醫學中歸屬于“癭病”范疇,而中醫藥在治療此類疾病方面有一定優勢,因此筆者結合導師臨床經驗,采用中藥柴芍清肝湯口服結合甲巰咪唑治療甲亢病人47例,取到了較好的臨床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6年8月-2018年2月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內分泌科門診確診的甲亢患者94例,依據隨機數字法將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47例。對照組中,男性患者13例,女性患者34例,年齡21~57歲,平均(33.72±9.15)歲;觀察組中,男性患者14例,女性患者33例,年齡21~55歲,平均(34.96±10.13)歲。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程等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診斷標準
①西醫診斷標準:參照《中國甲狀腺疾病診治指南》的相關標準[3];②中醫診斷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制定的相關標準[4]。甲亢屬于中醫學癭病范疇,辨證為心肝火旺證。主證:頸前腫大,頭暈目眩,心悸不寧,煩躁易怒,手指震顫,口苦舌痛,胸脅脹痛。次證:多食,消瘦,惡熱,多汗,不寐少夢,倦怠乏力,口渴多飲。舌脈:舌紅,苔黃而津少,脈弦數。
1.3 納入標準
①入組病例均符合西醫及中醫證候診斷標準;②年齡18~70歲;③患者知情并同意參加本臨床實驗,并定期配合隨訪觀察。
1.4 排除標準
①年齡不在18~70歲范圍內,過敏體質及對多種藥物過敏,孕婦及哺乳期婦女;②兼有嚴重心、肝、腎及造血系統疾病及精神病患者;③甲亢危象及各種甲狀腺炎患者,甲狀腺顯著腫大壓迫臨近器官需手術者;④不符合納入標準,未按規則用藥,無法評定臨床療效者。
2 方法
2.1 治療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甲巰咪唑基礎治療,劑量為10mg/次, 3次/d,口服,病情穩定后逐漸減量,酌情2~4周減量1次,每次減量5 mg,至癥狀明顯改善,并且在甲狀腺功能下降在正常范圍內時繼續維持治療。
治療組患者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聯合柴芍清肝湯治療,柴芍清肝湯組成:柴胡 12 g,黃芩 12 g,白芍15 g,玄參10 g,丹皮10 g,夏枯草15 g,香附10 g,枳殼 10 g,當歸 10 g,川芎10 g,炙甘草9 g。手指震顫加鉤藤、牡蠣;胃熱內盛兼有多食易饑加用知母、石膏;心悸不寧、少寐多夢加首烏藤、酸棗仁。制成復方顆粒劑,250 mL溫水沖服,1劑/d,早晚分服。治療組與對照組連續服用3個療程,以4周為1療程。若治療過程中出現嚴重并發癥或患者不能夠耐受,立即退出臨床研究并進行相關治療。
2.2 觀察指標
2.2.1 實驗室指標 血清FT3、FT4及TSH。采用電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檢測,檢測儀器:羅氏e602全自動免疫分析儀。采集治療前后患者晨起空腹靜脈血,測定兩組患者治療前后FT3(血清游離三碘甲狀原氨酸)、FT4(血清游離甲狀腺素)及TSH(促甲狀腺激素)水平。
2.2.2 中醫證候評分 中醫證候的輕、中、重分級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4]中甲亢分級量化表制定。見表1。

表1 中醫癥狀分級量化標準
中醫證候積分減少率的計算,依據公式:證候積分減少率=(治療前積分-治療后積分)/治療前總積分×100%。2.2.3 療效判定標準 按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4]中相關標準制定。痊愈: 治療后臨床癥狀及體征消失或基本消失,甲狀腺激素水平等實驗室檢查指標正常,證候積分減少≥95%;顯效: 治療后臨床癥狀好轉,體征減輕,甲狀腺激素水平等實驗室檢查指標趨于正常,證候積分減少≥70%;有效:患者臨床癥狀有所改善,體征有所減輕,甲狀腺激素實驗室檢查指標水平有所改善,證候積分減少≥30%;無效: 治療后臨床癥狀、體征、甲狀腺激素實驗室檢查指標水平均無明顯改善,證候積分減少不足30%。
2.3 統計學處理

3 結果
3.1 治療后兩組患者療效比較
治療組總體療效優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分布比較 (n)
3.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總積分比較
兩組治療后癥狀總積分均較治療前明顯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治療后癥狀總積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3.3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甲狀腺激素水平變化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血清FT3、FT4和TSH甲狀腺激素水平,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FT3和FT4甲狀腺激素均較治療前明顯降低(P<0.05),血清TSH激素水平均較治療前顯著升高(P<0.05);兩組血清FT3、FT4、TSH甲狀腺激素水平,組間差異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00)。見表4。


組別 例數(n) 治療前癥狀總積分 治療后癥狀總積分 差值治療組 47 22.51±4.67 6.45±6.02? 16.06±5.24??對照組 47 23.30±4.81 9.15±7.67? 14.15±7.10??
注:兩組治療前后組內比較*P<0.05,兩組治療后組間比較**P>0.05。


組別 例數(n) FT3(pmol/L) 治療前 治療后 差值 FT4(pmol/L) 治療前 治療后 差值 TSH(mIu/L) 治療前 治療后 差值 治療組 47 18.54±8.74 3.50±1.36? 15.05±8.53?? 31.39±8.94 13.47±3.61? 17.92±9.58?? 0.0039±0.0159 1.9941±1.3126? -1.9902±1.3104??對照組 47 17.26±15.72 5.66±2.40? 11.60±15.68?? 28.15±9.83 17.10±4.28? 11.05±8.59?? 0.0103±0.0321 1.3334±1.2317? -1.3230±1.2398??
注:同組治療前后比較*P<0.05,兩組間治療后比較**P<0.05。
4 討論
現代醫學表明,甲狀腺功能亢進癥(甲亢)的發病與環境、遺傳及機體應激等密切相關,并且其發病率隨著生活節奏和工作壓力的增加而增長[5]。目前,輕、中度甲亢主要以口服藥物治療為主。甲巰咪唑(MMI)為常用的治療藥物,其主要作用于甲狀腺過氧化物酶,抑制酶的活性,從而阻礙甲狀腺激素的合成。但其藥物不良反應多,臨床上多出現肝功能異常、白細胞減少,單獨應用臨床療效欠佳。并且甲亢病程纏綿難愈,復發率高,易產生多種并發癥[6]。甲亢屬于中醫學“癭氣”“癭病”“癭瘤”等范圍,其病因多與飲食失宜、情志失調、先天稟賦不足有關。如《諸病源候論·癭候》記錄:“諸山水黑土中……長食令人作癭病,動氣增患。”說明了情志內傷及水土因素在甲亢發病中的重要性。肝脾為甲亢主要的病變部位,其次為心。主要病機為肝郁氣滯,氣滯津聚,聚久生痰[7];脾傷氣結,脾虛釀生痰濕,痰氣交阻,久則血行不暢,氣不行血,血瘀脈阻,終致氣郁痰凝血瘀結于頸前,而成癭病;肝開竅于目,癭病日久,氣郁化火,火盛動風,風陽上擾則致眼突目赤,手指震顫;火郁傷陰則心神失養,呈現心悸不寧,心煩少寐之證,肝火旺盛,火熱迫津外泄則煩熱,汗出,性格浮躁;肝火及胃,胃熱則消谷善饑,甚則日漸消瘦。其病理性質以實證居多,久病易由實致虛,多見虛實夾雜之證候。辨證要點為痰氣郁結、心肝火旺的不同,治療宜清瀉肝火,涼血消癭,少佐。此次研究選用柴芍清肝湯治療,方中柴胡、白芍、共為君藥,具有疏肝解郁、柔肝緩急之效,現代醫學研究表明柴胡中的有效成分柴胡皂苷具有抗炎、調節免疫系統等作用,以及促進肝細胞再生、抗肝損傷的作用,可降低轉氨酶[8];白芍的相關藥理研究表明[9]其有效提取成分,有鎮靜功效,可有效平復患者情緒,提高機體免疫力,二者共為君藥;黃芩、丹皮、夏枯草、玄參清肝瀉火、涼血消癭,滋陰,是為臣藥。黃芩、丹皮中含有的活性成分均可抗炎、保肝,增強機體免疫力,且中藥黃芩的有效成分黃芩素還具有抗焦慮、鎮靜作用[10,11]。夏枯草瀉火明目、散結消腫,現代醫學研究表明夏枯草中的黃酮、苯丙素、甾體等具有抗炎和免疫抑制活性作用,及降低基礎代謝率的藥理作用[12];玄參滋陰瀉火,與黃芩、丹皮等清火藥配伍,補瀉結合,使肝火得清,肝陰得養。佐藥當歸、香附、川芎、枳殼,具有行氣活血、化瘀散結之功,可有效降低甲亢患者的高代謝率[13];四者與柴胡、白芍為伍,升降相合,并奏條達肝氣、疏肝解郁之效;佐使藥甘草調和諸藥。此次研究結果表明,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在療效分布、臨床癥狀改善方面顯著優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提示,自擬柴芍清肝湯中藥方劑可以多靶點調控甲狀腺激素合成與分泌,改善甲亢患者高代謝證候群,其機制可能與調節內分泌系統及免疫調劑有關,具體機制還待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自擬柴芍清肝湯合用甲巰咪唑口服治療甲狀腺功能亢進癥患者,臨床效果顯著,充分體現了中醫藥辨證論治與整體觀念的特色優勢,值得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