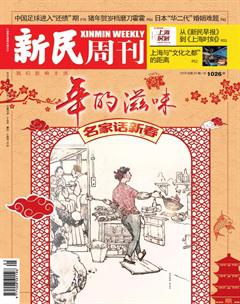過年的滋味
錢乃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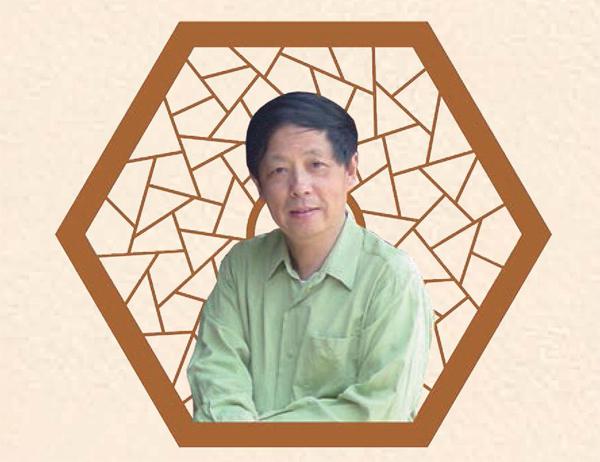
過年,是一個人心境最美好的日子,舊時過年從年底到年初,歡喜多多,從農歷十二月吃“臘八粥(粥中加紅棗、胡桃仁、菱角、棗泥、松子、栗子、花生、杏仁等)”就開始準備過年了。接著有十二月廿四“祭灶”,據說“灶君菩薩”是玉皇大帝派到家家戶戶來站崗的,所以在我幼時的記憶中,我母親對祭灶還是頗重視的,供奉麥芽糖、甜食和糯米團,用以黏住他的口,讓灶神“上天言好事”,再接來一個新的灶神“下界保平安”。
年底“祭祖”的事情也很隆重,不過后來隨著“移風易俗”的號召,許多人家就取消了,但是家內大掃除“撣遺塵”和個人大清洗“換新裝”的新年新風還長久保留著。
記得20世紀50年代底我14歲,到八仙橋西湖浴室去洗澡,大湯間里擠得人都碰來碰去,空氣實在太悶,我擦滿肥皂要去大池,突然朝后昏倒,旁邊便是轉角的大池石欄,幸虧擠在人堆里的浴室服務員剎那間將我一把拉住,拖到外面,立刻噴我一臉冷水,才使我清醒過來,避免了一場不堪設想的事故。本來我想洗完澡一身輕松,結果是一場大驚。不過從此以后我一想要舒適輕松,就認定去西湖浴室,仿佛特別有滋味、有安全感。直到90年代初有一次我在日本教學回滬休假,不假思索就到了八仙橋,不料這時的西湖浴室已經大幅漲價了,看了價錢嚇過一跳之后,我還是走了進去,一看也還是那么個池子,池里只有兩個人,替我擦背的人以為我是老板,苦苦且悄悄問我討小費。想起了西湖浴室曾經救過我一命,我多付了錢,不過浴室給我的感受已不比當年了。
年夜灑掃庭院之后,就要布置房間。我母親最歡喜水仙花。小時候過年前,母親會帶我去新城隍廟買水仙,因為福建漳州水仙貴,媽媽買了球部用細竹串插成一排六株的崇明水仙,重瓣花冠反而更香,放在長圓形的專養水仙的陶瓷盆里,用圓滑多姿的石卵子輕輕壓住其根,放滿清水供養在窗邊凈幾上。我母親歡喜水仙花的白色與芳香,也養成了我對水仙的熱愛,每到過年我就要去買水仙花。水仙一身燦黃嫩白蔥青,在我看來,最有仙氣又耐琢磨的,是它整齊散發、雪白素雅的根,冰雪為肌,形態端莊。
后來我每到過年就要養水仙,母親也幫我養,移盆曬太陽。買水仙最難的歲月,是“文革”的十年,養花種花已經掃蕩為“四舊”,我每年除夕前都得尋覓水仙,在上海居然還有除夕前賣水仙花的地方,僅豫園邊的一個花店。我每年便在除夕清早趕去城隍廟花卉店排隊。店門一開,長長的隊伍就開始混亂,插隊和后門使得人人情緒激昂,當我依次要排到之時,往往只余下來最后一點水仙,或者小或不整齊,但買回家來還是無限欣喜。雖然當時生活十分拮據,每年水仙依然陪伴我母親過年。1970年冬天,我母親突然中風半癱臥床,這一年,我只好暫停工作回到家來天天服侍我母親三個月。在貧病交迫之際,一日,我母親睜開眼睛,當她看到我仍舊買來了她歡喜的水仙花,我分明看到她眼睛一亮,歪斜的嘴唇上露出了一絲微笑。
我年年在除夕前清供水仙和臘梅直到今天。買天竹臘梅是從我的高中班主任語文老師王爾齡那兒學到的。1962年春節去王老師家拜年,看到老師家古色古香的方桌上放著一個高雅的瓷瓶,瓶中插著幾株黃似蜜蠟、清香的臘梅和兩串紅珠天竹,暗香浮動,煞是清雅,頓時打開了我的心竅,聯想起我曾在一張賀年片上看到的海派畫家吳昌碩畫的“歲朝清供圖”。大堂里還掛著一副紅對聯。王老師端來了一個“蓋碗”,蓋上有一個凸出的小圈,上面放著一顆青橄欖,江南俗稱“元寶”,吃起來滋味猶如蓋碗中的清茶一樣苦后生甜,稱為“吃元寶茶”。我跟王老師不但學會寫作文,還學來了新年里喝蓋碗元寶茶和清供臘梅天竹的習慣,加上如意佛手,引來滿室清香,在自家的門上自己寫春聯貼春聯的習慣也延續至今。

形式豐富的糖紙頭,大大豐富了童年的年味。
過去過年,主要精彩的是年前的忙碌籌備,最有勁的還是購買年貨,家家戶戶辛苦一年好不容易到頭,一家老小、親戚老友團聚一起大吃一頓在當年是并不容易的,各家各戶都忙著盡量把年貨準備充分一點。無奈在六七十年代,副食品供應都要憑票券,分大戶小戶發放小菜卡,副食品供應十分緊張。其中有一項“豆制品”定量供應,是在小菜卡上記錄打印的,多數是用鋼筆或圓珠筆打鉤寫數字,當年百姓很老實,沒有聽到過偽造或涂改的,否則簡直不堪設想,在豆制品供應那么拮據的年代,假得起嗎?上海人對豆制食品的多樣化制作,集江南的大成,雖是食物貧乏的年代,還是十分精美,大家喜歡的“烤麩”賣得最快,要缺貨,一見著有得賣,就排起較長的隊。
黃魚一旦賣起來真是軋得要命!盡管每戶都有一張黃魚票,但是小菜場上,如果隔日聽說有黃魚賣了,第二天不等到3點鐘,天還未亮,魚攤邊就開始排起長隊,有時在隊伍中多放一只籃頭、照看一只凳子。我有一次清晨4點鐘就去小菜場排隊買黃魚,到早晨還有一小時開市前,隊伍已經排得人山人海。當“黃魚車”將黃魚踏來,沸騰的隊伍軋坍,亂擠和罵插隊的噪聲響徹攤位,后面老老實實排著隊的老頭老太根本擠不上去。到我排到還是沒有買到一年沒吃過的配給的冰凍黃魚,總算買到一條后補的“叉鳊魚”掃興回家。

年,是窗臺邊一盆盛開的水仙。漫畫/ 崔泓
過年的弄堂里,家家戶戶熱氣騰騰,夫妻一起進了灶間,一個負責切洗,一個擔任炒煮,桌上疊滿生肉熟菜,空間炊煙繚繞彌漫;還有國家大聞,小道消息,多如小菜,嘁嘁嚓嚓,加上嘰嘰喳喳,像琵琶配上評彈,十分和諧,菜多人多,熱火朝天,龍頭用水,還須排隊,磕磕碰碰,在所難免。實在擁擠不過,只好輪班,今朝你家親朋來,明天我家拜年去,房間也可讓出來擺圓臺,椅子酒杯也可借過去聚餐,大家通用,親密哪比鄰居。當年大家都是團聚在家吃年夜飯,“螺螄殼里做道場”,處處道場做得不亦樂乎!年歲生活的滋味,其中有一種就是軋鬧猛的滋味。
五六十年代的小學生,課余生活豐富多彩,讀書外還有余暇唱少兒歌跳集體舞,加入各種自發的游戲,不少同學都有收藏的愛好,如集郵、集幣,收集電影說明書、電影票、電影明星照片,收集書簽、賀年片和糖紙頭。大量的水果糖是每顆用紙包的,紙面上有各生產廠家的名字,還寫明糖果的種類。有奶糖、蛋白糖、太妃糖、牛軋糖、司高去糖、求是糖、白脫糖、巧克力糖、麥乳糖等等,名稱華洋雜交。一方小小的包糖紙上,會有著那么多精心繪制的圖畫。糖紙頭文化是海派商業文化之一,我們童年對顏色的順口溜:“紅黃藍白黑,橘子檸檬咖啡色”,就是從水果糖上的顏色而來的。吃糖果,是我們最突出的童年甜蜜滋味的回憶。當年桌上陳列的果盤或果碟里最生動和吸引人的,就是糖果。過年時,很長時期各家糖果店都有集中各類漂亮的糖紙頭包著的1.28元一斤的什錦糖,吃了糖果以后留下的包糖紙,小朋友們就收集糖紙頭,剝開糖紙,先欣賞了一會兒糖紙收起,然后才去品味糖的滋味。一方糖紙上的小千秋,糖紙圖案上精心設計曾是感染我學習圖畫、打開思路的最佳途徑,這些當年不知覺夾在中小學課本中的糖紙,真正是“甜蜜的回憶”,居然因課本不沒收而躲過了“文革”掃四舊,保存了五六本,現在編成一本書《糖紙頭——海派文化的童年情結》出版了。
大年初一,先要“拜年”,一拜天地,二拜四方,迎春接福,吉祥如意;三拜長輩,福長壽長,開心健康。鄰舍相望,一句“恭喜發財”,或者“新年大喜”;有的草班來湊熱鬧,大唱:“恭喜發財,元寶搭臺,老兄今年大發財,大大元寶滾進來”。正月初四至初五接財神,正月十五過元宵節,十三就上燈,十五燈節高潮,十八收燈,所以春節要過到正月十八才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