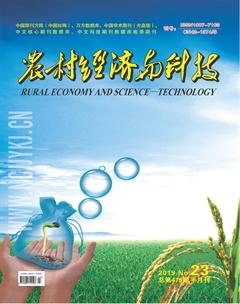我國低效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策略研究
馮莉
[摘要]集體建設用地入市能夠為鄉村振興提供優質的產業載體,立足于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具體策略對于促進城市和農村土地一體化和產業升級轉型尤為關鍵。結果表明:集體建設用地普遍存在著低效再開發的狀況,呈現出“三低、二高”的特征。其中,再開發能力、容積率和產出能力低,行政辦公和生活設施占用比和建筑系數高。研究建議:由“外延式”擴張為“挖內涵”的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模式、有效控制集體建設用地和農業內部調整對耕地的占用、建立建設用地標準控制體系、完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再開發管理辦法和配套政策工作。
[關鍵詞]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效益
[中圖分類號]F301.2[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我國城市和農村一體化進程快速發展,國有建設用地擴張迅速。我國,尤其是經濟快速發展地區的經濟增長方式正面臨著由“粗放經濟”向“集約經濟”的重大轉變。目前,建設用地,特別是集體建設用地的再開發成為“粗放經濟”向“集約經濟”轉型的關鍵。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通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這次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破除了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的法律障礙,刪除了原來土地管理法第43條——“任何單位或個人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使用國有土地的規定”,并增加規定農村組織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依法登記,并經三分之二以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意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農村組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個人直接使用,同時使用者在取得農村組織建設用地之后還可以通過轉讓、互換、抵押的方式進行再次轉讓。這在本質上是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關鍵措施。
在發達國家,由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低效建設用地再開發得到充分的重視,并形成了土地資源可持續開發的思維。因而,質量提高取代規模擴大成為發達國家發展的主流。發達國家通過低效建設用地再開發,解決大規模經濟結構調整所引發的很多現象。包括城市經濟衰退、生態環境惡化、城市景觀敗落、就業崗位不足、失業人員增加、社會矛盾加劇等。因而,全面盤活了土地資源,引入了全新的產業。對于無序向外蔓延的城市發展模式,新城市主義和城市更新運動通過再開發那些原來被荒廢的舊市中心區,并制定了對低效建設用地的再開發的“城市復興計劃”來推動。因而,發達國家在存量建設用地的界定、再開發政策研究、再開發模式等方面都相當成熟。更有甚者會依據不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制定不同模式的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運行組織形式和內容。相對而言,中國關于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研究略有不足。盡管有關專家學者根據不同地區的實踐經驗提出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模式。但是對比發達國家的低效建設用地再開發,國內的研究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仍無法為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提供經驗借鑒。對此,本文以廣東省為研究基準點,立足于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現狀,進一步探討集體建設用地的再開發方式,為中國一線城市的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提供土地政策方面的理論支持。
2 文獻綜述
對于土地再開發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古典經濟學家對農業地租現象的研究。他們在對高效再開發農業土地的研究中發現在一定面積土地上持續增加再開發時,其產出先持續增加,達到某一點后開始下降,他們同時認為,正是由于在不同土地上再開發生產要素數量的不同,導致了級差地租的產生。在國外實際案例研究方面主要有:Rainer Mulle-Joke(2003)把德國建設用地的提供方式劃分為三種類型,即中間購買模式、私人投資以及土地調整三種類型,并且重點分析了城市的土地調整方式給土地經營和開發帶來的影響。亦有學者對紐約早期的城市美化運動和舊城更新的方法做了詳盡的介紹,指出其主要解決辦法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和農村土地資源置換。其中涉及到土地整治和整理的政策依據、整理的目標和目標、實施組織的具體形式以及利益分配和補償的方法等,強調了在土地整治和整理過程中區域政府部門與開發商以及公眾的溝通的關鍵性。國內對于土地再開發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隨著城市和農村土地資源再開發矛盾的日益突出,這一現象開始受到關注。正如20世紀以來,陸邵明針對碼頭工業區潛在價值研究并取得明顯成效。之后,大批學者,如:鄭沃林等(2019)從目標實現、土地管理和開發效益三方面搭建舊村莊再開發項目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并評價廣州市白云匯項目、安華匯項目。焦勝(2003)等學者的“復合開發一模式研究,為從根本上解決濱水城市二次開發的空間方面進行理論探討。學者重視中心城區的土地再開發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雖然對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相對不足,但相關的研究仍值得本文參考。
3 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對策
3.1 由“外延式”擴張為“挖內涵”的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模式
政府部門首先需要嚴格控制集體建設用地規模,以避免亂建亂占現象;其次,加快低效集體建設用地的再開發,并且要重視產權主體亂建設的現象,以從根源上實行真正的再開發,以避免城市和農村土地資源的隱形浪費;再者把城市和農村當中的土地充分地再開發起來,銜接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機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規定。
結合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機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的規定,在原有橫向再開發集體建設用地的基礎上,從地下、地表、地上垂直式地開發再開發集體建設用地,以最大程度的發揮低效集體建設用地的潛力。
3.2 有效控制集體建設用地和農業內部調整對耕地的占用
以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的“集體建設用地入手”為基準,在盤活集體建設用地的同時,更嚴格地管理農戶亂占亂建等對集體建設用地的占用。此外,相關的政府部門要嚴格控制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的結構調整,嚴禁在村莊規劃之外非法占用耕地。
3.3 建立建設用地標準控制體系
政府部門要區分不同用途,制定經濟快速發展地區的集體建設用地最低控制標準體系,以規劃部門為主導,根據村莊規劃的產業轉型升級和節約集約用地的要求,提高低效集體建設用地的投資強度、產出率、容積率、科技率等指標要求,嚴格控制能耗、水耗等指標。土地所有權人,即村集體要嚴格按照上級部門的最低要求,擬定具體地塊的出讓條件,通過“三資平臺”的公開選商機制,實現低效集體建設用地的再開發。
土地、規劃、建設等審批部門要“抓大放小”,按照放權于民等要求,大力精減收件資料,簡化審批流程,壓縮審批時限,委托基層部門就近集中收件,減少土地使用權人的時間成本。對于重點產業項目,各部門要主動協調,面對面溝通交流,切實避免審批流程冗長、審批渠道不暢而影響低效集體建設用地的再開發。
尊重農村經濟組織的所有權人地位及其知情權、監督權,建立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協調機制。相關產業部門要定期向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權人披露產業企業的相關信息,并且通過群眾監督保障低效集體建設用地的高效再開發。因土地使用權人自身原因(如,資金短缺等)導致集體用地低效的,土地管理部門應主動介入,通過提供資金支持或者建議土地所有權人收回土地等措施,實現低效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
3.4 完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再開發管理辦法和配套政策工作
機制創新是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政策保障,建立城市和農村統一的權屬管理機制和集體建設用地交易市場,完成城市和農村統一的建設用地基準地價編制工作,以同地同權為目標,完善集體建設用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占有、使用、利益、處分權能,以“集資房”上市再開發與建設集體土地保障房為試點,逐步取消對低效集體建設用地的再開發產業導入的約束。同時,推動低效集體建設用地的產權聚集的規模化和集約化。引導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按照“自愿自主”的原則,把低效集體建設用地以共同合作、共同開發等多種形式流轉出去,依據村莊規劃的規定,適度集聚不同類型的產權,并且引入房地產開發企業和大型的產業企業進行再開發。此外,逐步推行集約化宅基地安居模式,完善宅基地審批機制,探索低效集體建設用地有償收購和退出機制,在法律層面要支持在低效集體建設用地集中建設公寓式產權主體住宅。
村組織建設用地的利益所得該如何分配,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大多數地區為按股份進行分配,其余由村財政統一支出。實際上由股份分紅給產權主體的比例一般不超過總收入的50%。利益分配不均,一方面導致產權主體對農村組織建設用地的再開發參與積極性不高,此外村干部擔心再開發后變為國有建設用地,害怕利益受損也不愿意主動推進低效建設用地的再開發,需要相關部門合理確定各利益相關者對集體建設用地的利益分配比例,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4 結語
集體建設用地總量大,產業類型差異大、建筑情況復雜是導致產業類型低端,產業效益低下和產業集聚不明顯的關鍵原因。同時對比村鎮工業用地,可以發現集體建設用地具有巨大的再開發潛力,但也存在較大的難度。作為村鎮建設用地再開發首要主體——村委和村民對于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意愿度有著明顯差異,并受到諸如現行政策、各自利益出發點的不同而表現對集體建設用地的支持、中立或反對的呼聲,并成為制約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關鍵因素。此外,村集體仍未形成有效的決策體系和機制,產權主體和村組織的意見難統一和不清楚該如何引進或者該引進怎么樣的產業,甚至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反公地悲劇”現象的出現。同時,外部的審批難,沒有“接地氣”、有效科學的政策,或某些政策準入門檻相對較高等因素,成為制約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關鍵。
綜上所述,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總體方向應該為“引導、讓利、放權”。相關的政府部門應該圍繞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產業升級轉型的目標,以政府部門為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主導,積極引導產權主體、村組織和企業進行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積極性,適當地讓利于產權主體、村委,支持村主體自發性開展、參與再開發,并提高基層管理的工作積極性,改進行政效率,加強反饋增加政策的靈活性,審批權限適當下沉,推動集體建設用地再開發的進程。
[參考文獻]
[1] 鄭沃林,吳劍輝,鄭榮寶.經濟快速發展地區農戶耕地保護的意愿與實施行為差異研究——以廣州市為例[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48(02):64-73.
[2] Rainer Muller-Joke.德國城市發展進程中的土地評估[J].國土資源情報,2003(07):25-28.
[3] 陸邵明.國外碼頭工業區的再開發[J].上海城市規劃,1998(02):38-42.
[4] 鄭沃林,徐云飛,鄭榮寶.舊村再開發項目績效評價研究——以廣州市白云區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9,38(03):125-129.
[5] 陶小馬,何芳.黃浦江沿岸地區土地置換模式研究[J].城市規劃匯刊,2000(05):34-40+79.
[6] 吳紅兵.關于工業用地置換模式探討——以株洲市石峰區核心區域城市更新規劃為例[J].株洲工學院學報,2006,20(02):122-125.
[7] 成漢賢.東莞城市工業用地二次開發策略研究[D].廣州:中山大學,2010.
[8] 焦勝,曾光明,何理,等.城市濱水區復合開發模式研究[J].經濟地理,2003(03):397-400.
[9] 鄭榮寶,張春慧,陳美招.低效產業用地目標識別與二次開發策略研究[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14(04):20-24.
[10] 鄭沃林,田光明.農村建設用地低效盤活的影響因素分析——以廣州市天河區和白云區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6,35(06):104-108.
[11] 鄭榮寶,鄭沃林,呂思敏,等.廣州市村鎮建設用地再開發的新思路與新途徑[J].規劃師,2016,32(05):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