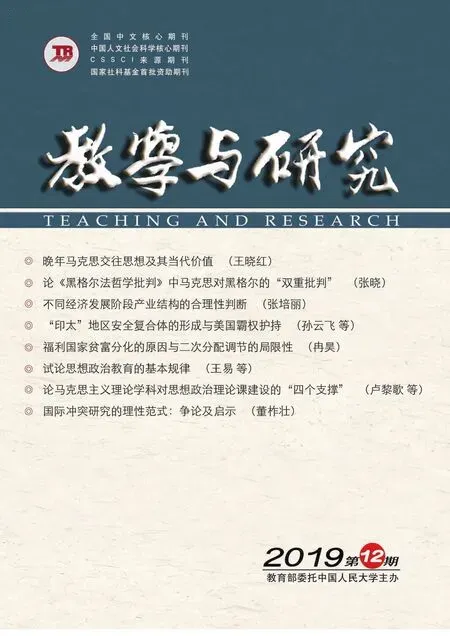福利國家貧富分化的原因與二次分配調節的局限性*
以英美等國為代表的西方福利國家的“黑天鵝”事件,并非偶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導致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普通百姓生活水平不升反降,致其對現狀不滿,希望通過手中選票改變現有政治格局。如英國最富裕的20% 人口和最貧困的20% 人群之間的財富差距是歐盟中最嚴重的三個國家之一。(1)冉昊:《英國脫歐公投后資本主義國家的極端思潮》,《學習時報》2017年2月13日。傳統觀點認為,福利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福利國家市場化改革有密切關系。那么,市場化促使貧富分化的原因是什么?福利國家二次分配的調節對貧富分化為什么沒有起到根本的抑制作用?福利國家的二次分配的局限性及其原因是什么?本文基于“生產-分配”的視角,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的解答。
一、福利國家改革以來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及其原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進行了一系列廣泛且影響深遠的改革。傳統觀點認為,福利國家這一系列改革,是以“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為代表的、體現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市場化改革,并由此導致了福利國家貧富差距的拉大。
1.福利國家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
弗朗西斯·福山(Frances Fukuyama)就認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政治特征便是自由主義思想的復燃和對政府擴張的逆反應。(2)弗朗西斯·福山:《國家建構——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4頁。“資本主義多樣性”學派的創始人皮特·霍(Peter Hall)就把英國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福利國家改革稱為“撒切爾夫人的保守主義實驗”,并將其主導下的改革視為“凱恩斯主義的崩潰”和產業政策方面的再私有化。(3)皮特·霍:《駕馭經濟——英國與法國國家干預的政治學》,劉驥、劉娟鳳、葉靜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132頁。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也把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視為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新古典經濟學對發展經濟學的勝利。(4)Gilpin R,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ter 12.皮特·普雷斯頓(Peter Preston)也將福利國家的改革視為新右派的重新崛起和市場化進程的重啟。(5)皮特·普雷斯頓:《發展理論導論》,李小云、齊顧波、徐秀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十四章。
一些數據似乎也在支持這一論點,即市場化被認為是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原因。在美國,如果加上資本帶來的收益,1%最富有的人擁有的財富占全國財富的比例自1980年已經翻了一番,大致從10%提高到2009年之前的20%以上;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其收入比例從1980年至今更是翻了兩倍,大致從4%左右提高到2009年之前的10%以上(見圖1)。更有甚者,財富總量的前0.01%人群——大概有16 000個家庭,平均收入超過2 400萬美元——其收入比例自1980年以來翻了兩番,從1%漲到了將近5%。(6)“For Richer, For Poorer”, Economist, Oct.13th,2012,p.2.企業首席執行官和一般工人的工資比,從福利國家改革前的30倍擴大到2000年之后的300倍。(7)張夏準:《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23個秘密》,孫建中譯,新華出版社,2011年,第216頁。如果把視界擴展到福利國家的主要構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我們會發現大部分成員國即當今世界上比較發達的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貧富差距都在擴大,OECD國家基尼系數增長平均值為0.3。(8)Provisional Data from 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Database,http://www.oecd.org/els/social/inequality.
2.福利國家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原因新釋。
但是,一些觀點認為,新自由主義引領下的市場化改革,并非西方福利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真正原因,或者說只是表面原因。如“中間選民”理論認為,市場化可以自動生發出再分配機制,而不一定會導致貧富持續拉大。(9)Meltzer AH and Richard SF,“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5): 914-927.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不認為市場是導致不平等的終極原因。(10)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聯合早報》2012年6月12日。那么,西方福利國家改革后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對此,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巴黎商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從資本回報率/經濟增長率比,以及資本/收入比兩個維度,給出了一種新的解釋。就前者而言,貧富不均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特性,原因正在于資本回報率始終高于經濟增長率,因而財富的獲取過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為勞動創造了財富,只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富有。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價值通過收入可以衡量,但最富有的那批管理階層、資本投資者的財富獲取明顯高于其所付出的勞動。(11)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2-248、117頁。就后者而言,資本/收入比越高,意味著資本存量越高,也說明國民收入相對于資本的比重更低,因而貧富差距也就越大。(12)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2-248、117頁。由此皮凱蒂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并不會自動導致收入和財富的均等化趨勢;相反,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是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正常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必然趨勢。
皮凱蒂關于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分殊的原因分析,基本適用于西方福利國家改革以來的情況,但亦存在兩個局限:(1)原理應用的周期性。皮凱蒂是從資本主義國家自1700年以來300年的大周期規律進行分析的,而福利國家改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過40年時間不到,更長周期的“大邏輯”固然適用小周期,但畢竟存在差異;(2)更為重要的是,關于貧富分化的動力性問題。果如皮凱蒂所言,資本主義國家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是一種“必然趨勢”,那么這種趨勢的動力到底從哪里來?
3.生產系統的市場化或商品化。
筆者認為,要回答貧富分化的動力性問題,須從福利國家政治經濟結構的雙翼——生產系統和分配系統入手。福利國家的生產系統最早可追溯至斯密“勞動乃國富之源泉”(1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3頁。的觀點,為生產系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為勞動是生產的基礎。馬克思比斯密更進一步,批判了生產過程中“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9頁。的三段論分析,取而代之以辯證唯物主義對其內在關聯進行分析,提出生產本身也是一種分配。馬克思雖然從未提及“生產系統”,但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提供了初步的邏輯鏈條,生產系統已經具有了雛形。福利國家的生產系統,是關涉一切與市場有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包括公營和私營企業(工業以及金融等方面的)、勞資利益行會(如商業行會和雇主聯盟)、勞動力市場制度、進行經濟決策的政府部門,以及這些組織之間的互通關系;相關的政策包括勞動力市場政策、宏觀經濟政策、貿易政策、工業政策,以及金融管制。(15)E.Huber and J.D.Stephens,“Welfare State and Production Regimes in the Era of Retrenchment”, in Paul Pierson, ed.,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2001, pp.107-145.因此,福利國家的生產系統,本質上是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相關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以及涉及市場自我運轉的政府與市場關系。
那么,皮凱蒂所說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必然趨勢”是如何發生的?卡爾·波蘭尼認為,一個完全自發的市場調節,其存在前提是人類社會變成純粹的商品。(16)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頁。也就是說,完全自發的市場經濟狀態,只存在于理想狀態之中——因為人類社會不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現實的狀況是,人類社會中的部分客體和領域可以被商品化,從而形成一種局部市場化的狀態。那么,哪些客體和領域可以被市場化?這一定是與市場相關的客體和領域。如前所述,生產系統是涉及市場發生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因而,市場化的部分必然發生在生產系統。這是生產系統市場化的經驗分析。如果進一步從邏輯上推演,則可以發現: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告訴我們,商品的價格可以包含剩余價值。反之,不包含剩余價值的價格的商品,其商品化或市場化程度就會大大降低。而資本家的天然逐利性決定了其擴大再生產的動力必然來自對商品剩余價值最大化的追求;一旦商品的剩余價值不足以彌補其生產的成本,資本家自然也就會喪失擴大再生產的動力。商品在市場上交易、分配和消費的整個過程,正是生產系統的發生過程。因此,資本家一定會想方設法追求市場化和商品化,這樣才能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么做的同時也就間接地推動了生產系統的市場化。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系統的市場化是一種天然趨勢;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就不會改變,資本家對商品剩余價值的逐利性就會繼續,進而生產系統的市場化或商品化就不會停止。因而,資本主義世界貧富差距的擴大,不僅僅是這幾十年才有的事,而是一貫如此。在皮凱蒂的分析中,1914年之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狀況就已經非常不平等了。在1910年,最富有的10%的歐洲家庭掌控著社會總財富的大約90%。由資本產生的租金和紅利讓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更高;最富有的10%獲得了社會總收入的45%以上。(17)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265頁。
因此,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定發展階段的福利國家,其生產系統的市場化或商品化特征,天然驅動了其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這個結論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發現是一致的,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必然會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極分化。當然,馬克思論斷更加深刻,即通過對資本過剩與勞動力過剩的分析進一步闡釋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內在機理,并揭示出貧富分化的必然性與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具有內在必然聯系。(18)參見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節選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9頁。
以上分析了對福利國家改革以來貧富持續分殊的原因,但卻無法解釋這樣一個事實:福利國家政府并非對其貧富差距拉大放任不管,但為何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呢?福利國家的二次分配具有怎樣的局限?這就有必要對福利國家的分配系統進行分析。
二、福利國家二次分配的調節及其局限
福利國家的分配系統,就是對資源、產品和財富進行再次分配的體系。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如霍布斯所言,人與人為了避免戰爭狀態,逐漸形成契約關系。(19)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05頁。然而,這種契約關系,在洛克看來,只是為了保存人的基本權利。(20)J.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90, reprinted in 1988, p.159.這種關系相對平等,沒有誰天然具有分配主體的資格。這就需要一個“利維坦”——政府,來對生產、資源和財富進行分配。可見,福利國家分配系統中,政府是主體,資源、產品和財富是客體,分配是方式,目的是對福利國家生產系統所產生的財富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進行調整。從理論上說,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市場化的固有特征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可以通過分配系統二次分配加以調節。進一步的問題是:福利國家分配系統的二次分配為什么能夠進行調節?
1.分配系統的非市場化或非商品化。
與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市場化或商品化特征不同,分配系統具有非市場化或非商品化特征。前文提到,人類社會在現實中不可能全部變為純粹的商品,勢必會有一部分與市場無關的客體和領域與商品隔絕,或者不被商品化。例如,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就不能被稱為“勞動力”,而是具有非商品化屬性的人。同理,未被商品化的領域也就與生產系統毫不相干——這個領域就是分配系統的領域。因此,在分配系統或二次分配過程中,那些出現的分配對象主要具有非商品化特性,不包含剩余價值,自然也就不具有商品化擴張的激勵效應,從而不太容易促發市場化。如果說生產系統市場化過程中的核心角色是市場,那么分配系統非商品化過程中的核心角色就是政府。由于分配系統的非商品化,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無法干預分配系統的運轉,于是市場之外與之對應的重要角色——政府,走到了分配系統運轉的核心位置。因此,政府的一系列二次分配手段,包括財政轉移支付、公共開支、社會保障的“兜底”,以及養老金的統籌調配等,都成為分配系統非商品化得以持續進行的重要推手——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二次分配手段是產生分配系統非商品化的原因——與生產系統的市場化類似,分配系統的非商品化也具有天然趨向,只要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存在,那么這種天然趨向就不會改變——二次分配的手段只是分配系統非商品化的催化劑而已。
福利國家分配系統的非商品化特征使二次分配對平抑貧富分化和財富不平等起到調節作用;然而,不爭的事實是,福利國家貧富分化的持續拉大,并沒有因二次分配的調節而有所緩解;福利國家百姓福利需求的持續增加,并沒有因為二次分配的調節而獲得滿足,致使意識形態思潮改弦更張。這說明福利國家的二次分配,存在其固有局限。
2.局限一:福利國家政府二次分配的加強無力扭轉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分配系統的二次分配始終在加強,福利國家的政府角色總體上在擴張。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考量二次分配的加強與政府角色的擴張。
宏觀上看,二次分配的加強與政府角色的擴張,可以概括為“福利的調適,而不是福利的緊縮(retrenchment)”。(21)Pierson P,“Coping with Permanent Austerity: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Affluent Democracies”,i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410-456.通過觀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OECD國家公共社會開支的變化情況(見圖3),我們發現公共開支占GDP百分比始終在上升。另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OECD主要國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占GDP百分比的數據也始終在上升,其趨勢并未因為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市場化改革而發生變化。(22)Atkinson AB,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Rolling Back the Welfare State,MIT Press,1999,p.24.以上兩個論據都表明,政府的角色并未因為福利國家改革中生產系統的市場化而退出,相反,由于公共支出和社會保障支付都是福利國家分配系統中政府進行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這表明在分配系統中政府的角色反而強化了。
從微觀上看,具體到福利國家的某一領域,政府角色擴張的表現也較為突出。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英國醫療保障領域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始終在增加,并且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增幅,大于GDP的增幅。(23)Seeleib-Kaiser M,Welfare StateTransformations,Palgrave,2008,p.134.而到了1998年以后,醫療和衛生的公共支出也在持續增加。英國國家健康系統(NHS)的GDP占比從1998年的5.8%增加到2008年的9%,增速大于之前50年。針對醫療保障體系所進行的內部市場改革,看似是一場市場化改革,實則因其改革并不觸碰醫療產權的國有化性質,而不具備市場化或私有化改革的實質。(24)Glennerster H,“Welfare Refrom”, in Flinders, M, Gamble, A, ec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olitics,2010,pp.684-698.這說明,即便在英國這樣的福利改革市場化或私有化最為顯著的國家,其在分配系統內的二次分配領域的改革(如醫療保障改革),不僅沒有沿著市場化方向前進,反而政府的相關支出持續上升,政府角色在二次分配領域的干預力度在加強。(2)國家統籌性質的養老金現收現付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如國家基本養老金的領取年限和數額都在提高,這說明政府角色實際上在增加;又如建立國民儲蓄組合(national savings scheme),它要求那些未加入職業養老金的人自動參加,其中個人繳納部分和公司繳納部分都被放入由國家持有的個人賬戶(personal account held nationally)。個人可以選擇把錢放入不同組合之中——但不論哪種組合都在政府的控制與監督之下,這也體現了政府角色的增加。可見,在英國的福利國家改革中,養老金制度不僅沒有再商品化,反而加強了國家的管制力度,體現了政府在二次分配領域干預度的加強。(3)英國政府的社會政策朝著有利于增進二次分配的方向調整。如在家庭和兒童政策上,更趨向于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更加普惠的福利政策,福利供給面因而有了較大的延展。總體上,英國通過增加政府公共開支,以及加強醫療、養老和社會政策的福利供給,使得政府的角色進一步擴張。
然而,福利國家分配系統二次分配的加強與政府角色的擴張,并沒有緩解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由圖4可知,西方主要福利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前10%的人群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持續顯著上升——如果假定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民總收入的變化幅度不大,那么剩余90%人群收入的國民收入占比必定下降,這也就意味著貧富差距在持續擴大——雖然這個結論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經得到證明,這進一步說明福利國家自改革以來其二次分配力度的加大,并沒能顯著緩解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這正是福利國家二次分配的局限所在。
3.局限二:福利國家政府二次分配的加強無法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福利需求,導致意識形態的改弦更張。
福利經濟學告訴我們,作為個體的“人”的福利需求,在制度恒定前提下會不斷增加。雖然福利國家政府二次分配不斷加強,但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卻始終不能滿足中低層選民日益吊高的福利胃口。民眾通過選舉,給政治候選人持續施加更高的福利需求壓力,使得候選人為了贏得大選,不得不許諾更高的福利保障。加之近年來西方經濟疲軟、收入下降、通貨膨脹等因素,以及難民潮涌入歐洲侵占勞動力市場造成就業的“排擠效應”,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使得民眾對福利國家長期以來奉行的基于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的經濟社會政策愈加不滿,進而導致他們對民主社會主義口號式的宣傳產生敵意,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替代他們認為已經失效(malfunction)了的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重新帶領這些中低收入群體過上好日子,恢復以往的“榮光”。民粹主義等思潮在歐洲福利國家之所以死灰復燃,正得益于這樣一個難得的歷史“窗口期”,恰逢其時地將民族隔閡、社會矛盾、經濟下行等一攬子問題包容其中,給中低層群體“畫一張餅”,重新登上了歷史舞臺。
一個較早的代表是2012年倫敦騷亂事件。自2010年英國保守黨時隔13年重奪執政權之后,基于古典自由主義及其派生的新自由主義的諸種執政方案,如前英國首相卡梅倫一手炮制的“大社會”(Big Society),希望政府只扮演“守夜人”角色,通過擴大社會力量參與社會管理,提升國家治理水平。然而,“大社會”并沒有真正關愛到社會每個群體,階層分化導致社會矛盾叢生,引發民粹風潮。
最新代表事件是2018年11月法國的“黃背心”運動(The Gilets Jaunes Movement),是為巴黎50年來最嚴重的社會騷亂。其導火索為法國油價上漲引發群眾不滿,但深層次原因是福利國家改革不成功帶來的連鎖反應,無論是早先社會民主黨奉行的“第三條道路”,還是自由派“大社會”式改革,都無法滿足普通工人階層提高福利保障的愿望。于是一個月后,當“黃背心”運動蔓延至德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愛爾蘭等歐洲其他國家時,這一福利根源性問題則展露無遺:德國人借用“黃背心”抗議房租過高和退休金過低;意大利的“黃背心”構成主要是農業移民、工人和失業者;比利時“黃背心”要求減輕賦稅;荷蘭“黃背心”直接抨擊了政府的福利政策,認為其“賴以依靠的福利社會已經消失”。
此外,歐洲傳統福利國家的一些中間道路的意識形態思潮,也因為基于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的福利分配系統二次分配擴張到一定階段后,無法進一步改善百姓福利狀況和遏制貧富分化,從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禁錮中破繭而出——典型性代表莫過于“第三條道路”和基督教民主主義思潮。
20世紀90年代,在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基礎之上衍生出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正是撒切爾政府時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早期建立福利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政策的折中產物。
21世紀初,基督教民主主義作為指導一些歐洲福利國家中右政黨的意識形態,逐步脫穎而出,如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在黨魁默克爾領導下已經在德國連續執政四個任期——比起德國傳統的老牌大黨社會民主黨而言,顯然贏得了更多選民的支持,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基督教民主主義可以取代社會民主主義,用以指導福利國家的進一步改革和發展。(25)Kersbergen K,Social Capitalism,A Study of Christian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Routledge,1995,p.7、p.28.這種觀點認為,基督教民主主義的獨特之處在于其與眾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政策模式,以及因具有宗教關懷而對迅速變化發展的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的快速適應能力,(26)Kersbergen K,Social Capitalism,A Study of Christian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Routledge,1995,p.7、p.28.在這方面,基督教民主主義或許超過了綿延上百年的社會民主主義。特別是在歐洲大陸地區,基督教民主主義不僅加入了上述兩種意識形態的混合,還對福利國家的發展路徑產生了顯著影響。福利國家理論研究的重量級人物、丹麥學者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早在其對“資本主義三個世界”的描述中,就對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所組成的黨派聯盟進行關注,而把新自由主義擱置在一邊,并進一步分析了這種新的意識形態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結盟對德國的就業以及福利保障政策所產生的新的重要影響。(27)Esping-Andersen G,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olity Press,1990,p.169.
可以說,福利國家自改革以來分配系統二次分配的加強,并沒能遏制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給了如民粹主義這樣一個仿佛已經“丟進了歷史垃圾堆”的意識形態思潮“舊瓶裝新酒”的機會,也給了如基督教民主主義這樣一些新興思潮占據傳統福利國家政治版圖的機會。這是福利國家二次分配的又一局限。
三、福利國家二次分配局限性的原因
福利國家分配系統二次分配之所以具有局限性,與生產-分配結構下的諸種因素有關,主要表現為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間功能的交疊、福利供給“公私”邊界的模糊,以及福利制度的路徑依賴等。
1.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間功能的交疊導致二次分配的無序介入。
如果假定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市場化或商品化,與分配系統的非商品化之間存在的“互逆運動”——正如波蘭尼對社會巨變中的市場對社會的嵌入與社會對市場的反向保護之間的互逆運動分析,假設二者能夠協調促進,那么生產系統市場化過程中初次分配遺留下的問題,由分配系統中的二次分配加以彌補和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相互配合,由此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可能性就會相對比較小。然而,現實情況在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間的功能并非涇渭分明,兩者存在交疊之處,這就有可能局限二次分配功能的充分發揮。
二次分配是根據初次分配所做的再調整。邏輯上,勢必是初次分配不到位,才需要二次分配。如果初次分配能夠完全解決分配問題,那么二次分配的歷史使命也就終結了。生產系統本身具有市場性和商品性,因而其首要功能是按照市場的邏輯進行生產,而非進行分配。只是由于生產本身和分配無法完全割裂,因而生產系統帶有一定的分配功能。如果生產系統的分配功能(即初次分配)能夠合理實現平等分配的目標,那么二次分配只需要停留在分配系統進行就可以了。正如企業的社會保障供給屬于生產系統的初次分配問題,如果雇主或資本家能夠完美地做好對勞動力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供給,從而把生產系統的初次分配功能最大化,則二次分配無須介入。然而,正是由于不斷發展的生產系統所生發出的多樣性市場經濟制度,對雇主形成了不同的福利供給激勵,這種激勵差異造成了初次分配結果的差異,導致多數制度環境下生產系統的分配功能(初次分配)無法實現最大化,于是分配系統中的二次分配不得已介入到生產系統中來,以彌補初次分配的不完善;但可能導致的問題是,原本應當由初次分配進行的,由于二次分配的介入而干擾了初次分配的進行,如本應由企業按工資比例提供給工人、進入個人賬戶的養老金,如果政府認為額度太低而不斷抬升國家提供給工人進入國家統籌賬戶的養老金的門檻,就有可能不斷吊高工人對于養老金需求的胃口,連帶工人要求政府提高企業發放的那部分養老金的比重,從而破壞原本在企業和工人之間達成的福利平衡,造成二次分配對初次分配的無序介入(見圖5)。
2.福利供給“公私”邊界不清導致二次分配的不當介入。
生產系統的不完全市場化及其具有部分分配的功能,促使福利國家采用市場化和非市場化相結合的混合手段來嘗試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既然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并非純粹的私有化或市場化,因此僅在分配系統加強二次分配是遠遠不夠的——當生產系統和分配系統結合在一起時產生的化學效應是一個復雜的組合。比如在籌資和服務供給領域的私有化改革,可能同時伴隨著管制領域的政府干預的加強。(28)M.Seeleib-Kaiser, “Multiple and Multi-Dimensional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in Martin Seeleib-Kaiser, ed.,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211-221、p.218、p.11.因此,福利國家改革不是簡單地福利膨脹或收縮,而應被理解為用不同的干預模式進行發展的混合福利政治經濟改革。例如,很多福利國家在養老金和失業政策上是私有化和商品化,卻在社區救助方面加強了公共責任,并同時允許公共服務供給中的市場競爭;又如一些福利國家的醫療領域,醫療的公共供給減小,但同時醫療的公共籌資卻增加了。這種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和分配系統結合后的混合態勢,被概括為福利“分離的集中”(divergent convergence)。它在制度和政策層面則表現為:制度層面趨同(convergence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與社會政策手段多樣化的結合,且政策產出也大不相同。(29)M.Seeleib-Kaiser, “Multiple and Multi-Dimensional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in Martin Seeleib-Kaiser, ed.,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211-221、p.218、p.11.因此,生產系統和分配系統“分離的集中”導致了福利供給公私邊界的模糊。(30)M.Seeleib-Kaiser, “Multiple and Multi-Dimensional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in Martin Seeleib-Kaiser, ed.,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211-221、p.218、p.11.其直接后果是在公私模糊領域原本應當由初次分配(個人負擔)進行的內容轉嫁給了二次分配(政府“兜底”)。如當前醫療改革中的“大病醫保”,政府在這一項的報銷比例最高達到80%,但怎樣才算作“大病”?這就是一個“公私”模糊地帶,雖然有一些客觀指標,諸如很多地方以是否住院作為重要依據,但就可能出現原本不該住院的住了院,真正生大病該住院的卻沒有了床位;不該由政府財政“兜底”的病“兜了底”,該由個人承擔的費用沒承擔。
3.福利制度的路徑依賴促使二次分配推動福利擴張的軌跡愈加固化。
福利國家的制度具有路徑依賴特征,這會促使二次分配沿著不斷擴張的軌跡繼續下去,甚至產生制度慣性,使福利無限擴張且愈加固化。如果用斯考切波的歷史制度主義框架來分析福利國家政府—市場的關系,則會發現由于制度路徑依賴的存在,生產系統領域因其天然的市場化驅動而形成的“小政府—大市場”結構愈加牢固;而分配系統領域因其天然的非商品化驅動而形成的“大政府—小市場”結構也愈加鞏固。原因在于,福利國家基本沿著福利擴張的邏輯而非福利緊縮的邏輯前進。(31)Pierson P,“Coping with Permanent Austerity: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Affluent Democracies”,in Pierson, P.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17.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決策機制,使得抬升福利變得容易,而緊縮福利則變得異常困難——因為福利關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選民會通過選票表達他們對福利的政治主張。福利緊縮的舉措,如政府要通過民主投票增加稅收并減少公共服務支出的難度顯然更大。同時,由于民主政治具有“否決性”特征——即表達批評和反對比表達支持和贊成更容易贏得民心,故而激進和快速的變革通過民主政治得以實現的概率相對較低(這也是社會民主主義極力推崇民主和普選以遏制暴力革命的重要原因)。
這樣一來,福利擴張的基本趨勢一旦形成,就會沿著既有路徑發展下去,使得福利制度不斷朝著有利于擴張的路徑前進,形成福利國家制度的路徑依賴。而福利的不斷擴張,意味著分配系統二次分配的不斷加強,加之前面談到的生產系統領域和分配系統領域功能的交疊與“公私邊界”的模糊,使得二次分配的無序介入和不當介入越來越頻繁。反過來,二次分配更頻繁地無序介入和無效介入,使分配系統的二次分配更加常態化,從而進一步加固福利擴張的路徑依賴。
對于這樣一種福利制度路徑依賴導致的二次分配不斷擴張的慣性,有學者尖銳指出,福利國家要想改革福利制度,很難緊縮福利,而只能重構(restructuring)或調整(recalibration)福利。這種由福利制度路徑依賴導致的二次分配持續擴張,體現了福利國家制度的韌性(resilience)。(32)Pierson P,“Coping with Permanent Austerity: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Affluent Democracies”,in Pierson, P.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3.由是,福利國家未來的發展有可能陷入一種更深層次的二元矛盾:不破除福利國家的制度韌性,就難以解決二次分配擴張固化的問題,進而無法根治二次分配的固有局限;而一旦破除福利國家的制度韌性,福利國家賴以存在的大廈之基就可能松動,整個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體系亦將可能土崩瓦解。福利國家的未來發展何去何從,我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