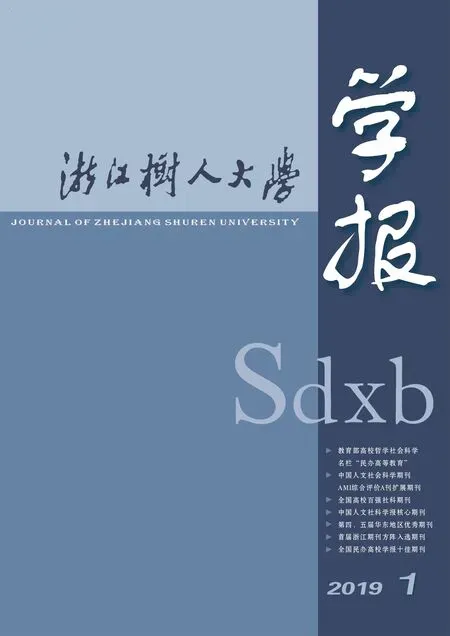《老子》簡本之釋“道”
賈海增
(杭州師范大學,浙江 杭州 311121)
《老子》以精辟的論述和深邃的思想囊括宇宙、自然、社會及人生各個領域。在這一宏大的理論體系之中,“道”為其根基,賦予《老子》鮮明的哲學色彩,從而奠定了該著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因此,探索《老子》的奧秘,理解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先秦道家的思想,離不開對“道”的體悟,它是打開老子思想世界大門的一把鑰匙。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大批戰國竹簡,其中有《老子》若干章節,相關內容與今傳本(以下簡稱“今本”)略有出入,對研究《老子》極具參考價值。在《老子》簡本(以下簡稱“簡本”)中,“道”是反復出現的一個概念,將這些論及“道”的文字整合起來看,可以歸納出一條相對清晰的線索,即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對“道”展開論述,雖隱曲如迷霧,卻也形象生動,初步形成了“道”這一哲學觀念的理論架構。郭店竹簡的抄寫年代不晚于戰國中期,具有一定的原始文獻資料的價值,因而其對老子之“道”的闡述更接近老子思想的原貌。對研究老子及其思想的學者來說,深入挖掘簡本中所記載的“道”,是重要且必要的。
一、靜態:原始混沌,至樸至大
以靜態眼光視之,在時間維度上,“道”是原始的,先天地而生;在空間維度上,“道”是混沌的,包納萬物而難以分識。簡本曰:
有狀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獨立不改,可以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①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狀”從“爿”得聲,今本作“物”,無如“狀”切意。“狀”即《老子》第十四章“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②老子著,湯漳平、王朝華譯注:《老子》,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52頁。,形容“道”的狀貌。“狀”與“象”意同,均給人以一種空間上立體的感覺,大而無邊,虛廓混成,將“道”那種難以名狀的形而上的特質描繪了出來。而“物”作為一個實在的指稱,不宜用之于“道”。“寂寥”,上字原從攴從兌,下字原從糸從穆,即今之“悅穆”。《文子·精誠》謂道者“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③王利器:《文子疏義》,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0頁。,無形之大,無聲之寂,構成“道”獨特的氣質。“獨立不改”
指“道”不依附于他物以運作,且永恒如一地存在。今本在此句后多了“周行而不殆”,蓋道家后學所衍。“可以為天下母”是由“道”的原始性決定的,“道”乃萬物之本源。這個原始、混沌、悅穆、獨立、永恒和為萬物之生源的東西,就像它本身一樣,沒有名的定義和束縛,暫以“道”稱之,這就是老子心中的“道”。
就人們對“道”的體認而言,“明道”并非最高境界。一方面,人們不可能實現“明道”。簡本曰:
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注]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頁;第26頁;第5頁;第6頁。
“道”之出言,平淡而無味,視之難見,聽之難聞,其深遠廣奧不可紀極。另一方面,“道”本身不需要被明了。簡本曰:
是以建言有之:明道如昧,夷道(如類,進)道若退。②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頁;第26頁;第5頁;第6頁。
簡本“夷道”后殘失,今本為“夷道若颣”。《說文解字》曰:“颣,絲節也。”[注]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72頁。引申為不平之意,與“夷”相對。“□道若退”據今本補為“進”。“昧”“颣”“退”押物韻,具有聲音上的美感。三句表明“道”既然是原始混沌的,對它的把握就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特點,即“昧”“颣”“退”,蘊涵著辯證法的色彩。以“明”求“道”,不若以“變”求“道”。“變”即辯證,反向思維與把握之意,這是體認“道”——原始混沌之存在的應有之義。
由此,老子指出古之善為士者,即善于治道之士所具有的特點:
必微妙玄達,深不可識,是以為之容:豫乎(其)如冬涉川,猶乎其如畏四 鄰,嚴乎其如客,渙乎其如釋,混乎其如樸,沌乎其如濁。④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頁;第26頁;第5頁;第6頁。
“微”原“非”字,兩者古音同在微部,故相通。“妙”原“溺”字,“溺”像人側身小便之形,后寫作“尿”,“溺”聲即“尿”,古音“尿”在泥紐藥部,“妙”在明紐宵部,宵藥對轉,故“溺”為“妙”之借字,與今本達到一致。也有另一種解釋,如陳錫勇(2005)認為,“溺”從“弱”聲[注]陳錫勇:《郭店楚簡老子論證》,里仁書局2005年版,第64頁。,簡本甲編有“骨溺筋柔而捉固”句,其中“溺”讀為“弱”,不排除“溺”亦可釋為“弱”的可能,如為“弱”,則意當作“弱其識”,那么這一句的意思就是“虛其心,弱其識,深達于道理”。利用互文性試作新解,且深入其髓,陳氏之見,亦可備一說。擁有道心的士人幽奧玄妙、深不可識,乃源于“道”本身原始混沌、視之不足見和聽之不足聞的特點。老子將大而無形的“道”人化了,體現為“道”對世人的自我修養作用。這種源于“道”的自我修養表現于外,即“豫乎”“猶乎”“嚴乎”“渙乎”“混乎”和“沌乎”。“冬涉川”與“畏四鄰”表現為猶豫,內里則意味著對自然有敬畏之心,與“進道若退”相應;“若客”表現為恭謹莊嚴,點“道”之“穆”;“若釋”表現為寬容舒靜,點“道”之“悅”;“若樸”表現為質樸自然。“混”原“屯”字,“屯”是《易經》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卦,屯卦的主卦是震卦,卦象是雷,“春雷一聲驚萬物”,象征生命的起始。屯卦的客卦是坎卦,卦象是水,喻險。萬物萌生大地,在生長過程中充滿險阻,但只要順應自然,就會欣欣向榮,這是屯卦的內涵,符合“道”化萬物的運行規律。“樸”本義為未加工成器的木料,《說文解字》曰:“樸,木素也。”[注]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15頁。它代表生命的原始狀態,也意味著順應自然、回歸本真。今本作“敦”,敦厚,或云“屯”“敦”音近相通,然未若“屯”作卦象之內蘊深厚;“若濁”表現為混沌,即“大白如辱”“明道如孛”之意。“沌”原為“坉”字,“坉”從土從屯,聲符為“屯”,“沌”亦從“屯”得聲,故兩者相通,意為水濁貌。老子用一系列比喻將抽象的“道”具象化,雖以人為論,卻處處切近“道”。
“道”是原始混沌的,具有“樸”的特點,也能發揮巨大的作用,成為高于天地和使萬物為其賓的存在。簡本曰:
道恒無名,樸雖細,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萬物將自賓。⑦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頁;第26頁;第5頁;第6頁。
“恒無名”即“未知其名,字之曰道”之意,體現“樸”的特點。“樸”意味著生命形態最初的樣子,是沒有被命名的階段,一團混沌、無所指稱,就像一塊未加工的璞玉。“道”由于始終處于“樸”的狀態,沒有世間之“名”的束縛,才能以莊子所謂“無所待”的境界至大至遠、至深至奧,變化無極而守中如一,這就是“道”自身所蘊含的辯證法色彩。一方面,“道”是“小”的。“細”原為“妻”字,“妻”是清母脂部字,“細”是心母脂部字,聲為一系,韻在同部,故相通。今本作“小”,義與“細”相去未遠,均與“道”之“大”相對而論。“細”與“大”對言,亦見于今本第六十三章和第六十七章,可見此處讀“妻”為“細”是具有文本合理性的。或云讀“微”,前“古之善為士者,必非溺玄達”,已有“非”作“微”之例,倘以“妻”再作“微”,何一本之中,通假字運用如此不統一?“微”“細”“小”三字雖在詞義上相近,但就讀音而言,“微”為明母微部字,在讀音上顯然是“細”更接近“妻”。故此處作“細”為宜。無名、樸質的“道”,是至小而無形的,又是無處不在的。因其“小”,故能成其“大”。“大”即“道”的另一面,體現在“天地弗敢臣”,且“萬物將自賓”。“天地”,今本作“天下”,應以簡本“天地”為是。“有狀混成,先天地生”,“道”先于天地而存在,是天地萬物之母。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第4頁;第5頁;第27頁。“天”和“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用“天下”來替代。“臣”,《說文解字》釋為“事君也,象屈服之形”。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曰:“(臣)象一豎目之形,人首俯則目豎。”[注]王力:《王力古漢語字典》,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018頁。“道”作為一切生命的本源,是不受任何東西支配的,包括在世人看來為至高之存在的天地。“道”不僅不為天地所臣,且能夠化萬物。“賓”,《說文解字》釋為“所敬也”,引申為賓服、歸順,與“臣”相應。“萬物將自賓”并不是使萬物賓服于“道”之意,“道”既支配萬物于無形,又具有自身的獨立性,這一獨立性表現在“道”不會被他物所主宰,也不會去主宰他物,當然不需要賓服。關鍵在于“自賓”,指自我主動地、像是本能一樣地順應自然,體現“道”無為而無不為的特點。“道”之大,正在于對天地萬物潛移默化的支配和影響作用。故簡本曰:
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③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第4頁;第5頁;第27頁。
今本“道大”在“天大”“地大”之前,是就“道”先天地生、創生萬物而言的,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邏輯上的一致。老子強調的并非在生成論范疇內“道”的抽象與獨立,而是將其融入天地萬物中,通過它們來體現“道”的運化,置于天地之后正取“道”寓于天地萬物間以發揮其作用之意。可見,簡本更符合《老子》的原貌。
綜上而言,“道”是原始的、混沌無名的、無形的。首先,“道”是原始的,先天地萬物而存在,看似遙遠但又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四時變化、人事興衰中都有其影子,仿佛融入了每個人的生命,似遠而實近。其次,“道”是混沌無名的,像一團迷霧般讓人難以捉摸,但又是宇宙間至真至明的存在,似濁而實明。最后,“道”是無形的,可以至小也可以至大,無狀可循、無所羈絆、自由自得、深遠又廣大,這就是簡本中意蘊復雜又難以名狀的“道”之靜態面貌。
二、動態:從有到無,返歸其本
“靜”其外、“動”其內,構成“道”溫靜容與而又生生不息的特質。“道”的動態生命力系于一字——“反”。“反”既有“返回”之意,也有“相反”之意。返回,即返璞歸真、返歸其本;相反,即相反相成、對立統一。前者強調樸真,后者強調辯證。事物在相反相成、對立統一中走向樸真,走向生命起步的地方。簡本曰:
反也者,道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④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第4頁;第5頁;第27頁。
“反”原為“返”字,“返”指向“始源”,即事物的本質。“夫物蕓蕓,復歸其根”,各返其所始也,以達到“樸”的境界。形之于人,則比于赤子。赤子是老子欣賞的一種生命狀態,是人返歸自我的結果。“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一句,運用逆向思維的方式道出世間萬物生長的過程,反過來便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意。 “返”的過程,是一個從“有”到“無”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憑借的是“弱”,以柔弱勝剛強,如水般善利萬物而不爭,此“道”之所用也。
與“弱”相映,“損”亦為“道”之所用。簡本曰:
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也。無為而無不為。⑤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第4頁;第5頁;第27頁。
老子將“學者”與“為道者”對比而論,將“道”之用弱的觀念表達得更為通俗易懂。《說文解字》曰:
“損,減也。”[注]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55頁;第99頁。《易》云:“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注]阮元校刻:《阮刻周易兼義》,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頁;第218頁。人后天所積累的一切物質和思想觀念都屬“下”,下者,損也;人本身所葆有的真質都為“上”,上者,益也。損下以益上,道之所行也。“損”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故曰“損之又損”,最終目的是“無為”。“無為”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它并非無所作為之意,而是蘊含著一個不斷損銷偽我、返歸真我的過程。“無為”的結果是“無不為”,當真我回歸之時也就達到無所不成的境界,這正是為道者高于為學者的地方。整體觀之,“損”看似是一個從“有”到“無”的過程,實則是一個由“小”而“大”、積跬步以至千里的過程。“有”而“小”,“無”而“大”,可見返歸之道并非退回原點,而是上乘大化。可見,事物返歸本真是一個由強而弱、由增而損的過程。具體到修身與治國,則應遵循知足守柔之道。在修身層面上,老子強調知足保和、功成身退。簡本曰:
持而盈之,不若已。揣而群之,不可長保也。金玉盈室,莫能守也。貴富驕,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注]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持而盈之”,“持”表示一直拿著不放的狀態,使所積累的東西越來越多,以至盈滿。盈滿之時,亦即出溢之時,得而復失之時也。故不若及時停止,行知足不欲之道。“揣而群之”,今本作“揣而銳之”,王弼注:“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折,故不可長保也。”[注]老子著,王弼注:《老子道德經》,古逸叢書景唐寫本,第4頁。《老子》第四章有“挫其銳”語,可與此處互映。“金玉盈室”,是“持而盈之”的具體所指。“莫能守也”,則是“不若已”的原因。《說文解字》記載“盈,滿器也”⑤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55頁;第99頁。,意為使容器滿。滿甚之,則轉為流而失之,故金玉固不可守也。在春秋戰國時代,追求富貴越來越成為一種主流價值觀念。老子一反時風,提出富貴而驕,是自遺災禍,過莫大焉。相反,功遂身退,才是修身保身之道。在此,老子把關注點放在如何處理物與我的關系上,特別是“得到”之后應該做的事,即守中有度、知足保和、以“退”為“進”。這是老子在戰亂時代得出的求生、益生之道,功成身退也成為世人的人生追求。相比“功成”,“身退”對世人來說更難以達到,它是人摒棄外物、返歸真我的過程,與萬物行自然周返之道而生生不息融為一體。
在治國層面上,老子強調無為而治。“無為”意味著用弱、守柔、不爭,順應天時、不耗人力、與民休息。簡本曰:
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強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果而弗伐,果而弗驕,果而弗矜,是謂果而不強,其事好長。⑥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這是老子運用“道”以治國的具體表現,說明老子筆下的“道”,不是脫離現實、空無一物的抽象概念,而是最終指向人事,觀照現實世界。《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注]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941頁。春秋戰國時代,國土分裂,戰亂不斷,軍事力量成為衡量國勢強弱的一個首要標準。在此背景下,老子提出“不欲以兵強于天下”,重在養民之力,不以無謂之戰傷民贅國。佐人主者,必以“道”輔,不私一己之利。“道”之用在“弱”,以弱用兵,意在“果而已”。《說文解字》記載“果,木實也”[注]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14頁。,《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注]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01頁。,謂行之成。此處“果”指殺敵,但達到目的即止,不應無休止地用兵。“‘果’猶現代哲學之‘度’,若及于‘度’,仍驕矜不已,仍逞強不已,則過猶不及。”[注]劉信芳:《荊門郭店竹簡老子解詁》,藝文印書館1999年版,第7頁。老子強調對“度”的把握,超過“度”就會得不償失。“果而不強”具體表現為“弗伐”“弗驕”和“弗矜”。“伐”意為夸耀自己。《尚書·大禹謨》云:“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阮元校刻:《阮刻周易兼義》,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頁;第218頁。“果而弗伐”,即戰勝而不自我夸耀之意。“驕”意為驕傲,《商君書·戰法》曾云:“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注]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9頁。“果而弗驕”,即戰勝而不驕傲之意。“矜”原為“”字,今本作“矜”,當為“矝”之形訛。《說文解字》曰:“命,使也。”[注]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6頁;第163頁;第20頁。又:“使,令也。”②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6頁;第163頁;第20頁。“命”與“令”轉注,故“”“矝”相通。《毛詩傳》釋“矜”為“偏獨憂憐也”。《論語·子張》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93頁。這里的“矜”即為“矝”,意為哀憐。“果而弗矜”,即戰勝而不自我憐惜之意。只看到自己的傷痛而加以憐惜,卻不推己及人,有違人道。以上三者謂為“果而不強”,不強者,乃以一顆包容、良善和謙恭的心對待戰爭,如此才能走得更遠。除了在戰爭上守“不強”之道,在治國的其他方面也應以“治人事天,莫若嗇”為準則[注]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頁;第33頁。。《說文解字》載道:“嗇,愛濇也,從來從,來者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⑤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6頁;第163頁;第20頁。丁原植(1999)云:“‘嗇’指一種態度,一種要求,一種把握,一種節制,也就是一種面對‘治人事天’之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于如嗇夫般勤奮地種植著、珍惜地節省著,并守護地收藏著。”[注]丁原植:《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54頁。將“嗇”的幾個義項包括“節省”“愛惜”“農夫”統一起來,與上述“道”之用“弱、虛、損”相應,指向“道”的深厚蘊涵。
以上就是“道”從有到無、返歸其本的動態過程。返歸其本,是事物向自身的回歸,這個回歸的過程不等同于倒退,而是向著至高之境前進。在此過程中,它需要以“弱”和“損”為憑借,“無為”以“無不為”。一方面,老子認為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無到有是事物的一般發展過程,也是必須經歷的過程。而天下之母“道”的體現,則在于事物的特殊發展,即由大歸小、由強歸弱、由有歸無。“小”“弱”“無”本身不代表至高之境,而是在返歸生命始源的動態過程中脫離了原始的純稚,走向更高層次的純熟,從而達到至高之境。另一方面,老子標舉“道”的目的在于用世,主要表現在修身和治國兩個方面。小到保身,大到治國,“道”均能給人以有益的指導。于己而言,貴在存身,故不重外物,知足知止而已;于國而言,貴在存民,故兵用不強,事天以嗇,順時任運而已。從抽象的“返”到具體的“返”,老子勾勒出“道”的動態運行之軌——從有到無,返歸其本。
三、結 語
簡本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對“道”進行闡釋,深化了人們對“道”的認識,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簡本關于“道”的討論,多立足于“道”本身,很少涉及排斥儒家的內容,其唯一正面論述的內容是:
故大道廢,焉有仁義。六親不和,焉有孝慈。邦家昏亂,焉有貞臣。⑦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頁;第33頁。
理解這段話的關鍵是“焉”,“焉”原“安”字,兩者均為影紐元部字,音同相通,而今本無此字。“焉”有三種解釋:一為疑問代詞,意作“哪里”“怎么會”,整句話的意思是“大道沒有了,怎么會有仁義?”將大道與仁義相容,這是違背老子思想的。因為“道”不管是從靜態還是從動態來看,都是指向“樸”的,即不假雕飾、純任自然,是“道”的根本性質。而仁義之屬,為人精神品格之修飾,與“道”之“樸”不可能完全相容。故釋“焉”為疑問代詞是不正確的。“焉”還可解為連詞,意作“則”“于是”,與今本文意相合,整句話的意思為“大道被廢棄,于是有仁義;六親不和睦,于是有孝慈;國家陷于昏亂,于是有忠臣”。該意與老子思想相合,當為確解。簡本丙組第一節有“信不足,安有不信”之語,意為“統治者缺乏誠信,也就得不到百姓的信任”。這里的“安”讀為“焉”,釋作連詞,與“安有仁義”之“安”是同一用法,進一步說明“焉”作連詞的正確性。仁義忠孝是儒家所標舉的道德人格,是成為“君子”所必須具備和修養的品質。在老子看來,所謂仁義忠孝君子之風,不過是大道不至的表現。大道不至,意味著“偽”行于人世。仁義忠孝,正是這種“偽”的體現。仁義是大道廢棄之偽,孝慈是六親不和之偽,正臣是邦家昏亂之偽。“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也,斯惡已”,仁義忠孝是世人所認為的“美”,而對“美”的肯定卻建立在丑惡的基礎上。人們往往只關注“美”而忽視“美”背后“惡”的存在,這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世人的偏執狹隘之處。
但是,老子并不否定“美”本身,而是認為“美”不能代表人們的終極追求,它只是一個必經的中間階段,達到“美”之后仍應回望自我、去偽存真、返歸樸質。最終無所謂美丑善惡,“和其光,同其塵”,一切都將混沌而純明,這就是老子所追求的“道”的境界。在這個意義上,儒家與道家并非截然相對、勢若水火,而是呈現某種包容性。不妨說,儒家是“功成”之道,道家則是“身退”之道,兩者共同指向個人的發展,這是儒家和道家包容性的一個體現。儒道互補能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所追求的人生范式,正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