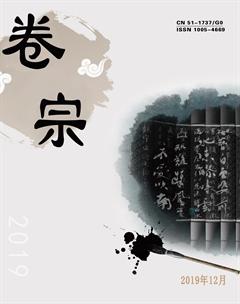證據法基本原則微探
摘 要:證據制度以證據原則為基礎,隨著證據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理論界不同學派對證據原則進行了闡述,司法實踐界對證據原則提出了新的挑戰。改革開放至今,證據制度經歷了從恢復到蓬勃發展的過程,[1]證據法基本原則也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由于我國沒有建立系統的證據法制度,加之通說對證據法原則的闡述具有偏頗性,大都以刑事證據原則為主,導致證據法基本原則近乎成了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的延伸。基于證據法原則應該具有的指導性以及普適性,本文著重對證據法基本原則的內容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原則;證據基本原則;指導性和普適性
1 問題的提出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當前我國法律實踐以及理論研究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審判依據從“靠人情說話”到“靠證據說話”的重要標志。改革開放至今,證據制度呈現出不斷進步、蓬勃發展的態勢,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完整系統的證據法,對于證據法原則的規定散見于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訴訟法以及一些條例等法律文件之中,缺乏統一而系統的原則體系。現行的證據法教學較為權威的課本,對于證據法基本原則的闡述也呈現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特點:卞建林學者主編的教材認為證據法的基本原則包括真實發現原則、證據裁判原則以及自由評價原則;[2]何家弘學者主編的教材認為包括證據裁判原則、自由心證原則、無罪推定原則和證據法定原則;[3]高家偉等學者主編的教材認為包括客觀真實原則、證據裁判原則、自由心證原則、直接原則和利益衡量原則;[4]劉品新學者等主編的教材認為包括遵守法制原則、實事求是原則、證據為本原則、證據裁判原則、直接言詞原則、公平誠信原則、法定證明與自由證明相結合原則;[5]陳光中學者主編的教材則認為證據法的基本原則包括證據裁判原則、程序法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和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原則。[6]縱觀各家學者的觀點,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分歧之處,但大都以刑事訟訴的基本原則為主,沒有從具體的訴訟法中抽離出來,概括出具有最基本價值和地位的基本原則。理論界尚且如此,加之我國沒有系統的證據法制度和證據法典,缺乏立法基礎,這就造成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刑事案件的證據重視程度高于對行政案件以及民事案件的重視程度以及在出現現有證據規則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沒有基本原則為指導,給予了法官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權,使得證據面臨著新的挑戰。
2 對證據法基本原則的思考及見解
上文已述,證據法的基本原則的內容應該最具概括性,價值應該最具指導意義,地位最具基礎性。證據法的基本原則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立法階段給予指導,司法階段彌補法律空白。它應該是能夠涵蓋“三界”,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是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共同遵循的基本證據原則。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固然重要,具有很強的代表意義,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在確立證據法基本原則時傾向于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否則就是去了基本的價值意義。無論基于理論還是實踐的現實情況這種傾向性都是清晰可見的,因此,在闡述基本原則的時候更應該糾正這種傾向,擺脫長期以來刑事訴訟原則對于證據法基本原則的影響,真正使證據制度在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訴訟中同等發揮作用。基于此,筆者認為證據法的基本原則應該包括證據裁判原則、程序法定原則、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相當標準原則以及救濟性原則。
證據裁判原則是指對于案件事實的認定必須依據證據。證據裁判原則是證據法基本原則的根本,是原則的原則。它強調以證據為本位,認定事實從證據出發,排除了人的主觀臆斷。普遍認為證據裁判原則經歷了神明裁判、法定證據以及自由心證三個階段,實現了審判中從求助于神明到從證據事實本身出發的歷史變革。我國沒有明文規定證據裁判制度,但是三大訴訟法以及最高法院 的司法解釋都有對該原則的相關表述。如何正確運用證據裁判原則是關鍵問題。首先證據裁判原則是用來證明案件事實的只能是證據,這是從正面規定了證據的主體地位,其次,用以裁判的證據必須具有關聯性、合法性、真實性,目前法律規定的證據的種類有八種,這八種證據的證明力存在區別,這里所說的證據強調了客觀真實性,要排除主觀臆斷等來認定案件事實。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強調證據的本位作用不等于對證據的極端化認識。司法實踐中正是因為強調證據的作用,而尋找真相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就衍生出了一種將證據極端化的做法——刑訊逼供。既然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依靠證據,那就為了有證據而不擇手段,刑訊逼供。這是走向了另一種極端,不是證據裁判原則所追求的價值,因此,對該原則的理解不能忽視第二層的含義,防止證據原則走向極端。
程序法定原則是指訴訟中如何收集、審查、判斷證據以及如何依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都應當由法律規定的程序加以規范,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及司法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如果說證據裁判原則是實體性的規定,強調認定案件事實必須有證據并且依靠證據,那么程序法定原則就從程序上給予了證據一層保護膜,強調證據運用實施過程的程序化以及法治化,再一次排除了主觀臆斷的弊端。對程序法定原則的理解也要注意這樣兩個方面,首先,立法必須保障訴訟活動有法可依,訴訟活動是證據法發揮作用最重要的舞臺,只有保證訴訟活動有法可依,舉證、質證、認證才能夠和諧有序進行,法官才能夠真正的做到兼聽則明,充分聽取雙方的意見,在客觀公正的基礎上做出最為合理合法的判斷。其次,執法人員必須做到嚴格執法,有法必依。執法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的程序進行,防止程序制度的落空。這里所說的證據程序法定不止是法官等執法人員的所遵循的程序,也包括糾紛雙方和代理律師等其他人員所進行活動的程序以及證據的采集、展示等程序。違反程序法定原則的后果就是非法證據排除,即使實質上是合法的也必須排除在外,這不僅是嚴格依法辦事的體現,也是一種價值倡導,即防止為了搜集證據而不擇手段,違背法律倡導的保護人的價值追求。
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強調的是證據的證明主體以及證明力。基于證據裁判原則的要求,一般主體不會隨意提起訴訟,而對于自己的主張,只有自己提供的證據對自己的主張最具有證明力,也一定是最充分最有優勢的。這也是權利義務相統一的體現,權利主體有權提出自己的訴訟請求,同時就有義務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我國的三大訴訟法舉證責任的規定都是該原則的體現。在行政訴訟中雖然舉證責任倒置,但是行政相對人是根據行政主體做出的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這種行為是基于先行為而采取的衍生行為,是一種抗辯而不是主張,而行政主體的舉證責任就是對自己做出行政行為主張的舉證。在刑事訴訟中都是控訴方負有舉證責任,因為無罪是不需要證明的,被告人的無罪主張實際上就是抗辯,而控訴有罪就是一種主張,必須舉證有罪才能說明罪行成立,這也是誰主張誰舉證的體現。總結概括可知,誰主張誰舉證貫穿了三大訴訟法,是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原則,應該納入證據法基本原則體系。從另一個角度看,主張人必定會舉證對自己最為有利的證據,這會促使法庭證據呈現的全面化,保證法官充分聽取雙方意見,接近案件事實,保證案件的質量。
相當標準原則是指在認定證據的過程中要保證證據的相當性標準,證據的呈現和事實的認定相當性,避免出現證據與事實的畸輕畸重。相當標準原則是連接證據與待證事實的橋梁,強調使得證據與事實粘合匹配度較高,是證明標準的問題,既不用過量過重的證據證明易于證明的事實,也不用無關的證據證明事實。基于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弊端——雙方均舉證最有利于自己的證據,相當標準原則是對該原則的限制,不能過度舉證,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舉證。該原則體現的是一種等量和效益性原則,在我國三大訴訟法中均有體現。民事訴訟中體現為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行政訴訟中也體現為證據的三性加上優勢證據原則;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要求以及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相當標準原則還是效益性的體現,用相當證據標準來證明案件事實可以減低訴訟中收集證據的成本,簡化舉證、質證過程中不必要的證據呈現,從而確保認證的準確合理高效。
救濟性原則是對于舉證有一定困難的特殊主體的一種司法救濟途徑,是指在負有舉證責任的主體舉證困難并且因此對案件結果有重大影響的情況下,可以為其提供一定的救濟手段的方法。該原則意在保護權利的行使,防止權利落空的現象。是對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一種補充。首先,該原則的適用條件必須是舉證有一定困難的特殊主體,對于“舉證困難”的判斷應該包括權利人的法律經濟狀況、法律文化程度、行為能力等綜合的考量;其次,如果舉證不能將會給案件結果帶來重大影響,極有可能導致案件結果的相反或者重大分異。最后,救濟的主體可以是法院也可以是律師協會或者法律援助中心等可以基于救濟的一切主體。之所以不限于法院為唯一救濟主體,一方面在于緩解法院的繁重工作壓力,另一方面在與發揮社會力量最大限度地還原案件事實,追求真實可靠的證據。救濟性原則不僅有利于解決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舉證中出現的困難境地,還有利于貫徹落實證據裁判原則。
證據裁判的證據裁判原則、程序法定原則、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相當標準原則以及救濟性原則這五大原則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關系。證據裁判原則是前提,程序法定原則是保障,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是關鍵,相當標準原則是對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限制,救濟性原則證據原則的補充,這五大基本原則在三大訴訟法中都有體現,是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系統性的基本原則體系。
3 推進證據立法以及確立基本原則的展望
對于證據法基本原則的學術爭鳴不斷,不論怎么樣的見解都需要回歸證據法基本原則的初心和價值追求,基本原則一定要具有統一性和普適性,否則何為基本原則呢?回首我國證據法發展的四十多年,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是沒有一部完整的證據法就使得證據法的各項規定在實踐中存在問題,因此,更應該確立證據法的基本原則,推進證據立法建設,完善證據法制度。隨著新型技術的發展,科技的突飛猛進,案件事實的逐漸呈現出復雜化,高技術化的特點,這對于證據法的運用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期待系統的證據制度的建立以及我國證據法研究的更深發展。
參考文獻
[1]張保生,馮俊偉,朱盛文.中國證據法40年[J].證據科學,2018,26(02):133-150.
[2]卞建林主編:《證據法學》(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6~91頁
[3]何家弘主編:《證據法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291頁
[4]高家偉、邵明、王萬華:《證據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193頁
[5]何家弘、劉品新:《證據法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6~97頁
[6]陳光中:《證據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130頁
作者簡介
鄭林彤(1996-),女,河北承德,河北工業大學,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