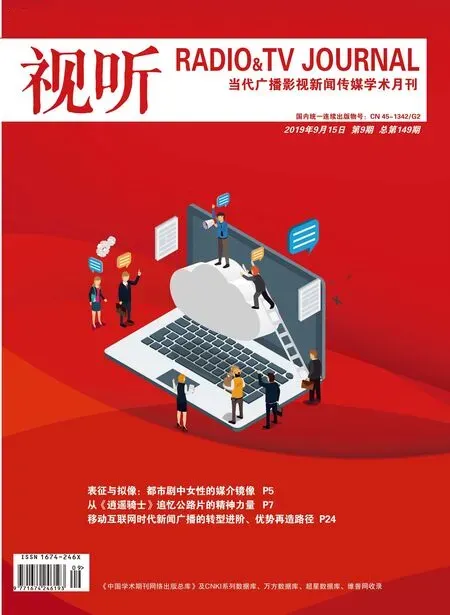新聞報道與未成年人隱私保護
——以“鳳凰少女性奴案”為例
□ 王雨康
一、新聞報道中未成年人隱私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當前,新聞媒體在報道某些民生問題時往往侵犯到未成年人的人身權益。在個人保護權益上升的時代背景下,媒體迫于社會輿論壓力,對報道行為進行了諸如隱藏未成年人個人信息之類的糾正,但作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如何規避新聞報道中侵害未成年人隱私權的問題,仍然需要引起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全社會的關注。近期對“鳳凰少女性奴案”的報道,就代表了對發生在小范圍內(某小型城市的一個區、小型縣級市、某鄉鎮、某村莊等范圍)未成年人受害事件報道過程中涉及侵犯隱私權的問題。
(一)對于小型區域所發生事件細節報道的處理不當
央視網在對“鳳凰少女性奴案”進行報道時寫道:“2019年2月13日,龍某和以‘搭順風車’為幌子將被害人龍某某騙至車上……”,對于當事人的介紹進行了隱晦報道。但是兩天后澎湃新聞的報道內容卻成了“龍某和從山江鎮古塘村開車去山江鎮街上跑車拉客,途徑山江鎮‘新農村’時,看見被害人龍某某(在校學生,16 周歲)在馬路邊招手搭車……”,文中對于被害人的年紀和事發地點進行了公開報道。隨后“澎湃新聞”官方微博評論中則有自稱受害者所在醫院的醫務人員透露傷情,之后多家媒體順藤摸瓜發布了有關當事人傷情的具體細節。
在小型區域民生新聞的報道過程中,細節報道對于作為未成年的當事者是十分重要的,小型區域內的醫院個數以及對應的可能的關聯人物數目相對較少,當對細節披露不當時,交叉點對于當事人的鎖定就非常關鍵。小型區域內的人際傳播強度大,社會環境會對案例中16 周歲在校女生有多大程度上的影響不得而知,但是當事人之后成長中的心態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大走向偏激人格的可能性。
(二)監護人和當事人通常擁有不平等的知情權
“鳳凰少女性奴案”事件中當事人的小姨曾在一周后接受過采訪,向《緊急呼叫》欄目介紹,其外甥女身體未恢復好,手被綁很久,被打了很多次,現在也上不了學,手連筆都拿不起來。這種報道在小型區域內很容易成為當事人被鎖定交叉點的重要環節,因此媒體和監護人應予以謹慎對待,這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考驗著新聞工作者的媒介素養。當采訪這類涉及未成年人的傷害類新聞時如何引導其監護人回答相應的內容,對于未成年的當事人也要有相應的知情權,不可因為其心理承受能力等的不完備而忽略其主觀意愿。
“鳳凰少女性奴案”中當事人的小姨曾對媒體說:“不敢問她,一問就受不了。”可見在該案例中除去辦案人員的多次案件問題引導與調查外,其監護人也是對當事人進行喚醒回憶,而當事人對于案件回憶的抗拒是明確的,但由于監護人的學歷層次限制,可能對于問題的敏感性以及對未成年人教育的了解程度有限,因而新聞媒體就需在采訪結束后換位思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從而在稿件處理的過程中對于資料的細節內容進行篩選,做好“把關人”。
(三)對于傷害性事件中未成年人的隱私報道引導不妥
3月25日,湖南鳳凰縣檢察院通過其微信公眾號“鳳凰檢察”通報一起該縣五十歲單身男子在自家房屋地下挖洞囚禁16 歲在校女生為性奴的案件,女生被囚禁24 天后被警方解救。檢察院對于事件的通報內容進行了相應的細節隱藏,之后持續發布公安部門抓捕犯罪嫌疑人和提交檢查意見書等一系列流程,對事件進行了及時的報道,滿足受眾對于該事件的關心,也對于未成年當事人進行了一定的保護,隱藏傷情的具體內容等敏感信息。
但是,之后曾有多家媒體通過聯系當事人就診醫院乃至公安部門,對了解到的具體細節內容進行報道,而這些報道相繼曝光后,對回到原生活環境的當事人的心靈傷害可想而知。同時,這也使得公眾輿論會受其引導,澎湃新聞披露該案件時對于當事人的年紀(在校學生,16 周歲)進行了報道,引起了受眾的共鳴與同情,隨后上升到知情人士在評論中描述當事人在案件發生前的生活狀態、家庭背景等,在網絡環境中引發極大的討論。
二、新聞報道對未成年人隱私權保護不力的原因
(一)新聞自由與未成年人隱私權的矛盾
小型區域的新聞報道往往會成為群眾“茶余飯后的談資”,但記者仍會行使新聞采訪權,力求擴大信息量從而提高媒體的瀏覽量。因此,公眾知情權和新聞自由權益的滿足與當事人隱私權的保護就處在一個對立的位置。在這方面,法律的規定模糊不清,在實際中更是難以操作。媒體往往引導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盡量獲取最多的相關信息,而作為當事人的未成年人則失去決定自身隱私權的話語權,因此,“鳳凰少女性奴案”這類小型區域內的新聞報道更具有了解當事人個人意愿的必要性,即使客觀上未成年人的心智等因素還不夠獨立做出決定。
(二)網絡環境缺乏相應的監管力度
官方新聞媒體對于事件進行權威報道后,自媒體開始撰寫報道以期搶奪受眾眼球,甚至不擇手段迎合受眾的窺探心理,這其實已經侵犯了未成年當事人的隱私權。更嚴重的是,網絡環境下所謂的“熱心人士”提供當事人更多的信息,身為“意見領袖”的自媒體對他人所曝光的言論加以傳播,使當事人的隱私權在言論自由的“綁架”下受到更嚴重的侵犯。當前,網絡的監管往往是依照慣例對于言語辱罵等惡劣行為進行懲治,但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還不夠,對于網絡環境監管具有關鍵意義的實名制的普及和監督力度還有待加強。
三、新聞報道中未成年人隱私保護的對策
(一)加強公眾輿論監管體系建設和學校教育
網絡監管的相關部門需要擁有更為敏感的意識,對于網絡上涉及他人隱私的評論和引導輿論負向性的新聞進行實名制認證并且進行批評教育。與此同時,需要完善對于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體系,在讓監護人行使監護權時需同時考慮其個人的綜合素養,要在足夠尊重未成年人個人意愿的前提下讓其行使發言權。同時,學校對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普及也要同步推進,把“育人”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方面,加強孩子的自我保護意識和對未成年人的人文關懷。
(二)新聞媒體要增強新聞技巧運用
在對“鳳凰少女性奴案”進行報道時,為了獲取受眾的共鳴與同情從而獲取更多流量,各大媒體的“報網端微”均采用了受害人在被解救時被鐵鎖鎖住四肢以及頸部的照片。其實,這類畫面的選擇具有很強的傾向性,顯示了新聞技巧的欠缺。這類畫面構建了一個悲情和慘痛的氛圍,同時也獲得受眾的同情,這種強調畫面吸引流量的處理方式在新聞報道中是基本要求之一,同時一些必要的新聞報道技巧同樣不容忽略。但是,“鳳凰少女性奴案”的新聞缺少了對于人性的思考部分,過度追求慘烈報道,讓披露“24日鐵鎖囚禁”這樣的信息變成挖掘當事人真實身份的導火索,反而成了侵犯未成年人隱私權的具體表現。
(三)加強隱私權與新聞自由權的法律界定
我國憲法和相關法律都認可和保護公民的隱私權以及媒體工作者的新聞自由權,但在新聞報道的具體實踐中,往往會遇到保護當事人隱私權和保障新聞自由之間的矛盾糾結。個人利益和媒體與公眾的公共利益一直是個動態的過程,而流動的因素主要受時代和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對于當事人的隱私權和媒體的新聞自由權的矛盾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細化基本的準則,從而找到兩者在新聞報道中的平衡點。當報道未成年當事人的民生新聞時,要明確界定媒體的新聞報道權和個人隱私權的界限,以使媒體不能為自身利益而超越報道范圍。這對于小型區域內所發生的新聞事件的報道更應如此,“鳳凰少女性奴案”的新聞報道給我們帶來了很沉痛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