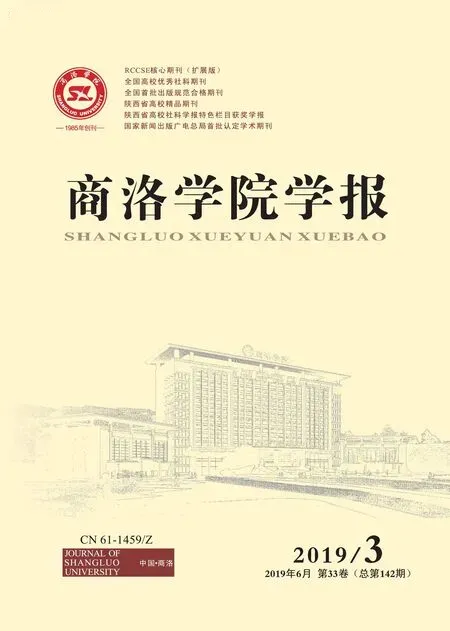論“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敘述
杜薇
(商洛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陜西商洛 726000)
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以來(lái),隨著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與城市化進(jìn)程的加快,書(shū)寫(xiě)農(nóng)民進(jìn)城、反映城鄉(xiāng)關(guān)系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熱點(diǎn),出現(xiàn)了打工文學(xué)與底層文學(xué)。這些文學(xué)作品真實(shí)地反映了農(nóng)民工在城市的際遇以及他們對(duì)城市的認(rèn)識(shí),同時(shí)也寄予了作家對(duì)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思考。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不平衡導(dǎo)致的城鄉(xiāng)對(duì)立一直是文學(xué)表現(xiàn)的重要內(nèi)容。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也有一些小說(shuō)反映了解放后的農(nóng)民進(jìn)城—返鄉(xiāng)的無(wú)奈與痛苦,初步表現(xiàn)了城市與鄉(xiāng)村的沖突。這些小說(shuō)有簫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康濯的《春種秋收》《水滴石穿》,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趙樹(shù)理的《賣煙葉》《三里灣》,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等。這些小說(shuō)反映了一部分農(nóng)村青年“向城—進(jìn)城—返鄉(xiāng)”的歷程,歌頌了那些熱愛(ài)農(nóng)村、建設(shè)農(nóng)村的農(nóng)村青年。它們通過(guò)描寫(xiě)一部分“不安分”的農(nóng)村青年的生存道路,意在告訴讀者:農(nóng)村是一個(gè)廣闊的天地,在農(nóng)村同樣能實(shí)現(xiàn)自己最大的價(jià)值。在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理論預(yù)設(shè)下,城鄉(xiāng)并不存在差別,城鄉(xiāng)是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兩個(gè)不同戰(zhàn)線,農(nóng)民、工人都是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建設(shè)者與勞動(dòng)者,并沒(méi)有高下之分。因而“十七年”的文學(xué)對(duì)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書(shū)寫(xiě)迥然不同于當(dāng)下的打工文學(xué)與底層文學(xué)。“十七年”文學(xué)雖然反映了現(xiàn)代城市生活相對(duì)傳統(tǒng)農(nóng)村生活所展具備的優(yōu)勢(shì),但并沒(méi)有像打工文學(xué)與底層文學(xué)那樣把城市與農(nóng)村置于二元對(duì)立的位置之上,還是寫(xiě)出了二者的統(tǒng)一之處。目前學(xué)界關(guān)于十七年文學(xué)研究論文很多,但從城鄉(xiāng)關(guān)系這個(gè)視角切入,探討十七年文學(xué)的研究文獻(xiàn)尚為稀缺。十七年文學(xué)在城鄉(xiāng)關(guān)系書(shū)寫(xiě)方面具有獨(dú)特的思想與美學(xué)特質(zhì),形成了獨(dú)特的寫(xiě)作策略與修辭方式,塑造出了一些不同于社會(huì)主義新人的人物形象,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問(wèn)題,對(duì)于今天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書(shū)寫(xiě)有極大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一、城鄉(xiāng)文化的差異與沖突
在中國(guó)現(xiàn)代話語(yǔ)譜系中,城鄉(xiāng)關(guān)系并不僅僅是一個(gè)空間并置關(guān)系,還蘊(yùn)含了深刻的文化、政治關(guān)系。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對(duì)于城鄉(xiāng)有不同的文化想象。“五四”時(shí)期,以魯迅為代表的那一代知識(shí)分子作家都把鄉(xiāng)村想象為落后、愚昧、停滯、保守、壓抑人性的藩籬,把城市想象為先進(jìn)自由、開(kāi)明、發(fā)展、開(kāi)放的世界,出現(xiàn)了一些表現(xiàn)追求個(gè)性解放、爭(zhēng)取進(jìn)步的知識(shí)分子從農(nóng)村來(lái)到城市的小說(shuō)。三十年代后期,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延安建立了以農(nóng)村為主體的革命根據(jù)地,農(nóng)村成為革命、開(kāi)放、先進(jìn)的世界,而城市的革命意義則被懷疑,城鄉(xiāng)問(wèn)題得以政治重構(gòu)并被賦予不同的符碼。“以前,城鄉(xiāng)沖突造成現(xiàn)代中國(guó)作家的道德困境,現(xiàn)在城鄉(xiāng)問(wèn)題的這種文化基礎(chǔ),逐漸讓位于一個(gè)城市話語(yǔ)服從于農(nóng)村話語(yǔ)的新政治結(jié)構(gòu)。”[1]新中國(guó)成立后,由于思維慣性,農(nóng)村話語(yǔ)或者說(shuō)農(nóng)民意識(shí)逐漸成為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影響到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定位,進(jìn)而影響到作家的創(chuàng)作。
值得注意的是,國(guó)家意識(shí)與國(guó)家意志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是不斷得到體現(xiàn)和表達(dá)的。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huì)上曾形象地把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進(jìn)駐北平稱為“進(jìn)城”,言外之意是城市與農(nóng)村有不同的倫理觀念,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應(yīng)該做好管理城市的知識(shí)儲(chǔ)備,他還說(shuō):“從現(xiàn)在起,開(kāi)始了由城市到鄉(xiāng)村并由城市領(lǐng)導(dǎo)鄉(xiāng)村的時(shí)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轉(zhuǎn)移到城市。”[2]簫也牧的短篇小說(shuō)《我們夫婦之間》就是一部講述革命勝利后革命干部進(jìn)城的故事。知識(shí)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與出身貧農(nóng)的干部張同志在革命勝利后進(jìn)入了北京城,雖然是第一次來(lái)北京,李克卻對(duì)北京的城市生活很熟悉,感到心情舒暢愉快。從來(lái)沒(méi)有到過(guò)城市的張同志本應(yīng)該更加興奮,然而她卻表現(xiàn)出對(duì)城市生活明顯的疏離感甚至反感。二人由此發(fā)生了矛盾,夫妻感情也出現(xiàn)了裂縫,甚至達(dá)到了離婚的邊緣,后來(lái)二人在相互諒解的前提下達(dá)成了和解,重歸于好。從話語(yǔ)層面看,這篇小說(shuō)表現(xiàn)的是解放后普遍存在的革命干部的婚姻危機(jī)問(wèn)題,而在故事層面,卻提出了嚴(yán)肅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問(wèn)題、現(xiàn)代生活與前現(xiàn)代生活的關(guān)系問(wèn)題。這篇小說(shuō)以夫妻二人的和解暗示城市文明與鄉(xiāng)村文明的和解,然而他們二人和解的基礎(chǔ)固然有李克在政治上對(duì)妻子的認(rèn)可,更多的則是因?yàn)椤拔摇钡钠拊诂F(xiàn)代城市生活的熏陶下對(duì)城市生活的認(rèn)同。“服裝上變得整潔起來(lái)了”,粗話沒(méi)有了,“見(jiàn)了生人也很有禮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買(mǎi)了一雙舊皮鞋,逢到集會(huì)、游行的時(shí)候就穿上了。”“我”的妻的生活習(xí)慣的變化說(shuō)明了城市文明、現(xiàn)代城市生活對(duì)人們極大的影響與滲透。“小說(shuō)還采用了第一人稱視角,以具小資產(chǎn)階級(jí)身份的‘我’為敘事主體,賦予‘我’以優(yōu)越的話語(yǔ)權(quán),從而可以自由地對(duì)其中的人物進(jìn)行評(píng)判,表達(dá)自己的見(jiàn)解與聲音。”[3]而改造者“我”的妻卻處于沉默、被評(píng)判的地位,預(yù)示了改造者的無(wú)力,這篇小說(shuō)也客觀地揭示了現(xiàn)代城市生活與傳統(tǒng)農(nóng)村生活的巨大差距,揭示了城市與農(nóng)村的矛盾。
小說(shuō)借李克的感覺(jué)寫(xiě)出了城市生活的美好與時(shí)髦,他對(duì)象征城市文明的高樓大廈、絲織的窗簾、地毯、沙發(fā)、潔凈的街道、閃爍的霓虹燈、爵士樂(lè)非常地向往與親近。
在十七年文學(xué)敘事中,我們不僅能看到知識(shí)分子對(duì)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且也可以看到城市生活對(duì)農(nóng)民的吸引。康濯的小說(shuō)《水滴石穿》中的張小柳就是一個(gè)對(duì)城市生活非常向往的農(nóng)村青年。張小柳是住在莊上二層樓上的一個(gè)苗條白凈的姑娘,初中畢業(yè)后在社里當(dāng)會(huì)計(jì)。她上過(guò)初中,她了解了村外世界的精彩,她不甘心做一個(gè)農(nóng)業(yè)社社員,一心想通過(guò)各種途徑去城里當(dāng)工人,過(guò)城里人的生活。不僅僅是張小柳,泉頭莊上的其他農(nóng)民也表達(dá)了對(duì)城市生活的驚羨與向往,他們對(duì)城市生活了解非常少,只能通過(guò)張小柳與張小柳的同學(xué)了解城市生活。男學(xué)生的皮鞋、棉夾克和栽絨帽子以及女學(xué)生的緊身小襖與鮮綠的頭巾為他們吹來(lái)一股清新的城市氣息,引得人們像看外國(guó)朋友那樣指指點(diǎn)點(diǎn),連他們站立的姿勢(shì)與走路的姿勢(shì)在農(nóng)民眼里都有一種迷人的氣派。他們旁若無(wú)人的拉手讓農(nóng)民們頗有點(diǎn)難堪,他們說(shuō)笑的聲音簡(jiǎn)直要蓋過(guò)連天震動(dòng)的風(fēng)箱聲。作者通過(guò)莊上農(nóng)民的眼睛形象地寫(xiě)出了現(xiàn)代城市文明給農(nóng)民帶來(lái)的巨大沖擊力。他們并沒(méi)有認(rèn)為這幾個(gè)城市女學(xué)生多么傷風(fēng)敗俗,而是充滿了驚奇與羨慕。在他們的眼里,只有長(zhǎng)相漂亮或者有文化的才能進(jìn)城過(guò)城里人生活。在申玉枝的婚姻問(wèn)題上,他們表達(dá)這樣的意見(jiàn):“我看呀,她最好早早走開(kāi)。”“趕快找個(gè)縣區(qū)干部,跟人家一走。要不的話呀,你別說(shuō)這會(huì)兒,就是往后她結(jié)了婚,咱們見(jiàn)了面怕也要?jiǎng)e扭得慌。”“是呀,玉枝少說(shuō)怕也要找個(gè)縣區(qū)干部,咱村里人們也都這么說(shuō)的。”申玉枝長(zhǎng)得漂亮,他們認(rèn)為他們農(nóng)村沒(méi)有一個(gè)人能配得上申玉枝,申玉枝只有嫁到城里,他們的心理才能平衡。這雖然是一種“我得不到,別人也休想得到”的嫉妒心理的自然流露,可是也反映了他們對(duì)城市生活的向往。這種態(tài)度正體現(xiàn)了鄉(xiāng)村背后的弱勢(shì)和被歧視地位。
小說(shuō)《百煉成鋼》中,秦德貴的母親說(shuō)有很多農(nóng)村姑娘都愿意嫁給城市工人。小說(shuō)《山鄉(xiāng)巨變》中,秋絲瓜張貴秋因?yàn)樽约旱拿妹闷帘銛x掇妹妹離婚嫁到城里;盛學(xué)文初中畢業(yè)后一心想讀高中,離開(kāi)農(nóng)村去城里工作;盛淑君也想去城里當(dāng)工人。
和其他進(jìn)城的女青年不同的是,《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徐改霞進(jìn)城不僅僅是為了尋求一份好工作,而且還有尋求人格獨(dú)立的意味。改霞一開(kāi)始擔(dān)心自己年齡大,上不了中學(xué),認(rèn)為不如趁早參加農(nóng)業(yè),搞互助合作,而對(duì)梁生寶的愛(ài)慕更加堅(jiān)定了自己的想法。梁生寶對(duì)她的誤解及冷遇讓她下定決心考工廠。考工廠的人特別多,不免讓改霞產(chǎn)生一種自卑心理,擔(dān)心自己考不上。對(duì)梁生寶的依戀讓她很惶惑,王亞梅的教育讓她順勢(shì)決定回到農(nóng)村和梁生寶一起搞合作化。回來(lái)后,改霞決心和生寶過(guò)了。她決定主動(dòng)追求生寶,但生寶怕兩人的情感影響互助組工作,讓改霞等到秋后再說(shuō)。這讓她重新思考二人的關(guān)系,最后去了北京長(zhǎng)辛店鐵路機(jī)車廠當(dāng)鑄工學(xué)徒。改霞之所以進(jìn)城,不是因?yàn)樗檩p怕重、愛(ài)慕虛榮,而是要尋求獨(dú)立人格。改霞擔(dān)心結(jié)婚之后,自己會(huì)成為一個(gè)做飯、生孩子的家庭主婦,這樣的生活是個(gè)性要強(qiáng)的她所不希望的。改霞熱心社會(huì)活動(dòng),不甘愿當(dāng)一個(gè)莊稼院的好媳婦,所以她毅然離開(kāi)了她熱愛(ài)的農(nóng)村,離開(kāi)了她依然掛念的生寶。
建國(guó)初期,農(nóng)村正在進(jìn)行轟轟烈烈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dòng),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dòng)的目的就是為了改變?cè)谥袊?guó)農(nóng)村存在了兩千多年的一家一戶的勞動(dòng)方式,消除小私有者的所有制形式,代之以集體勞動(dòng)的形式,使農(nóng)民取得與工人相同的勞動(dòng)形式。如果合作化運(yùn)動(dòng)建立在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展、機(jī)械化水平高的情況下,是可以提高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力的。問(wèn)題是當(dāng)時(shí)農(nóng)村的機(jī)械化水平不高,農(nóng)民們還沒(méi)有達(dá)到集體勞動(dòng)的覺(jué)悟,合作化運(yùn)動(dòng)難以達(dá)到預(yù)期的目的。在農(nóng)業(yè)社里,農(nóng)民們雖然是集體勞動(dòng),但勞動(dòng)內(nèi)容沒(méi)有根本的改變,還是以繁重的體力勞動(dòng)為主,必須消耗大量的體力,這讓很多社員吃不消。“另外,在積肥、插秧、收割等重要農(nóng)事活動(dòng)中,因?yàn)橐c單干戶比賽,也因?yàn)橐s時(shí)間趕農(nóng)時(shí),農(nóng)業(yè)社成員被要求不管刮風(fēng)下雨都要沒(méi)日沒(méi)夜地大干苦干,以至連年輕力壯的民兵也普遍感到睡眠不足。”[4]在合作化初期的新鮮勁頭過(guò)去之后,社員們的積極性大打折扣。為了保持社員們的積極性,農(nóng)業(yè)社實(shí)行高度組織化的管理體制與以勞動(dòng)競(jìng)賽為主要方式的激勵(lì)機(jī)制,這讓社員們不但感到疲乏勞累,而且感到不自由。“日常生活充滿了革命意味,已淪為殘酷而又刻板的范式。不存在什么人類普通的美的標(biāo)準(zhǔn),只有帶有階級(jí)性烙印的美的理解,‘無(wú)產(chǎn)階級(jí)或勞動(dòng)階層的美才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美,’革命把美學(xué)邊緣化的同時(shí),實(shí)際上把審美從日常生活中給驅(qū)逐了。”[5]城市工人為了完成國(guó)家訂購(gòu)任務(wù),也是沒(méi)日沒(méi)夜地加班加點(diǎn)。但他們畢竟還有工作時(shí)間的限制,下班之后,還是有相對(duì)寬松的業(yè)余時(shí)間供自己支配,他們的工資雖然不高,相對(duì)于農(nóng)民的工分畢竟還是豐厚的。他們有時(shí)間可以飯后散散步,周末逛逛公園,也有收入以便早餐喝杯豆?jié){、吃個(gè)雞蛋,周末有時(shí)間和家人在餐館吃飯,也有錢(qián)買(mǎi)幾件時(shí)髦的衣服。這是一種審美化的生活方式,這種審美化的現(xiàn)代城市生活無(wú)疑會(huì)對(duì)農(nóng)民們產(chǎn)生很大的吸引力。
二、城鄉(xiāng)敘述策略
十七年文學(xué)提出了一些值得觀察和思考的城鄉(xiāng)問(wèn)題,如“進(jìn)城”與“返鄉(xiāng)”、人物的矛盾與糾結(jié)等,這些問(wèn)題有其歷史必然性與現(xiàn)實(shí)復(fù)雜性。文本的敘述是建立在主體體驗(yàn)或者個(gè)體實(shí)踐之上,雖然說(shuō)有作家文學(xué)想象的成分,但更多可能是細(xì)節(jié)的相似或者存在,而這恰恰是文學(xué)深刻性與普遍性的形象表現(xiàn)。所以,我們觀察城鄉(xiāng)關(guān)系中的特定群體或者特定現(xiàn)象,可以認(rèn)識(shí)作家傳達(dá)出的詩(shī)學(xué)與史學(xué)的雙重意義。
在《我們夫婦之間》中,“我”是小說(shuō)的男主人公,“我”雖然有小資產(chǎn)階級(jí)生活情調(diào),但作家對(duì)“我”持明顯的肯定態(tài)度。“我”開(kāi)放、寬容、頭腦靈活、樂(lè)于接受新事物。“我”對(duì)生活的態(tài)度是:革命勝利了,應(yīng)該按照城市生活的習(xí)慣規(guī)則生活,可以在條件許可的基礎(chǔ)上適度地消費(fèi)。因而“我”想用稿費(fèi)買(mǎi)雙皮鞋、買(mǎi)一條紙煙、看一次電影、吃一次冰淇淋,閑暇時(shí)間跳跳舞。而“我”的妻卻是滿口臟話、不顧場(chǎng)合大聲嚷嚷、多管閑事,走路穿衣土氣十足。從現(xiàn)在來(lái)看,“我”的妻的行為是一個(gè)受過(guò)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思想教育的沒(méi)有多少文化的工農(nóng)干部在完全陌生的城市文化環(huán)境中的自然反應(yīng)。作者以寫(xiě)實(shí)的筆法寫(xiě)出她的種種可笑行為,就形成一種反諷的力量,同時(shí)表現(xiàn)了作者本人的城市文化意識(shí)。難怪小說(shuō)遭到了嚴(yán)厲的批判。有的文章認(rèn)為這篇小說(shuō)“從頭到尾都是玩弄她”,“是在糟蹋我們新的高貴的人民和新的生活”。“是由于作者脫離政治!在本質(zhì)上,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是一個(gè)思想問(wèn)題,假如發(fā)展下去,也就會(huì)達(dá)到政治問(wèn)題。”[6]批判者認(rèn)為作者的政治傾向出了問(wèn)題,顯然是夸大其辭。不過(guò),當(dāng)時(shí)的紅色批評(píng)家們的確看到了“我”不同于主流小說(shuō)中塑造的與工農(nóng)群眾結(jié)合的知識(shí)分子。
最能表現(xiàn)農(nóng)村知識(shí)青年進(jìn)城艱難、返鄉(xiāng)痛苦的是康濯的小說(shuō)《春種秋收》。這篇小說(shuō)是新郎新娘所講、別人補(bǔ)充的、作者認(rèn)為是絕對(duì)真實(shí)的一個(gè)故事中的故事。和當(dāng)時(shí)的其它農(nóng)村題材小說(shuō)一樣,康濯所贊頌的,也是基于服務(wù)農(nóng)村的新時(shí)代農(nóng)村青年獻(xiàn)身農(nóng)村的美好情操。小說(shuō)講述的是一個(gè)“向城—進(jìn)城—返鄉(xiāng)”的故事。農(nóng)村姑娘劉玉翠小學(xué)畢業(yè)后,沒(méi)有考上中學(xué),只好回到農(nóng)村,她不甘心留在農(nóng)村,不得不通過(guò)找對(duì)象的方式進(jìn)城,但沒(méi)有成功。在一個(gè)書(shū)記的幫助和一個(gè)農(nóng)村先進(jìn)青年的影響下,她回到農(nóng)村積極參加農(nóng)村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但是這篇小說(shuō)的主體卻展示了農(nóng)村青年劉玉翠向城、進(jìn)城、返鄉(xiāng)的經(jīng)歷,展現(xiàn)了劉玉翠對(duì)城市的向往、進(jìn)城不得的痛苦以及返鄉(xiāng)的艱難,表現(xiàn)了五十年代農(nóng)村知識(shí)青年的理想與愿望。劉玉翠上學(xué)期間,當(dāng)過(guò)團(tuán)干部,覺(jué)得自己知識(shí)多,長(zhǎng)相好。她對(duì)城市的向往很執(zhí)著,城市里的工人婦女、電燈電話、高樓大廈、花襯衫、洋襪子、婦女的卷發(fā)等對(duì)她充滿了無(wú)盡的誘惑。她住的小山村非常偏僻,野獸出沒(méi),是個(gè)荒山野洼。農(nóng)民雖然翻了身,可是仍然被拴在二畝硬土上,沒(méi)有俱樂(lè)部,趕個(gè)會(huì)、看個(gè)戲,出門(mén)得走二十里地。她回到村里,好比住進(jìn)了監(jiān)牢,見(jiàn)了人怕笑話,只好躲在家里佯裝看書(shū),可是一個(gè)字也看不下去,上地里勞動(dòng)又心不在焉,感到非常無(wú)聊。
小說(shuō)真實(shí)地描寫(xiě)了劉玉翠在農(nóng)村的尷尬,寫(xiě)出了既向往現(xiàn)代城市生活可是又找不到出路的農(nóng)村青年的窘態(tài)與痛苦。對(duì)于農(nóng)村青年來(lái)說(shuō),考不上學(xué),就只好靠找個(gè)城里對(duì)象來(lái)進(jìn)城,但是劉玉翠碰過(guò)四五個(gè)縣區(qū)干部都沒(méi)有談成。農(nóng)村不但物質(zhì)生活貧乏,而且精神生活也非常單調(diào),滿足不了劉玉翠想趕會(huì)、看戲等愿望。而這是一種正常的消費(fèi)。“消費(fèi)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種享受功能,而是一種生產(chǎn)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質(zhì)生產(chǎn)一樣并非一種個(gè)體功能,而是即時(shí)且全面的集體功能。”[7]因而,劉玉翠想進(jìn)城是很正常的,但是她的這種想法卻被當(dāng)?shù)剞r(nóng)村人們冠以資產(chǎn)階級(jí)的享受思想。而“享受會(huì)把消費(fèi)規(guī)定為自為的、自主的和終極性的。”[7]她的思想和行為遭到了同村人的鄙視與嘲諷。在村中人看來(lái),她不配享受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瞧不起婦女,并且風(fēng)來(lái)雨去地造她的謠,糾纏得她情緒不高。小說(shuō)用細(xì)膩的筆觸描寫(xiě)了劉玉翠進(jìn)城不得的痛苦,“‘他若是晚一點(diǎn)去省城,’玉翠傷心地想著,‘等跟我談好了,再讓我一塊同去,該多好啊……’接著又閃跳出了自己的前途大事:‘城市!學(xué)習(xí)!建設(shè)……莫非就注定了要一輩子困死在這個(gè)老山溝里么?’”“這一夜,劉玉翠根本沒(méi)睡覺(jué)。熬到天剛露明的時(shí)候,猛一下蹬開(kāi)被子,爬了起來(lái),扛上镢頭就走。她好像發(fā)了個(gè)狠——倒要看看周昌林是不是還會(huì)在坡上的地里等她。”農(nóng)村那幾個(gè)青年她看不上,團(tuán)縣委副書(shū)記看不上她,這讓她的自尊心大受打擊,因此她橫下心來(lái)接受周昌林的愛(ài)。這是一個(gè)艱難的抉擇,也是一個(gè)痛苦的抉擇。
這是小說(shuō)中最精彩、最生動(dòng)的一處心理描寫(xiě),寫(xiě)出了一個(gè)頗有點(diǎn)虛榮的農(nóng)村女青年在自尊受到打擊后的真實(shí)反應(yīng)。她美麗、純潔、有文化,不甘于農(nóng)村的艱苦生活,追求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這是一個(gè)想走出農(nóng)村卻沒(méi)有找到辦法的有代表性的五十年代的農(nóng)村青年,她的人生道路展示了一個(gè)向往現(xiàn)代城市生活卻又不得不留在農(nóng)村的矛盾與痛苦。小說(shuō)展示了她們不安而又躁動(dòng)的靈魂。
《山鄉(xiāng)巨變》中的盛學(xué)文是一個(gè)初中生,是盛佑亭的二兒子,他不但勤謹(jǐn)而且功課也好,很有希望考上高中;他也希望自己能上高中擺脫農(nóng)村的生活。盛學(xué)文、張小柳、劉玉翠等人物形象迥然不同于工農(nóng)兵文學(xué)中的社會(huì)主義新人形象。他們對(duì)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缺乏熱情,他們不能與廣大農(nóng)民打成一片,面對(duì)艱苦的生活條件,他們動(dòng)搖、苦悶、彷徨。這種人物塑造具有較多的人性內(nèi)涵,呈現(xiàn)出立體化的豐姿。無(wú)論是張小柳、劉玉翠、盛學(xué)文還是向往城市生活的人大都是上過(guò)學(xué)的農(nóng)村知識(shí)分子,他們見(jiàn)過(guò)世面,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把逃離農(nóng)村、向往城市的農(nóng)村青年設(shè)置為讀過(guò)書(shū)的知識(shí)分子,這既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反映,也說(shuō)明了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知識(shí)分子的懷疑心理。學(xué)校在這里充當(dāng)了連接城市與農(nóng)村的橋梁,小說(shuō)中的人物都是通過(guò)學(xué)校了解到了現(xiàn)代城市文明的美好,學(xué)校不僅為他們帶來(lái)了知識(shí),而且?guī)?lái)了想出去的沖動(dòng)。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學(xué)校是由農(nóng)村通往城市的階梯,清閑的工作、豐富的生活、優(yōu)越的地位甚至美麗的愛(ài)情,都因?yàn)閷W(xué)校而變得具體可感。
小說(shuō)通過(guò)人物“向城—進(jìn)城—返鄉(xiāng)”的經(jīng)歷提出了城鄉(xiāng)關(guān)系這一問(wèn)題。城鄉(xiāng)差距是一個(gè)歷史性的問(wèn)題,建國(guó)后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又加劇了城鄉(xiāng)差距。“只要城鄉(xiāng)差距還存在,城市化進(jìn)程仍在進(jìn)行,城鄉(xiāng)一體化沒(méi)有最終完成,不管是以顯性題材或隱性背景出現(xiàn),城鄉(xiāng)關(guān)系依然是當(dāng)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繞不開(kāi)的最大現(xiàn)實(shí)。”[8]溫鐵軍認(rèn)為:“國(guó)家工業(yè)化的資本積累是個(gè)特殊的時(shí)代。這個(gè)時(shí)代給我們留下的,不僅是數(shù)以萬(wàn)計(jì)的,以全民所有為名、部門(mén)壟斷的國(guó)家資產(chǎn),供后人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留下了一個(gè)城鄉(xiāng)分割、對(duì)立矛盾的二元體制。”[9]五十年代初期,國(guó)家不但把大批資金投向城市,而且把農(nóng)業(yè)積累的資金也投向城市,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農(nóng)村的交通、通訊、自來(lái)水、農(nóng)田水利設(shè)施嚴(yán)重不足,文化教育、衛(wèi)生體育等社會(huì)公共事業(yè)發(fā)展滯后,使得農(nóng)村屈服于城市,造成了城市與農(nóng)村的對(duì)立。既然城市與農(nóng)村存在較大的差距,那么就會(huì)產(chǎn)生對(duì)城市向往的人們,因?yàn)椤爱?dāng)社會(huì)生產(chǎn)出城市化的空間形態(tài)時(shí),同時(shí)也就相應(yīng)生產(chǎn)出人對(duì)城市空間的欲望表達(dá)形式。”[10]城鄉(xiāng)問(wèn)題的客觀存在,引起了文學(xué)想象中的一次又一次的“進(jìn)城”與“返鄉(xiāng)”的書(shū)寫(xiě)。不過(guò),“十七年”文學(xué)的城鄉(xiāng)書(shū)寫(xiě)還是遵循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要求,通過(guò)對(duì)人物行為的褒貶,教育農(nóng)村青年:農(nóng)村是一個(gè)大有可為的天地,只有扎根農(nóng)村、腳踏實(shí)地,才能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價(jià)值。通過(guò)“進(jìn)城”與“返鄉(xiāng)”的書(shū)寫(xiě),十七年文學(xué)成功地把農(nóng)村想象成農(nóng)村青年的美好家園,撫慰了當(dāng)時(shí)人們?cè)诔青l(xiāng)之間的巨大情感落差。
三、城鄉(xiāng)沖突的想象性解決
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城鄉(xiāng)關(guān)系是一個(gè)非常敏感的話題,因?yàn)橐坏┌盐詹缓茫陀锌赡芤莩鲋髁饕庾R(shí)形態(tài)的要求。《我們夫婦之間》之所以遭到嚴(yán)厲批判,最根本的一點(diǎn)是它表現(xiàn)了農(nóng)村文明被城市文明改造的事實(shí),委婉地表現(xiàn)了鄉(xiāng)村文明的弱勢(shì)地位。正如董健所言:“以農(nóng)村改造城市還是以城市改造農(nóng)村,這在當(dāng)時(shí)是大是大非的問(wèn)題。”[11]《創(chuàng)業(yè)史》寫(xiě)出了改霞一波三折的進(jìn)城故事,也沒(méi)有對(duì)改霞的進(jìn)城進(jìn)行批判,原因是作者熱情地謳歌了農(nóng)村正在進(jìn)行的社會(huì)主義合作化運(yùn)動(dòng)。在作者的描述中,農(nóng)村同樣也是青年人創(chuàng)業(yè)、實(shí)現(xiàn)自己價(jià)值的充滿希望的田野,柳青沒(méi)有把城鄉(xiāng)置于二元對(duì)立的位置上,沒(méi)有寫(xiě)出城市對(duì)農(nóng)村的改造與擠壓,這篇小說(shuō)與《我們夫婦之間》的命運(yùn)也截然不同。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應(yīng)該反映出農(nóng)村社會(huì)主義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dòng)熱火朝天的場(chǎng)面,塑造出腳踏實(shí)地、克己奉公、銳意進(jìn)取帶領(lǐng)農(nóng)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新人形象,表現(xiàn)出廣大農(nóng)民走社會(huì)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與主動(dòng)性,應(yīng)當(dāng)反映出城市與鄉(xiāng)村互相支援、互相合作的場(chǎng)景來(lái)。因而,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除小說(shuō)《我們夫婦之間》外,其它書(shū)寫(xiě)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小說(shuō)都沒(méi)有把城鄉(xiāng)關(guān)系作為小說(shuō)的顯性主題來(lái)表現(xiàn),而是作為一個(gè)隱性問(wèn)題來(lái)敘述。《春種秋收》的主題是通過(guò)講述農(nóng)村發(fā)生的新鮮事來(lái)歌頌農(nóng)村的光明前途,歌頌?zāi)切釔?ài)農(nóng)村、安心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農(nóng)村青年的優(yōu)秀品質(zhì)。《水滴石穿》表現(xiàn)的是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dòng)的偉大勝利。這些小說(shuō)雖然沒(méi)有把城鄉(xiāng)關(guān)系作為顯性主題來(lái)表現(xiàn),可是仍然留下了難以彌合的文本裂縫,讓讀者體會(huì)到城鄉(xiāng)問(wèn)題的嚴(yán)重。
城鄉(xiāng)對(duì)立有歷史原因,而新中國(guó)的工業(yè)化道路更加劇了城鄉(xiāng)對(duì)立,城鄉(xiāng)對(duì)立問(wèn)題是一個(gè)嚴(yán)峻的問(wèn)題。如何在文學(xué)中敘述這一問(wèn)題呢?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反映城鄉(xiāng)矛盾的小說(shuō)都以愛(ài)情的形式解決了城鄉(xiāng)沖突的問(wèn)題,以那些不安分的農(nóng)村青年找到理想愛(ài)情的方式來(lái)彌合城鄉(xiāng)對(duì)立。張小柳返回后依然得到了楊吉吉的諒解;劉玉翠贏得了鄉(xiāng)村優(yōu)秀青年周昌林的愛(ài)情;清溪鄉(xiāng)群眾也幫助盛學(xué)文找到了幸福的愛(ài)情;馬有翼贏得了王玉梅的愛(ài);范靈芝與王玉生成了幸福的一對(duì)。甜美的愛(ài)情稀釋了農(nóng)村枯燥的生活與勞累的體力勞動(dòng),增添了農(nóng)村生活的情趣。然而,這種解決方式只是暫時(shí)撫慰了農(nóng)村青年那顆躁動(dòng)不安的心靈,一旦條件發(fā)生變化,劉玉翠們、張小柳們的心靈將會(huì)再次蘇醒。小說(shuō)雖然以愛(ài)情的甜蜜稀釋了農(nóng)村青年城市夢(mèng)破滅的痛苦,但小說(shuō)還是留下了難以彌合的裂縫并暴露了城鄉(xiāng)問(wèn)題的嚴(yán)重性。
農(nóng)村面臨知識(shí)青年逃離的境地,更為重要的是,它從側(cè)面反映出農(nóng)業(yè)合作化改造的凝聚力問(wèn)題。張小柳的進(jìn)城引起了村支書(shū)以及申玉枝的關(guān)注,張德升對(duì)申玉枝說(shuō):“聽(tīng)永德說(shuō),有個(gè)什么學(xué)生老跟她捎信,可別是她……咳咳,咱們這頭一年剛辦的農(nóng)業(yè)社可不能留不住人哪!咱們?cè)僮ゾo說(shuō)服她和吉吉,該拉扯著他倆結(jié)了婚,才穩(wěn)妥呢!你說(shuō)是么?”農(nóng)村人才的出走,不僅使農(nóng)業(yè)社面臨勞力短缺的問(wèn)題,而且還關(guān)系到社會(huì)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問(wèn)題。為了回避城鄉(xiāng)矛盾,作家們?cè)O(shè)置了這類情節(jié):農(nóng)業(yè)社為鄉(xiāng)村知識(shí)分子提供了較清閑的工作。如馬有翼和范靈芝當(dāng)了村里的掃盲老師,張小柳在村里當(dāng)會(huì)計(jì),劉玉翠在村里主要干技術(shù)工作。為了讓農(nóng)村知識(shí)青年返回農(nóng)村,作家們?cè)O(shè)置了來(lái)自城市的非硬性的藩籬,目的是讓這些知識(shí)青年自己的失敗阻斷他們進(jìn)城的道路。如張小柳兩次考試失敗,她不得不回來(lái);劉玉翠也是因?yàn)闆](méi)有考上中學(xué),回到農(nóng)村;盛學(xué)文功課雖好,但他父親不再支持他考學(xué),他不得不回來(lái)。小說(shuō)并沒(méi)有設(shè)置來(lái)自城市本身的障礙,這樣的敘述緩解了城鄉(xiāng)的對(duì)立與矛盾。實(shí)際上,由于這些農(nóng)村知識(shí)青年所在學(xué)校的基礎(chǔ)條件、師資力量、學(xué)習(xí)氣氛與城市學(xué)校不可同日而語(yǔ),而錄取分?jǐn)?shù)相同,其中蘊(yùn)涵著深刻的教育不公,很多農(nóng)村青年在考試中落榜是必然的。
建國(guó)之初,城鄉(xiāng)雖然差距明顯,但是城市并沒(méi)有呈現(xiàn)出當(dāng)下打工文學(xué)中那種冰冷、冷漠的印象。“城市所需的豪華經(jīng)濟(jì)想象力于此刻依舊是匱乏的,故此,僅在空間的外在性上,城市的形象尚不足以產(chǎn)生令農(nóng)村不敢奢望的距離。恰恰相反,前者倒是為后者預(yù)留了一定的夢(mèng)想空間。也就是說(shuō),對(duì)于農(nóng)村而言,城市并非是不可親近的。”[12]因?yàn)楫?dāng)時(shí)城市工廠缺乏工人,通過(guò)考學(xué)或者城市工廠招工,可以吸收一部分文化水平較高的農(nóng)民進(jìn)入到城市,進(jìn)入到工廠,其它部門(mén)的農(nóng)民青年只要專心學(xué)習(xí)技術(shù),同樣能成為城市的一員。例如《百煉成鋼》中的秦德貴本來(lái)是一個(gè)農(nóng)民,由于自己刻苦鉆研技術(shù)、大公無(wú)私,成為優(yōu)秀工人。而當(dāng)下的打工文學(xué)片面渲染城市的冰冷、冷漠,描寫(xiě)農(nóng)民工與城市文明的不相容,夸大了城市文明與農(nóng)村文明的疏離。
我們不否認(rèn)農(nóng)民工在城市環(huán)境中面臨諸多的不平等,但這些不平等并不是城市或者農(nóng)村一方的責(zé)任,也不是市民與農(nóng)民之間有天然的鴻溝,更不是現(xiàn)代文明與傳統(tǒng)文明難以融合,而是中國(guó)在現(xiàn)代化過(guò)程中兩種文明之間必然的交融過(guò)程。在現(xiàn)實(shí)中,我們看到,很多農(nóng)民工逐漸融入城市,很多農(nóng)民工逐漸獲得市民身份,而城市也在逐漸改變對(duì)農(nóng)民工的態(tài)度。在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定位問(wèn)題上,十七年文學(xué)為當(dāng)下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書(shū)寫(xiě)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十七年”文學(xué)通過(guò)農(nóng)村青年進(jìn)城的軌跡提出了農(nóng)村青年的出路問(wèn)題,應(yīng)該說(shuō),農(nóng)村進(jìn)行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的確可以吸納很多知識(shí)分子,農(nóng)村知識(shí)分子也能在農(nóng)村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價(jià)值。“十七年”文學(xué)塑造出了很多扎根農(nóng)村、踏實(shí)苦干、帶領(lǐng)農(nóng)民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農(nóng)村的社會(huì)主義新農(nóng)民形象,如《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梁生寶、《三里灣》中的王金生、《山鄉(xiāng)巨變》中的劉雨生、《水滴石穿》中的申玉枝等。不能忽視的情況是,在大多數(shù)農(nóng)村,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知識(shí)分子在農(nóng)村并沒(méi)有發(fā)揮出應(yīng)有價(jià)值,反而被作為“干啥啥不行”的紅專典型遭到嘲笑。我們?cè)谛≌f(shuō)中看到,張小柳、劉玉翠、徐改霞、馬有翼等農(nóng)村青年就經(jīng)常受到農(nóng)民的嗤笑,這也是他們要離開(kāi)農(nóng)村的原因之一。“事實(shí)將會(huì)證明,劉玉翠們絕非一個(gè)偶然和短暫的現(xiàn)象。這一事實(shí)似乎也在提示我們,當(dāng)一個(gè)農(nóng)民對(duì)于土地不再秉持著那種同歷史與命運(yùn)息息相關(guān)的本真情懷時(shí),他極有可能轉(zhuǎn)變成的將不是梁生寶或宋東山,而是劉玉翠。”[13]
四、結(jié)語(yǔ)
建國(guó)之初,農(nóng)民不但有發(fā)家致富的夢(mèng)想,接觸了外界新思想的農(nóng)村知識(shí)分子也有了更多的理想與愿望,而農(nóng)村承載不了農(nóng)民日益豐富的生存和生活理想。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農(nóng)村知識(shí)分子以相同的結(jié)局回到了農(nóng)村,城鄉(xiāng)矛盾得到了延宕、和解。“十七年”文學(xué)反映了農(nóng)村與農(nóng)民的矛盾,也反映了城鄉(xiāng)對(duì)立關(guān)系,提出了初步的解決方案,但這可能是一種想象性的解決方案。“社會(huì)主義的城鄉(xiāng)敘事,并不是以城市與鄉(xiāng)村在現(xiàn)實(shí)中的對(duì)立為前提,在文化上所造成的想象性補(bǔ)充關(guān)系;相反,社會(huì)主義的城鄉(xiāng)敘事參與到打破城鄉(xiāng)對(duì)立的實(shí)踐中去了。”[14]對(duì)于那些向往城市而又不得不留在農(nóng)村的農(nóng)村青年來(lái)說(shuō),社會(huì)主義的城鄉(xiāng)敘事無(wú)疑給他們以情感上的慰藉、心靈上的撫慰,可以引導(dǎo)他們?cè)谵r(nóng)村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價(jià)值。十七年文學(xué)在這樣的特定歷史時(shí)期,看似相對(duì)簡(jiǎn)單的文本更能凸顯一定的個(gè)人想象與文學(xué)想象,使文本具備了內(nèi)涵的豐富性和無(wú)限的可能性,在國(guó)家意識(shí)與國(guó)家意志下具有特定的思考。同時(shí),在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長(zhǎng)期存在的情況下,“十七年”文學(xué)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書(shū)寫(xiě)無(wú)疑會(huì)給當(dāng)下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書(shū)寫(xiě)以及城鄉(xiāng)問(wèn)題的探討提供有價(jià)值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