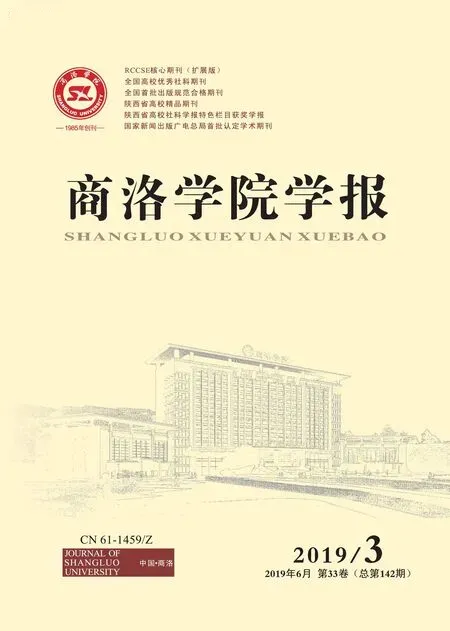族長的形象自覺及其文化意義
邰科祥,李繼高
(1.西安工業(yè)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陜西西安 716000;2.商洛學(xué)院 學(xué)報(bào)編輯部,陜西商洛 726000)
在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中,曾經(jīng)有一類人物形象讓讀者記憶猶新,那就是地主。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前,作家筆下的韓老六、杜善人、錢文貴、江世榮、馮蘭池、黃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等兇惡的地主形象早就固化在一代人的頭腦中。所以,當(dāng)《白鹿原》中的白嘉軒出現(xiàn)的時(shí)候,很多人不由得驚呼:“好地主”或者“新地主”出現(xiàn)了。
早在《白鹿原》出版的1993年,評論家蔡葵說:“作品的新,表現(xiàn)在寫了兩個(gè)地主,作為主人公、正面人物,在新文學(xué)中很少見,這種全新的地主形象,我們能接受,有征服力。”[1]431曾鎮(zhèn)南也說:“作品主要寫了兩戶地主和他的兒女們的命運(yùn),表面上消解了階級(jí)斗爭,實(shí)際上有更深刻的階級(jí)對抗”。[1]435直到2008年,還有評論者林覺民以《好一個(gè)“大寫”的地主——試析〈白鹿原〉中白嘉軒形象的創(chuàng)新意義》為題來表述白嘉軒的形象。此文說:“白嘉軒的形象顛覆了長期以來我們在文藝作品中司空見慣的‘貪婪、吝嗇、兇殘、狠毒、淫惡’的地主形象,而給讀者一種耳目一新的閱讀感受;同時(shí),白嘉軒還以其獨(dú)特的地主身份和經(jīng)歷,引發(fā)當(dāng)代讀者對地主這一特殊階層的重新審視和評價(jià)。”[2]
然而,筆者在2009年采訪作者陳忠實(shí)時(shí),他卻這樣回答:很多評論者都提到白嘉軒是一個(gè)好地主、新地主形象。如果放在文學(xué)史上地主類人物的形象畫廊中去看,他的確與以往的形象大為不同。但是,實(shí)際上一開始我根本就沒有這個(gè)意識(shí),我沒有想著去塑造一個(gè)新地主的形象,更沒有想著把白嘉軒與南霸天、黃世仁等有意區(qū)別開來[3]。
也就是說,在作者自覺的創(chuàng)意中,“好地主”或“新地主”的概念就不存在,他根本不想從這個(gè)視角去塑造他筆下的主要人物。“所以,我沒有自覺地反叛以往地主類形象的寫作意識(shí),而且在我的觀念里,我并不否認(rèn)現(xiàn)實(shí)中真有黃世仁之類的地主。我只是不想用以往的階級(jí)斗爭的觀念去描寫人物,如果非要說有反叛的話,這一點(diǎn)可能是明確的。我在80年代中期接受了一個(gè)文藝?yán)碚摷业奈幕睦斫Y(jié)構(gòu)學(xué)說,我是用這個(gè)理論來塑造人物的。”[3]
一
陳忠實(shí)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他塑造白嘉軒這樣的人物,是摒棄了以往的階級(jí)斗爭觀念,而用他所認(rèn)同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學(xué)說作為理論支撐。而且,他也著意選擇了一個(gè)新的字眼或概念來對他筆下的人物給予命名,這個(gè)字眼就是“族長”。
“我沒想著寫一個(gè)地主,而是要寫一個(gè)族長。”[3]當(dāng)我從他口中聽到這個(gè)名詞時(shí)有點(diǎn)意外,但更多的是困惑。在我最初的期待中,希望他承認(rèn)白嘉軒就是一個(gè)好地主或新地主的形象。然而,陳忠實(shí)不但明確否認(rèn)其具有這個(gè)意識(shí),而且還要換一個(gè)名詞,我在內(nèi)心中,當(dāng)時(shí)覺得他有點(diǎn)故意標(biāo)新立異,或者說玩文字游戲。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識(shí)到,族長的稱謂有其非同尋常的意義。
族長與地主根本不能劃等號(hào)。它與經(jīng)濟(jì)實(shí)力有關(guān)也無關(guān),不是誰地多業(yè)大就能成為族長,除了地多,還要有其他方面的資質(zhì)。正如作品中的朱先生提醒白嘉軒說:“房是招牌地是累,攢下銀錢是催命鬼。”擁有過多的土地,成為地主,早已不是實(shí)踐朱先生思想之白嘉軒的目標(biāo)。《白鹿原》中的鹿子霖從土地的擁有量上說不弱于白嘉軒,甚至幾度都超過他,而且從本心里,鹿子霖也特別想做這個(gè)族長,但事實(shí)是他就是做不成。用陳忠實(shí)的話說:“也不是誰都可以做族長,一般來說族長不會(huì)是窮人,當(dāng)然也不一定是大地主,常常是我們稱作財(cái)東的人為多。”[3]
族長不是一級(jí)行政官吏,不是政治身份的標(biāo)志,他沒有行政權(quán)。他們沒有國家賦予的行政權(quán),他們主要依靠一個(gè)宗族自己制定、延續(xù)的鄉(xiāng)約來規(guī)范和約束族中人的行為,這個(gè)鄉(xiāng)約其實(shí)是儒家思想的通俗化[3]。所以,族長其實(shí)就是一個(gè)文化符號(hào),是民間鄉(xiāng)約、秩序的代表,是族眾自發(fā)推舉或擁戴的精神領(lǐng)袖。他們在鄉(xiāng)村的地位凌駕于同層次政治與經(jīng)濟(jì)人物之上。在鄉(xiāng)村最有權(quán)威的人是宗族勢力,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族長[3]。
族長是一個(gè)歷史概念,它具有鮮明的時(shí)代印記。在封建制度延續(xù)的時(shí)代,它是一直通用并具有實(shí)際功能的民間自治領(lǐng)袖。但在民國之后就逐漸被淡化,直到建國以后就再也不復(fù)存在。地主的形象雖與之有一定重合,但地主這個(gè)階級(jí)概念的出現(xiàn)已到了20世紀(jì)20年代之后。所以,要描述新舊交替時(shí)代區(qū)間的這類人物就只能用族長的稱謂。
另一方面,對《白鹿原》主旨的設(shè)計(jì)同樣呼喚著族長的形象。陳忠實(shí)說:“我想得最多的是,處于封建制度解體、民國建立這種改朝換代的特殊區(qū)間的中國人到底做了什么?我們傳統(tǒng)人格中一個(gè)完整的人是什么樣的?”[3]
在這個(gè)改朝換代的特殊區(qū)間的中堅(jiān)人物就是族長,正是他們承襲著老祖宗的文化基因,艱難地維持著家族的穩(wěn)定。同樣,傳統(tǒng)人格中完整的、理想的代表仍然是族長。所以,《白鹿原》傾其心力塑造了白嘉軒的形象。
在陳忠實(shí)看來,只有族長的形象才能夠完整地顯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者價(jià)值觀對個(gè)體性格的塑造過程與結(jié)果。白嘉軒是傳統(tǒng)文化的踐行者,儒家思想的精華與糟粕在他身上完整地得到體現(xiàn)。他做到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行。他做事光明磊落,從不偷偷摸摸;他為人言出必行,說到做到;他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對兒子犯錯(cuò)從不護(hù)短,對長工鹿三敬重如兄;他嫉惡如仇,見善必行,連他的腰也總是挺得很直,讓黑娃一輩子都感到敬畏。可以說,做一個(gè)君子似的好人和洞達(dá)世事之人是白嘉軒的理想與信念,當(dāng)然也是小說作者陳忠實(shí)的希冀與追求。
白嘉軒的君子之風(fēng)無需多言,但對他圓融通透的行事準(zhǔn)則還要多提幾句。眾所周知,朱先生是《白鹿原》這部小說的靈魂,更是白嘉軒的人生導(dǎo)師。他以大儒的睿智,同時(shí)也以兄長的豐富閱歷和人生體悟指點(diǎn)白嘉軒:“房是招牌地是累,攢下銀錢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養(yǎng)頭黃牛慢慢搞。”他傳遞的是儒家中庸思想的精髓,所謂:不過亦不能不及,不貪或知足常樂是幸福的真諦。
當(dāng)時(shí),處于盛年的白嘉軒還想發(fā)家致富,振興家族,所以似乎不愿接受這種有度發(fā)展,見好就收的提醒。他更沒有充分意識(shí)到這句話的文化分量,直到他進(jìn)入暮年方逐漸領(lǐng)悟。他勸做了縣長的兒子白孝文要有收斂,不要張揚(yáng)。尤其是小說結(jié)尾的描寫既展現(xiàn)了白嘉軒經(jīng)歷了氣涌頭頂、血蒙雙眼的巨大刺激后對人生的頓悟過程,也曲折傳達(dá)出作家陳忠實(shí)的某種價(jià)值象征——世事似應(yīng)糊涂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白嘉軒重新出現(xiàn)在白鹿村村巷里,鼻梁上架起了一副眼鏡。這是祖?zhèn)鞯囊桓彼^眼鏡,兩條黃銅硬腿兒,用一根黑色絲帶兒套在頭頂,以防止掉下來碎了。白嘉軒不是鼓不起往昔里強(qiáng)盛凜然的氣勢,而是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尤其是作為白縣長的父親,應(yīng)該表現(xiàn)出一種善居鄉(xiāng)里的偉大謙虛來,這是他躺在炕上養(yǎng)息眼傷的一月里反反復(fù)復(fù)反思的最終結(jié)果。微顯茶色的鏡片保護(hù)著右邊的好眼,也遮掩著左邊被冷先生的刀子挖掉了眼球的瞎眼,左眼已經(jīng)凹陷成一個(gè)丑陋的坑洼。他的氣色滋潤柔和,臉上的皮膚和所有器官不再繃緊,全都現(xiàn)出世事洞達(dá)者的平和與超脫,驟然增多的白發(fā)和那副眼鏡更添加了哲人的氣度。他自己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拉著黃牛到原坡上去放青,站在坡坎上久久凝視遠(yuǎn)處暮靄中南山的峰巒。
總之,儒家思想的精髓及其價(jià)值觀念主導(dǎo)著白嘉軒一生的行止。由此可見,陳忠實(shí)有意區(qū)分“地主”和“族長”的人物稱謂顯然不是簡單的用詞之別,而是蘊(yùn)含了他自覺的思考。
二
族長形象的塑造盡管是對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人物畫廊的一個(gè)嶄新貢獻(xiàn),但它的意義卻不限于此,我們還可從更廣泛的背景上加以思考。
首先,族長的形象塑造有助于揭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白鹿原》中的族長不能單單理解為白鹿兩族的首領(lǐng),實(shí)際上,在作者的思考中,其也是中華民族世代脊梁的代表。陳忠實(shí)顯然不是講述一個(gè)家族的故事,而是反思整個(gè)中華民族延續(xù)幾千年而不衰落的原因。為什么作為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華民族,其歷史唯一沒有間斷,就是依靠著像族長這樣的精英和脊梁才得以持續(xù)。所以,白鹿家族是中華民族的縮寫,白鹿原的族長也是中華民族世代英雄的化身。
陳忠實(shí)還特別指出,延續(xù)幾千年的傳統(tǒng)文化中盡管有腐朽的基因,但主要是優(yōu)良基因在發(fā)揮著作用。“我是有一個(gè)很清醒的理念:那就是如果傳統(tǒng)人格、文化全是腐爛的、糟朽的,在鄉(xiāng)村具有重大影響的人都是黃世仁、劉文彩,那封建社會(huì)還能延續(xù)兩千年嗎?雖然有些朝代的皇帝昏庸無能,但總體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沒有改變,決不能簡單的用腐朽一詞來概括。王朝更替,人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不變。準(zhǔn)確地說,支撐我們民族延續(xù)幾千年的文化因素是最優(yōu)良的基因與最腐朽的基因的結(jié)合物。”[3]
建國以后,受階級(jí)論觀點(diǎn)的影響,封建社會(huì)被視為腐朽透頂?shù)闹贫龋瑳]有任何正向的價(jià)值可言,這種簡單的文化虛無主義導(dǎo)致了較長時(shí)間中國人對自己歷史傳統(tǒng)的嚴(yán)重誤解甚至全盤否定,實(shí)際上也給自己造成一個(gè)難以自圓其說的巨大困惑。按照一般的邏輯,一個(gè)制度中如果沒有進(jìn)步的、合理的因素,它怎么能存在幾千年之久?然而,很長時(shí)間以來,沒有人愿意或敢于認(rèn)真地思考這個(gè)問題。《白鹿原》應(yīng)該是在文學(xué)領(lǐng)域最早直面這個(gè)話題的作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陳忠實(shí)是為封建主義唱了一首贊歌。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其實(shí)在《白鹿原》出版的當(dāng)年,費(fèi)秉勛就專門指出過,可惜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費(fèi)秉勛說:“對于中國封建制度生命活力和長命因緣的揭示, 也應(yīng)成為中國文學(xué)用武的一個(gè)領(lǐng)域。白嘉軒這一人物的塑造,就不期而然地做了這種獨(dú)特的工作。”[4]
這種“生命活力”或優(yōu)良基因?qū)嶋H上已經(jīng)內(nèi)化為中國人心理的深層結(jié)構(gòu),成為左右中國人幾千年行為的集體無意識(shí)。
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在我看來是一個(gè)深層的人性特征。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外形上好辨別,差異不大,無非一個(gè)是黑眼睛、黑頭發(fā);一個(gè)是藍(lán)眼睛、黃頭發(fā)。這些很表面,真正的差別在心理結(jié)構(gòu),尤其是做人。《白鹿原》中提到的鄉(xiāng)約實(shí)際上就是普及到中國鄉(xiāng)村的心理結(jié)構(gòu),它能判斷人和事的好壞、高下、是非[4]。
這個(gè)集體無意識(shí)具體地說就是以儒學(xué)思想為主體的價(jià)值觀,不論是改朝換代還是政黨紛爭,不管是作為個(gè)體的為人處世的準(zhǔn)則還是作為協(xié)調(diào)人際關(guān)系的基本規(guī)范,幾千年來,都是它在一直發(fā)揮著支配性的作用。
其次,族長的形象的成功塑造揭示了推動(dòng)歷史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在《白鹿原》之前的同類題材的作品,意識(shí)形態(tài)的立場成為作家審視世界的唯一工具,一方面沿用階級(jí)分析的觀點(diǎn),對人群進(jìn)行簡單的歸類;一方面局限于歷史教科書的材料,對眾所周知的事件給予人云亦云的解釋。尤其是涉及到建國前國共兩黨的敏感話題,就更沒有作家敢于跳出這個(gè)閾限。
但《白鹿原》則試圖站在民間的立場,為中華民族書寫一部人類的秘史。這個(gè)秘史并非軼聞趣事,更非宮闈私密,而是中華民族的心靈史。此前的歷史教科書還是歷史小說,大多注目表層的社會(huì)事件和領(lǐng)袖人物而忽略或無視人心的軌跡以及普通民眾的生活。這樣的歷史敘事無疑只能就事論事,浮于表面,難以挖掘出歷史背后的動(dòng)力。我們常說一句熟語:人民是歷史前進(jìn)的動(dòng)力,這當(dāng)然沒有問題,但人民的“什么”在推動(dòng)歷史才是我們更加關(guān)心的問題。這個(gè)問題數(shù)千年來沒有人主動(dòng)回答或去自覺地探索,《白鹿原》借助族長這個(gè)形象的塑造正好回答了這個(gè)問題。一個(gè)家族的興盛有賴于他們數(shù)代祖先所總結(jié)、流傳下來的經(jīng)驗(yàn),就像白家的“匣匣經(jīng)”保證了他們家族的不敗和強(qiáng)大。一個(gè)民族的昌隆同樣有其被時(shí)間反復(fù)驗(yàn)證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白鹿原》中有這樣一段話:
白嘉軒從父親手里承繼下來的,有原上原下的田地,有槽頭的牛馬,有莊基地上的房屋,有隱藏在土墻里和腳底下的用瓦罐裝著的黃貨和白貨,還有一個(gè)看不見摸不著的財(cái)富,就是孝武復(fù)述給他的那個(gè)立家立身的綱紀(jì)。[5]
白鹿宗族繁衍不亂的傳統(tǒng)就是這個(gè)內(nèi)在的“綱紀(jì)”和我們在前文反復(fù)提到過的鄉(xiāng)約: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
那么,中華民族幾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的精神支柱無疑就是“仁義禮智信”等等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白鹿原》通過白嘉軒作為族長的正面形象以及鹿子霖作為“鄉(xiāng)約”的負(fù)面形象完整地演繹了人性的內(nèi)在動(dòng)力。
陳忠實(shí)以一部長篇小說為自己贏得生前身后名,《白鹿原》之所以長銷不衰并逐漸地成為當(dāng)代文學(xué)經(jīng)典,其奧秘恐怕都在這里。
三
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價(jià)值觀至今還在支配著華夏兒女的思維和言行,它已經(jīng)內(nèi)化為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shí)。“十八大”以來,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得到重新表述,更具時(shí)代色彩,但不管是從國家層面、社會(huì)層面或者個(gè)人層面,其精神指向依然與傳統(tǒng)價(jià)值觀一脈相承。所以,我們凸顯《白鹿原》借助“族長”形象的塑造所傳達(dá)的深層意義也正是在反溯現(xiàn)代價(jià)值觀的根系,從另一個(gè)側(cè)面為“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等核心語匯提供思想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