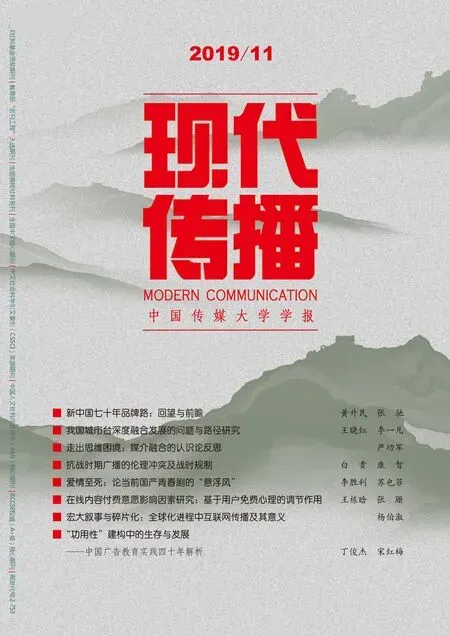智媒傳播中的人機融合關系及其實踐維度*
■ 別君華
在今天,智能技術如毛細血管般廣布、滲透于人們的日常工作與生活,而與智能技術緊密聯結的智能化人類、智能技術和智能環境等亦成為了當今社會系統的基礎坐標。人類身處幾乎全新的物質環境與文化環境,可以說,人、技術與環境三股力量在互動中推動人類邁入智能化生存的新階段。然而,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當代中國傳播學研究在對智能化的生活世界和時代精神的詮釋、反思、批判等層面上,并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要真正思考與辨析這一問題,一個基本的出發點便是隱含于智能化日常傳播實踐中的人機關系轉型。這一日益顯著的趨勢昭示了人與技術正逐步進入人機融合共生之境,人機融合裝置正逐漸成為新階段人機關系的重要命題。
一、智媒崛起與智能傳播
從傳播學視角看,不僅要將人工智能視作一項跨領域的新興技術,而且應該將這一能改變信息的清晰度和結構方式,通過“數據化”介入并促進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人際交往、數據交互和信息交換的技術視作一種獨特的媒介。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深度神經網絡、全腦模擬和智能動力學等方式,獲得類似人的感知智能(能聽會說、能看會認)、認知智能(能理解、會思考)、運算智能(能存儲、會運算)、運動智能(能抓會握、能走會跑)以及情感智能(能理解情緒、會作出反饋),從而延伸人類的相應智能,因此,人工智能已成為當前傳播環境下最具代表性的“智能媒介”。從媒介“后視鏡”向后看,“智能媒介”就是信息技術進化的新階段。它并不單指某一項智能技術或某幾項智能產品,而是以“技術體”——技術并非單一的人工物,而是一個包含技術知識、原理、工具以及產品在內的復雜的綜合性系統——的形態出現,并且不斷拓展著自身的邊界。因此,包含智能傳感、智能芯片、算法模型、專家系統在內的智能媒介基礎層,和包括自然語音交互、圖像識別、人臉識別在內的智能技術層,以及虛擬現實、無人駕駛、無人機、智能音箱、陪護機器人等一系列智能產品在內的應用層,均為智能媒介。
智能媒介在當前的崛起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舊有的、傳統的媒介敞開自身的邊界吸納智能技術,進而組合為新的、智能化的媒介(例如,從普通收音機到智能音箱);新的智能媒介又在智能進化機制的作用下持續演化、重組、應用、再升級,踏上不斷升級的智能化演進之路,同時也帶動網絡傳播進入朝向未來的下半場——一個嶄新的人機協作、萬物皆媒的智媒傳播階段。智能媒介正在顛覆和改寫傳統新聞傳播行業,包括內容生產、傳播方式、組織機構和經營模式等不同板塊都正在經歷重構。在這種重構中,以職業媒體人為主體的新聞生產—消費過程正在發生變化,智能媒介通過改變新聞生產、新聞分發、新聞呈現與效果反饋等方面,構建了新的新聞傳播過程。可以預見的是,以上領域將在新技術的引領下發生無邊界重構,形成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傳播的物質環境與文化環境。
在智能傳播語境下,人機交互和人機對話的方式越來越“自然”和“友好”,人臉識別、手勢識別、語音識別、語音合成等技術既豐富了信息的輸入輸出方式,也模糊了人與媒介原本過于清晰的二元對立界限。我們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正超越傳統的技術使用范疇:一方面,技術不再單純地執行人的指令,它可以給出更多的智能反饋或建議。比如手機等移動便攜智能設備,可根據用戶個體所在的獨特時空情境,為用戶提供個性化、社交化、多模態化的高維信息服務。因此人們自然地視手機為人體的外接“大腦”,聽從其指揮。另一方面,技術的操作對象已經超越了外在環境,開始對人體進行改造,技術與身體結合為跨界裝置。換言之,人開始“吸收”技術,并成為媒介的延伸。人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媒介的伺服系統,通過人機融合的智能技術與人類自身智能的相互補充,實現人機共同進化。
二、人機融合:新型人機關系
在《新浪漫主義賽博格:浪漫主義、信息技術和機器的終結》一書中,學者馬克·科凱爾伯格在深入研究了技術的歷史后,提出了一個新問題:似乎隨著機器變得越來越像人類、越來越信息化,機器與人類的融合成為人機關系的一個顯在趨勢。①有學者甚至直接指出:“數據爆炸之下的人正在變成機器,掌握巨量數據的機器正在變成人。”②可見在智能傳播語境下,人機融合這一新型人機關系愈發顯著。新技術引發的媒介融合,不但呈現為媒介形態與社會形態的融合,而且其根本之處在于技術與人的融合。③
在這一狀況下,主流傳播學視閾中人機二元對立的技術觀便無法支撐我們去認識、理解智媒時代中愈加顯著、愈加自然的人機融合實踐。恰恰是這種傳播學維度理解的有限性,為技術哲學的出場留出了空間,因為它有效地提供了能夠解釋智媒傳播中人機融合的理論視角。實際上,麥克盧漢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這一著名觀點,就昭示了關于人機融合關系的技術哲學表達。在泛媒介論者看來,幾乎所有媒介技術都是對人體器官的延伸,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與所有出現過的媒介技術都能夠構成一個人機融合的信息系統。從媒介性質角度來區分,書刊、報紙這一系列傳統媒介只是人的肢體的一般性延伸,與人體之間不能結合為信息系統;而電磁、電子技術可以作為神經系統的延伸,與人體之間能夠構成信息系統④,因此,肉身神經脈沖與智能媒介(例如植入體內的芯片)電子脈沖能夠進行直接的數據交互。移動互聯網、智能傳感器、人工智能和虛擬現實等一系列智能技術的崛起,對現階段的人機融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智能技術的出現與普及,有效的人機融合才從“科幻”或“病患”領域轉移到日常傳播實踐中,形成人與智能媒介技術融合的復合裝置。
人類無法脫離技術而單獨生存,按照唐·伊德(Don Ihde)的觀點,人對現實經驗的感受和認知受到技術中介的暗中轉化,技術在這里并不是“像對象一樣的東西”,而是“融入到”人的身體經驗中,導向環境中的行為,或者作用于環境,形成人—技術—世界的具身關系。⑤因此,“對于人類來說,沒有技術的生存只是一種抽象的可能性”⑥。站在現象學立場上,不論是胡塞爾、梅洛·龐蒂還是海德格爾,都將具身實踐作為參與生活世界的方式,具身化的實踐活動顯著地包含了對人工物或物質化的技術的應用。⑦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是從批判卡爾·雅斯貝爾斯的技術哲學觀點開始的。雅斯貝爾斯在著作《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論述技術對人類的目的性時,曾如此表述:“技術是一個科學的人類控制自然的過程,其目的是塑造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免于匱乏,并使人類環境具有諸事取決于自己的形式。”⑧他認為技術的本質在于人在使用工具的過程中幫助人達成自身的利益目標。海德格爾反對雅斯貝爾斯那種將人視為主體、將技術視為工具的觀點,他認為“現代技術不是目的的單純手段,而是本身參與到自然、現實和世界的構造中”⑨。在對技術的本體性追問中,海德格爾指出人的存在與技術緊密關聯。他使我們認識到技術只是一種現象,其背后必然有某種東西使其成為了自身,而且只有弄清技術之所以成為技術的本質規定性,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認知和使用技術。學者安德魯·芬伯格、唐·伊德、邁克爾·海姆都是這一思想脈絡的代表人物,他們認為作為現代社會的“座駕”,技術具有一定的強制作用。媒介技術或人工物直接介入了人們的知覺,融入到人類身體的經驗中,作用于人們的感官知覺,從而建構了整個經驗世界,逐步改變了社會文化結構。
在如何看待人與技術的關系問題上,麥克盧漢的思想立場與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具有相通之處。從技術哲學的角度來看,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媒介環境學派是指“從人本主義和技術邏輯出發,研究人類與媒介技術相互關系問題的媒介技術哲學譜系”⑩。他們所秉持的媒介技術哲學,是總體性的技術哲學的一個分支。媒介技術哲學譜系的學者們,從帕特里克·格迪斯、劉易斯·芒福德到麥克盧漢、保羅·萊文森、約書亞·梅羅維茨等,都擅長分析人與媒介技術的互構關系,他們反對將媒介技術作為工具對待,其媒介技術本體論的核心觀點是“媒介并不是主體間或主體與客體之間傳遞信息的中性管道”,它有其自身結構意向。通過作用于人體感知,媒介技術與人在互動延伸中確立各自的存在。“媒介是人的延伸”意味著媒介技術對人的主體性的建構作用,而這一觀點充分體現了媒介環境學的人本主義關懷。任何一種新的媒介都能夠為人體感知帶來一種新的尺度,改變人體感知比率,它不僅為人類認識世界編織了意義之網,更為每個主導媒介階段的社會文化設置了偏向。媒介自身具備能動性,它是與人互為主體的行動者。在人與媒介的關系中,人始終處于優先位置。在最理想的情境中(即上手狀態),媒介技術的工具性和中介性應當被“懸置”,它和人是結合在一起的,甚至成為人體的一個器官。比如,當前手機幾乎成了人體的一個器官,我們被卷入借助手機進行的交流而忘了手機的存在。又比如鼠標作為手的延伸,只有當它的光標指示不準確時,人們才能發現鼠標這項技術是外在于人的;當它正常工作時,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鼠標延伸了右手,和右手融為一體。因此,技術不是“合目的的手段”,它和人不是相互外在對立的關系,技術外在地延伸了人但卻內在地把人寓于其中。在優質的人與媒介技術關系中,媒介幾近透明,人的感覺和生存狀況處于優先位置。“麥克盧漢的延伸論挑戰了一種冷峻地看待人—技術關系的功利主義視角,并用人—技術親密組合的關系論調取而代之。”美國媒介技術哲學家邁克爾·海姆在《虛擬實在的形而上學》中將麥克盧漢和海德格爾并列為20世紀的思想巨人,他們都把技術問題放到了研究社會的中心位置。
如上所述,當前人與智能技術的融合以及人與智能技術的組合式進化愈加成為一項顯在的社會經驗。為更好地理解智能傳播階段人機融合的現象和趨勢,本文將智媒時代人機融合概括為智能化實體人、智能化虛擬人以及類人化機器三種基本類型。
其一,智能化實體人。智能技術吸納人的身體,結合為人機復合的跨界裝置。這類常見的人機融合形態包括人與手機、人與可穿戴設備的結合,將來通過人體植入芯片的方式形成的人機融合態或將逐步普及。通常這類人機融合所涉及的是“人機互動的自然化”,可折疊軟性屏幕、傳感系統、人臉識別、指紋識別和自然語言交互等為人與技術在自然狀態下進行數據交互提供了技術支持。“機器感知提升人機交互質量,目標直指人機融合,即從單向性的人機學習走向雙向深度態勢感知”,人與智能技術能夠自然“溝通”,兩者組合為人機一體的數據交互網絡。這類人機融合的特征是,人從技術那里尋求數據(以0/1方式存儲的信息)處理能力的強化,通過人機融合增強自己的信息匯總、數據處理、體外記憶等能力,從而使自然狀態下的人機交互成為人類自身智能的補充。
其二,智能化虛擬人。在網絡游戲仿真空間和VR仿真敘事中,人利用可支配的軟硬件設備及交互系統突破身體與物理時空的局限,在人—機深度交互的基礎上以“節點人”的形式進入虛擬空間,以光速自由參與傳播活動,進行人際交往,并因此越來越成為人工經驗的產物。就人類作為“原子結構的人”被仿真地數字化為一種隱匿性的數碼符號這點來看,在理論上構成了“數字化人”或“比特人”這一數字化生存的媒介技術哲學問題。沿著這樣的路徑繼續前進,有可能導致人體的虛擬化,甚至是一種廢棄身體的存在,轉而以電腦的機器身體替代肉身,保存意識的自由穿梭,成為突破肉身之局限的機體人,而這又意味著人的存在能夠完全擺脫肉體的限制。
其三,類人化機器。在公共場所和私人領域協助或替代人類工作的智能機器人是這類人機融合的典型。通過聯結主義、符號主義與行為主義三種基礎運算方式,智能技術表現出包括感知智能、認知智能、運算智能、運動智能和情感智能在內的類人“智能”。雖然機器通過數據訓練形成智能的方式與人類智能的生成方式并不相同,機器智能也不等同于人類智能,但一次次的智能程序在專業領域擊敗人類的事件卻鮮明地展現了機器智能的能動力量,“類人化機器”亦成為當前社會網絡中積極的行動者。
可見,智能媒介的技術創新“正在顛覆長期以來形成的人與工具之間的控制與被控制、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在以上三種人機融合類型中,智能化實體人和智能化虛擬人是通過“肉身+技術”的方式完成對人的身體功能的超越,而類人化機器則是通過“技術+模擬人智能”的方式來完成對人的自身能力的超越。雖然說前兩者是人機融合的基礎形態,但第三種以機器為主體的人機融合樣式也是不可忽視的,其啟發意義在于類人化機器極具代表性地揭示了智媒時代人的脫肉化和人機共生趨勢。
三、融合實踐:三個關鍵維度
如上所述,技術哲學為我們理解智能化傳播階段的人機融合提供了有效的理論視角,當下人與智能技術的融合就體現為智能化實體人、智能化虛擬人和類人化機器三種基礎形態。但值得思考的是,人機融合不僅僅是人的生命形態在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轉換的問題,至少在主體觀念、身體—技術關系和傳播實踐這三個關鍵維度上,人機融合也為我們反思人的技術化生存提供了一個可能性的理論起點。
1.人機融合主體
人機融合首先涉及在智能技術的作用下,主體觀念的變革。“任何一次技術革命的背后,實際上是一種主體性質的觀念革命。”媒介技術進化到智能階段后開始“進入了重造主體的階段”,因此人機融合不僅是一種關于在人與技術的主客體界限模糊處生成新生命形態的問題,更是關于主體觀念從現代主體向后人類主體轉換的問題。生命形態和主體不是一種二元分離關系,它們緊密關聯而又處于不同層面,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話語表述。如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說,智能技術“有可能改變人性并因此將我們領進歷史的‘后人類’階段”。“主體不是先在的,而是在關系網絡中處在一個不斷建構與解構的過程中”,如果說“媒介是一種與當時的物質環境、物理載體本身有共生性的復合性質的對象,那么,人的主體性價值和立場,是通過媒介技術的把控及其操作流程來完成的,在本質上和大的社會生產力演進的趨勢相一致”。這正延續了克拉里對現代化的理解,現代化所涵蓋的“不只是政治與經濟構成的結構性改變,同時,也涉及知識、語言、空間與傳播網絡,以及主體性本身的廣泛重組”。
有關后人類的一個共識是:當代科學和生物技術影響了生物結構,并改變了人們對于什么才是今天的人類基本參照系的理解。后人類立場是反人文主義的,它打破了西方現代主體話語中主體/客體、理性/感性、身/心、人類/自然等二元對立、主客分離的傳統。“我思”不再是主體的本質,主體更主要地表現為身體對身體技術、遺傳基因技術,甚至其他生物的依賴,或者與它們的結合。主導性的媒介界面培育了新的主體觀念,“在這個媒介域的操作狀態中,發現人本身成為媒介,這才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智媒時代中,人與技術共生共融,形成了人機結合裝置。如同德勒茲的蘭花與黃蜂結合的意象,人也鮮明地吸收了智能技術因素,構成人機復合的主體形象。
2.人機融合身體
人機融合又涉及在智能技術的自主性效應下,身體—技術關系的變革。實際上,身體自尼采以來就開始顛覆柏拉圖設定的靈魂/身體二元對峙、靈魂高于身體的哲學傳統,成為人的決定性基礎。但長久以來,“以大眾媒介為主要經驗場域的主流傳播學未能將身體維度納入研究的視閾中”。因此,在大眾傳播研究中,身體非但沒有成為研究的對象,反而被視為需要克服的障礙。而在新技術環境/條件下,人機融合這一新生命形態特意將大眾傳播所忽視的重要的身體維度標注出來,將身體—技術關系納入到傳播學的考察范圍中。
從媒介歷史來看,身體具有傳播第一媒介的地位,“傳播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脫離身體”。人的身體本身是傳播活動充分且必要的物質條件,在原始部落面對面的傳播中,對話、唱歌、跳舞這些親密的肢體互動對人類社會發展初期傳遞信息、凝聚共識并建立共同體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英國學者克里斯·希林認為,現代信息技術在激活身體能動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進入智能媒介技術階段后,身體作為社會力量源泉的作用就凸顯了出來,一定程度上,肉身處于主體借助媒介行動的中心,或者說,“身體是釋放媒介動量的觸發機制”。這點可以通過歷時性的三個階段來分析:首先,在智能媒介技術初期,電力媒介激發了肉體行動的速度和對于行動邊界拓展的可能,麥克盧漢聲稱“當你‘在播放中’時,你就同時處在這里和其他許多地方,仿佛你無形無象,宛若天使”,這是最初的肉身與技術結合以增強人的能力的寫照。其次,網絡媒介在電力媒介的基礎上進一步抬高了身體的重要性,“身體是網絡技術的能動源泉,促進并拓展了個體的自愿規劃”,“節點人”溝通了全球范圍內的時間和空間,許多新型的體驗都成為可能。最后,隨著人工智能的崛起,生物邏輯與技術邏輯走向互嵌結構,身體與媒介技術之間的關聯增強了。人機融合突出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智能技術的能動性和自主力量,智能技術在傳播實踐中的應用普及推動了人與智能技術融合實踐的常態化進程。技術開始吸納身體,促使人機關系進入普遍化的人機互嵌、人機合一狀態,促進生物態的人進化為人機融合裝置。
智能技術使“身體性存在與計算機仿真之間、人機關系結構與生物組織之間、機器人科技與人類目標之間,并沒有本質的不同或者絕對的界線”。但為什么人與機器能夠聯通?信息論和控制論為計算機技術革命提供了一套操作原理,“今日社會的每一重要活動都正被帶入控制論原理的指導范圍之內。通過計算機進行的‘信息處理’正迅速成為我們技術文化的標志”。信息技術的革命性在于它將世間的一切轉化為數據/符號,由于它們共享一個相同的結構基礎,共同的語言和編碼能夠形成肉身、技術和社會文化的轉換器,幾乎所有異質物包括生物體和非生物體通過信息中介實現跨界物質之間的交互,從而建構起一種人、機器和環境普遍交互的可能。因此,“信息、控制和傳播,三大強力要素聯合行動,將會造成有機體和機械體前所未有的綜合”。
3.人機融合傳播實踐
人機融合還涉及在智能技術的作用下,人類日常傳播實踐的變革。智能媒介“不僅僅是一種信息生產方式,更是圍繞著它所依托的介質和載體所產生的組織性、結構性的活動,重新結構社會性的生產關系”,人機融合作為人類進化的最新生命形態,增強了這一控制論系統與外界進行信息交互的能力。技術與人的共同進化進一步觸發了溝通的可能,使傳播的軟硬件配置得以升級、傳播的邊界得以拓展,傳播有效性得以提升,原本無法產生的溝通得以激活,原本淺層的低效溝通模式得到深化,以及原本的傳播模式發生轉型。由此,智媒傳播中的人機融合正在成為智能化網絡社會中一個“終極的媒介”,它作為智媒時代傳播網絡中的基本節點,“以動態、持續、滲透性的實踐方式嵌入日常生活”。社會系統以智媒傳播中的人機融合為基點進行重組,Web 2.0時代分眾化的傳播再次細化為以個人為中心的場景傳播,“極大地推動了更多植根于本地的、更加個人化的交流與傳播的實現……也使更多的物理距離或社會意義上的遠程操作變得可能”。
技術的生產意義不僅在于它是“擴大社會再生產的軟件范疇”,更在于其對于人類經驗邊界的拓展,可以說“作為工具的技術只是節省了勞動,而作為裝置的技術則產生出一個人工的世界,它開啟了新的經驗”。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把對媒介技術功能的認知建立在技術是真正可觸摸、可制作、可修改的物質層面的現實基礎上,而現在人們對技術的認知正從單獨的機器、工具轉換為一個綜合的自主技術環境。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圍繞著技術不斷更新、變化,新技術影響了資金運作方式、勞動力派遣方式、商業運作方式和關于身份的建構方式,文化不可分離地融合于復雜的技術系統和環境之中。
四、結語
從技術哲學思想出發,智能媒介技術作為技術演化的新形態,通過人機融合革命性地將人類帶入新的生存和進化階段。一方面,借助“人—機交互的效率和人—機接口水平的提高”,媒介技術智能對人類智能形成補充,人類的信息匯總、數據處理和體外記憶等能力得到飛躍式提升;另一方面,人機融合通過對人類所處的時間、空間這兩個基本存在維度的操作促進了社會結構變革,“虛擬時空集中體現了互聯網的社會向度,并為社會生活的再結構、再組織過程提供了框架和邏輯”。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本文更需要重申技術倫理的重要性。首先,人是技術的目的。在面對技術對身體定位/延伸的雙重境況時,希林的明確態度是,“互聯網之類的技術往往是對社會關系的進一步補充,而不是徹底轉化。它所導致的并非革命,而是為特定類型的創新和變化提供了機會”。當前,人機互嵌而成的人機融合裝置,是人的生物態的革新,是關于人的主體觀念和主體話語的革新,而非人的本質的變革。其次,如同康德所說,人是存在的目的,具有永恒的價值和尊嚴。因此,人們應當理性看待智能技術的能動性,只有通過不斷反思并采取行動,人們才有可能更好地與技術共生,開啟一種可持續的有機生活。
總之,人與技術越來越深地相互糾纏,兩者的共存開始從主客體關系轉為人—技術的協同進化關系。在與技術的協作中,人類已經進入并將持續走向更高級的存在階段。同時,在智能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將身體交付技術以重新設計的趨勢引起了關于人類存在界限及相關倫理問題的一系列反思,提醒著人們關注人類的本質、價值、尊嚴和邊界。
注釋:
① Mark Coeckelbergh.NewRomanticCyborgs:Romanticism,InformationTechnology,andtheEndoftheMachine.London:MIT Press,2018,109:228-229.
⑤ [美]唐·伊德:《讓事物說話:后現象學與技術科學》,韓連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頁。
⑥ [美]唐·伊德:《技術與生活世界》,韓連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頁。
⑦ 唐伊德:《如何用海德格爾談當代的技術哲學》,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173809957679870&wfr=spider&for=pc.
⑧ [德]卡爾·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和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頁。
⑨ [德]岡特·紹伊博爾德:《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技術》,宋祖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頁。
⑩ 李曦珍:《理解麥克盧漢:當代西方媒介技術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