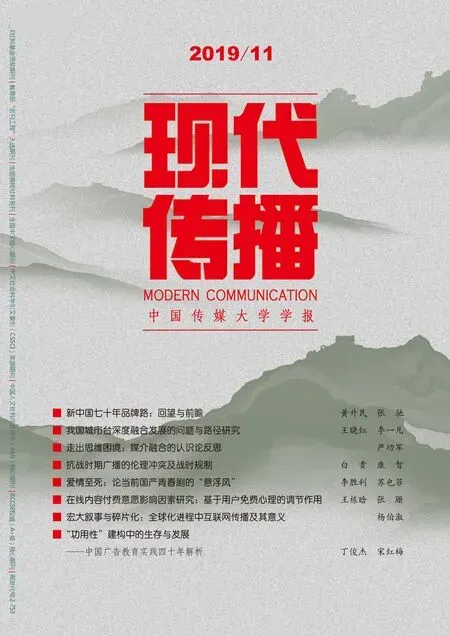抗戰時期廣播的倫理沖突及戰時規制
■ 白 貴 康 智
1923年1月,美國人奧斯邦在上海開辦了“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臺”,成為了我國境內的第一家廣播電臺。北洋政府積極發展廣播事業,1926年哈爾濱廣播電臺正式成立,隨后1927年天津、北京的廣播電臺也開始了播音。之后,國民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都十分重視創辦與經營無線電廣播電臺。
在媒介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中,其一方面是信息傳播的載體與平臺,是技術發展與變革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又不斷豐富著社會文化形態與意義空間。隨著媒介社會化進程的推進,它將更深入地影響社會發展,如信息傳遞、人際互動交往、社會治理運行等。特別是新媒介的出現,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在短時間內更為明顯,可能會塑造一種新的社會價值標準與倫理道德體系。同樣,隨著廣播的發展,其社會化進程不斷加快,與之而來的媒介倫理問題也頻頻發生。特別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戰時環境下的廣播倫理問題與規制引發了民國社會的廣泛關注。從媒介社會化視角考察抗戰時期的廣播倫理問題及規制,是對民國媒介生態環境的另一種全新認知。
一、亂象叢生:大眾的廣播倫理批判
(一)廣播誕生之初的倫理困境
民國時期文盲率極高,相比于傳統報刊的傳播模式,廣播大大降低了信息獲取門檻,豐富了信息的直觀生動性,提升了傳播效力。作為民國社會的新媒介,廣播不但加速了信息的傳遞,還豐富了民眾生活,改變著社會交往模式,成為了當時受人追捧的“寵兒”。
廣播事業開創初期,一方面,社會各界贊譽肯定廣播帶來的新貢獻;但另一方面,由于廣播倫理引發的社會問題也同樣受到了各界的指責。簡單來說,政府與社會對于廣播的教育功能、統一思想功能、信息傳遞功能期許滿滿,但現實中由于資本的作用與內外矛盾等因素,廣播所發揮的作用與人們的期待相去甚遠,也偏離了初衷。廣播不但在積極作用方面沒有取得過多的成就,反而影響了整個社會的風氣,十分危險。制造假新聞,節目粗制濫造,內容淫穢且低俗、缺乏社會教育意識等倫理問題層出不窮。吳侍中談到“有幾個播音者,實在缺乏道德。于播送節目時間,往往加入幾張粗俗而肉麻的唱片,與不堪入耳的污穢言辭,或者竟肆扣謾罵。還有幾個播音者,時常喚街頭賣藝之流,來唱一曲小調,歌一段情詞,算是播送特別節目。”①黃鑑村認為,與其廣播民眾所樂聞者不如廣播其所必需者:“以迎合民眾之心理,而廣播其所喜好者,此種方針為害於民眾實非淺也。觀目下滬上各種廣播電臺,均以迎合民眾之心理為務,而廣播低級之音樂與卑劣之對答,有害無益,尤應請當局者注意及之,而加以糾正,使民眾得收聽高上有益之廣播。”②而雙十播音社也用區別于其他“靡靡之音”電臺的方式來突出本電臺的社會責任意識,“諸君子,以為此是何種播音呼,不是特別蘇灘,必以為時新申曲,不是越調粵謳,必為最新舶來之歌舞名曲,豈知完全出于不可思議之舉。比所謂蘇灘申曲,越調粵謳,以及歌舞名曲,故足以愉悅性情,為公余消遣解悶之資。而本社所播送者,乃以有益民眾,宣揚國粹為原則,欲研究于游息之間,獲裨益于聲樂之外……本社同仁,自愧無狀,本人應服務社會之精神,宣揚國學,演講青年職業界應有之知識與技能,及提倡家庭兼青年男女之高尚修養與娛樂,用敢廣播于空間。”③葉圣陶、魯迅、茅盾等當時的社會公眾人物對廣播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廣播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武器,反對廣播的低級趣味,提倡正確利用現代廣播“團結大眾”“傳授知識”“報告消息”,以發展其正面價值。
(二)凈化環境:抗戰廣播的不良內容
然而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隨著日本侵略野心的昭然若揭,國內大眾對于廣播倫理的注意力開始轉移,一方面,繼續批判廣播的“泛娛樂化”傾向,抵制低俗節目;另一方面,更加注重無線電廣播的思想動員與輿論引導作用。特別是在“七七事變”后,戰時廣播倫理與社會責任問題被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統一各類媒體,摒棄不良內容,形成輿論戰線,團結各方力量積極抗戰成為了首要任務。
隨著國內外矛盾日益加劇,國際間的廣播宣傳戰愈演愈烈,如果不能好好利用廣播加以引導與宣傳,中國更加會成為一盤散沙。然而當時的廣播界依舊娛樂成風,到處是陳詞濫調、靡靡之音,形成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民眾對此十分不滿。“為商戰而利用播音,電波音所生產的,當然是類于迎合那種小市民,站在賣主的立場,那種低級為廣告而生存的職業團——如話劇,彈詞,歌唱,申曲……這些長時的或短時的職業團,為生活而藝術,才去每天走上七個或八個電臺,跟牛馬一般的工作著,嘶喊著,盡著他們的全力來播送,我們大眾之前的,紅樓夢,濟公活佛,三笑,特別快車,活捉……這一幅活生生的為人生而藝術的怪現象,已撕破了她的衣服,赤裸裸地暴露在我們面前。而所剩余的必然結果,就是中國市民的文化水平降低,以及中國大眾墮落麻醉的深刻。”④廣播已經淪落為商業戰與娛樂的工具,每日粗制濫造的小調雜曲,聲聲不息。電臺為投其所好,吸引更多的聽眾,賺取廣告費而不擇手段,絲毫不去考慮此類行為會產生什么樣的社會效果。《音圈小訊》稱,“曼娜已脫離中國無線電劇社,脫離原因據說該社老板覺得她所播之話劇,不能迎合社會上低級趣味的聽眾,因此連帶動搖廣告生命線,故將其辭退。”⑤又如“每當黃昏時候,這里一簇那里一簇的包圍著從內地來到上海混飯吃的鄉曲姑娘,聽他們唱各色各樣的小調子,你的這些調子大多是下流而淫穢。”⑥由此可見,當時廣播環境烏煙瘴氣,節目粗制濫造,多為迎合低級趣味的淫詞穢曲,而這些內容極大地影響著社會大眾,營造出頹廢不堪的氣象。特別是在面對外敵侵略的時候,這樣的節目內容使得廣播的社會責任與戰時思想動員作用大打折扣,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
對此問題,民國社會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人支持摒棄全部娛樂,發揮廣播的教育作用,而多數人支持逐步改良,寓教于樂,提倡高級的廣播娛樂。
《益世報》刊文稱:“我們需要知道,無線電并不是只為娛樂而設,我們需要借助無線電的力量,提高我們的文化,灌輸各種常識,團結全國人民精神,聯絡各地感情。此外再加上一部分的娛樂節目,以免有干燥乏味的癖病。……更希望各種娛樂如昆曲、國劇、音樂、雜技、大鼓、單弦等均加以改良,并擇其合適于鼓勵人民愛國心與道德觀念的游藝,加以廣播,而提高人民娛樂的程度,使娛樂高級化。”⑦徐卓呆先生認為,首先應該從播音臺管理入手,因為這些電臺都有登記備案,召集相關負責人和播音員由教育行政機構給其開會傳達要義。要表明廣播電臺的良好發展對于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性;告訴他們不良材料的危害與影響;教會他們如何甄別有害內容,播音時如何避免不良內容;要明確一旦出現問題,播音臺要負全部責任;其次,要將舊游藝進行淘汰與創新,編寫新的游藝材料。⑧二人觀點不謀而合,摒除全部的廣播娛樂不太現實,缺乏娛樂會使得廣播枯燥乏味,不利于傳播。但長期低級、媚俗的娛樂會敗壞社會風氣,影響民眾思想。可行的途徑只有嚴格把控游藝娛樂的質量,激勵民間藝人不斷創新,使娛樂高雅健康化。
二、強化管理:政府的戰時廣播倫理規制
民國社會就對戰時廣播的重要性具有清晰的認知,陳立夫將廣播稱為“第四條戰線”。在內憂外患的處境下,較早就有學者意識到中國廣播管理權的問題,“中國政府處于兩姑之間,左右為難,無線電臺只在今日,已成為軍事商業之利器,如任外人設立電臺,把持管理,則平日貨價之起落,匯率之高下,其以盡操于外人之手;一旦戰事發生,則凡關軍事之秘密,一不明白宣布與敵人之前,更不勞其間諜之偵探矣。”⑨王承樟論述戰時廣播電臺的重要作用時稱國際廣播戰為“潛性戰爭”,他講道“殊不知無線電播音,在戰爭的宣傳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消息之傳播,國際間及民眾間之宣傳,對敵國軍民之忠告,以及干擾敵方無線電臺之反宣傳,其對于宣傳的力量是何等的重大。無線電在戰爭上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故各國在這火藥氣味四溢全球的今日,都致力于建設更強大的無線電臺,除用于商業上和軍事上之通訊外,更利用無線電廣播,來宣揚自己破壞他人,無形中便成了一種潛性戰爭。”⑩
在20世紀30年代后,國內外矛盾日益加劇,國際間的廣播宣傳戰愈演愈烈,同時日本的侵華意圖愈發明顯,而國內的階級斗爭矛盾尖銳。就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局勢下,國內廣播卻整日沉浸在靡靡之音與低俗娛樂中,對于國民思想意志毫無裨益,嚴重影響了社會風氣。戰時特殊時期中,如若廣播無法滿足對外國際宣傳與對內鼓舞民眾抗敵士氣的話,那么后果將不堪設想。介于此種狀況,當局者意識到應當加強廣播管理力度,著重對廣播節目編排、廣播不良內容、社會教育職責與戰時廣播新聞等內容推出了具體的倫理規范措施。
(一)國統區的戰時廣播規制
自廣播誕生起,中國政府便十分重視對無線電廣播的經營與管理。1924年8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公布《裝用廣播無線電接收機暫行規則》,允許民間裝設收音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無線電廣播的法令。自此之后,國民政府加大了對全國的廣播電臺管控力度,出臺了一系列政令法規約束與規制廣播倫理問題。
面對國內廣播節目內容粗制亂造、淫穢低俗的問題,社會局十分重視,出臺相關條例,取締與改造不合規的廣播電臺。如上海等地開始整頓廣播荒謬節目,“本市自有無線電播音以來,各商店即利用做夸大宣傳,甚且為迎合低級趣味起見,各電臺往往播送荒誕乖謬之節目,如頹廢的哭,及下卑污、不堪入耳之小調,諸如此類。對于民族前途,養成頹廢風氣,影響非小,殊堪痛恨,本局有慮于此,認為非取締不足以振頹風而遏潛禍,故慎重斟酌之下,采取迅速處置……無線電播音他國視為教育利器,本市為全國文化中心,不予糾正,后患必多,應是取締荒謬播音節目一舉,市政局已具有堅毅決心。”又如頒發政令,告誡各廣播電臺務必遵循,“乃近查市內各無線電播音臺,播音材料,類多彈詞歌曲每于言聲調之間,含有污穢傷風之意,殊足影響社會風化。茲為防微杜漸起見,合行令另仰電臺遵照,此后關于播音材料,務應鄭重選擇,俾免流弊,而維風紀為要。此令。”足見,當局對于廣播內容低俗污穢的問題十分重視,下大力度整治廣播節目,摒除不良內容,提倡發揮廣播的社會教育職能,凈化社會環境,以求形成戰時的輿論與思想統一。
1937年4月交通部頒布實施了《指導播送節目辦法》,著重對廣播內容做了嚴格規范。例如“播送節目之內容未經審査核準,擅自播放,而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予以停播一日至七日之處分。破壞民族固有道德侮辱國人共同敬仰之先哲或時賢;鬼神妖異荒誕不經之故事;詞句不但粗鄙及誨淫誨盜;違禁物品或違禁出版品之廣告;危害身心之藥物或場所之廣告;違反民族平等之旨引起國際惡感。”對于那些屢教不改之電臺,當局毫不留情,予以取締處罰,如“有數處電臺,屢不遵照辦理,分情節輕重,酌予處罰,以儆效尤,而重宣傳為荷……查自各省市廣播電臺轉播中央臺節目后,兩個月以來,據本處偵察組報告,每日收聽上海各民營電臺所播娛樂節目,內容詞句,其情調頗多迎合低級趣味,冶蕩頹靡,其影響社會風俗人至巨,尤不合于蔣委員長所提倡新生活運動之精神,亟宜詳密取締,以振民志,而維習俗,從該組報告內關于各省節目由為淫靡鄙陋者,列表一紙,隨函送達。”國民政府密切關注廣播動態,為了確保戰時廣播質量與信息傳遞,當局下令要求地方與民營電臺每日必須轉播中央臺的部分節目,并設立了偵查組監聽各廣播臺播送內容,及時發現問題予以處置。同時規定中央臺與國際頻道定期和國外電臺互動轉播,采用多國、多民族語言進行播報。一方面及時報道國內戰爭實況,發揚戰斗精神,爭取國際援助;另一方面轉播遠東盟軍廣播,播送新聞、時評、樂劇等以助士氣。法規條例的出臺在很大程度上規范了廣播倫理,控制了廣播內容低俗污穢的勢頭,對于戰時輿論與思想的統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寓“教育”于廣播 從觀念上筑牢倫理之基
1935 年5月,教育部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商定,制定了利用中央廣播電臺播送教育節目,并于1936 年7 月設立了教育部“播音教育委員會”,出版了《播音教育月刊》,其內容“以講稿為主體,此外還載有關于國內外播音教育消息和播音教育的法令。”同時國民黨對各大城市的廣播內容進行了嚴格的篩查與規范,設立了針對不同人群的教育節目,普及各類知識技能。這項廣播教育活動是對以往知識學習方式的改變,通過建立“空中課堂”實現了對不同階層與人群的知識傳授,給不識字的普通老百姓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同時通過廣播教育,傳輸思想,強化國家與民族意識,激發民眾的家國情懷,共同抵御外來侵略。
1937年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上通過了《廣播教育實施辦法》,該辦法確立了四項原則:廣播事業應以改革習俗振作人心,以及統一思想語言為主要旨趣;廣播事業應確定為國營事業,由中央及省市政府經營之;廣播事業應使成為教育事業之一單位,其取材標準,以教育之需要為依據;廣播人員應受專業訓練。四項原則從政府管理層面將廣播事業納入到國家宣傳與教育中,利用廣播統一思想,強化愛國意識,推行國家普及教育并對從業者的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從根本上將廣播事業推向了新的高度,提升了廣播的質量要求,強化其社會功能屬性。《廣播教育實施辦法》還對廣播事業發展與管理提出了具體要求:電臺創辦方面,禁止私人設立廣播電臺,之前設立的私營電臺如果其影響力較大,需要登記備案,接受政府監督。同時,外國人禁止在中國境內創辦電臺。在播音內容方面,要對廣播播音材料進行審查,將材料分為準播、禁播與改編三類,未經審核的稿件不得播送;在人員管理方面,主管部門要對廣播從業者進行信息統計,備案在冊;在播音語言方面,要求使用國語,外語禁止使用(除特殊情況)。同時,中央對廣播人員開設培訓班,從思想、技術、語言、管理等方面進行培訓,以提升廣播從業者的整體素養。以上實施辦法從各個方面對廣播的經營、管理、審查等方面進行約束與管控,加強廣播的規范性與統一性,從而為國家政治、經濟、教育服務。
廣播的重要管控方面在于內容,對社會產生影響的也是播音內容,因此《廣播教育實施辦法》特意對播音使用的材料做出了規范,如下:“根據文化事業計劃綱要所定之原則,一面應將既有之材料選擇介紹,一面應將理想之材料編纂提供。關于新聞廣播,除國內外重要新聞外,對于各該地方之改進事業,如筑路造林衛生消防以及農工商各項消息亦應播送;關于演講題材,以切合人民生活之改進及國家建設之需要為目標;關于廣播節目,應就各項廣播材料針對人民之生活為有系統之編排。”政府對廣播內容的選取采取文化當先、改善人民生活當先的原則。在抗戰時期加大對民眾的文化與思想上的教育,喚醒國民意識,激發抗戰斗志,同時要求播音材料應為民眾提供生活上的幫助、文化上的熏陶、思想上的統一與升華。
(三)紅色廣播的戰時管理條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廣播事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在新聞史研究中依舊是特別重要的一個階段。自從“七七事變”后,中共中央為了更好地團結群眾與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籌劃建立自己的廣播電臺。經過多方努力,1940年春天,中共中央成立了廣播委員會,周恩來擔任委員會主任,同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正式播音,這是共產黨第一座廣播電臺,標志著紅色廣播事業拉開序幕。
1941年5月25日,為了適應戰時宣傳服務的需要,中共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電臺廣播的指示》明確了中共廣播的作用,廣播要服務于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用事實宣傳根據地的實際情況。短短一句話卻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明晰廣播的重要作用,遵循廣播客觀、真實規律。同時,為了適應廣播傳播特性,指示中要求:“廣播材料應力求短小精彩,生動具體,切忌長篇大論,令人生厭的空談”。“廣播均應采取短小的電訊形式,每節平常以三百至五百字為適當,至多不得超過一千字,當地負責的講演與論文,如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應摘要廣播,至多亦不得越過一千字。”從這一項規定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細節,廣播不同于報紙,如果是長篇大論、不著重點,首先難以使聽眾留下印象,其次容易讓聽眾產生厭煩。特別是在抗戰期間,短小簡練的電訊恰恰容易告知聽眾重點,提高傳播的有效性。在廣播縱向管理與對外宣傳方面,中共也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一切對外宣傳均應服從黨的政策與中央決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區黨委負責同志的公開發言,尤應嚴格遵守此原則。”“各地方報紙下的通訊社,應成為對外宣傳的重要機關。并設立廣播委員會專門負責廣播材料的審查編輯,并由宣傳部指定一政治上堅強的領導人,并經常檢查其工作。”規定表明了中共加強對廣播的行政管理,明確隸屬管理,對廣播材料加以審查編輯,確保信息的真實性與及時性。同時根據戰時需要,中共還創辦了日語廣播,主要是宣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酷罪行,介紹日本反戰同盟活動,煽動日本士兵反戰、厭戰情緒,瓦解敵人斗志等。中共中央對廣播電臺的管理措施,不光規范了廣播內容形式,同時還團結了各方力量,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綜上所述,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都密切關注廣播事業的發展,在戰時特殊時期,對廣播泛娛樂化、內容淫穢低俗、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等倫理問題加強了管控,出臺了一系列的法規條令,阻止靡靡之音擾亂社會風氣。同時也對廣播的具體管理、播音方式與操作細節方面提出了明確規定,提高了戰時廣播內容質量與傳播效果。更為重要的是在戰時遏制了社會不良風氣,通過廣播鼓舞大眾抗戰斗志,激發愛國情懷,共同抵御外來侵略。
三、戰時廣播行業的倫理自律
隨著1937年以后日本開始全面侵華,一方面,廣播繼續為民眾傳遞國內外新聞與推行社會教育;另一方面,還肩負起對外宣傳與對民眾思想、精神之鼓舞使命。在這期間,廣播的倫理問題依舊會引起各界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廣播行業開始步入正軌,行業自律與規章逐步發揮了作用。廣播經過十幾年的探索發展,在借鑒與對比中加深對國內外廣播的研究,社會對廣播事業的特性、功能等認知更加清晰,這也更加有利于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有利于自我規范。
抗戰時期,中國的廣播行業展現出積極的抗戰態度,全力投入服務抗戰事業,行業倫理自律不斷完善。1937年,為了團結群眾抗戰,集中力量做好宣傳與動員工作,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宣傳委員會擬訂《戰時廣播電臺統一宣傳辦法》。該辦法明確規定了戰時廣播管理、播音內容與規章,是一次廣播行業內部的自發實踐。《戰時廣播電臺統一宣傳辦法》規定了戰時廣播電臺節目設置,主要以這八類為主:“1.時事報告(取材申、新、時事、大公、時事午刊、新聞夜、大公晚、申晚); 2.勸募救國公債; 3.勸募慰勞物品及其他征集事項; 4.各類戰事指導; 5.外國語言演講及時事雜評; 6.抗戰歌曲演唱; 7.名人演講; 8.游藝勸募或宣傳。”從節目類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以往占絕大多數的廣播娛樂節目被剔除,所有節目的設置均圍繞抗戰與募捐,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同時,上海各界在丁守業、徐卓呆等人的建議下,聯合廣播界同仁成立了中國無線電播音協會,致力于推進播音事業,以輔助社會教育之實施,及改良材料,務期增加聽眾之知識,矯正國民之陋習,振作民族之精神。茅盾先生對此也大為贊賞,他認為廣播界進入了戰時狀態,風花雪月情調的開篇沒有了,平日里的平劇、大鼓、蹦蹦戲也不播送了,代替為抗日救亡歌曲與防空防毒演講,電臺還會將當日的新聞用半文半白的形式播送,一改往日之娛樂氣氛。《戰時廣播電臺統一宣傳辦法》還對節目進行了具體的規范,例如“時事報告節目可以自由播送,但是必須要在規定的報紙范圍內取材,不得無故刪減新聞原意。勸募救國公債節目由宣傳委員會統一撰寫稿件,各廣播臺宣讀,每三日更新一次。該辦法從根本上消除了廣播泛娛樂色彩,將各廣播臺統一起來,凝聚力量搞宣傳,為抗戰救國做服務。”
到了20世紀4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界對播音業務上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反思,逐步確立起廣播業務操作過程中的細節與規范。廣播從業人員對于廣播新聞的編輯問題提出了規范,認為新聞具有真實感,要讓受眾如親臨現場般的感受新聞事件,這樣才能把戰事新聞發揮最大化效果。廣播新聞常常會被新聞稿所拘束,不容易體現新聞的真實感,只有提升廣播新聞稿的編輯水平,方可實現。1.給性質分類,大體上不外乎國內和國際兩大類,如果是對國內播音,我們對于國內新聞自然可以分得較為詳細,政治軍事經濟等等;2.重新組織,將列舉式改為綜合敘述式;3.刪去瑣碎不重要的新聞和語句;4.把發電地點,通訊社以及日期編入新聞本身之內,來源相同的新聞可以合并時,則以上發電地點等三項不必重復;5.關于地點及日期,應以此地此時為標準,例如通信機構所供給之新聞原稿為華盛頓3日電,昨日此時,應改為據華盛頓的電報,2號那天華盛頓;6.第一次遇到人名地名,都應該說出全名,即使是很有名的,也應該如此。以上這些廣播新聞業務細節方面的改變,逐步提升了廣播新聞區別于報刊新聞的特性,增強了新聞的真實感與感染力,也讓聽眾更容易明白其內容,這也極大地提升了戰事新聞的傳播力,再現了戰場的真實情況。
同時,抗戰時期廣播工作者表現出的責任意識與愛國敬業精神更是可歌可泣,彰顯出媒體人高尚的職業道德素養。史料記載:“歷年來各電臺為國家為社會均竭誠服務,聊盡國民天職……國軍因戰略而西撤,同業等雖遠離祖國懷抱,而仍忠貞堅持發揚正義,不為敵偽利用,不怯強暴威脅,以國家至上民族為重,不惜犧牲一切,因之各電臺負責人時遭敵憲兵隊及偽警務處抓拘。”又如“在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的時期,重慶所有的民眾幾乎完全躲在防空洞里,那時重慶上空的炸彈如雨點般降下,重要的建設幾乎全部夷為平地,但中央廣播電臺的工作同志仍舊穩坐在號稱廣播大廈里面的麥克風前,執行他們神圣的職務,并不曾因為敵寇的疲勞轟炸,而有一分一秒鐘懈怠職守的情形。中央電臺工作同志,這種威武不屈的精神,在中國廣播史上實在是值得稱道的。”
廣播行業隨著社會化進程的加快與國際環境的變化而不斷進步,在大眾的監督與“批判”下,廣播的倫理思想發生了諸多改變。從起初的抵制廣播泛娛樂化與三俗,而后推行大眾廣播教育,提升國民文化素養;面對外國侵略,中國廣播界同仇敵愾,團結一致,摒除不良娛樂,充當對外宣傳與振奮國民之宣傳武器,為民眾提供服務;廣播行業從新聞業務出發,規范廣播新聞的稿件、內容、播音方式與形式,大大提升了廣播新聞的真實感與傳播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強化了抗戰廣播的感染力。各界對無線電廣播發展議題的批判與討論,推動了廣播媒介倫理思想的發展,逐步形成了抗戰廣播的倫理與責任框架。
注釋:
① 吳侍中:《廣播無線電播音者與收音者應有之道德》,《無線電問答會刊》,1932年第19期。
② 黃鑑村:《廣播無線電之使命》,《無線電雜志》,1934年第6卷第1期。
③ 雙十文化社:《雙十文化社播音宣言》,《雙十播音講義》,1933年第1期。
④ 《現階段所需要的播音》,《音苑》,1934年第7期。
⑤ 白狼:《音圈小訊》,《滬聲》,1936年第1卷第5期。
⑥ 竹銘:《無線電播音與社會改革》,《音苑》,1934年第3期。
⑦ 郭榮:《本市無線電》,《益世報》,1936年2月13日。
⑧ 徐卓呆:《無線電播音》,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3頁。
⑨ 楚狂:《中國無線電臺應收回自辦》,《民大政治學會月刊》,1925年第3期。
⑩ 王承樟:《無線電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戰時記者》,193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