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視閾下城市記憶的建構(gòu)與傳播*
■ 鄧 莊
城市是靠記憶存在的,歲月的積淀形成了城市的文化品格,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城市記憶,賦予了城市鮮明的個(gè)性特色,可以說(shuō),城市的個(gè)性特色是城市與植根于此的歷史、文化和社會(huì)實(shí)踐之間的關(guān)系的結(jié)晶,融入了關(guān)于城市的獨(dú)特性的集體歷史和記憶。2012 年,中央城鎮(zhèn)化工作會(huì)議明確提出新型城鎮(zhèn)化要“望得見(jiàn)山、看得見(jiàn)水、記得住鄉(xiāng)愁”。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huì)議提出“保護(hù)弘揚(y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延續(xù)城市歷史文脈,保護(hù)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chǎn)。”因此,加強(qiáng)城市記憶的研究,尤其是超越物質(zhì)環(huán)境的維度,開(kāi)掘在文化領(lǐng)域的深度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城市記憶領(lǐng)域內(nèi)分屬物質(zhì)空間、精神文化和社會(huì)交往等不同層面的問(wèn)題與現(xiàn)象整合到傳播立場(chǎng)加以考察,分析地理景觀、大眾媒介和日常生活三個(gè)空間場(chǎng)域中城市記憶的建構(gòu)與傳播,探討其價(jià)值與意義。
一、城市、記憶與傳播
城市與記憶密不可分。城市是人類(lèi)集體記憶的場(chǎng)所,城市記憶具有空間性,強(qiáng)調(diào)在城市空間中產(chǎn)生的記憶,是反映城市中的社會(huì)群體對(duì)城市各個(gè)時(shí)間斷面內(nèi)所有有形物質(zhì)環(huán)境和無(wú)形精神文化的共同記憶。①
一方面,城市是記憶的源泉,透過(guò)地方的生產(chǎn)是建構(gòu)記憶的主要方式之一,因?yàn)橛洃浽谌藗冋鎸?shí)的地方時(shí)和社會(huì)經(jīng)歷中,地方是重要的助記符。建筑學(xué)家多洛蕾斯·海登指出,由于地方對(duì)人的各種感官的綜合刺激,使地方成為強(qiáng)大的記憶源泉,位于都市地景歷史的核心②。哲學(xué)家凱西指出,機(jī)敏而鮮活的記憶自動(dòng)會(huì)與地方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在地方找到有利于記憶活動(dòng)并足以與記憶搭配的特質(zhì)。③因此,記憶自然而然是地方導(dǎo)向的,或至少是得到地方支撐的。
另一方面,記憶也賦予地方以情感和意義,使人們產(chǎn)生對(duì)于地方的依戀,成為創(chuàng)造地方感的重要方式。各種歷史文化景觀充盈著城市的記憶,塑造著城市地方感。當(dāng)我們把記憶和意義融入感知體驗(yàn),使城市成為一個(gè)個(gè)具有意義和情感的地方,就造就了令人難以忘記的地方特質(zhì),將一處處單純的物質(zhì)空間轉(zhuǎn)變?yōu)槊篮煤土钊擞鋹偟娜诵曰瘓?chǎng)所。正如故宮、胡同之于北京;外灘、豫園、石庫(kù)門(mén)之于上海;西關(guān)、沙面之于廣州;西湖、靈隱寺之于杭州;夫子廟、中山陵之于南京一樣,城市記憶賦予城市以個(gè)性化的鮮活生命力。
城市記憶離不開(kāi)媒介和傳播。建筑學(xué)者認(rèn)為,城市記憶是一種由城市記憶客體、城市記憶主體和城市記憶載體相互作用的連續(xù)演變動(dòng)態(tài)系統(tǒng)。城市記憶載體作為記憶顯形、保存和傳遞的媒介,使人們?cè)诨貞浥c體驗(yàn)中產(chǎn)生對(duì)城市的依戀與認(rèn)同。④由于科技發(fā)展,人們更多依靠書(shū)籍、報(bào)刊、電視或網(wǎng)絡(luò)等外在化記憶載體或裝置,而不是與人體、人腦密切相關(guān)的內(nèi)在記憶。傳播學(xué)者認(rèn)為,城市是一種媒介,此媒介不僅是大眾傳媒,它包含了傳播的各種方式和工具,如日常交流、郵政交通、印刷出版、各種物質(zhì)和文化空間,“城市的實(shí)質(zhì)是經(jīng)由傳播構(gòu)筑的網(wǎng)絡(luò)化的中介關(guān)系。”⑤。由于人們?cè)诂F(xiàn)代城市空間的體驗(yàn)是融合性的,物質(zhì)空間、傳播媒介、社會(huì)實(shí)踐共同構(gòu)筑了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的傳播、交往、溝通的過(guò)程,因此城市記憶是在實(shí)體空間、虛擬空間與人們的空間實(shí)踐中生成的。城市記憶傳播的意義不僅在于傳遞信息,還有社會(huì)交往、意義共享;傳播的媒介不僅是大眾媒介,還有物質(zhì)空間,乃至一切連接主客體的中介;傳播的目的不僅在于社會(huì)整合,還包括地方感的營(yíng)造、儀式感的實(shí)現(xiàn)、人與人關(guān)系的建構(gòu)。
總之,城市是人類(lèi)集體記憶的場(chǎng)所。城市記憶是時(shí)間的,也是空間的;是過(guò)去的,也是當(dāng)下的;是個(gè)人的,也是社會(huì)的。記憶客體和載體的豐富性、記憶生產(chǎn)者的靈活性和記憶消費(fèi)者的顛覆性,決定了傳播在城市記憶中的重要作用,媒介是城市記憶元素重要的培育者。
二、空間嬗變與城市表征
實(shí)體空間體現(xiàn)為地理意義上的物理性空間,城市正是利用物理的存在和物理性空間來(lái)營(yíng)造意識(shí)及意識(shí)空間,使意識(shí)能夠獲得最有力的表達(dá)和顯現(xiàn)形式。新文化地理學(xué)認(rèn)為,城市實(shí)體空間可以被納入媒介范疇,履行傳播信息的功能,構(gòu)成一個(gè)言論空間、內(nèi)容空間、情感空間和價(jià)值空間,可以通過(guò)符號(hào)學(xué)分析其能指和所指。⑥建筑符號(hào)學(xué)認(rèn)為,建筑形式作為一種象征符號(hào),意味著它要成為“能指-所指”的統(tǒng)一體,形式作為能指,總指向某個(gè)意義,“使有形的能指(物質(zhì)、材料和圍護(hù)體)清晰地表達(dá)出它的所指(生活方式、價(jià)值、功能)。”⑦每個(gè)城市都有屬于自己特色的城市景觀和城市建筑,包括紀(jì)念碑、歷史文化街巷、民居、博物館、工業(yè)遺產(chǎn)、特色商店等懷舊和紀(jì)念空間,它們是城市文化傳播的載體,也是城市特色的表征,具備獨(dú)特而豐富的傳播特性。
1.不同城市形態(tài)的記憶文本
城市記憶存在兩種不同形式,一種是由社會(huì)權(quán)力和體制保證的官方記憶,另一種是通過(guò)日常生活和人際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民間記憶。城市記憶的價(jià)值取向應(yīng)從大多數(shù)人的角度出發(fā),而非只考慮少數(shù)人的利益,或在大的官方記憶框架內(nèi)包容來(lái)自民間的豐富多彩的“小敘事”,使各種形式的城市記憶達(dá)成互補(bǔ)多元的發(fā)展,使城市成為一個(gè)可供不同個(gè)體解讀的多元文本。城市形態(tài)是城市實(shí)體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具體的空間物質(zhì)形態(tài),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獨(dú)特的城市文化傳承方式,反映了城市集體意識(shí)和價(jià)值觀等豐富意蘊(yùn)。⑧與官方記憶和民間記憶兩種不同記憶形式相對(duì)應(yīng),在城市形態(tài)的生成與發(fā)展中也表現(xiàn)出兩種不同的方式,體現(xiàn)出不同的象征意蘊(yùn),表達(dá)出不同的價(jià)值取向。
一種是自上而下的,預(yù)先經(jīng)過(guò)規(guī)劃設(shè)計(jì)的城市形態(tài),如紀(jì)念碑、紀(jì)念館等大型建筑、儀式大道等標(biāo)志性建筑,通常采用規(guī)整、有序、統(tǒng)一的結(jié)構(gòu),成為向公眾傳輸國(guó)家或地方的政治權(quán)力、社會(huì)等級(jí)觀念和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的記憶文本。它將城市物質(zhì)形態(tài)、儀式場(chǎng)所的秩序和形狀,由城市紀(jì)念碑與城市空間構(gòu)成的象征性場(chǎng)面等,預(yù)先規(guī)劃和確定下來(lái),在形式上成為城市鞏固制度,加強(qiáng)社會(huì)認(rèn)同的象征符號(hào)。如民國(guó)時(shí)期,國(guó)民黨政府就利用中山陵、中山紀(jì)念碑、中山紀(jì)念堂、中山公園、孫中山故居等一系列紀(jì)念空間的建構(gòu),傳播孫中山符號(hào)和三民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鞏固國(guó)民黨的統(tǒng)治,強(qiáng)化對(duì)中華民國(guó)的國(guó)家認(rèn)同。⑨
另一種是自下而上、自發(fā)隨意、無(wú)規(guī)則的城市形態(tài),諸如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庫(kù)門(mén)和里弄等眾多蘊(yùn)含民間記憶的普通民居和街巷,它們與表現(xiàn)城市歷史大事件的少數(shù)標(biāo)志性建筑相呼應(yīng),構(gòu)成城市的基礎(chǔ)單元。這種自然生長(zhǎng)的城市空間,在不規(guī)則和隨意中匯集了神話、傳說(shuō)、土制、慣例等各種本土傳統(tǒng)文化,隱藏了在使用方式、土地特征、社會(huì)習(xí)慣等方面的特定秩序與意義,展現(xiàn)了民眾的生存感知、生活體驗(yàn)相關(guān)的錯(cuò)綜復(fù)雜的生活世界。⑩尤其是歷史久遠(yuǎn)的傳統(tǒng)街區(qū)具有儲(chǔ)蓄、組織和再現(xiàn)城市記憶的功能,通過(guò)將場(chǎng)所意義向城市空間傳播與擴(kuò)展,能夠成為所在區(qū)域的文化核心,具有永恒的歷史文化價(jià)值。近年來(lái),傳統(tǒng)街區(qū)大規(guī)模拆舊建新,使得記錄歷史發(fā)展軌跡和城市空間演變的城市記憶載體消失,導(dǎo)致了嚴(yán)重的文化危機(jī)和城市“失憶”。
奧地利藝術(shù)史家阿洛伊斯·里格爾將紀(jì)念物劃分為“有意而為”和“無(wú)意而為”兩種。前者是指建筑物在建造之初就有著特殊的目的,從一開(kāi)始就是作為紀(jì)念物出現(xiàn)的;后者則是指那些為了滿足當(dāng)時(shí)人們的一般需求而建造的數(shù)量龐大的普通建筑。作家馮驥才說(shuō):“對(duì)于城市的歷史遺存,文物與文化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文物是歷史過(guò)程中具有經(jīng)典性的人文創(chuàng)造,以皇家和宗教建筑為主;而文化多為民居,正是這些民居保留著大量歷史文化的財(cái)富,鮮活的歷史血肉,以及這一方水土獨(dú)有的精神氣質(zhì)。”一座城市固然需要代表官方記憶的宏偉建筑,更需要富于民間和生活氣息,浸染地方傳統(tǒng)和文化記憶的民間建筑,構(gòu)筑一個(gè)由不同個(gè)體共同想象與認(rèn)同的城市。
2.作為記憶承載者的“非共時(shí)城市”
藝術(shù)家赫爾曼·呂博說(shuō):“那些在我們這個(gè)世間同時(shí)存在的非同時(shí)之物,從來(lái)沒(méi)有像今天這樣如此眾多。”在上海的城市景觀中,就可以解讀封建王朝時(shí)代、租界時(shí)代、社會(huì)主義時(shí)代、改革開(kāi)放時(shí)代等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文化景觀。塞爾維亞建筑師兼藝術(shù)家波格丹諾維奇由此把城市定義為“收藏記憶的倉(cāng)庫(kù)”,空間化的歷史具有一種結(jié)構(gòu),而這種結(jié)構(gòu)正是在文化殘跡的疊加與沉積中“有機(jī)生成”的。德國(guó)文化記憶學(xué)者阿萊達(dá)·阿斯曼將柏林稱為“羊皮紙城市”,羊皮紙上新舊相疊、層層堆積的文字喻示著幾經(jīng)興廢變遷的城市,它循環(huán)往復(fù)地改變、覆蓋與沉積,造成了歷史本身的層層相疊。作為記憶承載者和歷史物化紀(jì)錄的城市,其意義就在于保留參差異質(zhì)的城市面貌,體現(xiàn)思想和歷史參與者的多樣性,互相矛盾的歷史圖景才能夠始終得以被識(shí)讀,成為一座“非共時(shí)的城市”。
外灘建筑群,作為上海開(kāi)發(fā)最早、最集中的近代建筑群,見(jiàn)證了中西文化和不同社會(huì)群體對(duì)上海都市空間操控權(quán)的爭(zhēng)奪,也表征了上海近百年來(lái)城市特質(zhì)的變遷,但無(wú)論風(fēng)云變幻,始終與上海現(xiàn)代性發(fā)展的命運(yùn)聯(lián)系在一起。20世紀(jì)90年代對(duì)外灘的“上海再造”突出了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對(duì)話與融合,無(wú)論是浦西舊有景觀的修復(fù),還是浦東陸家嘴的建設(shè),均營(yíng)造出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shí)連接的空間氛圍,使外灘成為一個(gè)既傳承地方歷史文化,又建構(gòu)日常公共交往的城市空間,其核心是現(xiàn)代性的交流交往本質(zhì);而上海的人民廣場(chǎng)則與之相反,在大規(guī)模重建改造中切斷了歷史傳統(tǒng)的再造,成為消除歷史文化物理空間記憶的場(chǎng)所。
可以說(shuō),每一代人對(duì)于過(guò)去、現(xiàn)在和未來(lái)的需求都必須在空間中進(jìn)行重新的考量與安排,每個(gè)時(shí)代需要將反映當(dāng)代社會(huì)生活與時(shí)代精神的信息有機(jī)結(jié)合進(jìn)歷史的物質(zhì)遺存中,使創(chuàng)造與保護(hù)之間的沖突得到新的協(xié)調(diào)與解決。城市景觀塑造著城市記憶,因此,從簡(jiǎn)單的大拆大建或?qū)Τ鞘袀鹘y(tǒng)歷史形式的單純復(fù)制模仿轉(zhuǎn)向?qū)τ诔鞘猩顚拥奈幕c精神內(nèi)涵的關(guān)注與發(fā)掘,才能為保留過(guò)去與發(fā)展未來(lái)尋找最佳平衡點(diǎn),使城市空間成為蘊(yùn)含豐富的情感、記憶和個(gè)性特色的場(chǎng)所。
三、媒介敘事與地方記憶
虛擬空間是運(yùn)用各種策略和手段編碼組構(gòu)賦予空間以社會(huì)歷史意義的文化和精神性空間。大眾媒介在城市集體記憶的社會(huì)建構(gòu)中有重要作用,影視、新聞、文學(xué)、廣告等建構(gòu)了城市記憶的文化空間和精神性空間,成為城市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21世紀(jì)以來(lái),城市記憶的媒介敘事在多個(gè)層面展開(kāi),從對(duì)西方現(xiàn)代性和中國(guó)現(xiàn)代化諸多問(wèn)題的反思批判,到對(duì)地方文化和鄉(xiāng)土記憶的追溯發(fā)揚(yáng),特定歷史事件的平反式敘述,懷舊消費(fèi)書(shū)寫(xiě)的盛行,乃至普通民眾生活史、特定群體口述史的勃興,城市記憶的書(shū)寫(xiě)呈現(xiàn)了多樣化的敘事與想象方式,建構(gòu)了不同的城市記憶與記憶中的城市。但任何城市書(shū)寫(xiě)都是片段和局部的,選擇性記憶或遺漏仍是媒介塑造集體記憶的核心機(jī)制,我們要追問(wèn)的是選擇什么,為何如此選擇,以及如何呈現(xiàn)。從敘事主題與策略來(lái)看,城市記憶書(shū)寫(xiě)呈現(xiàn)懷舊化、問(wèn)題化、平民化、商品化、視覺(jué)化、典律化等特點(diǎn),發(fā)揮了塑造城市意象與地域意義,召喚市民認(rèn)同,示范都市消費(fèi)風(fēng)尚,實(shí)施都市文化治理的功用。
1.塑造城市意象與地域意義
城市記憶的書(shū)寫(xiě)營(yíng)造出一種懷舊感,是對(duì)本土和傳統(tǒng)失落的憶念。現(xiàn)代化及其全球化帶來(lái)本真性和家園感的喪失,引起了地方的焦慮和反抗,懷舊成為抵觸和反抗全球化的一種反應(yīng)。懷舊敘事經(jīng)常選擇富有地域特色的老建筑、歷史人物、民間藝術(shù)、民俗、美食、傳統(tǒng)手工藝等作為對(duì)象展開(kāi),提供地方性知識(shí),塑造獨(dú)特的城市意象,彰顯地域獨(dú)特性,借此建構(gòu)對(duì)地方的認(rèn)同與歸屬。
從物質(zhì)世界到精神生活,懷舊書(shū)寫(xiě)勾勒出城市的“傳統(tǒng)形象”,如自然性、鄉(xiāng)村價(jià)值觀、詩(shī)意和空間性,構(gòu)成一個(gè)和諧完整的“傳統(tǒng)世界”。在書(shū)寫(xiě)者的描述中,這是一個(gè)緩慢、悠閑、舒適的世界,缺乏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快捷性、流動(dòng)性和變化;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功利和物質(zhì)性相比,它代表著一種非功性和精神性;現(xiàn)代化是反自然的,它是與自然和諧一致的;它還聯(lián)系著詩(shī)意,具有一種特別的美學(xué)形式。傳統(tǒng)的世界并非死去的“過(guò)去”,在懷舊書(shū)寫(xiě)中被表現(xiàn)為與當(dāng)代都市人的自我認(rèn)同和鄉(xiāng)愁記憶相關(guān)的“精神家園”,成為反思現(xiàn)代性、療治現(xiàn)代都市病的良藥,每個(gè)城市都在建構(gòu)屬于自己城市的“傳統(tǒng)”。
2.展現(xiàn)個(gè)體記憶和多元爭(zhēng)辯
城市記憶的書(shū)寫(xiě)中體現(xiàn)出記憶是要加以質(zhì)疑、追問(wèn)、詮釋和闡述的場(chǎng)域,需要聯(lián)系各種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尤其是提出不同的記憶來(lái)質(zhì)疑和補(bǔ)充原先不假思索的主流記憶書(shū)寫(xiě)。城市記憶書(shū)寫(xiě)的問(wèn)題化特征,體現(xiàn)在諸如城市災(zāi)難敘事中的創(chuàng)傷記憶、舊城改造中的民間記憶、寓含鄉(xiāng)土情感的本土文化記憶、城市歷史敘事中的微觀個(gè)體記憶、相對(duì)于主流官方敘事的平民記憶、相對(duì)于國(guó)族史觀的少數(shù)族裔記憶,乃至彌漫于文化消費(fèi)中的懷舊記憶中,都包含了獨(dú)立性、反抗性的記憶元素,表現(xiàn)出對(duì)官方記憶和主流記憶的補(bǔ)充與抵制。
城市記憶的書(shū)寫(xiě)還展現(xiàn)出對(duì)平民日常生活的關(guān)注以及個(gè)體私密獨(dú)特經(jīng)驗(yàn)的表陳,往往揭示的是那些為正史所忽視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民俗禮儀、世態(tài)風(fēng)情等,如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lè)、老街巷的前世今生、民間手工藝的起落興衰等等。它呈現(xiàn)了豐富多樣的個(gè)人城市體驗(yàn)和記憶,指向的是微觀的、邊緣的“小歷史”,而不是宏觀的、主流的,受制于一定意識(shí)形態(tài)標(biāo)準(zhǔn)而寫(xiě)成的、對(duì)人類(lèi)社會(huì)發(fā)展有重大影響的“大歷史”。歷史學(xué)者認(rèn)為,歷史書(shū)寫(xiě)有三種范式:認(rèn)知性的歷史、認(rèn)同性的歷史與承認(rèn)性的歷史。記憶的平民化體現(xiàn)為一種新的歷史書(shū)寫(xiě)范式:承認(rèn)性的歷史,強(qiáng)調(diào)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歷史書(shū)寫(xiě)中的在場(chǎng),重現(xiàn)個(gè)體的經(jīng)歷,描述曾經(jīng)的生存狀況,而不是尋找真理與規(guī)律,與重視個(gè)人權(quán)利的歷史發(fā)展趨勢(shì)相適應(yīng)。
3.示范都市消費(fèi)風(fēng)尚
媒介記憶的書(shū)寫(xiě)凝聚在商品上,連接上物的邏輯,在消費(fèi)領(lǐng)域營(yíng)造生活風(fēng)格,成為按圖索驥的消費(fèi)游憩指南,體現(xiàn)出記憶商品化的特色。無(wú)論是商品還是非商品化的消費(fèi)經(jīng)驗(yàn),都是日常生活的基礎(chǔ)和根本經(jīng)驗(yàn),也是喚起和塑造記憶的線索。記憶的書(shū)寫(xiě)和商品、消費(fèi)的聯(lián)結(jié)可以分成以下幾類(lèi):一是媒介記憶凝聚的商品引發(fā)購(gòu)買(mǎi)、收藏和懷舊消費(fèi)的欲望,如郵票、書(shū)籍、旅游地紀(jì)念品,以及任何可以買(mǎi)賣(mài)收藏的商品;二是媒介采取重返歷史現(xiàn)場(chǎng)的方式來(lái)尋找恢復(fù)記憶的可能,其中提及的很多地點(diǎn)場(chǎng)景是店家或商圈,直接指向消費(fèi)的體驗(yàn),如各種小吃飲食和懷舊食品;三是媒介記憶制造了關(guān)于地點(diǎn)的審美神話來(lái)激活現(xiàn)代城市生活的平庸和乏味,引發(fā)人們的審美沖動(dòng),循著媒介記憶蹤跡和游憩休閑指引,尋訪史跡和自然生態(tài)景觀,而這也經(jīng)常是商品和消費(fèi)之旅。對(duì)于城市地點(diǎn)的想象和記憶演化成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親身體驗(yàn),媒介環(huán)境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發(fā)生一種互文關(guān)系,媒介記憶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建構(gòu)意義可見(jiàn)一斑。
4.實(shí)施都市文化治理
記憶的典律化,指記憶書(shū)寫(xiě)具有指引市民記憶和認(rèn)同的示范效果,蘊(yùn)含著特定記憶凸顯與遮蔽的邏輯,體現(xiàn)出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正當(dāng)化的作用。當(dāng)前主流媒介的城市記憶書(shū)寫(xiě),一般由媒體編輯記者、文藝界人士、學(xué)者專(zhuān)家或具有一定文化資本的市民,即由中產(chǎn)階級(jí)文藝人士主導(dǎo)或代言,文本著重于文字或意象的審美雕琢,反映出特定的文字風(fēng)格和影像美學(xué),相對(duì)排除了底層民眾、青少年、上流階層、罪犯、同性戀、少數(shù)族裔等的城市記憶。城市歷史與記憶的敘事雖然豐富多樣,但不免有美化和隱惡揚(yáng)善的傾向,較少直接呈現(xiàn)城市社會(huì)的多元競(jìng)爭(zhēng)與沖突。雖然敘事中常言及多元和異質(zhì)并陳,但往往以正面角度視之,并指出其增加城市活力,或歸諸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步的負(fù)面效應(yīng),缺乏批判性視野。記憶的問(wèn)題化所開(kāi)啟的可能性仍被收束在特定的慣例與典律之中。
通過(guò)對(duì)傳統(tǒng)的挖掘和反省,城市記憶話語(yǔ)表達(dá)了對(duì)國(guó)家、民族和地域文化身份的認(rèn)同與對(duì)全球同質(zhì)化的反抗,建構(gòu)起包括城市共同體的多個(gè)層面的想象共同體,維系并強(qiáng)化個(gè)體的地域歸屬感和文化認(rèn)同。城市記憶在社會(huì)實(shí)踐場(chǎng)域上連接了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和文化經(jīng)濟(jì),通過(guò)塑造城市獨(dú)特意象,將歷史文化元素轉(zhuǎn)化為商品,鼓勵(lì)對(duì)商品化的城市“本真性”的消費(fèi),進(jìn)而充實(shí)文化產(chǎn)業(yè)的根基,成為都市文化治理的重要內(nèi)容。
四、日常生活與城市記憶
城市日常生活空間并非單純的精神文化空間或物質(zhì)實(shí)體空間,而是兼具兩者,以物質(zhì)為質(zhì)料,以文化為靈魂,既是真實(shí)的又是想象化的一種亦真亦幻的生活場(chǎng)所,索亞稱之為“第三空間”。日常生活領(lǐng)域由日常消費(fèi)活動(dòng)、日常交往活動(dòng)和日常觀念活動(dòng)構(gòu)成,承載著人們的日常交往、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休閑娛樂(lè)、購(gòu)物消費(fèi)等社會(huì)生活內(nèi)容。當(dāng)代社會(huì)學(xué)肯定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日常生活世界是為社會(huì)生活提供基本意義的世界,這一世界所包含的各種日常實(shí)踐構(gòu)成了我們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主體,正是這些不言而喻的活動(dòng)支撐起人類(lèi)社會(huì)的大廈。”城市記憶往往來(lái)源于民眾日常生活史,身體化的操演記憶是記憶的重心,民眾正是通過(guò)各種社會(huì)性、日常化的行為實(shí)踐來(lái)體驗(yàn)、傳播與認(rèn)同城市記憶。
1.日常生活實(shí)踐與城市記憶
日常生活能有效觸發(fā)記憶,克里斯汀·波斯?fàn)栐凇都w記憶的城市》一書(shū)中指出:“不同于歷史,記憶是與人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是沉淀和傳承在人的生活世界的歷史。”身體實(shí)踐表達(dá)和保持著集體的記憶,城市記憶不能脫離公眾而在公共生活之外產(chǎn)生,需要民眾通過(guò)社會(huì)性、日常化的行為實(shí)踐來(lái)維持與認(rèn)同,并向下傳遞延續(xù)。
當(dāng)代以來(lái),一種新的空間觀興起,強(qiáng)調(diào)空間的身體性或身體空間,涉及人類(lèi)感知的多樣性或身體經(jīng)驗(yàn)。以身體體驗(yàn)作為感知城市的方式,一個(gè)城市空間就可能轉(zhuǎn)變?yōu)楸徊煌黧w所占有和使用的多樣性場(chǎng)所,開(kāi)掘出城市空間的嶄新意義。較早關(guān)注身體空間的是法國(guó)哲學(xué)家梅洛-龐蒂,在他看來(lái),空間是一種身體化空間,“我的身體在我看來(lái)不但不只是空間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沒(méi)有身體的話,在我看來(lái)也就沒(méi)有空間”,即一切空間的結(jié)構(gòu)與意義都需要身體的參與。美國(guó)社會(huì)學(xué)者保羅·康納頓強(qiáng)調(diào)了習(xí)慣的身體操演對(duì)于表達(dá)和保持記憶的重要性,他認(rèn)為,記憶在身體中有兩種沉淀方式:體化實(shí)踐和刻寫(xiě)實(shí)踐,體化實(shí)踐強(qiáng)調(diào)身體的在場(chǎng)性,用在場(chǎng)的動(dòng)作和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記憶,“每個(gè)群體對(duì)身體自動(dòng)化委以他們最急需保持的價(jià)值和范疇”,其存在方式和獲得方式使它具有特別記憶效果,即沉淀在身體上的習(xí)慣記憶可以更好地保存過(guò)去。人文地理學(xué)家戴維·西蒙認(rèn)為,理解地方的關(guān)鍵成分是身體移動(dòng)性,他用“身體芭蕾”“時(shí)空慣例”“地方芭蕾”等概念來(lái)表達(dá)地方生成的過(guò)程,身體的日常移動(dòng),作為一種具身實(shí)踐,在反復(fù)持續(xù)中形成生活經(jīng)驗(yàn),孕育出基于地方的主體認(rèn)同,地方正是透過(guò)人群的日常生活而日復(fù)一日操演出來(lái)的。市民在長(zhǎng)期相處過(guò)程中結(jié)成了豐富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這種無(wú)形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對(duì)于市民生活及居住區(qū)的穩(wěn)定、對(duì)于維持共有的城市記憶有著強(qiáng)大的內(nèi)在力量。因此,地方歷史和市民對(duì)空間的集體記憶和每日生活行走的體驗(yàn),建構(gòu)出富有豐滿歷史意義、個(gè)人情感和感官體驗(yàn)的城市“地點(diǎn)”,濃重的地方認(rèn)同令市民對(duì)此類(lèi)城市空間形成強(qiáng)烈的共同感情,增強(qiáng)了城市的可溝通性。比如上海石庫(kù)門(mén)民居就是一種地方的、禮儀的空間,包含著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地方記憶和親密的鄰里關(guān)系,石庫(kù)門(mén)的改造雖保留了老弄堂的建筑特點(diǎn),但人際關(guān)系、鄰里文化,特有的弄堂經(jīng)濟(jì)、特有的街頭文化已經(jīng)發(fā)生改變了。故而只有保護(hù)地方居民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保留其長(zhǎng)期積累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使居民日常交往方式、交往距離、交往頻率得以維系,才能使城市記憶在生活世界演進(jìn)中得以傳承,將城市的歷史脈絡(luò)延續(xù)下去。
2.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與城市體驗(yàn)
隨著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網(wǎng)絡(luò)對(duì)日常生活的中介和滲透是全方位的,重新建構(gòu)起一個(gè)以意義和體驗(yàn)為基礎(chǔ)的新空間。在這個(gè)空間中,真實(shí)與虛擬交融,物質(zhì)屬性與社會(huì)屬性相互嵌入,人類(lèi)的生存空間被徹底改變,即人們不僅生活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也生活在虛擬世界里。這種利用數(shù)字化中介手段在虛擬空間進(jìn)行的“在線”實(shí)踐活動(dòng),與人們?cè)趯?shí)體空間的“在世”形成了一種相互嵌入的生存關(guān)系。因此,在新媒體助力下,促進(jìn)城市記憶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形構(gòu)一種虛實(shí)交融的日常傳播實(shí)踐,促成了一種體驗(yàn)式傳播空間的形成。
近年來(lái),基于智能手機(jī)應(yīng)用的文化遺產(chǎn)導(dǎo)覽與體驗(yàn)在全球范圍內(nèi)不斷涌現(xiàn),體現(xiàn)出城市文化傳播從信息化到圖形化再到體驗(yàn)化的數(shù)字化進(jìn)程。在此類(lèi)應(yīng)用中,借助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虛擬現(xiàn)實(shí)(VR)、增強(qiáng)現(xiàn)實(shí)(AR)等技術(shù),突破時(shí)空限制,再現(xiàn)歷史場(chǎng)景,人的感官得以延伸和放大,用戶體驗(yàn)得以優(yōu)化,能夠沉浸式地認(rèn)知感受歷史與文化。如上海思南露天博物館的最大特色是體驗(yàn),大屏幕、二維碼、真實(shí)虛擬電影院、VR攝影機(jī)等嵌入實(shí)體空間,使其成為一個(gè)被技術(shù)信息流貫穿的物質(zhì)場(chǎng)所,人們?cè)诳臻g中游走體驗(yàn),身體感官被全方位調(diào)動(dòng)。思南展陳的歷史文化地標(biāo)、遺跡等都標(biāo)志了二維碼,參觀者通過(guò)電子地圖尋找零散分布的20個(gè)展品,手機(jī)掃描二維碼后進(jìn)入由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構(gòu)成的虛擬空間,人的感官在實(shí)體與虛擬空間之間來(lái)回穿梭,人們感受的思南是融合了虛實(shí)的“復(fù)合空間”。又如2017年百度 AR 實(shí)驗(yàn)室發(fā)布的一個(gè)AR技術(shù)應(yīng)用中,用戶打開(kāi)手機(jī)百度 App 對(duì)準(zhǔn)北京正陽(yáng)門(mén),就可以呈現(xiàn)出古人進(jìn)出城門(mén)的生活場(chǎng)景;英國(guó)泰恩-威爾郡檔案館開(kāi)發(fā)出一款運(yùn)用 GIS 技術(shù)的手機(jī)應(yīng)用,當(dāng)用戶行走在街道上,打開(kāi)移動(dòng)應(yīng)用終端,就會(huì)呈現(xiàn)出所在街區(qū)的老照片等,并講述相關(guān)歷史或趣聞。在此類(lèi)應(yīng)用中,傳播從單一的虛擬空間轉(zhuǎn)變?yōu)閷?shí)體空間與虛擬空間并存、轉(zhuǎn)化、融合的狀態(tài),傳播由此成為一種城市體驗(yàn)活動(dòng),讓人從視覺(jué)、聽(tīng)覺(jué)、觸覺(jué)、嗅覺(jué)、知覺(jué)多個(gè)維度感受城市,建立起直觀而深刻的城市形象。
數(shù)字媒介極大推動(dòng)了更多植根于本地的、更加個(gè)人化的交流與傳播活動(dòng)。自媒體的快速發(fā)展,活躍的個(gè)人日常信息的傳播與發(fā)布,使得日常傳播成為一個(gè)充滿創(chuàng)意、表達(dá)、認(rèn)同與抵制的多樣空間。比如人們到長(zhǎng)沙太平老街游玩,品嘗小吃,購(gòu)買(mǎi)禮品,感受老街的懷舊風(fēng)情,并在大眾點(diǎn)評(píng)網(wǎng)上發(fā)表自己的評(píng)價(jià),在朋友圈上傳照片,在微博上交流感受體會(huì)。通過(guò)這樣的移動(dòng)傳播實(shí)踐,人們實(shí)現(xiàn)在物理、社會(huì)和想象空間之間的移動(dòng),豐富了自己的體驗(yàn)以及與社會(huì)的關(guān)聯(lián)。
在這些實(shí)例中,數(shù)字技術(shù)嵌入日常生活實(shí)踐的身體體驗(yàn),促成了大眾與城市記憶的接觸與對(duì)話。因此,城市記憶不僅僅是城市景觀、建筑、文物等各類(lèi)物質(zhì)實(shí)體,也不僅僅是文字、影像中的虛擬敘事,它借助新媒體技術(shù)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將城市看作是一個(gè)由地理、信息與意義網(wǎng)絡(luò)交織而成的交流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城市文脈是表現(xiàn)在、潛藏于、滲透進(jìn)這多重網(wǎng)絡(luò)之中。”新媒體的價(jià)值體現(xiàn)在打通這些網(wǎng)絡(luò),創(chuàng)造出新的社會(huì)實(shí)踐,使得傳播成為人與人、人與城市的交往與對(duì)話。
五、結(jié)語(yǔ)
城市的功能除生產(chǎn)、消費(fèi)和居住外,其重要的價(jià)值在于創(chuàng)造和傳播文明。如劉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通過(guò)集中物質(zhì)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類(lèi)交往的速度,并將它的產(chǎn)品變成可以儲(chǔ)存和復(fù)制的形式。通過(guò)它的紀(jì)念性建筑、文字記載、有序的風(fēng)俗和交往聯(lián)系,城市擴(kuò)大了所有人類(lèi)的活動(dòng)范圍,并使這些活動(dòng)承上啟下,繼往開(kāi)來(lái)。”由此可見(jiàn),城市文化的塑造、城市凝聚力的增強(qiáng),需要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shí)的交流融合,城市共同體的建構(gòu)依賴跨越時(shí)空的傳播編織意義網(wǎng)絡(luò)。城市記憶的傳播需要給不同的記憶內(nèi)容與形式提供空間,給不同價(jià)值觀、審美趣味以充分的尊重,最大限度促成民眾對(duì)話、交流和理解,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取向的多樣性和對(duì)多元文化的認(rèn)同,真正建構(gòu)以人為主體,以有益于人的體驗(yàn)和解放為價(jià)值取向的城市空間。
注釋:
① Rossi A.TheArchitectureofTheCity.Cambridge:MIT Press.1984:79.
② Hayden D.ThePowerofPlace:UrbanlandscapesasPublicHistory.Cambridge:MIT press.1995:18
③ Casey E.S.Remembering:APlenomenologicalStud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186.
④⑧⑩ 朱蓉,吳堯:《城市·記憶·形態(tài):心理學(xué)與社會(huì)學(xué)視維中的歷史文化保護(hù)與發(fā)展》,東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8、70頁(yè)。
⑤ 孫瑋:《城市傳播:重建傳播與人的關(guān)系》,《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7期。
⑥ 李蕾蕾:《媒介—空間辯證法:創(chuàng)意城市理論新解》,《人文地理》,2012年第4期。
⑦ 周正楠:《媒介·建筑——傳播學(xué)對(duì)建筑設(shè)計(jì)的啟示》,東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頁(yè)。
⑨ 陳蘊(yùn)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hào)的建構(gòu)與傳播》,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頁(y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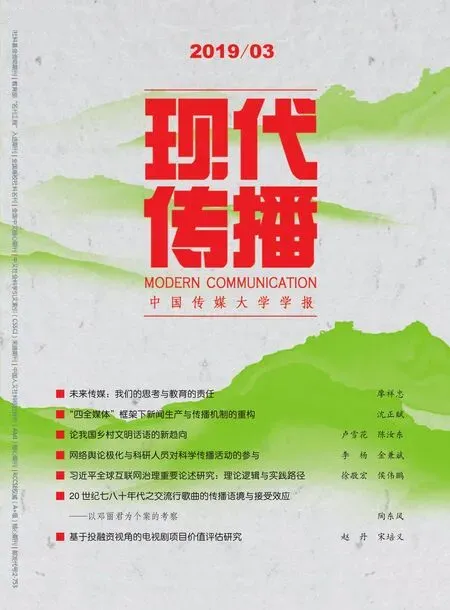 現(xiàn)代傳播-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年3期
現(xiàn)代傳播-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年3期
- 現(xiàn)代傳播-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Twitter涉華輿情極化現(xiàn)象研究
——以中美貿(mào)易爭(zhēng)端為例 - 傳媒公司共享型領(lǐng)導(dǎo)對(duì)內(nèi)創(chuàng)業(yè)行為影響研究
- 基于投融資視角的電視劇項(xiàng)目?jī)r(jià)值評(píng)估研究*
- 文化價(jià)值主導(dǎo)型電視劇綜合評(píng)價(jià)體系構(gòu)建研究
- 記憶、詢喚和文化認(rèn)同:論傳統(tǒng)文化類(lèi)電視節(jié)目的“媒介儀式”*
- 列寧主義與蘇區(qū)黨報(bào):中央蘇區(qū)“新聞干部”對(duì)列寧報(bào)刊思想的理解與執(zhí)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