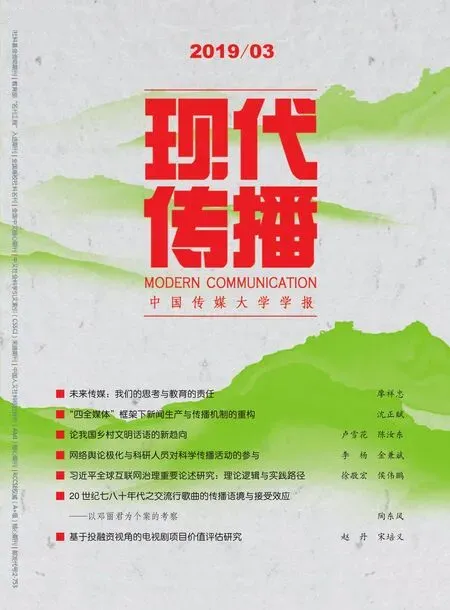以破碎的整體感重構產業美學:移動音頻生產的本土經驗
■ 戰 迪
伴隨著數字互動網絡技術的高速迭代,信息傳播和交易的成本大幅降低,從而催生了包括喜馬拉雅FM、蜻蜓FM、荔枝FM、企鵝FM、鳳凰FM、木耳FM等在內的一大批新型移動音頻App產品。作為獨立于中國傳統意義上國有媒體的“公用媒介”(public use media),移動音頻產品以人人均享的信息發布、傳播、分享、接受的模式創造著前所未有的聲音信息資源形態,實現了以社會資本為主體,國家權力管控,市場調節的對自由資源的整合營銷機制。如果說在我國20世紀30年代因電波資源稀缺、私人電臺盛行而一度造成了產業秩序的混亂,新中國成立后所有電臺收歸國有后秩序井然,1986年珠江經濟廣播電臺開播所締造的“珠江模式”、1992年上海電臺和東方電臺所創造的“廣播活動+品牌主持人”的“東廣模式”,以及此后不久北京電臺推出的“音樂/交通臺模式”再造了商業廣播的傳奇,那么,在新世紀伊始,隨著電視業的蓬勃發展、新媒體的推陳出新,受眾接受習慣的改變令傳統廣播業再次陷入低谷。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移動音頻產品應運而生。2013年3月喜馬拉雅App正式上線,時隔不久類似的音頻軟件紛紛亮相搶灘市場份額。而2013年也無疑因此成為了中國移動音頻產業元年。QM數據平臺顯示,2017年移動音頻電臺產品日活躍用戶規模已達到1400萬人,每日使用共1.2億次,日均累計使用時長達到4.3億分鐘①。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廣新媒體副總裁李向榮聲言,“當前出現了網絡視聽產品用戶規模和使用率進一步提升、網絡自制內容全面進入精品化、用戶付費意識養成,用戶需求更加細分化等趨勢。”②據易觀千帆數據統計,截至2017年末,國內移動音頻用戶呈爆炸式增長,移動音頻用戶一線城市居多,占比43.4%;中高消費者占比46.25%;用戶年齡集中于36—40歲,占比35.27%。面對著如此優質的消費群體,傳統廣播擁抱新媒體的信心倍增,為迎接新一輪的技術挑戰蓄勢待發。
一般認為,美學是以美的本質、審美意識、審美創造和審美鑒賞等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學科。相應的,產業美學作為美學研究與產業研究的交叉學科,是以現代化產業活動中審美生產與接受為研究對象的新興領域。作為新媒體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移動音頻生產集文化、審美、市場于一體,具有高度的綜合性和應用性特征。它建基于后現代產業系統,生產流程的現代性和媒介產品的后現代性同在,并融合和適應于生態美學、技術美學、審美經濟學、審美應用學和審美經濟學等學科基礎。特別是作為傳媒藝術的試驗田,其前沿的媒介性、大眾參與性、科技性特征與傳統藝術形態對舉,別開生面。對移動音頻產品的本土經驗進行深入探索,不僅延展了傳統廣播產業的理論與實踐范疇,更為產業美學的創新實踐提供了絕佳的現實藍本。
產業美學就是打破文化工業的創作慣性,以美學思維重構文化產業。在工業時代,這種理念僅僅是一種構想,但在后工業時代,特別是技術賦權和審美日常化的綜合語境中,產業美學獲得了全新的生成空間。而大音頻產業的勃興就是明證。在這種生產時空中,碎片化的音頻片段被整合為一副整體性的審美印象。特別是根據具體用戶的喜好,大數據,算法革命更是將一個個分散的音頻信息編織成一幅幅宏大的百衲衣,具有整體性的美學圖景。
一、從PGC、UGC到PUGC:深度參與的接受美學機制
當下國內移動音頻產業的版圖基本由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兩部分構成,前者以喜馬拉雅FM、蜻蜓FM、荔枝FM三大巨頭為代表,吸納了國內超過8000萬的用戶資源;后者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開發的中國廣播、HITFM,以及地方電臺相繼開發的聽聽FM(北京電臺)、阿基米德(上海東方廣播)、大藍鯨(江蘇電臺)等為代表,這些App產品以移動電臺的新模式創新了傳統廣播的傳播方式。
客觀而言,相較于民營移動音頻產品,傳統廣播電臺出品的移動產品存在如下幾方面的短板和劣勢:由于傳統廣播電臺商業化運營模式的保守性、大數據使用和社交互動性等方面的不足,使得其運營能力偏弱;對傳統廣播內容模式的依賴性較強,難于形成互聯網化的創新內容體系,因此原創能力不足;同時,由于對傳統電臺廣播內容版權保護能力有限,導致盜版內容泛濫成災,直接影響了移動電臺的收益。不難想見,在疾風驟雨的新媒體傳播環境中,傳統電臺的移動化進程并不順利。反觀民營移動音頻產業,其高度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卻具有超強的自我調節和自適應能力,由此在互聯網商業的浪潮中激流勇進。舉例為證,喜馬拉雅FM以粉絲經濟和社群經濟為著眼點,不僅依靠傳統廣告收益,還推陳出新,開發了“音頻淘寶”、主播工作臺等應用程序,便于受眾檢索聲音信息和發布個性化聲音信息,以此來吸引會員。同時,與運營商合作分成、針對地方有聲文化地標產品服務收益、對受眾內容付費習慣的培養等,都以靈活多變的方式擴大了收益渠道,創新了商業模式。同樣作為民營移動音頻產品的荔枝FM,竭力打造社群電商模式,與運營商合作建立閱讀基地,用“打賞+會員制”的方式開通虛擬物品商業路徑。再以企業人力資源和對資本市場的融入為切入口,調研發現,市場占有率第一的喜馬拉雅500人左右的員工隊伍涵蓋了技術研發、智能硬件、大數據分析、產品運營、派駐海外等多個工種,其集約、高效程度均遠超傳統媒體。加之C輪融資億元以上,創造了200億人民幣的企業估值。市場占有率居第二、三位蜻蜓FM和荔枝FM的員工也僅有400人和200人,經融資后市場估值分別達到25億和30億。可以說,民營移動音頻產品盡管沒有強大的政府資金支持,卻借助船小易掉頭的優勢,以小博大,先發制人,及時跟進市場,創新產品。
不同于傳統媒體,互聯網行業音視頻內容的發展經歷了從用戶原創內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專業生產內容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和專業用戶生產內容PUGC(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三個明晰的發展階段。如果說以早期人人網、優酷視頻、土豆視頻為代表的UGC生產方式伴隨著Web2.0概念的提出而倡導上傳與下載并重的個性化體驗,將個人內容共享推向主流,以重組后的優酷土豆網率先創辦《邏輯思維》《暴走漫畫》《飛碟說》等合伙人原創視聽品牌節目為代表,PGC產品用專業化的內容生產強化了多元視角、民主傳播和虛擬社會關系,那么,喜馬拉雅FM倡導并率先推出的PUGC產品則打通了上下游的區隔,增強了深度參與的用戶體驗,重構了互聯網音頻的生態鏈。
值得強調的是,移動音頻App內容生產以“UGC+PGC+獨家版權”的形式呈現,也就是說,以UGC表現形態的內容,卻產生出接近于PGC的專業化效果。但PUGC產品卻很大程度上克服了UGC產品內容粗糲,PGC產品因生態閉環而缺乏受眾參與等方面的不足。在上游運營機制方面兼具個性化色彩,用戶深度參與和專業化水準的同時,也為草根主播提供了系統性的孵化通道;中游聯通了手機、車聯網等技術平臺,充分借助大數據技術支持為主流用戶“畫像”,靶向式定位目標受眾,從而以算法推送的方式為用戶智能推薦;而下游則采取移動終端用戶、智能硬件、公共交通工具等多線布局。
一般而言,與傳統媒體的內容生產方式不同,包括私營與國營在內的移動音頻產品努力打破傳統媒體線性傳播的束縛,創造各種環形通路來實現點對點的互動式傳播效果,進而激發用戶的深度參與熱情。特別是在其內容序列中,一般意義上的新聞報道、述評已經不是主流。相反,生產方另辟蹊徑,將延伸自傳統廣播文藝的諸多內容形式反復打磨,形塑為帶有強烈個性化色彩的付費內容。基于用戶在使用移動音頻App產品時對有聲小說、人文講座、情感故事、經典相聲和時尚脫口秀等語言類產品的青睞,明星與素人相輝映的整合營銷方式被廣泛采納。艾寶良播講的“盜墓”系列小說、高曉松主講的《曉說》、青音的心理談話節目、郭德綱的《品俗文化史》、點擊量超過3000萬的素人脫口秀《然哥脫口秀》等一大批風格迥異的音頻內容相繼亮相,在滿足目標用戶復雜的口味的同時,也利用評論、點贊、打賞、訂閱、收藏等種種途徑構建起傳受雙方的深度對話機制。
媒介化生存背景下,藝術與審美的疆界大大泛化,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文藝理論的創新互為表里。曾幾何時,發端于18世紀的現代美學極力將藝術與工藝、藝術與非藝術在其核心概念中加以厘清。20世紀中葉,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精神領袖阿多諾對文化工業的激烈批判成為了一代知識分子的集體精神記憶,以古典主義文學藝術來救贖社會的呼號猶在耳畔。今天,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然過半,藝術顯然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和專利。泛媒介時代最顯著的特征莫過于普羅大眾在技術賦權的背景下將18世紀貴族把玩的藝術,19世紀新興資產階級收藏的藝術,20世紀大資本家壟斷的藝術收歸己用,并通過充分改造,形成服務于現代社會需求的文明系統。杜威就曾在其《藝術即經驗》中曾聲言,要建設一種嶄新的美學樣態,“這種美學要尋找藝術與非藝術、高雅藝術與通俗藝術、藝術與工藝之間的連續性,而不是像以前的許多美學家所做的那樣,致力于區分。”③今天,我們謳歌包括移動音頻產品在內的一切文化創意產業,正是從一個側面為藝術的人民性正名,同時,也是對既往孤芳自賞的古典主義美學態度的一種反駁。找尋文化創意產業與藝術理念的連續性問題,可以作為一條通路,探索后工業文明生態中產業美學的共性與個性。顯然,傳媒藝術的大眾參與性是這其中不容規避的一個重要現象和規律。
在傳媒藝術的時代譜系中,作為深度參與者的新媒體用戶,其規模之巨大、卷入程度之深入、對技術美學之熟稔是前所未有的。用戶的審美習慣和欣賞趣味逼催著創作主體以時不我待的激情積極投身創意創新的洪流。作為一種創造美的技術,藝術的發展離不開技術的支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媒介社會中,藝術的表達途徑和作用范疇空前放大。大眾參與的技術支持與權力增殖不僅彰顯了審美領域中的民主意識,更為接受美學的實踐提供了絕佳的注腳。如果說傳統視聽媒介研究領域對受眾意識的關注還停留在闡釋學的視角,強調受眾期待視界與審美距離的辯證關系的話,后工業文明語境中的接受美學方案則打破了傳者中心與受者中心的博弈,以某種反中心話語的張力勾連起傳受雙方求同存異、平等對話的機制。而巴赫金所倡導的對話未完成性也在人人共享的文化廣場中最終得以印證。亦如接受美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伊瑟爾所提出的“召喚結構”,文本中埋藏著諸多“空白”,“一種尋求缺失的連接的無言邀請”④。
高曉松在《曉說》這樣一個純粹的聽覺文本中,常常被聽眾戲稱為“坑王”,他時而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社會文化熱點縱談某一話題,聽取用戶的建議調整節目方案,補充、添加故事信息,時而會在“種草”后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取消預定主題,任性地選取自己嶄新的話題。這樣的案例在《小沈龍脫口秀》《李誕脫口秀》等素人音頻節目中時有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曉說》等移動音頻節目并非完整而自足的文本闡釋鏈,而是一種碎片化的啟發性結構,留給聽眾更多的“空白”,邀約他們自行閱讀、填充、完型。從這個意義上講,移動音頻產品從UGC、PGC向PUGC演變的歷程正是技術迭代導引下受眾深度參與的接受美學機制的形成過程。
二、從工業噪音到聲音風景:聽覺文化的復興與推廣
20世紀60年代西方后現代文化的初興引發了學界關于視覺文化的思考,直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米歇爾正式提出“圖像轉向”的概念,則標志著“讀圖時代”業已得到全面確認。當代高度發達的視聽傳媒技術在助推 “媒介化生存”的現實圖景的同時,也不斷佐證著“視覺中心主義”的話語地位。在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人們一直信奉著“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思維理念,并篤信視覺文化的力量遠超聽覺。即便1997年學者韋爾斯在其專著《重構美學》中大膽地提出了大眾文化聲音轉向的觀點,也并沒有引發過多的學術關注。值得注意的是,韋爾斯聲言:“聽覺文化的興起可以說是電子傳媒一路暢行之后的必然結果,它更具有一種后現代氣質,固然它沒有視覺文化的延續性和同質性,但是它具有電子世界的共時性和流動性。”⑤然而,在唱響電視、唱衰廣播的21世紀前后,這種觀點因得不到實踐的支撐,顯然不能獲得廣泛的認同。
令人詫異的是,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移動音頻產品的異軍突起,在“視覺霸權”的大眾文化領地中另辟蹊徑,獲得驚人的產業奇跡,不能不說,現代人內心深處深藏的聽覺基因被全面激活。曾經從大眾傳播、分眾傳播到今天垂直傳播的理論構想已經成為現實,移動音頻產品的自我訂閱和基于算法推送的內容共同建立起用戶專屬的“聲音List”,麥克盧漢所言的“重新部落化”構想在聲音產品的粉絲社群中被搭建成型。自此,以小博大,挑戰視覺文化的聽覺文化也重又浮出水面。對此,有學者不無夸張地預言:“人類和我們星球的繼續存在,只有當我們的文化將來以聽覺為基本模式,方有希望。因為在技術化的現代社會中,視覺的一統天下正將我們無從逃避地趕向災難。惟有聽覺與世界那種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號的關系,才能扶持我們。墮落還是得救,災難還是拯救這就是不同選擇的圖景,人們正試圖以它來搭救我們,打開我們的耳朵。”⑥
在西方學界,作為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聲音文化(Sound Culture)一般被認為是“研究對音樂、聲音和噪音以及相關科技的物質生產及消費,以及上述這些是怎樣在歷史和不同的社會里變遷的”⑦。將這一概念接榫到國內實踐語境中,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移動音頻產品的橫空出世不僅驗證了聲音文化相關理論推演的合法性,更為相關產業美學的勃興帶來了現實啟發。如果說“五四運動”時期的演說作為一種聲音政治直接促成了新文化運動的興盛,那么,近年來南開大學文學院周志強教授所反復批判的“唯美主義的耳朵”則直指后現代工業文明下流行音樂生產領域中的“工業噪音”。誠然,在后工業時代,泛娛樂化、戲仿、機械復制等生產機制一定程度上異化了聲音美學,導致“靈韻的消逝”,但我們依稀可以看到,在移動音頻產業所搭建的文化藝術舞臺中,精英話語有的放矢、平民話語異軍突起,二者同臺競技,形成了彼此制衡又平等對話的良性氛圍。借用西方學者雷蒙德·默里·謝弗的提法,“聲音景觀”(Soundscape)的價值正日益凸顯。
聲音文化的重裝出場并非歷史的巧合,作為視覺文化的補充,它填充了現代人視覺依賴的種種不足。作為一種哲學和美學的實踐,移動音頻產業具有著先天的認知優勢。首先,從生理狀態出發,日常生活中的人們可以“閉目”,但無法做到“塞聽”,于是,作為信息的接收者,傾聽主體處于一種開放的狀態,特別是在移動音頻產品的收聽方面,用戶本能地基于一種內斂的主體性體驗來接受信息,兼聽則明,這無形中抑制了主體性的張揚與泛濫;其次,相較訴諸于感性的視覺文化,聽覺文化的深度性較強,“傾聽主體不是要像現代視覺文化中視覺主體表現出的欲望貪婪和止于圖像表層,也不是要鼓噪饒舌地制造無盡的噪音污染,而是要通過傾聽他者的聲音,進入事物本質的深層,真正達到對世界存在的本真理解并在這種理解過程中實現對自我生存意義的高度升華”⑧;最后尤為重要的是,移動音頻產品本身并不負載過高的技術含量,更多訴諸于聲音形式的美感和聲音內核的理性法則,是真正意義上的“內容為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視覺文化生產中過度張揚的技術理性起到糾偏的作用。
在大音頻產業系統中,借助新媒體平臺發軔并廣泛釋放的聲音能量,不再僅僅局限于訴諸聽覺的物理性傳播情態,而是通過技術與審美、物理與心理、社會與文化的綜合疊加形塑為豐富的意義系統。西方學者早前曾指出:“聲音直接引起激動,作為有機體本身的震動。聽覺與視覺常常被列為兩種‘理智的’感官。實際上,盡管聽覺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理智范圍,耳朵在本性上卻是情感的感官。”⑨一如視覺風景,當聲音圖譜被打磨、加工、復制、擴散為聲音景觀時,聲音文明與社會變遷的相關性必然越發緊密,它既是一種對自然界的超越,也是對政治、經濟、社會、思想領域的全面擁抱。聽者當然可以用審美的耳朵聆聽伊甸園般的“聲音花園”,也可以用社會學的耳朵傾聽多元的批判話語,更可以用政治學的耳朵體悟社會變遷的精神動力。總之,移動音頻產品的高超之處恰恰在于以某種生活審美化的方式打造出用戶專享的私人領地,而“解讀聲音景觀問題的總鑰匙,不在于聲音自身,而在于選擇性聆聽、塑造聲音變遷的聽覺性感知與思維”⑩。
如果說早前的廣播可以被視為監聽公共空間的聽覺背景,那么,新媒體語境下的音頻產品則是耳機深處的“私密事件”。可以說,在以耳機為媒介的獨一無二的個性化聲音世界里,無論是流行歌曲、經典小說、文化講壇、心理訪談,還是作為聲音雜耍的脫口秀,都將聽者與真實世界暫時隔離,在健身房、私家車、安睡前的床頭塑造出一個自足的聆聽時空,極大地滿足了人們便攜、自由訴求的同時,也扮演著后現代流浪者的角色,亦如“自給自足的城市旅行者,為了應付各種天氣和各種情況并在一個自我包圍、自我設置的聲音氣泡中穿過城市所必需的裝備”。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移動音頻不僅成功地將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聽覺產業化運作和推廣,更在聽覺主體性的建構中有意無意地充當了語境化的動力系統,從而實現“對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對于神秘的虛懷敞開”。
三、破碎的整體感:技術驅遣下的“品位共同體”建構
關于后現代文化中“碎片化”閱聽體驗的相關論述已屢見不鮮。當然,從技術決定論的立場出發,我們當然可以相信技術文明對審美文化領域的僭越已是不爭的事實。現代傳媒技術的高速迭代發展豐富了傳媒藝術的表現手段,擴大了審美接受和體驗的范圍,特別是通過產業手段強化了信息傳播與分享的民主化進程,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技術賦權的驅動下,碎片化的垃圾信息泛濫成災,非個性與偽個性的媒介內容以商業性取代了審美性,直接導致了閱聽者審美感受力的鈍化和惰性。既往學者多以批判的眼光審視技術理性對表現理性的傷害,并直陳消費民主性不等同于文化民主性,認為前者以市場交換為基本邏輯遮蔽了商品背后的世俗性和功利性,后者盡管在形式上被區分為若干圈層和層級,卻在本質上相互滲透、融通。
作為創意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移動音頻產品具有顯著的大眾消費屬性,在垂直付費的引導下,被細分為無數復雜的枝系,碎片化特征十分明顯。特別是草根話語的崛起似乎抹平了藝術與生活的距離,再次脫去了古典藝術神秘而不可見的外衣。隨著多元話語在新媒體平臺的泛濫,南京大學周憲教授所言的“意義的通貨膨脹”顯而易見。“審美文化在符號的生產規模方面和能力上,早已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意義的生產上,卻和這樣的規模正好形成鮮明的反比關系。產品越多,意義卻越平庸越淺薄。”當然,這種“意義貶值”的現象在傳媒藝術產業化進程中是一個難以逾越的特殊階段。特別是UGC、PUGC互聯網視頻生產的崛起,更以喜劇性為主導性審美范式消解了“宏大”與“崇高”的美學傳統,助長了理想型文化向世俗型文化的轉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相較于傳統視頻產品和當下流行的短視頻產品,移動音頻產品依托聲音傳播本身開放性、深度性、理智性的認知特質,并借助垂直性付費模式的支持,在私密化的信息接受氛圍中重構了用戶的審美趣味與閱聽習慣,進而形成了不同類型、層級的聲音文化彼此平行、交叉傳播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在移動音頻產品中,審美文化領域中的古典文化、現代文化與后現代文化并非各自鐵板一塊,擁有著彼此絕緣的專屬領地。相反,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回歸傳統與倡導和諧的古典文化在有聲讀物的歷史、人文板塊被娓娓道來,并在文化名家散文化的講述方式中被賦予了現代性啟示;相應地,在《曉說》《領讀者》《邏輯思維》中曾經被認為與大眾文化格格不入,“拒絕交流”與“拒絕闡釋”的現代主義文化在保留了其思想自主性、趣味對抗性和文化嚴肅性的前提下,也俯下身軀,以道德關懷和審美堅守的名義反思社會現實,希圖起到批判與重建的應有之義;特別是一度被認為擊碎“元敘事”,打通藝術與非藝術、審美文化與非審美文化之間的區隔,并“生活在碎片之中”的后現代文化,努力尋求各不同社會、自然層級領域受眾之間的可通約性。喜馬拉雅點擊量過4000萬的《然哥脫口秀》《上班脫口秀》等產品亦為典型代表。
從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相關理論出發,當代文化產業中存在著“有限生產場”(The de-limited field of production)和“大規模生產場”(The large-scale field of production)兩類場域。如果說前者指稱藝術生產和消費的群體同為文化界圈內人士,而后者則將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相剝離。實際上一直以來前者都是通過“命名權”對后者行使宰制性權威的。然而在移動音頻生產領域,兩個場域之間的界限已經相當模糊,生產者和消費者彼此交合,在錯綜復雜的傳受鏈條中,碎片化的聲音信息被縫合成一張色彩斑斕的百衲衣,呈現為不同個性人群的“品位共同體”。而這些“共同體”群落既不是以古典、現代、后現代三大審美文化形態和結構來進行劃分,也不是基于社會政治、經濟地位進行劃分,而是在復雜的分化和整合機制中被一種“破碎的整體感”所籠罩。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盡管宏大敘事依舊失語,“中心情結”蕩然無存,畸形審美仍然存在,但慶幸的是,邊界的消弭和類型的重組令嚴肅藝術不再絕緣,知識分子的優越感得以復現,草根達人在縱情狂歡之余也會在產業美學的發展脈絡中找尋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動力。最終,在移動音頻生產領域,“品位共同體”漸次被搭建成型。
總之,移動音頻產業所構造的產業美學是以技術理性為先導,大眾深度參與為表征,現代化工業化流程為手段,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體驗”與“品位”為內核的后現代媒介文明。誠如杰姆遜對審美文化的現實構想,紀念碑式的作品已然不復存在,“而是對以前存在的文本碎片的無窮重組:一種拆除其他書以裝配自己的元書,一種核撿其他文本碎片的元文本”。
注釋:
①② 《共商媒體融合大計 首屆“廣播新聲音大會”在杭州開幕》,中國新聞網,http://www.zj.chinanews.com.cn/news/2017/1222/9051.html,2017年12月22日。
③ 高建平:《文化創意是產業時代的藝術追求》,《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④ [德]伊瑟爾:《本文與作者的交互作用》,《上海文論》,1987年第3期。
⑤ [德]沃爾夫岡·韋爾斯:《重構美學》,陸揚、張巖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頁。
⑥ 陸濤:《文化傳播中的聽覺轉向與聽覺文化研究》,《中州學刊》,2016年第12期。
⑦ Trevor Pinch and Karin Bijsterveld.Introductionto“SoundStudies:NewTechnologiesandMusic”.Special Issu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4(5),2004:636.
⑧ 肖建華:《當代審美教育:聽覺文化的轉向》,《中國文學研究》,2017年第3期。
⑨ John Dewey.ArtasExperience.New York:Perigee Book,1980:264.
⑩ 王敦:《“聲音”和“聽覺”孰為重——聽覺文化研究的話語建構》,《學術研究》,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