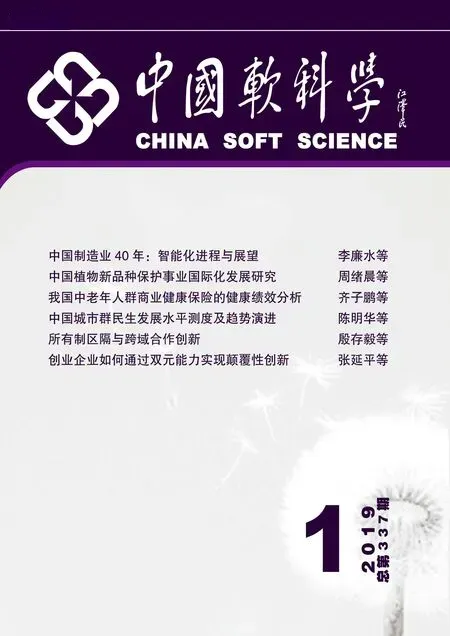我國中老年人群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分析
——基于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的經驗證據
齊子鵬,周韻晨,夏 蕾
(1. 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中央財經大學 保險學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出,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實現國民健康長壽,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標志,也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1]。黨的十八大報告也提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戰略目標。中國有著近14億人口,醫療衛生問題關系著億萬人民健康,是一個重大民生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啟動醫藥衛生體制改革。1998 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我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正式確立[2]。2003 年,國務院轉發由原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標志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逐步建立,針對農村戶籍人口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正式建立[3]。2007 年,依據國務院《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我國各地開始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工作,目標是覆蓋城鎮非就業人口[4]。2016 年,國務院出臺《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要求“推進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制度整合,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此后全國各地開始探索三大基本醫療保險管理機構的整合方式[5]。
經過近40年的發展,制度層面的“全民醫保”已經基本實現,除了少數重復參保、遺漏參保的人員,城鎮職工、新農合、城鎮居民三大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已基本實現“應保盡保”。與此同時,三大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等的建立以及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使得全體國民“病有所醫”的目標基本實現[6]。從效果上看,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對促進醫療服務可及性、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有效緩解 “看病難”和 “看病貴”問題、 提高居民消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近20年來我國醫療保險的發展令世人矚目[7-8]。改革的成就應該得到肯定,但是也應看到,我國醫療保險制度尚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雖然職工醫保籌資水平較高,但是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籌資水平則較低,籌資水平的城鄉、人群差異造成了醫療保險待遇的城鄉差異、群體差異,“全民醫保”制度的公平性有待完善;由于公立醫院改革未破除逐利機制,高昂的醫療費用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由于部分地區籌資水平較低,農村居民自費醫療費用占其收入的比重在相當部分地區近年還在上升,“看病貴”仍是農村居民就醫的首要難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居民對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服務和產品型消費品有著越來越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保基本、兜底線、可持續”的框架設計使其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差異化、多層次的保險需求[6];此外,由于許多歷史原因,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存在的分散管理體制、費用繳納方式差異等問題也都成為醫療保險制度發揮應有作用的阻礙。
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逐步建立、完善和演進的,是和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醫藥衛生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等相配套的,因此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中的保障水平不高、差異化不足等問題短時間內難以取得進一步的進展,只能尋找其他的方式作為突破口和替代方式。從國際經驗看,社會保障制度較為健全的國家,其醫療保障體系一般是通過政府和企業合作構建起一張以基本醫療保險為基礎、以商業健康保險為補充的“雙層結構”的安全保障網[9],公民的基本醫療保障由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網提供,在此之外的風險保障則由商業保險公司承擔。因此,在我國醫療保障體系建設中,要建立高效的醫療保障體系,商業健康保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健康保險應該承擔費用補充型和項目增補型保障的角色[10]。商業健康保險具有經營范圍廣、方式靈活、保障程度根據社會需求隨時變動的特點,可以充分運用市場機制調節供求之間的不平衡,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的健康保障選擇,彌補基本醫療保險無法覆蓋的領域[11]。
由于我國醫療保險制度幾經變革,截至目前才形成較為穩定的框架,并且國內外不同國家的“醫保”制度存在較大差異,為避免概念混淆和誤用,本文將國內外與個體健康有關的保險統稱為醫療保險,在這個概念下,我國的醫療保險包括基本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等。
商業健康保險是以被保險人的身體為保險標的,保證被保險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傷害時的直接費用或間接損失獲得補償的保險,包括疾病保險、醫療保險、收入保障保險和長期看護保險[12]。商業健康保險與基本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農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商業健康保險與基本醫療保險都是以人的身體和生命力作為保障標的,但是商業健康保險在參與方式、費率厘定、保費繳付方式、保障程度與經營主體方面存在差異。參與方式方面,商業健康保險是通過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自愿保險合同而形成的損失補償機制。費率厘定方面,商業健康保險保費純粹以個人面臨的風險大小而定;繳費方式上,商業健康保險采用個人繳付方式,且繳費額與保障程度呈正相關關系;保障程度方面,基本醫療保險注重“保基本”,而商業健康保險則可以提供特殊的醫療保障需求;經營主體方面,商業健康保險均為保險公司自主經營,是完全的市場化行為。2017年,我國商業健康保險保費收入達4389.46億元,商業健康險占全行業保費收入比重達12.0%,健康險深度為0.53%,健康險密度為315.8元/人。從1982年我國恢復商業健康保險業務以來,盡管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無論是深度還是密度都與發達國家有一定差距,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13]。
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對醫療保險的績效進行過實證檢驗,他們對于醫療保險的績效研究主要集中在醫療保險的經濟績效和健康績效兩個方面。經濟績效方面,醫療保險的正向經濟績效已被實證結果廣為驗證,但是關于醫療保險健康績效的實證研究則較少[14],并且研究結論出現了一定的分歧:實證結果表明醫療保險對于個人的健康績效可能具有正向影響[15],也可能并沒有顯著影響[16]。那么作為我國醫療保險一部分的商業健康保險,它的健康績效如何?在我國三大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完善的情況下,商業健康保險能否改善和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對于這些問題,目前學術界還缺乏相應的探討。因此,正確評價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對于我國醫療保險體系的完善以及制定科學合理的商業健康保險發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利用CHARLS數據,對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進行實證研究。由于國內外學者關于健康保險對參保者健康水平影響的研究較少,因此醫療保險的“健康績效”尚無統一定義。本文參考程令國、張曄相關研究中的定義,將醫療保險的健康績效定義為保險對提高參保者健康水平的作用[17]。
本文共分為如下幾個部分: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第三部分介紹本文的數據來源。第四部分對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模型以及變量設置進行介紹。第五部分為實證部分,對CHARLS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并進行相應的分析。最后一部分為本文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橫跨計劃經濟時代和市場經濟時代,不同時期的指導思想、操作辦法有很大差別,保險的績效不能概一而論。本文將醫療保險的范圍確定為基本醫療保險領域(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農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健康保險領域。目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三大基本醫療保險的績效方面,鮮有關于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績效的實證研究。
(一)基本醫療保險
現有關于基本醫療保險績效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基本醫療保險的經濟績效和健康績效兩個方面[13]。由于本文聚焦醫療保險的健康績效,因此文獻綜述部分就不展開醫療保險的經濟績效。就健康績效而言,基本醫療保險對于個人健康績效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衡量,一是醫療保險可能會影響個人對于醫療服務利用的選擇;二是醫療保險是否會顯著提升個人的健康水平。
醫療服務利用選擇方面,Lei and Lin(2009)認為,新農合雖然取得了較大的覆蓋率,但是所發揮的作用有限。通過整理和運用CHNS數據(2000,2004,2006),他們發現新農合在促進個人采取積極的預防措施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參合人員更加注重事前的體檢,但是參合者在正規醫療服務方面的支出并未顯著增加[18]。Sun等(2009)對山東臨沂的農戶進行了實地調研,結果表明,在實施新農合前后,擁有新農合的個人大病支出的發生率僅僅從8.98%下降到了8.25%[19]。就城鎮居民而言,官海靜和劉國恩(2013)指出,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在改善居民住院服務利用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有限,經濟條件較差的個體更容易出現應住院未住院的情況[20]。黃楓、甘犁(2010)以城鎮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利用CLHLS數據(2002—2005年)通過比較兩部分模型、樣本選擇模型及擴展的樣本選擇模型同樣得出,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鎮老年人的家庭自付醫療支出,但是總醫療支出反而相較無保險個體高出28%—37%[21]。Xin等(2013)利用2008年CHARLS數據及兩部模型分別研究了城居保、城職保、新農合三種醫療保險制度對于門診及住院行為等醫療服務的影響,結果表明三種制度的影響有所不同,總體來看,盡管對于提高醫療服務利用率有正向作用,但效果仍然有限[22]。
個人使用醫療服務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追求健康,因此健康保險對于參保者健康水平即健康績效的影響必須得到考慮[23]。胡宏偉等(2012)利用傾向得分匹配和雙重差分相結合方法對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城居保)的作用進行評估,發現“城居保”沒有顯著改進所有居民的健康,但顯著改善了低健康者的健康水平,其中主要是促進了老年人和低收入群體的低健康者的健康改善[24]。李湘君等(2012)的研究發現,新農合促進了參合農民選擇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就診的機會,提升了農民對醫療服務的有效利用,同時也提高了參合者的健康水平,但是新農合首先提高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到定點醫療機構就診的概率,之后這種影響擴大到低收入和高收入參合者[25]。程令國等(2012)采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CLHLS)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新農合可以提高參合者的健康績效[17]。但是有些學者的研究對基本醫療保險的健康績效提出了質疑。Chen等(2010)的研究僅僅發現新農合對于教育水平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是未發現新農合對于樣本的健康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26]。吳聯燦等(2010)采用CHNS數據對新農合的健康績效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新農合制度對農民健康改善具有積極影響,但效率不高、影響有限[27]。于大川等(2016)基于傾向得分匹配方法對社會醫療保險對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的作用效果進行評估,研究顯示社會醫療保險可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認知功能等健康指標,但相較而言,對于自評健康和日常活動能力的改善效果則較為不明顯[28]。
(二)商業健康保險
關于發達國家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JM Froelich等(2013)在文章中稱擁有健康保險并不等于享有醫療保健,他們的研究表明,擁有保險并不等同于在單一機構獲得門診骨科護理,每個群體面臨的獲得醫療服務的費用負擔并不清楚[29]。Thornton等(2008)利用1999-2000年州層面的面板數據,通過以企業規模和工會會員身份作為工具變量,發現為未參保人群提供商業健康保險保障后,大大降低了成年人死亡率并且每年成功挽回超過75000人的生命[30]。Kang等(2009)以最普遍的胃癌作為健康衡量指標,針對韓國補充私人醫療保險(SPHI)與胃癌病人的患病、治療、醫療服務利用以及生存率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實驗結果表明補充私人醫療保險是促使個體增加醫療服務利用、并提高胃癌生存率的關鍵因素[31]。就發展中國家而言,關于商業健康保險健康績效額研究較少。Nyman等(2005)使用巴西的數據來估計在獲得私人補充醫療保險的情況下健康狀況方面的改善,發現通過健康保險獲得的可調整的生活質量的成本與增加福利的成本效用比率是一致的[32]。田玲等(2014)分析了基于新農合的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比較了既是新農合參合者又購買了商業健康保險的群體與僅參加新農合的群體之間的健康水平的差異,研究結果表明商業健康保險對于個人健康水平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33]。
通過對有關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目前大多數研究主要針對基本醫療保險的經濟績效和健康績效展開,對于商業健康保險的關注十分有限,更鮮有關于商業健康保險健康績效的實證研究。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居民的消費需求愈發多樣,商業健康保險的獨特作用愈發突出,但是與商業健康保險有關的研究卻稍顯不足,這為本研究的開展提供了思路。
三、數據來源
本文個人層面的數據來自“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簡稱 CHARLS)” 2013年和2015年開展的全國基線調查。CHARLS是對中國中老年人家庭及個人進行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是隨機抽取的家庭中 45 歲及以上的人。CHARLS問卷內容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家庭結構和經濟支持,健康狀況,體格測量,醫療服務利用和醫療保險,工作、退休和養老金、收入、消費、資產,以及社區基本情況等。CHARLS 項目于 2011年開始進行全國基線調查,對樣本以后每兩年追蹤一次,CHARLS數據目前更新至2015年。為了保證樣本的代表性,CHARLS基線調查覆蓋了全國150個縣、區的450個村、居,至2015年全國追訪時,其樣本已覆蓋總計1.24萬戶家庭中的2.3萬名受訪者,總體上代表中國中老年人群。
為排除其他形式的補充醫療保險對于考察商業健康保險績效的影響,本文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這三大類作為社會醫療保險的代表,去掉所有參加公費醫療、醫療救助及其他保險的樣本。整理CHARLS數據可知, 2013年,共有17039個樣本擁有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其中354個個體擁有商業健康保險,16685個個體未購買商業健康保險;2015年,共有17938個樣本擁有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其中604個個體擁有商業健康保險,17334個個體未購買商業健康保險。

表1 2013、2015年調研樣本參保情況
四、模型設定
(一)內生性問題
通過對前人研究的梳理發現,個人對于新農合等政策性醫療保險的購買是綜合多方面因素考慮的結果,包括家庭經濟狀況、個人自身的特征等等,這意味著擁有和不擁有醫療保險的個體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差異,即這兩類個人以及家庭的特征變量分布也可能是不同的。由于商業保險屬于個人自愿購買,個人的經濟、社會因素更會影響個人的保險選擇行為,因此商業健康保險必然存在自選擇行為[34]。如果我們觀察不到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效應,可能就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可能是醫療保險確實不影響個人或者家庭的健康水平。第二種可能是醫療保險具有健康效應,但是由于沒有考慮自選擇問題,從而得到有偏的結果。
為了盡量消除自選擇帶來的有偏估計問題,需要將數據分為控制組和干預組,以便形成對照。由于本文所采用的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估計量(PSMDID)法是一種加入時間變量的因果推斷方法,因此需要不同時間點的數據。基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本文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本文將2013、2015兩年的數據按照時間順序分為前、后兩期。接下來本文將干預組定義為前期參加了社會醫療保險但未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但是后期擁有了商業健康保險的個體的集合,將控制組定義為前期和后期都僅擁有社會醫療保險的個體的集合。對于2013年和2015年的調查數據而言,干預組為“2013年參加社會醫療保險但未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但在2015年擁有了商業健康保險”的個體,控制組為“2013年及2015年都僅擁有社會醫療保險”的個體,由于CHARLS為大規模人工調查,因此存在數據缺失等問題,經過篩選,最終選取的干預組與控制組如下表所示。控制組樣本數12990個,干預組樣本數311個,二者共13301個。

表2 2013/2015年控制組和干預組分組情況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主要衡量個人的健康水平。已有研究中,Lei等(2009)使用“自評健康”和“過去四周內生病或受傷次數”考察新農合的健康績效[18],本文參考Lei和Lin的研究方法,同時予以擴展,將衡量健康水平的指標分為以下四類:一是個人的自評健康水平;二是個人醫療服務使用情況,包括醫療服務使用情況、生病與治療情況;三是個人的認知健康水平,包括記憶、繪畫、計算等衡量指標;四是個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所有指標通過受訪者對問卷相關問題的回答進行評價,變量匯總說明情況見表3。
2.解釋變量
調查數據表明,超過90%的受訪者擁有社會醫療保險,因此本文先將沒有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少數群體剔除,把“只有社會醫療保險”的個體當作控制組;“既有商業健康保險,又有社會醫療保險”的個體當作干預組,進而將“是否參加商業健康保險”作為解釋變量。該變量為虛擬變量,對干預組賦值為1,控制組賦值為0。干預組和控制組的定義參見模型設定中內生性問題一節。
3.協變量
協變量是實驗者不能操控,但可以影響實驗結果的獨立變量。本研究中,為了得到商業健康保險對于個人健康績效的準確估計,本文引入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情況、家庭過去一周支出、家庭過去一月支出、家庭過去一年支出、家庭過去一年收入,上述控制變量組成觀測協變量。
(三)模型設定
本文利用基于核匹配(Kernel Matching)的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別對干預組和控制組進行了處理,為改善樣本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偏差,本文構建了一個比較試驗,干預組為參保群體,控制組為未參保個體但是與干預組非常接近的個體(可以作為反事實代替干預組在沒有參保時的情況)。通過比較兩組的健康水平,我們就可以識別商業健康保險對于個體健康水平的影響程度。
在評估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時,我們必須要考慮由于居民自愿選擇是否參加商業健康保險所引發的選擇性偏誤。該偏誤可能基于參保年齡、收入、財富狀況等可觀測特征,也可能基于參保時健康狀況、預期未來收入流的穩定性等不可觀測特征。為消除這種偏誤,本文采用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該方法的優勢在于,一方面,作為非參方法,即使在商業健康保險對投保人的影響為非線性時,也能保證結果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同時結合了傾向得分匹配(PSM)與雙重差分方法(DID)的優點,通過傾向得分匹配對控制組實現更精確處理,在構造控制組時只選擇落到“共同支持(common support)”區間的未投保商業健康保險的個體,即為每個干預組個體在控制組中找到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 即利用Logistic或Probit模型估計出的個體參加商業健康保險的概率值)相近的對象進行匹配分析。配對后兩組個體除“是否參加商業健康保險”存在差異,其他各方面特征均盡可能相似,從而可消除參保行為非隨機性所引發的、基于可觀測特征的樣本選擇性偏誤和因混淆因素所產生的偏誤[35]。而在此基礎上的雙重差分可有效排除來自不可觀測且不隨時間變化的特征所引發的選擇性偏誤,即通過在傾向得分匹配基礎上,對比干預組健康水平在所選調研期間的平均變化與相匹配的控制組在所選調研期間的平均變化之間的差異,最終得到同時消除基于可觀測特征及不可觀測特征的樣本選擇偏誤,得到“干凈”的政策處置平均效應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具體而言,ATT可表示為(Rosenbaum & Rubin 1985;Heckman 1997)[36-37]:


(1)

在具體實現過程中,本文利用了Probit模型來估計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同時在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時,采用了核匹配(Kernel Matching)方法。本文通過STATA 14.0軟件實現計量分析。

表3 變量匯總說明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變量描述
表4給出了2013年和2015年干預組和控制組相關變量的描述統計分析結果。由表4可看出,在2013年未參保商業健康保險之前,干預組和控制組的差異較為明顯。自評健康方面,控制組的均值高于干預組高出19.7個百分點;在個體認知能力方面,干預組低于控制組的指標有記憶力自我評價、繪畫能力;而干預組高于控制組的指標有計算能力和識別能力;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干預組高于控制組的指標僅有“對未來充滿希望”和“很愉快”兩個;醫療服務使用情況方面,干預組在1個月內去醫院頻次、1個月內生病頻次略高于控制組,但是在1年內住院頻次方面干預組略低于控制組,干預組和控制組在醫療服務使用情況方面的差異并不明顯;控制變量的指標中,干預組的平均年齡小于控制組,受教育程度也低于控制組,家庭支出和收入方面,干預組均高于控制組。
相較于2013年調研樣本,2015年在干預組參加商業健康保險之后,兩組調研樣本之間的差異仍較為明顯,在大部分指標保持了一致性的基礎上,也有一些指標出現了反轉和擴大。自評健康方面,與2013年相反,2015年干預組的均值略高于控制組的均值;個體認知能力方面,干預組在記憶力自我評價和繪畫能力上低于控制組,而在計算能力和識別能力上總體高于控制組;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干預組僅在“對未來充滿希望”和“很愉快”兩個指標上高于控制組,這與2013年的情況相一致;近期醫療服務使用方面,兩組之間三個指標最大的差別僅為1.3%,這與2013年的情況也是相一致的。控制變量中,干預組的平均年齡小于控制組,受教育程度高于控制組,收入和支出方面,干預組均高于控制組。
通過2013、2015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干預組和控制組在社會與經濟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差異性,這可能是產生商業健康保險自選擇問題的重要原因。
(二)匹配結果檢驗
用上述Probit模型估計出傾向得分之后,本文選取核匹配方法對干預組和控制組樣本進行匹配。為實現對匹配效果的檢驗,本文利用傾向值匹配平衡性檢驗(Balancing)對控制組和干預組個體在匹配前后所有的社會人口及經濟特征上的差異進行檢驗,如表5所示。其中,Unmatched為匹配前所對應的控制組和干預組樣本,而Matched代表通過傾向匹配后“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共同支撐域(common support)且分布近乎一致的控制組和干預組樣本。
由表5可看出,在未對樣本進行匹配處理之前,控制組和干預組所對應的各個變量在均值上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家庭過去一年收入等變量,二者的差異甚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而在進行核匹配后,控制組與干預組在所有特征變量上的均值差異都大幅地下降,其標準偏誤絕對值相對減少了39.2%—57.7%不等。同時,匹配前顯著存在差異的婚姻狀況、家庭過去一周支出、家庭過去一年收入等變量在控制組與干預組之間的不同此時在統計上也不再顯著。Rosenbaum等認為當匹配變量標準偏差的絕對值小于20%時,匹配結果是可靠的[36],由表5可以看出,除年齡外,匹配后其他變量的標準偏誤均在20%以內,因此匹配結果是可靠的。
因此,總體而言,運用匹配方法之后有效地消除了樣本匹配前控制組和干預組在各類個體特征方面的差異,進而得到了更具有可比性和可靠性的控制和干預組。
(三)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分析
以上通過初步的統計分析對比了商業健康保險對于個人健康的相關關系,由于商業健康保險的需求存在自選擇效應,因此通過PSMDID方法研究消除掉自選擇偏差后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
1.控制組與干預組的健康水平
運用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方法對2013/2015年控制組和干預組的數據進行處理,得到的結果如表6所示。

表4 2013年和2015年數據變量描述統計分析

表5 干預組和控制組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檢驗結果

表6 2013/2015年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
對于自評健康來講,2013/2015年PSMDID的數據顯示參保群體的自評健康水平相對未參保者上升23.9%,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商業健康保險的參保者對于自身的健康評價程度相對于沒有商業健康保險的個體來講要更好。
對于個體認知能力而言,參加商業健康保險后,參保者的計算能力、繪畫能力和識別能力均得到顯著提高,但是記憶力水平并沒有明顯變化。
醫療服務使用情況方面,統計結果顯示1年內住院的情況顯著提高,也就是說商業健康保險增加了醫療服務使用情況。
心理健康水平方面,數據表明,“很愉快”指標的符號顯著為負,表明個體的快樂水平有顯著下降,“因一些小事而煩惱”、“難以集中注意力”、“感覺做任何事情費勁”、“感到害怕”等指標的符號均顯著為負,表明參加商業健康保險顯著緩解了上述情況,有效提高了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
由于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于2011年開始每兩年進行一次調查,并且關于本研究所涉及的個體參保和健康水平的調查問題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保持不變,因此可以運用同樣的方法對2011年和2013年的數據進行處理,觀察2011-2013年期間參加商業健康保險對個體健康水平的影響,表7展示了2011/2013年PSMDID的估計結果。整理2011年和2013年CHARLS的數據可以得到,2011/2013年的控制組樣本數12318個,干預組樣本數156個,二者共12474個。由于處理2011/2013年數據的方法與2013/2015年的相同,為節省篇幅,在此僅展示2011/2013年PSMDID的估計結果,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量不在此列出,需要者可向作者索要。

表7 2011/2013年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
由表7可知,2011-2013年,參加商業健康后,僅有參保者的“計算能力”以及“對未來充滿希望”、“很愉快”等指標有顯著提高,而其“繪畫能力”、“識別能力”則顯著下降,“因一些小事而煩惱”、“難以集中注意力”、“睡眠不好”的情況顯著增加,這與商業健康保險可以改善參保者健康水平的預期相反。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參保人數的增加,參考表6可知,2013-2015年,參保者的“繪畫能力”、“識別能力”、“因一些小事而煩惱”、“難以集中注意力”指標的系數符號與2011-2013年相比均相反,表明參保者的健康情況在上述方面得到顯著改善,而“自評價康程度”、“計算能力”、“睡眠不好”的系數符號則保持不變。“很愉快”指標的系數符號從2011/2013年的正向變為2013/2015年的負向。通過對比表6和表7可知,隨著參保人數增加、樣本量擴大以及商業健康保險在我國的發展,商業健康保險對提高參保者健康水平的作用逐步得到體現,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也逐步得到證實。
2. 區分城鄉群體
由于社會醫療保險對于城鎮和農村群體的保障政策具有差異,因此有必要對城鎮與農村的樣本進行分組研究。表8列示了城鎮、農村群體的PSMDID估計結果。

表8 2013/2015年農村和城市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
從2013/2015年農村和城鎮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結果可以看出,自評健康方面,農村與城鎮分組均為正值,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購買商業健康保險后,農村和城鎮居民均認為個人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個體認知能力方面,農村居民在繪畫能力上顯著為正,但是在識別能力上顯著為負,城鎮居民則在計算能力、繪畫能力和識別能力上都顯著為正。醫療服務使用情況方面,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均在“1年內是否住院”上呈現1%的正顯著,說明商業健康保險增加了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醫療服務使用情況。心理健康水平方面,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呈現出較多的不同。對于“因一些小事而煩惱”指標,農村居民顯著為負,但是城鎮居民卻顯著為正。“難以集中精力”方面,農村居民顯著減少了此種情況,城鎮居民的結果雖然為負,但并不顯著。“感到情緒低落”指標,城鎮居民顯著為正,但是農村居民并不顯著。對于“感覺做任何事情費勁”指標而言,農村居民此種情況得到顯著改善,城鎮居民的統計結果沒有表現出顯著性。“對未來充滿希望”和“很愉快”兩項指標,農村居民均為顯著為負,但是城鎮居民均為顯著為正。“對自己的生活滿意”一項,城鎮居民有顯著提升,農村居民雖然也有所提升,但并沒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
綜合全樣本數據和農村、城鎮分組數據,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可能是以下四個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是商業健康保險的保障范圍更廣、力度更大,更能滿足個人在基本保障之上的補充保障需求,更為精確地滿足了消費者的特定健康需求,從而促進了個人健康水平的改善。二是商業健康保險的激勵措施更為得當,保費優惠措施和免賠條款等一系列激勵手段使得個人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的管理,使個人醫療服務使用情況更為合理。三是商業健康保險的保障水平與所繳保費呈正相關關系,因此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保障力度有所差別,這就使得本文的實證結果在城鎮和農村兩個群體具有一定差異性的原因。四是從個體認知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兩類指標可以看出,商業健康保險作為一種保障型商品,不但滿足了人們對于疾病風險的保障需求,而且顯著減緩了煩惱、害怕等不良情緒,進而給人帶來了更為健康的生活狀態。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以商業健康保險作為研究對象,重點研究和評價了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本文選取四個維度的指標表征參保者的健康水平,進而作為商業健康保險健康績效的評價依據。實證結果表明,隨著時間推移和參保人數增加,就全樣本而言,商業健康保險能夠改善我國中老年人群參保者的健康水平,具有正向健康績效。具體表現為,購買商業健康保險后,個人對健康水平具有正向評價;個體的認知能力,如計算能力、繪畫能力和識別能力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商業健康保險顯著減少了參保者因小事而煩惱、難以集中注意力、做事費勁、感到害怕等多種負面情緒;醫療服務使用情況方面,商業健康保險對參保者使用醫療服務表現出了較為積極的作用。
由于城鎮與農村群體在社會醫療保險、經濟狀況、社會特征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本文將參保者分為城鎮群體與農村群體分別進行了實證檢驗。分組檢驗的結果與全樣本的實證結果基本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心理健康水平層面,城鎮群體和農村群體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因小事而煩惱、對未來充滿希望、很愉快等指標出現反向變化的情況,這些差異提醒了政策制定者和商業保險公司需要更加注重和辨析參保個體的經濟和社會特征,為今后商業健康保險發展政策的制定以及產品的個性化、定制化設計提供了參考。
本文的實證結果支持了商業健康保險可以改善參保者健康績效的結論,這既為全面科學地評估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也為我國下一步大力推進商業健康保險制度建設提供了相應的現實依據。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本文對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進行了實證研究,但是關于商業健康保險健康績效的研究仍有可以改進的地方。第一,本文使用的是中國中老年人的數據,所以我們看到了商業健康保險在中老年人群中的健康績效。雖然我們相信商業健康保險存在的價值之一在于其能夠改善所有參保者的健康水平,而不只是中老年人群,但為嚴謹起見,仍需使用各年齡段的數據對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績效進行更準確的評估。第二,雖然PSM方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觀測數據的偏差,但是由于PSM方法只控制了可測變量的影響,如果存在依不可測變量選擇,該方法仍會帶來隱性偏差[38]。第三,由于CHARLS不是專門針對健康領域的調查,因此評價受訪者健康水平的指標可能比較有限,如果想更為全面地評估受訪者的健康水平,則有待于更為全面的調查數據。
(二)政策建議
2017年末,全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為11.7億人[39],憑借“保基本、廣覆蓋、有彈性、可持續”的實施原則,社會醫療保險從覆蓋率的角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對目前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政策性色彩濃厚的社會醫療保險對于個人醫療服務的利用情況和健康績效的改善作用有限。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商業健康保險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快發展商業健康保險,有利于與基本醫療保險銜接互補、形成合力,夯實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健康保障需求[40]。2017年,財政部,稅務總局、原保監會發布通知,將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策實施范圍推廣到全國,旨在通過購買商業健康保險可以抵扣個稅的方式促進商業健康保險業務的發展[41]。從政策層面可以看出,國家已經將商業健康保險作為我國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發展。
本文認為,我國在推動和發展商業健康保險的過程中,需要著重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堅定支持商業健康保險發展。本文的研究結論表明,商業健康保險可以作為社會醫療保險的有效補充,解決一些社會醫療保險覆蓋不到的問題,有效提高參保者的健康水平,因此國家應大力支持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其次,營造有利于商業健康保險的政策環境。雖然目前我國已出臺相關政策,以抵扣個稅的方式鼓勵公司或個人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但是從市場反應來看,抵扣個稅的政策對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作用有限,居民購買商業健康保險的潛力仍需激活,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應在行業聯動和頂層設計、稅收抵扣力度和簡化抵稅流程、保險產品監管和鼓勵服務創新等方面發力,為商業健康保險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第三,將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納入國家醫療保障體系建設統籌謀劃。鼓勵商業健康保險公司有序參與各類醫療保險經辦服務,承辦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形成商業健康保險服務國家醫療保障體系建設的途徑和方式。最后,有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的覆蓋率不足10%[42],與發達國家30%以上的覆蓋率相比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除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因素外,民眾保險意識仍弱,購買保險的意愿相對有限也是商業健康保險發展受限的重要原因。因此利用政府的公信力,培養居民的風險意識,使居民形成自我健康防范和預防習慣,對于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