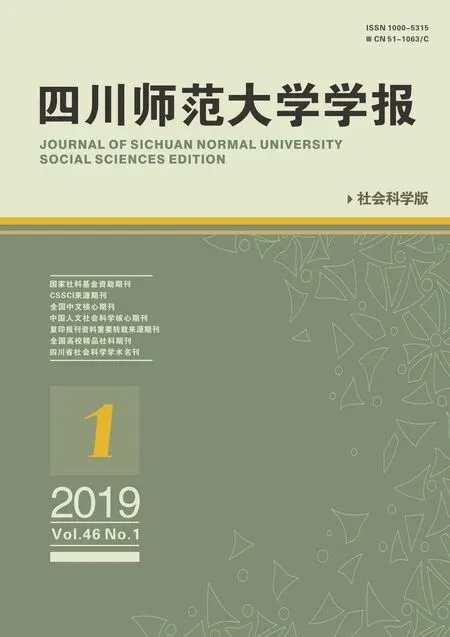論交流敘述文本的構成
(信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在交流敘述學的視野中,敘述文本并非是一個固定的存在,即來自作者的文本與接受者最終形成的“接受者文本”并非同一,二者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組成“作者文本”的要素和組成“接受者文本”的要素并非完全重合。這是敘述文本進入交流必然出現的現象。那么,在交流敘述學視野中,敘述文本的構成并非基于傳統認知,即在傳統觀念中,敘述文本是來自作者的符號構成物,是一種具有邊界的自足的獨立的結構系統。但在交流敘述學視野中,傳統理解中來自作者的敘述文本在交流中是作為“主敘述”存在的,除此之外,影響交流敘述文本建構,或者說組成這一文本建構的還有“輔敘述”、“非語言敘述”和“零敘述”。換句話說,敘述文本進入交流,在接受者那里,敘述文本的組成具有了復雜狀況,最終組成“接受者文本”的元素除了來自作者的主文本(主敘述)之外,還包括其他元素。
一 主敘述
所謂“主敘述”是指敘述主體創造的敘述形態,是構成敘述文本的核心部分,是有效參與敘述交流,并影響交流效果的核心部分。主敘述是經典和后經典敘述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按照一般的理解,主敘述文本的構成可分為故事和話語,或者底本和述本,還包括“有意伴隨文本”。這里有必要回顧敘述文本的理論建構歷程,并將之納入一般敘述和交流敘述的研究框架下考察其形態演變的影響因素。也就是說,在交流敘述學框架下,敘述文本的建構并非是一種“主體單向”,而是一種“主體-接受雙向”。
主敘述的構成因敘述類型的不同而異,對于虛擬交流敘述而言,其文本形態往往已經成型,是可見的,因此,主敘述就是已經具形的符號文本,如文學敘述文本、電影、錄制的戲劇、文字新聞或錄制的新聞、歷史著作等等。接受者所面對的是不能增殖也不能減損的文本形態。對于真實交流而言,由于交流雙方都在場,文本是在二者的交流中動態形成,構成文本的素材并不確定,因此,主敘述就包括一切能影響交流進程、效果,且能夠有效形成敘述文本有機組成成分的因素。比如現場性舞臺演出,其敘述構成往往并不簡單為戲劇情節本身,而是包括演員與臺下觀眾之間的互動,以及戲劇外因素對戲劇敘述效果的影響等等,演員的眼神、插科打諢等等會影響敘述交流,都可構成敘述的一部分;再如庭辯敘述,控辯雙方的某個動作、某個眼神都可進入敘述文本的構成。
這里其實涉及真實交流中的靜態文本與虛擬交流中的動態文本的區別問題。靜態文本由于媒介局限,會屏蔽掉許多影響敘述的內容,這些內容有的形成文本空白,有的則純粹為丟失的信息。空白經過接受者的努力可以填補或部分填補,但丟失的部分則無法還原。再加上虛擬交流中交流的某一方缺席,這些空白或丟失的信息無法通過及時反饋來填補,經驗就會在此處形成斷裂,這些只有在二次敘述化過程中來建立經驗連接,彌補經驗鏈條中的遺失部分。動態文本一般在真實交流中形成,由于交流雙方都在場,經驗反饋很及時,因此,相對于虛擬交流而言,真實交流的空白和信息遺失較少,即使交流中有所遺失,也會在交流反饋中得到補充和修正,否則,就會因為這種遺失使經驗鏈接被切斷,并進而影響正常的交流進程。同時,經驗的及時反饋可以有效彌補敘述媒介的局限性,某方面的局限會通過其他形式獲得補償,使局限性對交流的影響減到最低。因此,真實交流中的動態文本構成較為復雜,主敘述包括各自信息媒介,比如視覺媒介、聲音媒介,甚至味覺媒介等等。正因為真實交流的媒介復雜性,經驗反饋的即時性,所以,動態文本的主敘述構成就會極其復雜,它包括進入敘述并影響敘述交流的各種因素,只要這些因素參與了敘述意義的交流性共建,都可以被看作主敘述的一部分。
因此,主敘述,無論在虛擬交流中的靜態文本還是真實交流中的動態文本,指的是得到交流敘述參與各方認可的、邊界一致的敘述文本。也就是說,主敘述文本有一種雙方認可的邊界,有共同承認的敘述媒介、材料、方式等等。但,主敘述并不是交流敘述文本的全部,因為除了交流參與方都一致認可的文本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交流敘述的意義建構。
二 輔敘述
輔敘述指的是在交流敘述中,交流雙方為達到某種交流效果或者接受效果,在主敘述之外有意增加或者無意攜帶一些對交流起輔助作用的因素,這些因素對于敘述文本的意義建構起到了一種輔助作用。輔敘述是影響敘述文本意義建構的非主體部分,有些是靠交流對方的信息提取獲得,而這種信息不屬于信息所有方有意參與交流的部分,即這些信息是所有者無意之中被對方獲取并影響交流的因素;輔敘述還包括敘述交流的參與各方為輔助敘述交流而有意為之的部分。如“說書”藝人的“看官有所不知”、話本小說中的“看官聽說”等都不是故事的一部分,而是為了交流順暢而進行的“情況說明”。
趙毅衡注意到文本邊界模糊不清問題,指出:“實際上,符號文本的邊界模糊不清:看起來不在文本里的成分,必須被當作文本的一部分來進行解釋;許多似乎不在文本中的元素,往往必須被‘讀進’文本里。因此,文本的邊界取決于接收者的解釋方式。”[1]215趙毅衡將文本附加的、嚴重影響對文本的解釋又經常不算作文本一部分的因素叫作“伴隨文本”。由此可見,伴隨文本是一種影響接受方理解的因素,并不與敘述發出方共享。其實,除此之外,在交流敘述中,還有另一種情況,就是敘述發出方有意或無意增加一些影響解釋的因素,這些因素也輔助了意義文本的生成,就是“輔敘述”。輔敘述包括伴隨文本,但大于伴隨文本。輔敘述也許并不為交流對方所知,它輔助理解或輔助表達,甚至表達者不想被認為他是有意為之、接受者也不想讓對方了解太多有關幫助自己理解的構成因素。后者是敘述本身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文本的天然伴生物,它有效參與文本的意義建構過程。因此,輔敘述是交流敘述中的一種交互現象,它有些是交流雙方的共享因素,有些則是隱秘因素,有些是有意為之,有些則是無意流露并為對方捕捉。這里之所以強調交互性,主要針對真實交流敘述,因為交流雙方的在場性使輔敘述無論對發出方還是接收方都同樣起作用。
輔敘述包含兩方面:一是發出輔敘述,即來自敘述發出方的輔敘述;一是接收輔敘述,即來自接收方的輔敘述。發出輔敘述發生在敘述文本的形成過程中,他通過或公開或隱秘的方式、用各種手段來輔助敘述文本的意義建構,但這些方式并不一定需要接受者知道,甚至有時候故意隱瞞;接收輔敘述發生在敘述文本的理解過程中,接受者為了對敘述文本的理解,讓多種因素參與自己的理解過程,有時,這些因素并不為交流對方知道,甚至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來理解對方的真實意圖,比如信息提取、對對方的各種資料收集等。
在交流敘述中,意義的合作共建是一種常態。但絕不能因此排除敘述(包括來自作者的一次敘述和來自接受者的二次敘述)的個人化行為。因為在交流敘述中,參與各方的目的并不一定重合,沒有百分之百重合的交流敘述。為了各自目的而進行的敘述必然充滿個人化的東西。再者,由于個人的生活、經驗背景、知識結構等等不同,對于敘述符號的理解運用也存在差異。尤其在敘述博弈中,這種個人化行為會更多、更復雜,各懷心思是這種敘述交流的常態。但這種個人化行為并不影響交流敘述的意義共建,因為正是這種個人化行為才會出現意義的延展,經驗在這種個人化行為方式中得到增殖并進而生長為一種“共識”。經驗就是在這種“個人化”向“公共化”轉變中得到積累。
輔敘述根據敘述者(包括一次敘述者和二次敘述者)的意圖可分為有意輔敘述和無意輔敘述兩種。
有意輔敘述是指交流敘述的參與各方為了促進對方的理解,為了協助主敘述完成意義建構的任務而有意在交流敘述中加入輔助成分,同時對方也準確地理解這種成分的作用,并使這種成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種有意輔敘述是公開的,并期待其發揮作用的敘述輔助部分。如帶有創作意圖的電影海報,其目的是幫助觀眾獲得解讀電影的方向。再如在真實交流中,信息接受者會用某個動作來展示給發出者來求證其理解的準確與否。
無意輔敘述是指交流敘述的參與者在自己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某個動作、語調、文字等提示給對方一些信息,這些信息被對方有效提取并影響交流。這些提取的信息與意義的連接要靠提取者來完成,“信息提取就是為別人的行為賦予意義,至于賦予何種意義,就完全靠觀察者的觀察能力了”[2]69。無意輔敘述往往在真實交流中意義更大。在敘述博弈中,無意輔敘述有時能夠決定交流的成敗。因為無意輔敘述有時會帶來“輔敘述矛盾”,即敘述者無意之中提示給對方的信息被對方獲取,而且這種信息與敘述者所要表露的信息出現矛盾,敘述者的真實意圖通過這種無意流露而被交流對方通過信息提取的方式獲得,并影響其進一步的交流行為。就是說,敘述者的這種無意表露的信息不是其想要參與交流敘述的意向,盡管這種意向也許是其真實意圖,但不是其交流意圖。也就是說,在真實交流敘述中,交流雙方的言語行為只有部分參與了交流敘述的意義共建,另一部分則不是有意為之,而是無意之中流露出自己的某種真實心態,是一種無意流露被捕捉、被讀取而影響讀取者的交流行為。如人的身體被認為是一種敘述符號,“以身體作為敘事符號,以動態或靜態、在場或虛擬、再現或表現的身體,形成話語的敘事流程,以達到表述、交流、溝通和傳播的目的”[3]56。
信息提取是交流敘述中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在虛擬交流敘述和真實交流敘述中都會出現。在虛擬交流敘述中,信息提取的方式會與真實交流有時不同。上述在真實交流中的信息提取往往當場完成并影響交流的意義共建,但在虛擬交流敘述中,信息提取可能會發生在交流敘述之前或之后,比如對敘述發出方的側面了解,也許有些信息敘述者并不想讓交流方獲知。對于圍繞敘述者或敘述文本的信息提取,無論之前還是之后,都會影響到交流的效果。有時候,信息炒作者會利用這一點來達到某種社會效應,它們甚至虛構事實來達到某種接受效果。當然,一旦這種虛構被揭穿,交流敘述的結果會朝著相反的方向運動,直到其效果達到足夠抵消虛構事實帶來的負面影響為止,如引起公憤使虛構者受到法律、道德懲罰。如此情形在網絡時代屢見不鮮。
輔敘述誤讀,指在交流敘述中,信息接受者在組建“接受者文本”過程中,錯誤地接受了某些雜音,導致某種錯誤判斷,并進而影響交流效果,產生了輔敘述誤讀。在審判、庭辯等敘述類型中,由于接受者錯誤的“信息提取”產生輔敘述誤讀的現象極為常見,以輔敘述誤讀而產生的后果有些時候非常嚴重,尤其是在法律領域。
三 非語言敘述
以交流為視角研究敘述,使敘述中的非語言因素獲得重視。尤其對于面對面的交流敘述而言,更是如此,“語言選擇和伴隨的種種非語言行為形式(包括面部表情、身體姿勢、具有副語言特征的聲音的發出、笑聲、手勢和注視)之間,通常有很高的互動”[4]135。就是說,在很多情況下,完成一種意義表達需要語言和非語言之間的互動配合。非語言敘述多數情況下是一種片段性敘述,敘述的施受雙方靠共享經驗、語境來補充、建構一個完整的敘述行為。共享經驗與共享語境是非語言敘述成功參與敘述交流的基礎,其表達的內容越多,交流參與各方共享經驗與語境就會越龐大。“語言外交際在記憶和推理時要求更多的知識和更大的努力,只有這樣,它才能傳達更復雜的信號”[2]32。非語言敘述不同于聾啞人手語,因為手語是一種具有約定規約的符號系統,是已經被語法化的語言系統,手語其實是語言的另一種符號形式。非語言敘述不存在規約性的東西,而是靠共享經驗、語境而聯系起來的敘述方式,它沒有固定的表達方式,一張圖片、一個動作、一個指示符號,甚至某種聲響、氣味等等,均可以作為一種非語言敘述方式,只要交流雙方能懂得即可,而不必對交流關系之外的人透明。如一個人可以用手指著放在桌子上的書告訴別人書在那里,也可以用下巴朝書抬一下來指示。
正因為非語言敘述的非規定性,注定不會單獨完成一個復雜的敘述過程,而只能作為該過程的一部分。一旦非語言敘述的表達方式被固定下來,成為一種語法意義上的交流手段,非語言就變成了具有獨立表意功能的符號語言了。
盡管非語言敘述是一種非規定性的符號表意,但這種非規定性在一個具有共同經驗基礎的文化環境中,卻可以形成某種約定俗成的動作語言。格雷馬斯將人類動作分為自然動作和文化動作,指出:“盡管由于機理原因,動作語言表述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但它一旦被傳授學會,就和其他符號系統一樣,構成了一種社會現象”,“一個關于社會化了的人體語言的類型學不僅能說明文化分野(見接吻技術),或者性別的分化(見‘脫羊毛衫’的操作程序),它還能解釋并假設一個自主的符號向度的存在,僅就這一向度在文化、性別和社會集團之間造成種種分化差異而言,它就讓各文化、各社會和各集團擁有了表意功能”,“于是,自然動作語言搖身一變成了文化的動作語言”[5]58。這種“文化動作”由于攜帶文化內部共享經驗的表意特征,而被符號化了。盡管如此,這種動作語言往往是一種語言或經驗鏈條的攜帶物,它一般不單獨構成一個具有語法化特征的表意鏈條。因此,動作語言只能夠輔助話語或經驗完成表意,或者在一定的話語、經驗語境中傳達表意信息。如卓別林的無聲電影,靠動作完成某種表意鏈條,這種表意鏈條必須在特定的經驗語境中完成,也就是說,動作之間靠共享經驗來連接,從而構成完整表意信息。而當經驗無法完成這些動作連接時,則不得不靠字幕輔助完成。單純的動作無法提取為語言符號,但可解釋為某種文化符號,動作之間靠共享經驗獲得連續性,并形成完整的敘述。但,這些動作卻無法拆分而形成單獨的表意符號。
基于此,非語言敘述只能是復雜敘述的有機輔助部分,而不能成為敘述交流的主體,是一種輔敘述。它可以輔助話語完成某個敘述過程,也可以通過共享經驗鏈接不同非語言敘述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敘述文本。在某些看起來只靠非語言完成的敘述文本中,其實蘊含了一種經驗語言,這是一種內化的語言,如果需要,它隨時可以轉化為話語符號。在這種非語言符號構成的鏈接而形成的敘述文本中,話語符號已經內化為經驗符號,動作語言必須經由經驗進行鏈接來獲得整體的存在感。因此,電影的默片、舞臺的啞劇等等非語言敘述,之所以能夠形成敘述文本,接受者的二次敘述非常重要,二次敘述形成的二度文本中,沒有經驗鏈接是不可想象的。
非語言敘述參與交流也可分為有意和無意兩種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無意非語言敘述有時更能傳達發出者的真實意圖(如庭辯敘述中無意流露出的某種情緒)。此時,交流敘述的發展方向會變得撲朔迷離,所謂表情比表達更真實。
照片、連環畫、漫畫、繪畫敘述也是非語言敘述形式,它們靠兩方面獲得交流通行證:一是靠伴隨文本;二是靠畫面呈現的具有共享性質的經驗邏輯。但這兩種通行方式不能百分百保證交流的預期效果,因為二者均具有不充分性特征。因此,此類敘述在交流中往往容易引起誤解、容易斷章取義、容易不充分解讀。如新京報網曾經登出一組“大媽碰瓷老外”圖片[6]:圖片中的大媽和一騎摩托車的外國人發生碰撞,外國人一臉無辜,大媽趴在摩托車上,甚至把老外的羽絨服扯爛了。再加上圖片發出者的標題“大媽碰瓷老外”,使接受者對大媽產生一致譴責,甚至辱罵。有圖有真相,再加上大家對碰瓷者的憎惡,這種一致的譴責并非出人意料。光靠圖片及簡單的文字信息,使圖片的事實被文字這一伴隨文本所誤導。事實上,這的確是一種誤導,即大媽并非是碰瓷者,而是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被逆行、超速且無駕照的外國人騎的摩托車撞了,大媽和其論理,被其辱罵,且二人產生撕扯,導致外國人羽絨服被扯爛,后經公安機關進一步了解,此外國人與其父在中國工作但無工作簽證。這個事件表現出了有圖有真相的弊端,有圖并非是有真相的充分條件,靠不充分的伴隨文本提供信息并不能達到客觀公正的交流效果。更何況信息爆料人有意的歪曲報道。后來,此組圖片的爆料人公開道歉:有意的歪曲爆料要承擔責任[7]。利用圖片的非語言敘述的不充分性特點,來達到某種接受效果,同樣也要承擔責任。
非語言敘述無論哪種方式,都可還原為一種語言描述,即用語言符號描述敘述本身或者交流敘述過程。非語言敘述不但表達經驗,也建構經驗。
非語言敘述往往成為敘述文本的表達方式,在中國傳統戲劇敘述中,有兩種非語言敘述方式。一種是約定俗成的動作語言方式,即已經程式化了的戲劇動作,如上馬動作、抬轎動作、表達憤怒情緒的動作等等。這些動作因長期與觀眾的交流而形成固定的表意,觀眾通過這些動作可以直接獲得理解,而無須話語傳達。另一種是跨層動作語言,即演員面對觀眾的表情和肢體語言與觀眾達成交流協議,即這種非語言敘述只有觀眾和表達者共享,而對故事中的其他人不透明,這樣就構成中國戲劇特有的插科打諢。電影中對人物細微表情的特寫即是用非語言敘述來傳達人物的內心隱秘,這種隱秘同樣是電影的作者與觀眾達成的某種交流默契而對故事中其他人不透明,這其實也是一種跨層交流。這種特寫鏡頭,以傳達演員某種隱秘動作的方式,暴露了攝像機的存在,也就是暴露了銀幕外敘述者的存在,是銀幕外敘述者與觀眾形成了交流語言,而對故事內的人物來說是不透明的。這種信息的不透明構成觀眾的某種心理優勢或接受意向,這往往成為影視敘述文本吸引觀眾的一種方法。
四 零敘述
零敘述是指敘述交流中的符號空白,它不具形為某種符號,但它本身攜帶意義,是一種“空符號”,是能夠被交流雙方感知并形成交流經驗、取得交流效果的敘述現象。零敘述可發生在故事層面,也可發生在敘述層面,但歸根結底是敘述發出方的選擇行為,因為故事不會自身消失或隱匿,因此,筆者認為,從敘述發出方區分這兩個層面的零敘述沒有意義,只有在敘述的交流中討論零敘述帶來的意義才具有價值。
零敘述在交流敘述中有多種表達式,可大致有如下類型。
其一,欲言又止。由于某種語境壓力或者道德壓力,說話人不得不回避某些不可明言的內容,使敘述成為空白。如《雷雨》中魯侍萍對周萍說:“你是萍——憑什么打我兒子?”《祝福》中,當魯四老爺了解祥林嫂被婆家的人綁去時說道:“可惡!然而……”。欲言又止實際上屏蔽掉了說話人所應承擔的道德倫理等各種責任,它使接受者有一種領悟感,似乎比說出來更具心理內涵。說話人在屏蔽掉所應該承擔的言語后果的同時,也把自己的心理秘密通過這種零敘述隱秘地傳達給接受者。
其二,避免重述(重復)。這種零敘述方式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常常出現,比如對過去經歷的回顧,敘述者往往采取“如此這般地重說一遍”等敘述干預來省略重復給讀者帶來的厭煩感。中國傳統“說話”(說書)藝術也是如此。避免重復除了為避免復述過去事件(一般情況下,這種過去事件是被接受者了解的)外,還有另一種形式,即為避免重復未來事件,即敘述內容在將來還要敘述,因此采取零敘述方式省略。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古典名著中常常出現為應對將來某個事件而采取什么樣的行動方式,用“如此這般”等等省略,在未來的敘述中這種省略內容會逐漸展開。在電影中這種手法也非常常見。這種為避免未來重復而采取的零敘述策略還有一個重要的交流目的:獲取交流期待。
其三,非語言替代。在交流敘述中,尤其在真實交流敘述中,非語言成分參與敘述的交流進程,而且有時候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非語言替代式零敘述是一種非語言敘述。在交流雙方獲得共享經驗的前提下,一方采取某種非語言方式暗示對方某種狀況,對方會根據共享的經驗還原這種暗示所表達的內容,交流就算完成,因為意義傳達的目的已經達到。非語言替代的這種暗示效果實際上是一種語言轉換,比如本來可以用說話的方式傳達的內容用動作代替,動作本身雖然在某些時候也可以被解讀成語言,即動作語言,但很多時候它不具有語言的普遍語法化特征,而只是一種小范圍動作語言,如只有交流雙方的某種約定,因此,非語言替代式零敘述是一種小范圍的交流敘述方式,它因為不透明性而對局外人產生神秘感。敘述文本往往采取這樣的方法使敘述交流中的接受者有進一步解密的興趣。非語言敘述有很多種方式,某個動作、某種聲音,甚至某種氣味等等均可以成為一種約定性的敘述,如間諜電影中常常將花瓶正放表示正常、放倒表示有危險。
偵探小說、警匪電影、武俠電影、懸念電影、舞臺戲劇等等往往采取這種零敘述方式。如用某個神秘事物代替某種往事,這種代替對于劇中人也許是透明的,但對于接受者卻是需要解密式閱讀或觀看才能獲得。非語言替代式零敘述在庭辯中也常見,如代表案件過程的物證,局外人無法獲知,但對局內人則是無需明言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墻上的斑點》,一個墻上的斑點引發主人公無限遐想,每一次的思想滑動,斑點就會代表一件往事,斑點成為許多故事的重要生發點,此時,斑點就相當于一種非語言的零敘述,其所代表的每一個故事均與主人公形成某種無言約定:外人無法確知斑點與故事的神秘聯系,只有主人公與斑點之間形成的這種“約定”,才形成了斑點(及其所可能代表的故事)與主人公之間抵近心靈的交流,由于它不共享,讀者永遠不知道主人公接下來會聯想到什么故事,意識流在這種不可預知的思維流動中獲得“文本-讀者”之間的交流張力。
其四,經驗性省略。在交流敘述中,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某些敘述成分被人為省略而完全不影響交流效果,即接受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補充被省略的內容使敘述獲得“殘缺的完整性”效果。如電影中,如果一個鏡頭顯示一個殺人場面,下一鏡頭則顯示罪犯受審的畫面,那么觀眾會很自然把二者的中間環節通過自己的經驗判斷連接起來:罪犯因殺人而被逮捕受審。但有時候,敘述文本作者會利用“既成經驗”這一點,為敘述文本設置接受懸念。如影片《肖申克救贖》開頭杜福瑞受審與其酒醉后拿槍走向案發現場進行蒙太奇剪輯,但杜福瑞對妻子與其情人被殺沒有責任,這種組接為影片設置了一個懸念:觀眾的接受經驗受到考驗。因為,觀眾會根據以往電影剪輯的經驗,自然認為杜福瑞是兇手,但事實上,影片一步步顛覆了觀眾的這種經驗期待。再如,電影中一個人物說他明天要開一個會議,下一鏡頭他出現在會議現場,觀眾會感覺很自然,因為,電影敘述已經把足夠的信息提供給接受者而使其能夠對故事建立起經驗連接。
經驗性省略在敘述交流中可有兩種利用方式。一是順向利用。即根據交流敘述中交流雙方的經驗共享(或者延展性共享,即通過既成的共享經驗進行推導得出),順向利用這種共享來獲取經驗連接,使這種方式的零敘述獲得最佳交流效果。二是逆向利用。即利用接受者的既成經驗,使其產生誤判,使敘述獲取接受動力,并在適當時機揭示觀眾判斷的不可靠性,使其獲取意想不到的接受體驗。
因此,經驗性省略在很多時候是一種敘述技法,它有效利用交流雙方共享的經驗而使敘述的效率獲得提升,電影對觀眾經驗的培養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任何敘述,無論對參與敘述交流的任何一方,都有一個經驗培養的過程,它使某些個人化經驗通過這種培養而轉變成公共經驗,使敘述在技法層面得到發展。應當指出,敘述的經驗性省略作為零敘述的一種,其對敘述交流各方的經驗培養從方式到程度是不同的。而且,經驗性省略在某些敘述類型中運用較為謹慎。如庭辯敘述,詳盡的敘述過程對于庭辯敘述及其法律效果是至關重要的。再如在醫療敘述中,小到一個敘述動作都會影響醫療師對于病人心理狀況的分析與判斷。而要求客觀真實的新聞敘述,經驗性省略的零敘述無疑會引起觀眾的懷疑。經驗,有時候只能限定在可控范圍,因為我們無法保證某些經驗會對所有人都有效。
其五,視角盲區。對于敘述文本來說,現代小說敘述一個重要開創就是限制視角的運用。正是這種運用,使敘述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域,即敘述的可靠性問題得到廣泛討論。限制視角,即采取故事中某個人物的視角,使敘述視野受到該人物視野的限制而出現視角盲區。在人物視野之外發生的故事,在敘述中受到限制,出現敘述空白,即視角盲區式零敘述。限制視角使敘述受到視野限制的同時,也被敘述者進行了個人化過濾,使故事充滿變形、情緒化,表達的也是一種個人化經驗。這種零敘述把判斷的權力通過交流讓渡給接受者,使故事與敘述同時受到評判。限制視角帶來的交流敘述效果,從理論層面講,它轉移了接受者對故事的過分關注,調動了接受者參與文本價值建構的熱情,增加了接受者的裁判權。另一方面,它也要求接受者須有較高的審美判斷力。
視角盲區式零敘述增加了意義的多向性,因為未敘述部分需要在敘述交流中被填補,然后才能對敘述進行整體的意義建構。而這種填補必須從已敘述部分尋找線索。接受者的能動性被這種敘述技巧所調動,并且不是調動一端,而是整體調動,包括故事整體性建構、價值判斷、意義判斷等等。
其六,媒介缺陷。媒介的表達能力是有限的,對于敘述的普遍性而言,有時候,某些媒介會顯得力不從心。如以視覺為主的靜態圖片,包括繪畫、照片等等,其表達永遠是事物的一瞬,如果想表達一個連續的場面,不得不采取多幅圖片組合的方式來解決。如《韓熙載夜宴圖》,通過五幅畫面來敘述整個夜宴過程。但我們不得不說,每幅畫面也只是某個敘述環節的一瞬,而無法完全呈現整個事件過程。靜態畫面的局限性使大部分的連接性事件被省略而成為零敘述。小說無法直觀呈現某一畫面、場景,描述性語言只能是一種模糊表達。即使《紅樓夢》對大觀園的描寫再精細,不同的專家也會繪制出不同的大觀園景觀。釋夢者手段高明也不足以還原夢境,邏輯、時空混亂的夢敘述使任何“二次敘述”都變得不完美。電視劇對名著的改編帶來的惡果是,使那些再看原著的人思維受限,因為文字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帶來的審美魅力被瞬間定格成畫面。因此,對于學生來說,用看電視劇代替閱讀不僅不能培養審美思維,而且會帶來思維僵化的惡果。
媒介局限帶來的敘述空缺是敘述者不能回避的“技術性”難題。他能做的只有兩方面:其一,修補媒介局限,但這種努力往往會得不償失,因為這里往往需要技術支撐,或者進行“跨媒介修補”,比如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展出的《清明上河圖》,就是一種跨媒介修補,使繪畫版本在電子媒介轉換后獲得了動感;其二,利用局限性,即巧妙利用媒介局限使敘述在交流中獲得“意外收獲”。
媒介局限式零敘述是把雙刃劍,帶來獨特審美效果的同時,也會帶來因不充分表達而在交流敘述中歧義叢生局面。合理利用媒介局限,會提高敘述質量、提升魅力,獲得意想不到的接受效果。
熱奈特在論及敘述的時距時,在“省略”條目下提到“省敘”概念,指出:“從時間觀點看,對省略的分析歸結為對被省略故事的分析”[8]68。熱奈特進一步把省敘分為“明確省略”、“暗含省略”和“純假設省略”。“明確省略”的讀者可以從文本感知時間的流動,如“三年過去了”;“暗含省略”讀者只能推導出某個時間空白;而“純假設省略”則無法確定時間,甚至通過倒敘透露出的時間無法找到其確定的位置。熱奈特的省敘概念是時間在敘述中的變化方式之一,這種省略似乎是一種不摻雜經驗成分的文本形式,它不連接文本外的作者與讀者,即使“暗含省略”是一種讀者推導,但說到底只是一種文本現象,僅此而已。
中國古代藝術講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白居易《琵琶行》的接受效果是“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中國國畫講究“虛白”帶來的意境氛圍,并影響深遠。張藝謀在講到其電影對國畫意境的運用時說,他在電影中常會用到國畫的意境。比如到關鍵時刻,鏡頭不留給演員,給空鏡頭,讓觀眾有深遠、空靈、意味深長的想象空間[9]40。《道德經》之“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就是講究空缺帶來的接受效果,其前提是這種空缺建立在交流雙方有效的意義共建基礎上。“無論是解釋者還是發送者,他們在具體符號過程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對符號文本進行解釋和意義的再生產”[10]161,而零敘述就是要靠這種再生產獲得敘述身份。
需要指出,在敘述交流中,敘述文本的零敘述所出現的空缺,需要交流來填補。如果交流鏈條出現斷裂,零敘述交流就會有問題。這與省敘意義相近,但零敘述是建立在已經形成的交流經驗基礎上,雖然出現敘述空缺,但并不影響交流的連續性,相反,零敘述可以節省文本時間,可以增加敘述者與接受者心照不宣的交流。零敘述出現在知識、經驗共享的基礎上。但如果濫用零敘述,則會使交流敘述的流暢性受到影響,甚至交流一方因不堪忍受敘述空缺帶來的理解障礙而退出交流,甚至拒絕交流。這種情況在電影史、文學史上屢見不鮮。也許這并非敘述文本作者的缺點,而恰恰是其前衛性或前瞻性,這就需要假以時日,讓接受者的經驗獲得提升,然后才可能使其敘述文本獲得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