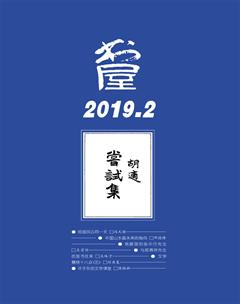野老丹心,劍影俠魂
裴高才 楊佳峰
一
“北有周有光,南有劉緒貽。”劉公是筆者十分景仰的鄉長,德高望重的杏壇巨匠,武漢大學最長壽的著名教授——享年一百零六歲。他學貫中西,桃李芬芳,著作等身,享有芝加哥大學杰出校友之譽。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說:劉先生離休三十多年間一直筆耕不輟,晚年學術成果累累,經常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成為一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典范。
“我外公外婆家是黃陂姚集喻家畈的,那我們還是正宗老鄉啊。”這是劉老與筆者首次見面說的第一句話,仿佛仍在耳邊回響。因為劉公1913年出生于湖北黃陂木蘭鄉劉咀村羅家沖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與筆者的老家姚家集街道毗鄰。
在同道心中,劉緒貽是一位人品鐵骨錚錚、學品鼎鼎大名的大家。一次,筆者拜訪馮天瑜先生,他因十分景仰劉公的道德、文章而親手繪制了一幅劉公素描肖像,十分傳神,我當即抓拍存檔。劉公是經歷武漢大學新、舊中國兩個時段的著名學者。“能否從事學術研究、研究什么、如何做研究,卻每自不由人”。劉公曾多次拒絕高官厚祿,堅守學術崗位;也有幾次,因客觀環境被迫離開學術崗位。
劉公生前回憶自己的青春期,可謂羅曼蒂克。本來,他以績優生取得了清華大學的官費,但為了追求與學妹周世英的愛情而不能自拔,竟在清華二年級時因掛科而失去了公費生資格。此時,一貧如洗的他面臨著當兵與讀書的兩個選擇。他一時拿不定主意,就問計于師長陳范九。陳先生對他說:中國抗戰勝利后還要建國,需要大量人才,而你的資質和性格有做學問的潛力,我認為你應該回清華繼續學習。同時,還為他謀得了一個代課教員職位,解決了他從武漢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上學的路費問題。
在西南聯大社會學系求學期間,劉緒貽不僅重新考取了官費,還師從陳達、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等名家。社會學系主任陳達很器重這個敢言的學生。“我的課程論文和畢業論文他都給我打了九十五分,畢業時他還要留我做他的助教。雖然后來我決定去重慶,但他仍然幫我給他重慶的朋友寫介紹信。一直到我留美,他還跟我說讓我繼續搞社會統計學,將來回清華教書”。
社會學家費孝通是吳文藻教授最得意的學生。在燕京大學學習期間,經吳先生精心安排,費于1933年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人類學家史祿國(Shirokogorov)教授學習人類學,1935年獲碩士學位后又考取了公費赴英留學。時至1939年上學期,剛從英國回來不久費先生開始到西南聯大兼課講授“生育制度”,劉因選了這門課而成了他的學生。當時,費先生只比劉大三四歲,性格類似,所以他們的關系是亦師亦友。
在劉緒貽的記憶里,費先生講課自成風格,不用教科書,也沒有講稿,中文和英文雙語兼用,講的內容包羅萬象,旁征博引,杜絕了“上課記筆記、下課背筆記、考試抄筆記”現象。“生育制度”課結業考試時,他出了兩道題并要求:做兩道可以,做一道也行;按照講課內容答可以,自己活學活用言之有理有據別出心裁也行。出題以后,他并不監考。劉公當時只做了一道題,而且完全是根據自己關于這門課程的知識和推論來作答的。結果,費先生給了他全班最高分。
費先生待人接物表現出的豪爽情懷,也讓劉緒貽有著深刻的印象。記得1940年初,劉從費先生借給他的一本書上發現其在扉頁上摘錄了龔自珍《金縷曲》詞中的一句話:“愿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劉不禁感慨道:“當時我猜想,他在摘錄這句名言時,一定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本來,劉緒貽1940年取得清華大學社會學學士學位后,可以留學或隨在云南大學任教的費孝通先生做社會學研究工作,這些都非常契合他的職業抱負。可是,已經二十七歲的他與熱戀中的周世英難舍難分。周雖是學妹,但她在重慶的工作薪水豐厚,面對戰亂物價飛漲,她豈能為了劉而放棄這份可以養活一大家人的工作。糾結中的劉緒貽就向費先生傾吐心聲,費先生也中肯地告誡他:“愛情是暫時的,學問才是永久的。”然而,劉緒貽再次選擇了真愛,斷然前往重慶與周世英相聚。雖然此次與費先生失之交臂,但此后數十年間,他們師生一直保持君子之交。直到1997年,費先生還親筆為劉緒貽主編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學研究》巨著題寫了書名。
劉緒貽追求真愛,也與老師的熏陶息息相關,直到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恩師們幸福的家庭生活。他回憶,常到潘光旦先生家里去蹭飯。當時潘先生家住在昆明郊區,師娘很能干,自己買了個石磨做豆漿吃,每次到他們家里都可以喝到新鮮豆漿。潘先生人很風趣,和他在一起總是感到很愉快。
在吳文藻先生家里,劉緒貽贊賞師母謝冰心“很有生活情趣”,甚至還經常關心弟子的婚姻問題。“我說我很窮,沒有女孩子會喜歡我,她笑著說那可不一定”。有一次,他見證了吳先生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一行清華同仁度周末的情景。席間,冰心就將丈夫的“傻姑父”故事寫成一首寶塔詩,把“一腔怨氣”發泄在清華身上。詩曰: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梅先生聽后靈機一動,便幽他一默地續了兩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話音剛落,逗得在座的清華師生忍俊不禁,冰心只好搖頭擺手承認“作法自斃”。
二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劉緒貽就是一位善于自省、知錯即改的君子。2006年經文化學者余坦坦建議,他們開始合作撰述口述史《劉緒貽口述自傳》。劉公提出了前提條件:“寫口述史必須絕對說真話,還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點和問題。”從他與著名詩人曾卓“相逢一笑泯恩仇”即可窺見一斑。
那是1955年“胡風案”狂飆驟起之時,曾卓因“莫須有”鋃鐺入獄。那時,人們都知道劉緒貽與《長江日報》副社長、武漢市文聯副主席曾卓是同鄉好友,又同在宣教戰線工作。在層層動員、人人過關、舉國一片“口誅筆伐”的高壓背景下,時任武漢市總工會宣傳部長的劉緒貽,為了表明自己立場堅定,于1955年7月寫了一篇批判曾卓的長文《揭露曾卓對于武漢市工人文藝活動的罪惡陰謀》,大有“踏上一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意味。此文經《長江日報》發表后,被各級媒體轉載,領導多次表揚。可是劉緒貽卻高興不起來,常常為此感到不安!尤其是他重返武漢大學任教后進一步反省:舊日曾卓如此傾心地與自己相交,自己卻寫出如此上綱上線的文章攻擊人家,越想越是感到有愧。因當時與住牛棚的曾卓音訊不通,無法當面表達懺悔之意。直到1979年曾卓平反昭雪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劉緒貽想找機會向曾當面致歉,但又始終勇氣不足。
機會終于來了。1997年,劉緒貽編纂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學研究》一書出版,他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農知曉劉的心思,就善意地以劉的名義將此書贈予曾卓。曾卓收到書后當即修書向劉致謝:“近年來常在報刊上讀到大著,文筆酣暢,思路清晰,見解精辟。可見精力仍旺盛,甚為欣慰。”劉緒貽接到來信后,驚喜交加,立即給曾卓回信,向他談及1955年那樁不愉快的公案,坦言四十余年來自己心里始終難以抹去的愧疚。向來豁達的曾卓復函寫道:“五十年代的舊事,不值一提。當時那樣的形勢,大家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劉的心情這才輕松了不少。難怪劉緒貽的長女、武大退休教授劉東這樣評價其父:“偉大的父親,坦蕩的君子,正直的學者。”
1998年5月29日,同是黃陂老鄉的《長江日報》周刊《長江周末》主編羅建華得知此事后,在周刊召開改版座談會時,特意邀請劉緒貽和曾卓同時出席,終使他們“相逢一笑泯恩仇”。座談會后,劉氏不禁思緒萬千,覺得陸游與曾卓這兩位古今詩人可謂神交千載,于是詩興大發,賦七絕一首贈曾卓。詩云:“心有靈犀一點通,參商半紀喜重逢。古今詩叟其誰似,野老丹心一放翁。”曾卓收到贈詩后的復函這樣寫道:“承贈詩,感謝而又有愧。詩樸質情深,自有一種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過去寫過一些不能稱是詩的詩,只是表達一些個人的感受和情懷,老來多病,只有擱筆了,但還有一點憂國憂時心耳。”
在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看來,劉緒貽先生不趨炎附勢,只說真話,絕不說假話,因而是“不合時宜”的人。作為布衣教授,劉公畢生著述三十多部,是中國美國史研究的奠基者,但他既不是博士生導師,連他的徒孫都是“人文社科資深教授”,而他卻不是所謂的“資深教授”,這豈不是咄咄怪事?1996年9月,湖北人事廳編纂的《湖北專家大辭典》收錄了四千三百二十一人,劉緒貽與劉道玉二位先生竟被排斥之外。
三
劉緒貽一生的精彩華章,是他致力于美國史、社會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是中國美國史研究事業的重要奠基人與“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創立者之一。
盤點劉緒貽一生的著作發現,其主要著述大都是他六十歲以后出版的。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也迎來了學術研究的第二春天。這一年,他與國內美國史同仁共同發起創立了“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出任研究會副理事長并兼任秘書長,秘書處設在武漢大學長達十年。還是這一年,他和楊生茂教授應人民出版社之約,開始共同主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六卷本三百萬字的《美國通史》,最后兩卷《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代》和《戰后美國史》的編撰工作被不少學者回避,劉緒貽“迎難而上”,承擔了這兩卷的主編和編撰任務。他創新性地揭示了羅斯福“新政”導致經濟“滯脹”的規律。其學術思想最有建樹的部分,是他對壟斷資本主義特別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史的開拓性研究,得到了學術界高度評價,被譽為“具有獨到見解的美國史專家”。
1987年離休后,劉緒貽繼續研究美國史。諸如,他的專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美國史論叢》,與人共同主編《美國研究詞典》、主編主撰《當代美國總統與社會》,主編并參與撰寫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學研究》,以及主持、參與或審校的《一九〇〇年以來的美國史》、《美國社會發展趨勢(1960—1990)》、《羅斯福與新政》、《多難的旅程》等十一種譯著等,多半是在離休之后的二十年中完成的。1988年,在其譯著《注視未來——喬治·布什自傳》出版后,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專門致函劉先生,感謝他“為增進中美兩國之間的了解所做的努力”。
“生命在于運動,生命在于思想。人永遠不能當閑人。”劉緒貽認為,如果他在離休后像一些老人一樣,真的終止工作享清福,他恐怕早就病倒了。對于自己的養生之道,劉緒貽常與人分享“自我按摩術”。早在1936年考入清華時,他在《中學生》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說洗了臉以后,就摩擦臉部,每天摩擦五十至八十次,八十年間他從未間斷過。從七十年代開始,他又堅持全身按摩,每天大概要花四十五分鐘左右。
如今,劉公雖然遠行了,但筆者將其傳記《從黃陂走出的“美國通”》收入《無陂不成鎮》一書,讓更多的海內外讀者了解其事功,弘揚其高風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