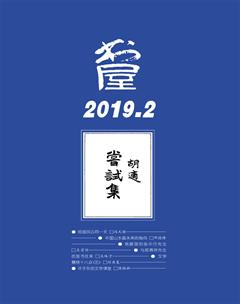清光照人影
胡喜云
“我做助手、秘書、學生在陳老身邊三十年,把人生最寶貴、美好,精力最旺盛的青春歲月都做了此工作。”這是劉乃和先生的一句話,可以概述她與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先生的關系。劉乃和先生生于1918年,祖父劉學謙與柯劭忞、徐世昌是同科進士;外祖父徐坊富藏書善鑒定,曾任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的前身)副監督(副館長);父親劉毓瑤字貢揚,長于金石書法。劉乃和于1939年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1943年畢業后留校,入史學研究所跟隨陳垣先生攻讀碩士并兼歷史系助教;1947年碩士畢業后任輔仁大學歷史系專任助教,1949年晉升為講師,1952年院系調整后改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師,兼任校長辦公室副主任、文書科科長、陳垣校長秘書,直至1971年陳垣先生病逝。
一
抗戰勝利后,陳垣先生看到日寇雖降而戰事仍頻,心情苦悶,隔三四天就去劉乃和家小坐,與她父親談書論篆,聽她的母親講年輕時在家中聽來的徐坊與柯劭忞、張之洞、繆荃孫等人的軼事趣聞。陳先生多次拒絕國民黨政府請其南飛的邀約,1949年1月8日,他得知國民黨政府又派人來接他去機場,他一早就到劉家躲避,一直待到晚飯后才走。1949年2月1日,在柴德賡、劉乃和的陪同下,他從輔仁大學步行十幾里到西直門大街,站在人行道上和群眾一起歡迎解放軍進城。
陳垣先生多次邀請從解放區歸來的劉乃和的二弟劉乃崇至家中,聽他講述解放區的見聞,并找來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論著,手持放大鏡一字一句認真閱讀。1949年4月,受《新華日報》上刊登的藍公武與胡適的一封信的啟發,在大家的幫助下,陳垣先生決定用公開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新氣象寫出來。經過陳先生反復講述,由劉乃和執筆,再經他親筆改定而成《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1949年5月11日,這封公開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1951年5月28日,七十一歲的陳垣先生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第二團總團長,在劉乃和等人的陪同下,帶領五百三十一人分批由北京出發前往重慶,參加西南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剛到重慶,陳垣先生即開始鬧腸胃病,總團部為照顧他的身體,準備讓他與劉乃和等人坐鎮重慶,后經爭取,同意他們到巴縣參加土改。在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過程中,聽劉乃和讀土改材料、貧農悲慘控訴,陳垣先生多次流下熱淚。9月27日,陳垣先生由重慶乘飛機回到北京。10月21日,他在西南土改工作團工作總結會上深情表示:“在實際斗爭中,我認識了農民的偉大的力量與無窮的智慧,看見了青年人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到自己所不及的。”11月2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陳垣先生撰寫的《我參加土地改革后思想上的轉變》。
1959年1月28日,七十九歲的陳垣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12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回顧了自己以前的彷徨困惑,新中國成立后參加輔仁大學反帝斗爭,參加土改、反右運動,參加科學院學部工作和科學規劃。此時正值全國史學工作者百余人齊集北京討論中國歷史提綱,唐長孺先生即席賦詩一首:“八十爭光樹赤幟,頻年知己效丹衷。后生翹首齊聲賀,嶺上花開徹骨紅。”侯外廬撰寫跋語,并執筆寫在織錦封皮的宣紙冊頁上,出席會議的史學工作者一百零五人簽名祝賀。
二
陳垣先生自1943年開始寫作《通鑒胡注表微》,至1945年7月完成,劉乃和參與校勘。1949年前陳垣先生的著作大多發表在雜志上,也曾印成“勵耘書屋叢刻”,包括八種著作(共十六冊),由書店代售。1954年,書店屢次前來接洽,請陳垣先生考慮加印。那時已沒有地方承印木板印刷,但他仍想找人自己印。劉乃和便騎自行車滿城奔走,輾轉找到會印刷的老工人訾瑞恒,并計算木板數量、紙墨質量、紙張大小和數量,購買紙墨,核算定價等。自1956年4月起,至1957年、1959年共印過三次,整印“勵耘書屋叢刻”五十套左右,其余是散種,有多有少,印一次兩次不等,大部分贈送給高校、研究機構和圖書館,也由“通學齋”、“修綆堂”、“來薰閣”等書店代賣給讀者,劉乃和還負責登記賬目。
1955年至1958年,科學出版社重印了陳垣先生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史諱舉例》、《通鑒胡注表微》;1958年出版分工調整后,中華書局于1965年8月前重印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歷》、《校勘學釋例》、《釋氏疑年錄》等七種舊著。劉乃和負責與出版社溝通、點校舊著、起草重印說明、出席工作會議等具體事宜。其中《史諱舉例》出版于1928年,是為紀念錢大昕誕生二百周年而作,成書倉促,引文有誤且未注明出處。劉乃和于1955年11月開始核校引書原文,至1956年8月校點完畢,正其謬誤,補出卷數。陳垣先生在《重印后記》中稱:“今本系劉君乃和校本。劉君于本書用力至深,曾將全部引文一一檢對原書,正其謬誤,其須加卷數及引號者并加注卷數、引號。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讀者。”在這部著作中,多次出現“乃和按”的小注,這是陳垣先生著作中未出現過的做法。其實,陳垣先生自己也曾多次校過該書,有許多“乃和按”是他起草后讓劉乃和謄改在書中的。《中西回史日歷》出版于1925年,從公元元年編至1940年。1960年,中華書局糾結是出版《中西回史日歷》還是出版《兩千年中西歷對照表》,向劉乃和咨詢二書不同之處,她回復了一篇《重印說明》。后經征求多方意見,中華書局決定重印《中西回史日歷》,劉乃和協助陳垣先生將“中西回史日歷對照表”中的時間延長至兩千年。
1965年北京師范大學開展“四清”運動時,調查陳垣先生刷印木板書之事,工作組于7月8日和8月20日兩次傳喚劉乃和,讓她上交書面材料,承擔“偷稅”的責任。至1966年7月,劉乃和兩次被學校組織監禁,交代陳垣先生著作的出版情況,承擔“違背了黨的政策,破壞國家經濟制度”的罪名。
新中國成立后,陳垣先生不僅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范大學校長(1952年院系調整后輔仁大學并入北京師范大學),還先后擔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自《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之后,劉乃和負責起草陳垣先生的所有文稿。
三
1958年中華書局開始籌劃點校二十四史,1959年出版了《史記》點校本,1960年出版了《三國志》點校本。1961年,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組成立了二十四史工作小組,確定了承擔點校各史任務的有關研究單位和高等院校。1961年2月25日,陳垣先生正式承接了新、舊《五代史》的點校整理工作。其實早在1960年9月,陳垣即開始為接受新、舊《五代史》的點校任務做準備,他根據過去研究《舊五代史》的經驗撰寫了《標點〈舊五代史〉問題》一文,內容包括引書卷數問題、附注問題、卷末考證問題、輯佚問題等,都是針對點校《舊五代史》所特有的情況而擬定(《舊五代史》并非原本流傳,而是由后世輯佚編成)。這篇整理意見陳垣先生曾四易其稿,直到1963年11月23日才考慮成熟送交中華書局編輯部。
承擔點校新、舊《五代史》的任務后,陳垣先生以柴德賡、劉乃和為助手,做了《〈新五代史〉不列傳人名索引》、《〈舊五代史〉不列傳人名索引》、《〈冊府元龜〉部分人名索引》(唐朝末年的未包括在內)、《有關五代史論著書名錄》、《五代十國年表》等工具書和索引,將《舊五代史》的熊本、劉本各與殿本對校,將劉本與熊本互校,列成各本的異同表。動手點校時,遇到疑難問題即用索引檢查,利用本校、他校和對校等方法來校勘。1961年4月17日,陳垣先生在給蒙文通先生的回信中稱:“敝處所標點《舊五代》,初稿雖早已完成,但尚須細細重勘數過,斷不能如傳說所云本年六月可以交卷。”4月28日,《文匯報》刊登了陳垣先生在劉乃和先生協助下整理新、舊《五代史》的照片,《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人民畫報》等也相繼登載宣傳。1964年4月26日,經北京師范大學協商,柴德賡至北京協助點校新、舊《五代史》。1966年3月17日,中華書局趙守儼拜訪陳垣先生,了解新、舊《五代史》的點校進度,說中宣部正在催促,中華書局擬于1969年國慶獻禮,則各史須在1967年底交稿。
可惜,先是柴德賡于1966年6月14日被調回蘇州參加“文化大革命”,接著是劉乃和于當年7月被調離陳垣先生身邊,到學校集訓隊學習、勞動。1967年5月15日,中華書局來人要走新、舊《五代史》的材料(新、舊《五代史》各一部,張森楷、張元濟新、舊《五代史》校記,校勘記四本),聲稱將重新開始點校工作,人選未定。12月11日,中華書局又來二人取走劉乃和整理的《五代史》材料。至此,新、舊《五代史》的點校工作徹底被擱置。1971年2月,九十一歲的陳垣先生已病重不能下床,開始鼻飼、導尿。他聽到周恩來總理指示二十四史還要點校,由中華書局負責組織工作,顧頡剛先生總其成的消息后,立即讓劉乃和向住在他隔壁病房的顧頡剛先生表達心意,稱“他對顧老負責此事,非常高興,但對兩部《五代史》未能繼續完成,表示非常遺憾”。
四
劉乃和一生手勤筆勤,凡陳垣先生的字跡,她都片紙不遺地珍藏;聆聽先生講話或參加學術講座以及出席各種會議時,她皆認真記錄。
在陳垣先生“勤筆免思”的鼓勵下,劉乃和記錄了先生所談自學過程、查書辦法、治史心得、史籍優劣、寫作的甘苦、思想的收獲、做學問的得失,以及他吟詠的詩句、購買文物的樂趣、朋友的往來等,積累了六大厚本。陳垣先生把這六大本翻閱了幾天,糾正了不少錯誤,補充了不少內容,并親筆題名《集腋集》,副題是“勵耘書屋論學記”,說“想不到平時隨便講的零散內容,記錄積累了這樣多”,“將來整理后可以出版,也可以叫作《陳垣語錄》罷”。不幸的是,“四人幫”肆虐時,北師大造反派戰斗隊在陳垣先生書庫亂翻了一天,說要翻檢書中有無“反革命詞句”。他們看到《集腋集》是鋼筆記錄,以為可能有“反革命”的內容就給抄走了,后散佚。目前,僅見第七冊的兩頁零一行。
陳垣先生的原配夫人鄧照圓久居廣州,第三任夫人徐蕙齡久居天津,十一個子女中僅二子陳仲益留在北京,但并未生活在一起。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決定讓劉乃和負責照顧陳垣先生的日常起居,還為陳垣先生另外配備了兩名護理人員。
1966年7月,劉乃和先生被調離,到學校集訓隊學習、勞動。陳垣先生的二子陳仲益和保姆袁姐在家照顧他。10月17日,劉乃和從集訓隊出來,但被要求在校辦參加“文化大革命”,被安排在大串聯接待站的問訊處,不能回到陳垣先生身邊工作,只得每隔幾天找機會跑到陳垣先生家中,念念大字報或談談外邊的情況。10月27日,八十六歲的陳垣先生睡覺翻身時摔到床下,摔壞了手指甲,自己掙扎著爬起來后用鉛筆寫了一張紙條,“從床上跌到地上,自己爬起”。劉乃和后來一直把這張紙條壓在書桌的玻璃下,“每看到它,總想起他那時的苦悶和恐懼不安的情景,仍不禁心酸落淚”。直到1970年1月6日,因陳垣先生的二子陳仲益病逝,劉乃和才被調回。
1971年6月21日,因肺炎、呼吸衰竭、心力衰竭不治,九十一歲的陳垣先生病逝于北京醫院。6月24日下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告別儀式。劉乃和曾回憶:開過追悼會后,她重回興化寺街五號,院里屋里再也看不到勵耘書屋主人了。她獨坐在書屋外臺階上,感到異常空蕩,滿院滿地碎紙殘片,都是連日搬拉書籍什物時拋棄的。她在廢物堆里撿到一些很好的字幅和殘斷篇頁,還拾起幾個小紙條。這些不起眼的小紙條是陳垣先生生前讀書時隨手記下夾在書里的,收拾書籍時抖落出來。小紙條上的字也可能是費多少時間才查出來的,但離開原書就一點用也沒有了。她拿著拾起的廢字卷、紙條等,不禁對著勵耘書屋大聲痛哭……